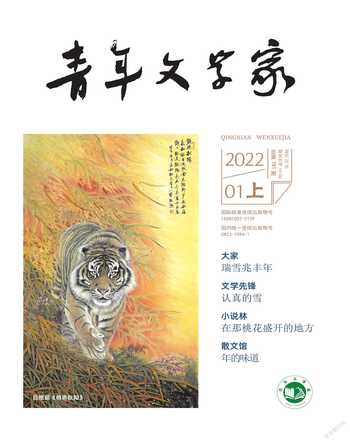论《我与地坛》的创伤书写
崔紫薇
“创伤”(trauma)最初主要指外在力量在身体上造成的物理性伤害,但经弗洛伊德等人的阐发,该词现在更多是被用来指精神性伤害。后来,创伤研究逐渐从心理学层面转向文化研究层面,并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受到西方评论界的认可,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的研究方法。
创伤理论所关注的是重大事件给人带来的严重的心理创伤,或是在生活中遭遇的日常事件带给个体的创伤性体验。随着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创伤理论逐步由对个体創伤的认知发展到对集体创伤的体认,进而关注到记忆、媒介等与创伤之间的复杂关系,发展出了多个维度的研究。
身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位特殊作家,身体残疾必然为史铁生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而他也一直在借文学的方式对创伤进行书写。《我与地坛》正是这样的一篇散文。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去解读《我与地坛》,进而解读史铁生,应该说,也许能够更进一步了解史铁生的创作心态,以及其对文学的追求。
一、创伤的经历者和观察者
史铁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坛极为特殊的一位。双腿瘫痪成为他写作的起点,一方面,他努力融入中国文学的浪潮之中;另一方面,残疾人的身份又让他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生命的审视,并促使他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生命的思索。可以说,残疾是史铁生创作无法逃避的一个关键词。而对残疾的描绘,很大程度上是和史铁生自己的“创伤”联系在一起的,这在其自传体散文《我与地坛》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所谓创伤,是指自然或社会灾难带给人们的心理阴影,“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因此,对于史铁生而言,创伤指向的便不只是身体疾病,更是这些疾病带来的生存问题,即无法找到在整个社会立足的位置—“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
本来是大有可为的青年,却因为一场病症一下子成了一无所有的待业人员。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生命的惶惑和抑郁。无处可去成了一种生命的常态,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史铁生,别人可以上下班,他却只能窝在地坛里耗着,这种与他人之间的对比更进一步加深了其心理的创伤。生命的荒废和意义的缺失必然把他推向“死”。于是,他开始思考生和死。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属实不易,史铁生自己也坦言思索了“好几年”。在这冥思的几年之中,史铁生有过快乐,有过平静,但更多的是“沉郁苦闷”,是“恓惶落寞”,是“又软弱,又迷茫”。所以,史铁生因社会位置的缺失而逃离到地坛的行动,以及长久在地坛中的思索都可以纳入他整个的创伤体验—他之所以能够在地坛中沉思,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无处立足,而沉思又总是伴随着抑郁的情绪。在这里,史铁生首先作为创伤的体验者和经历者存在。他是创伤的主体。
但随着在地坛长久地待下去,他发现了地坛的其他存在。在对他人的观察之中,他从创伤的亲身经历者转变为了创伤的观察者。在这十五年间,因种种原因来到地坛的不止他一个。这些人之中,有来散步的,比如那对老人;有来施展歌喉的,比如那个唱歌的小伙子;有来喝酒的,比如那个老头……
然而,史铁生很快注意到另一类人,他们来地坛不是为了消遣,而是和他一样,是为了逃避。这群人和他一样是创伤的经历者。
长跑家因种种原因被埋没,于是,“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但无论他取得怎样的成绩,他获奖的照片总是没有被放置在展览的橱窗里。终于,在他三十八岁的年纪再一次取得好成绩,一位教练注意到了他。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命运总是让长跑家和梦想失之交臂。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对兄妹。蹲在路边捡拾小灯笼的小女孩,咿咿呀呀地和自己说话,她的哥哥则在她附近捕捉知了博她的欢心,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然而,在那个让人心碎的上午,史铁生看到一群人在欺负小女孩。那时,他才发现原来小女孩患有智力障碍。这给史铁生带来了无法言说的震撼:“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长跑家的创伤更多的是社会作用的结果,但这个小女孩的创伤和史铁生一样,是上天给予的苦难。于是,对他人创伤的审视让史铁生对命运的思考更加深入。
正是在这体验和观察之中,史铁生开始了对创伤的审视,并开启了对生命的哲思。也就是说,自我的创伤仅仅让他思考个体命运的问题,但当他发现他人和他同样经历着创伤时,他的思考便由个体转向了群体,走向了更广泛的形而上的生命沉思。
二、地坛:承载记忆的场所
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他人的想象与观察促使史铁生审视身体残疾带来的心理创伤,并最终构成《我与地坛》创伤书写的一部分。不过,《我与地坛》是以追忆的形式对创伤进行书写的。在整个回忆之中,地坛一直处于核心的地位,并最终融入了整体的创伤书写。
创伤与记忆密不可分,或者说创伤本身就是记忆的一部分。“哈特曼指出,相互矛盾的两种因素构成了创伤的内核:没有被认知或意识到的创伤性事件,以及对该事件的记忆。”记忆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始终和一定的时空联系在一起。为了保存记忆,就需要一定的中介或场所。对于史铁生而言,地坛正是其用来承载记忆的场所。
史铁生几乎所有的创伤体验都是在地坛中体认的。地坛作为一个废园,和现代社会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因此成为他逃避的最好去处。为了保证地坛承载记忆的合法性,史铁生在一开始便建构了“我”和地坛之间的关系—“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于是,以地坛为中心,史铁生开始了追忆。回忆从十五年前开始,“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一直到现在,“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在十五年的跨度中,他回忆地坛中的自己:最初是为了逃避而来到地坛,在地坛中,身体的不便和光阴的虚度把他推向了生与死的思考。在进行思考的同时,他又在观察地坛中的其他人。一直到后来,他躲在地坛中写作,乃至于成名之后也常常回到地坛寻找心灵的依托。地坛已经和他的记忆融为一体。
不过,地坛一方面承载了史铁生早年的创伤记忆,但另一方面,在回忆中,他又发现了逃避于地坛所带来的新的创伤—对母亲的亏欠。新创伤的发现,不是在这十五年间,而是在回忆这十五年间的现在。于是,由身体残疾导致的心理创伤进一步扩展,从个体的心理问题转变为了家庭的伦理问题。史铁生终于认识到,当初躲到地坛的行为给母亲出了怎样的难题,残疾带来的情绪崩溃又给母亲带来了怎样的心理压力。每次当他发疯似的离开家时,母亲是怎样焦急等待;当他归来却又着了魔似的一言不发时,母亲又是怎样纠结。在这每一天的漫长等待里,母亲,“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更令史铁生痛苦的是,对母亲心情的感知是在多年之后,是在母亲已经猝然去世之后。因此,当前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和喜悦都已经失效,因为一切都“来不及了”,母亲已经不可能和他一同分享这些喜悦了。感情的亏欠必将成为史铁生一生的创伤,融入他未来的生命之中。
地坛的意蕴因此发生了一些改变。十五年前,地坛是一个逃避社会的世界;十五年后,地坛成为揭露伤痕的场所。每一次进入地坛,史铁生都会想起母亲,都会想起母亲寻找自己的足迹,以及自己那近乎无理的倔强—明明看见了母亲,却决意不喊她,任由母亲焦急地寻找。而这份倔强,如今带给史铁生的,只有无尽的懊悔。
可以说,地坛已经成为一个记忆符号,它承载着史铁生几乎所有的创伤记忆:对身体残疾的懊恼、对无处立足的不安、对母亲的亏欠、對他人创伤的审视、对命运的诅咒和思考……
但地坛不仅作为创伤记忆的载体而存在,其也为史铁生审视创伤提供了可能。正因为地坛承载了史铁生这十五年来的诸多记忆,所以对地坛的审视,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等于对记忆的审视。当他重新体察地坛才发现,地坛不仅承担了他所有的苦难和创伤,地坛中的自然生命也在无意中维系了他的生之意志,这里的一草一木让史铁生在对“死”的思索中看到活着的希望。也就是说,地坛已然成为史铁生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他“生活的支点,是他自己在顽强地扶起来的那座纪念碑”。
三、冥思与写作:疗愈的可能
在创伤身份和记忆都得以梳理之后,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史铁生必须找到疗愈的方式。
归根到底,创伤是一个心理医学问题,而“创伤治疗的根本途径是患者能力的恢复和新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心理学家赫尔曼提出了三个治疗创伤的基本步骤:首先,恢复患者的自主权,使其感到有存在的安全感;其次,帮助患者完成对创伤的审视;最终,使其和社会重新建立联系。
史铁生不是心理医生,但他的自我疗愈无意中也大体符合这三个治疗步骤。残疾带来的孤独和心理落差让史铁生常常想到死亡,然而,他终究还是顽强地活了下去。最初继续活下去,不是寻找到了什么解决方法,而是史铁生在冥思之中明白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既然死神不会提前将他带走,那么不妨活着试一试,试一试也不会带来什么损失,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当个体生命跌落谷底,那么每一次的“试一试”都意味着一次向前。在死的问题解决之后,剩下的便是怎样活的问题。在这漫长且痛苦的思索中,他终于意识到,“怎样活”这样的问题不是他个体所面临的难题,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命题。自古以来,多少先哲都在力图解决这个难题。既然如此,活的问题便不着急寻找一个可靠的答案,因为毕竟要“试一试”。在死和活的问题都暂时解决之后,史铁生感觉轻松多了,自由多了。心态的变化意味着,他终于能够自主地把握自我的存在,不会再为生存感到不安。
生命存在的安全问题解决之后,史铁生把生存的意义交付给了写作。写作对于史铁生而言,既是正视创伤的方式,也是重返社会的工具。最初开始写作,只是想“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儿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于是,他躲在地坛里,偷偷地进行创作。小说幸运地得以发表,并且让人觉得“还不错”。于是,他继续写下去。后来,一些作品也获了奖,得到社会和专家的认可,他终于成了一个作家,终于凭借作家甚至是知名作家这一身份,走出了地坛,复归于整个社会中。对于他来说,写作,“不再仅仅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而是一种寻找生命意义的方法和途径”。
与此同时,在写作中,史铁生不断与自己的“心魂”对话。“一个作家,无论是在搜集材料、进行构思的前期准备阶段,还是在展示想象、虚构和抒情的创作过程中,他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走进记忆,揭开尘封的往事,接受记忆的邀约”,史铁生也正是这样。通过写作,他能够沉下心来,重返记忆之中。如果说,他的小说创造还只是借助虚构的方式书写“知青”这一群体记忆的话,那么散文这样一个求真的文体则让他直面自己个体的记忆。从《秋天的怀念》《合欢树》等对逝去母亲的追忆,经过《好运设计》中对命运“上帝”般的设计,到了《我与地坛》,史铁生终于鼓足勇气回顾残疾以来所有的创伤体验。以地坛为空间中心,以十五年为时间跨度,他终于完成了对创伤的追忆和叙述。写作使他以“过来人”的身份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伤经历,这立足当下对过往的回忆,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怨天尤人,只有一颗平常的心,在静静审视着过往的一切。对创伤记忆的正视意味着,史铁生最终从创伤记忆的困顿中走出,把所有的创伤都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于是,依托过去,他立足于当下的土地,向着更美好的未来走去,就像他常常听到的唢呐声一样,它们“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变”。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对自我创伤书写的又一次实践。身体残疾的他,既是创伤的亲身经历者,也是他人创伤的观察者。对创伤身份的体认是在以地坛为中心的回忆中完成的。地坛成为承载史铁生创伤记忆的场所,也为史铁生的自我疗愈提供了场域。在地坛中,他通过对生与死的思考寻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并借助写作等方式实现了对创伤经验的追忆,在对记忆重述中完成了对创伤的平常审视,最终借助写作获得了“作家”这样一个社会身份,和社会重新建立了新的联系,完成了对创伤的超越。
3520501908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