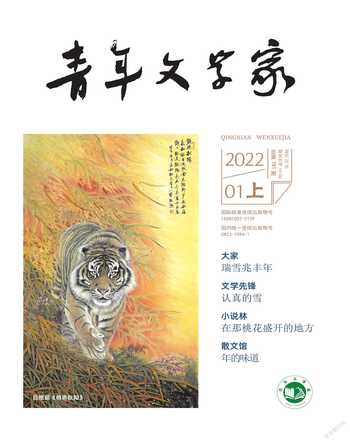北支河冬雪如梦
祁怀清
有这样一首咏雪的打油诗:“天地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四句话把冬雪笼罩的天地万物,形象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其实,每个人儿时的冬天似乎都那么漫长,都那么温馨,我也不曾例外。人在儿时的有些经历可能直接影响其一生的言行,以我为例,北支河的冬雪以及与之有关的动人往事,对我来说有着难以名状的甜与美。
如今细想,我儿时见到的最大的河就是我们汉川的北支河。北支河西起天门市净潭乡,东接民乐渠和汈汊湖东干渠,全长46.8公里,宽50~60米,纵贯大半个汉川市。北支河曾经是古汉江的主河道,从我的老家北边流过,步行2公里即到。每个人都有对某一条河流的特别记忆,令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儿时见过的最大的雪,就是落在这条北支河里的。
我们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但是在我的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我那水资源非常丰沛的老家却没有养鱼之说。那时所有的沟渠塘堰里面,随处可见土生野长的鱼虾龟鳖,随便到有水的地方转一转,都不会空手而归。成年人对于家门口的鱼虾,犹如兔子对于窝边草一样,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注意力在遥远的江湖。每年秋收过后,父母都会随同村里的渔民一起,到汉江、长江,到洞庭湖、鄱阳湖去讨生活,老家的俗话叫讨业事,直到小年前后才回家乡过年。然后,次年正月十五前后,走完亲戚,等小孩们都上学了,他们再次出发去那些地方讨业事,等到插早秧前回来务农。如此为了生计轮转往复。
在我10岁那年,父母照例在小年后回来。与往年不同的是,那年是一个枯水年,家门口的小河完全干涸,父母的渔船撑不进家门口,只得暂时停靠在北支河边。那时的渔船是仅次于房子的第二号家当,父亲就安排我和大我3岁的二哥去照看。
那天是腊月二十五的下午,父亲带着我和二哥,从烤着柴火的温暖的家里出来,走进下得正紧的风雪中。迎着凛冽北风,在积雪厚及脚背、杳无人迹、看不出道路轮廓的雪地里,向北迤逦而行。到了我家的渔船边,父亲手把手地教我们支好拖子,那是一种捕捞鱼虾螺蚌的传统工具。用尼龙绳编织成口径2~3米、长2米左右、尾端收口的密眼大网兜。使用时上端用竹竿固定,以便浮在水面,下面系上铁块石头,利于紧贴河底。再在竹竿的两端系上绳子,用人力牵引着在河中拖行,把在河底休眠的鱼虾螺蚌纳入网兜中,让我们拖鱼虾。
我满腹疑虑地问父亲:“这么大的风雪,这么冷的天,我们会不会冻病?”神情一向严肃的父亲用难得的温和语气说:“做事的时候是不会觉得冷的。”我还是不放心,问:“这样的天气,能拖到鱼虾吗?”父亲依然温和地说:“试一试你们就知道了。”
按照父亲的指点,我们小哥俩支好拖子,逆着水流的方向拖行。每隔50米左右就把拖子收拢来,清点收获成果。尽管每次拖到的鱼虾都不多,但好在每一次都有收获。拖了两个多小时,收获了两三斤小鱼小虾。这时候,浑身发热了,父亲让我们停下来,说今天的收获相当丰富。表示要亲自做一顿饭,对我们今天优良的表现进行奖励。
父亲还会做饭?印象中从没见他拿过锅铲。在家时,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时间总是在用毛笔抄写旧得发黄的经书。对于父亲做饭,我们充满了疑惑和好奇。
渔船上的炊具是现成的。父亲吩咐我们把鱼剖好,把虾清理干净,把萝卜切成丝,分别放在两个碗里备用。然后,他亲自动手,把米煮到八九成熟,我们老家称作饭生子。接着,连米带汤一起倒进筲箕里,筲箕下面用汤碗接住米汤。再把鱼虾放进锅里煎,等到煎出微微的金黄色后,加盐、水、萝卜,盖上锅盖用小火煮。等到看不见有明显的汤汁后,把沥干的饭生子倒进去,堆成小山形。用筷子在饭堆上插一些气窟窿,顺着锅沿点一些水,加一把大火,烧到能够闻到饭香,就熄火,揭开锅盖。一锅铲铲下去,盛到碗里,正好饭在下面,菜在上面。我们吃几口饭菜,喝一口米汤。那餐饭,吃得至今都口齿留香。
我请教父亲,这是一种什么烹饪方式。父亲说:“这叫船家饭菜一锅闷。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煎鱼虾时不要随便翻面,也不要煎煳了,火候的掌握很重要。以后你们长大了,会学到‘治大国若烹小鲜’之类的话,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大道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吃素的,怎么能吃鱼虾呢?对于这个问题,父亲非常坦然地回答说:“你们要学会观察。我把我碗里的鱼虾都给你们了,我吃的是萝卜。对于肉边菜,吃斋之人是可以吃的。”
那一次在风雪中的北支河里拖拖子,以及父亲亲手做的那餐饭,所说的那些话,如同在我的身体里面种下了一些种子,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让我学会了面对事物如何观察联想,怎样设身处地地待人处事。
比如读《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章,看到“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起一天大雪来。那雪早下得密了”“那雪正下得紧”“那雪正下得猛”……纵然是在盛夏酷暑时节,读到这些文字,都感觉浑身凉飕飕的,从头凉到脚。倒不是下雪时真有多冷,下雪不冷化雪冷的常识,相信很多人都有体会和感受。设身处地地讲,我认为林冲感觉冷,除了天气原因,更多的是心理和情感方面的。那时他孤身一人,身边没有父亲兄弟,被逼无奈,无路可走,当然感觉到冷。同样大雪纷飞,有父亲和哥哥在身边作为依靠,我感觉落到大地上、落进北支河、落在我身上的雪都是暖融融的。
读牛郎织女的故事,看到天兵天将押着织女飞上天空,牛郎挑着一双儿女在后面追赶,眼看就要赶上了,这时王母娘娘驾到,拔下头上的金簪一划,霎时间一条天河横亘在牛郎和织女中间,无法跨越。只有每年七夕节,才能在鹊桥上“金风玉露一相逢”。对于这个故事的一些细节,我表示强烈质疑。我认为当时王母娘娘拔下的应该是银簪,而非金簪,不是用“金簪一划”,而是把“银簪一扔”,化作银河,把牛郎织女隔开。如果是金簪,则天河应该称作金河,而非银河。金簪和银簪我都见过,都是长不到1拃、宽約1厘米、厚不足1毫米,上面都雕刻有精美的缠枝纹或波浪纹。把一个银簪无限放大,就是一条银河。我还坚信,王母娘娘肯定有一支碧玉簪遗落到了人间,化为北支河。大雪落进北支河时,河面呈现出的碧绿通透的色泽,唯有巧夺天工的王母娘娘的碧玉簪才能散发出来。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我还要说父亲亦是一条滔滔流淌的河。不久前回老家给离世10年的父亲上坟,经过碧玉簪化作的北支河,童年往事涌上心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那么怀念与父兄在一起,感受大雪落到北支河时的甜美时光。那犹如铺满梦境的北支河冬雪,温馨着我们的一生。
3118501908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