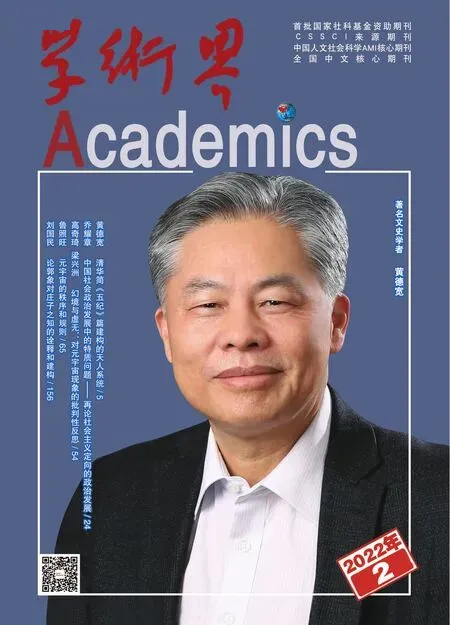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自立自强”〔*〕
——基于创新演化观视角的分析
张军涛, 程浩岩
(1.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2.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首次将“科技自立自强”相关内容摆在五年规划各项任务之首。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自立自强”对我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危”“机”转化逻辑?如何在经济学领域对创新及技术变革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技术创新与制度之间是怎样的互动关系?上述问题的厘清对于理解我国新发展格局中“科技自立自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议题有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然而,在以牛顿主义机械观为启源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创新”始终被视为外生给定的“黑匣子”,无法触及新奇创生、技术涌现、创新扩散、技术与制度互动、经济结构跃迁等有关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难以对上述问题进行完备解答。面对这种“无解”状态,以达尔文主义演化观和批判实在论为哲学基础的演化经济学将研究生成(becoming)而非研究存在(being)视为根本,为认识和理解创新提供了一条值得探索的渠道。
一、创新主题的演化经济学解读
目前,演化经济学流派纷杂,仍处于统一与融合阶段。按照贾根良的观点,演化经济学传统及分化出的流派主要包括:老制度主义传统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法国调节学派、复杂系统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数理建模阵营、反数理应用阵营等。〔1〕此外,还有聚焦于欠发达经济体利益的“新李斯特”学派,一般将其归于“演化发展经济学”。〔2〕有关演化经济学流派及其经济学家的界定标准仍莫衷一是,〔3〕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以交换、物质资本、资源配置为焦点不同,演化经济学以生产、知识、资源创造为核心,创新主题可谓无处不在。本文尝试沿以下三条主线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是创新生成的基础假设,即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相对立的异质性能动偏好理论决定了演化观的多样性原则。相关思想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闲散好奇心”和不确定性等人性观、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和“真”个人主义、批判实在论的“涌现”机理等。前两者质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建立了破坏性创新的人性本能论,对此相关学者已有较为详尽的梳理和评述。其中,关于哲学隐喻与类比的梳理,〔4〕即新古典经济学借鉴牛顿范式机械、静态、封闭的世界观与演化经济学借鉴达尔文范式有机、动态、开放的世界观之间的对比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代表性。而批判实在论有关新事物生成机制的“涌现”关系在演化经济学中尚未被充分挖掘。贾根良已尝试将批判实在论哲学思想运用于“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多为演化经济学思想来源)的综合,〔5〕杨虎涛分析了演化经济学的两种系统分析进路,〔6〕指出批判实在论是法国“调节”学派的根本基础,但他们均着眼于批判实在论的层级本体论或能动性与结构转化本体论。“涌现”机理是批判实在论对演化经济学更为本质的贡献,“能动性—结构”本体论本身就是一种“涌现”关系。杨虎涛已洞悉到凡勃仑制度主义的缺陷之一就在于,虽然认识到了涌现现象的重要性却没有发展出任何关于涌现机制的内在因果理论。也有学者察觉到了“涌现”哲学思想运用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优越性。〔7〕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对“涌现”思想与演化思想进行清晰而明确的融合性理论构建的尝试。
二是创新的扩散机理,即创新生成(突变)及复制机制,体现了演化观的遗传原则和选择原则。老制度学派揭示了本能和制度的“习惯性”特征以及“技术制度”和“礼仪制度”间的累积因果关系,强调了制度对个人的塑造作用。“新熊彼特”学派的成果是演化经济学对于创新扩散机理的开拓性贡献,对“惯例”理论和“搜寻”概念的提出、对“利润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批判、对“满意”假说的吸收是创新演化理论的实质性突破,并且发展出了国家创新体系概念以及技术、结构、制度共演分析模式。与此相关的,有学者总结了技术创新的演化趋势、〔8〕科技创新的国家集成能力等,〔9〕借鉴演化思想或演化博弈的制度分析也已成为重要拓展方向。〔10〕杨虎涛质疑了老制度学派的“技术—制度”二分法,认为制度主义者们忽视了技术工具和知识之间的差异。贾根良认为“新熊彼特”学派的经典著作遗漏了老制度学派的重要贡献,但分别将企业惯例和制度作为基因类比物体现了二者的连续性。〔11〕近年来,有关知识扩散、〔12〕研发投入与危机应对,〔13〕以及制度、技术、结构变迁下的演化增长理论被学者们持续关注。〔14〕应当说,技术、结构、制度共演模式的提出完成了对熊彼特经济思想中“动态创新活动”与“静态循环流转”等精神分裂式矛盾的批判和超越,使演化观在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的互补性综合中构建起了创新扩散机理相对完整的理论逻辑链条,是演化经济学核心思想相对集中的体现。黄凯南将创新机制、扩散机制、选择机制及其互动总结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结构,以期搭建各种演化范式的交流平台,并强调了个体认知、技术和制度的共同演化;〔15〕但是,黄凯南在对各组关系进行描述和辨析时忽视了“结构”这一重要元素及其与技术、制度的互动关系。此外,“新熊彼特”学派从经验研究发展而来,相关理论成果尚缺乏哲学层面的升华。贾根良对此早有洞察,且认为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从本体论、认识论、分析方法三方面探讨了“新熊彼特”学派与批判实在论之间的一致性。〔16〕然而,贾根良的研究只着眼于思想层面的分析与梳理,旨在实现相关学派之间的交流与综合,对于将批判实在论所揭示的超验实在、深度机制原理、“涌现”关系、能动性与结构转化关系在创新扩散机理逻辑分析链条中进行具体而清晰的“实质性”融合,他少有涉及。
三是创新的经济效应,即对创新作用于经济实践的分析或解释,体现了演化观的实用价值。上述“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结构、制度共演分析模式已涉及创新的经济效应(即创新引致结构变迁),而演化观的经济效应学说远不止于此。熊彼特较早洞察到了企业家创新活动与商业周期的关系,运用创新理论预测了资本主义的前途。〔17〕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借鉴而来的法国调节学派研究了资本积累与社会经济危机之间的“调节机制”,着重分析了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金融积累体系的内在危险。复杂经济学的研究揭示了技术竞争、报酬递增与锁定效应的技术演化机理,〔18〕论证了经济的非均衡性、动态性和复杂性,〔19〕其中“路径依赖”概念〔20〕被诺斯(Douglass C.North)引用到了“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并有学者基于路径生成的内生性特征批判性地提出和发展了“路径创造”理论。〔21〕近年来,演化观的创新经济效应学说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的关系、〔22〕技术追赶、〔23〕贫困陷阱、〔24〕技术陷阱〔25〕以及“新李斯特”学派关于维护欠发达经济体利益的政策思想研究,〔26〕这些学说为反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提供了参考。我国学者对此已有借鉴性研究,〔27〕且预测到了“去全球化”的长期趋势并提出了政策建议。〔28〕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我国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有关创新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产业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29〕高质量经济活动、〔30〕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政治范式的探讨,〔31〕以及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反思〔32〕和对财政货币制度革命的思考。〔33〕然而,对于“双循环”战略、“科技自立自强”等政策议题的内在逻辑尚缺乏基于技术、制度、结构等创新演化观元素的系统性分析。
综上,尽管“创新”在演化经济学中无处不在,却缺乏基于创新主题维度的理论化提炼;将批判实在论运用于演化经济学分析时只注重对比性说明与解释,并未尝试将相关哲学思想具体、清晰而明确地运用于理论构建;对当前发达国家“去全球化”以及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缺乏基于演化观的系统性解读。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阐明“创新演化观”的核心思想与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创新演化观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自立自强”进行更本质的阐释。
二、创新演化观的核心思想与分析框架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达尔文主义“遗传—变异—选择”的基本分析框架、批判实在论的超验实在与深度机制原理、“涌现”关系和“能动性—结构”转化关系,对各流派、学说进行综合可以获得“创新演化观”的核心思想:新奇创生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新奇不断产生新知识、新技术、新制度,通过技术与制度之间永无休止的互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跃迁,新奇、技术、制度、结构之间动态的、持续的共演过程所形成的“新奇创生—技术涌现—制度协同—结构变迁”演化通路最终促成了经济不断增长。据此构建如下页图1所示的“创新演化观”逻辑分析框架,具体可描述为以下三组互动关系:
一是新奇创生与技术(惯例)和制度(惯例)的涌现关系。涌现关系是批判实在论“超验实在主义”的体现,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经验实在主义”相对立。所谓涌现,即系统作为整体往往表现出个体所不具备的特征,这些特征内生于个体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却不是个体特征的简单加总(不可完全还原性),类似于凝聚态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W.Anderson)所说的“More is different”。涌现现象揭示了新事物的发生机理,且批判实在论认为“不同涌现层次具有独立的突现特性与因果作用力”。个体(个人、企业等)的新奇本能不断产生新技术和新制度,新奇与技术(惯例)、制度(惯例)均是涌现关系,因而新奇创生会受到现有技术和制度的启发或限制。
注:技术(惯例)包括企业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水平;制度(惯例)包括企业制度(生产组织模式、企业文化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产业政策、地域文化、技术标准和规范、社会习俗等;结构指企业产品结构、区域或国家产业结构、区域或国民经济构成等。
二是技术(惯例)与制度(惯例)的协同演化关系。技术与制度构成“协同演化共同体”,技术演化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决定并影响着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同时制度对技术存在锁定效应,二者相互塑造、协同演化。因此,技术(惯例)和制度(惯例)在各自的演化进程中表现出路径依赖或自我锁定现象。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体”与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是一种选择性开放机制,存在着户籍、人才签证、技术标准、关税、外汇管制等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细胞膜性质的交换壁垒,一般只允许有益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通过,阻止(甚至向外界输出)有害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通过。可编码知识的复制机制可以使一部分技术和制度从外界经济体习得和引进,参与到演化进程中。发生的间断性技术引进和制度引进,影响和决定着“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体”的演化进程。
三是“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体”与经济结构之间的“能动性—结构”转化关系。“能动性—结构”转化关系即批判实在论开创者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在《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中的“社会—个人关系模型”(The Transformational Model of Social/Person Connection)所阐述的结构与行为者关系问题。能动性与结构在互动过程中往往体现出条件与结果二重性,即结构先在于个体有目的的能动性实践,同时也是众多能动性实践的无意识结果;能动性决定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趋势,也接受了结构所带来的便利或受到了结构的制约。技术与结构、制度与结构之间均为搜寻与选择关系,技术和制度在面临演化压力(竞争)时会各自以“满意”原则进行不断搜寻,从而产生新的技术(惯例)和制度(惯例)并最终决定着结构的变化;结构对技术和制度进行选择的同时也会对其产生锁定效应。“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体”通过新奇创生不断发挥着自主能动性作用,进而表现出“路径创造”效应,激发、重制、改变着产业和经济结构,同时也被产业和经济结构的“锁定效应”所促进或制约。“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体”与经济结构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相互构成。“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体”与结构之间的“能动性—结构”转化关系本质上也是“涌现”关系(具有不可完全还原性)。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现实当中一轮轮科技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周期性演进过程总要借助流动性(货币资本)力量来满足“购买力的创造”和“企业家信贷需求”,〔34〕货币供给自然成为“技术—经济”演化体系中有关“结构”和“制度”的重要因素,对经济周期与危机产生着放大效应。
三、创新演化观视阈下的“科技自立自强”
(一)“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性与“国内一体化”的必要性
从创新的演化观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涵在于以下两点反思:一是依靠后发优势的发展模式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即“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何者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二是“全球一体化”与“国内一体化”何者能够真正实现“技术创新—制度调整—结构跃迁”演化路径的良性循环?
1.“技术引进”的不可持续性
从技术演化机理来看,技术引进无法使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存在默会知识。技术演化本身存在着大量“不可编码惯例”或“默会知识”,它们是以“技巧”或“经验”形式存在的,这种知识无法以语言文字等编码形式进行清晰的程序化表达以便于复制和遗传,而只能通过技术研发及应用者在特定交流模式与合作氛围下的无数次操作、试错、“干中学”等过程中习得,且“默会知识”在价值链高端环节知识体系中往往处于核心位置,从而使技术引进受到很大局限。二是存在链主压力。〔35〕“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体”的选择性开放,使价值链高端环节技术被链主国及其跨国公司控制,它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必然会对后来者进行遏制和技术封锁,拒绝可能对自身形成竞争压力的信息、知识和能量向演化体系外溢出。三是存在协同脱耦。〔36〕一项技术经过长期演化会形成设计、材料、工艺制造、测试检验等全产业链协同演化技术生态,在相对自由的市场条件下,比较优势带来的分工深化使不同环节的核心技术往往分处不同经济体系内,在彼此依靠供应链系统互通有无、长期投资形成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的同时也会形成协同演化壁垒,后发经济体在此种格局下试图通过技术引进实现经济追赶是不现实的,更可能的结果是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在英国学者佩蕾丝看来,成熟技术(第一种机会窗口)中不可能存在追赶机会。对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真正有意义的是“第二种机会窗口”,即处于酝酿阶段的新技术革命,这种技术或知识往往是公共的且处于实验室阶段。〔37〕相较于发达经济体受困于成熟技术经济范式的锁定效应而言,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一张白纸”的“船小好调头”状态,若能更快培育起可行的颠覆性技术体系并顺利进入良性循环的“技术—经济”演化进程,就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
2.“国内一体化”的必要性
创新演化观的逻辑分析框架是一个内生非线性相互作用的一体化系统,也是不断与外界进行着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耗散结构,有一个扮演着麦克斯韦妖角色的生物体细胞膜存在,永远对外界保持选择性开放。价值链高端环节收益递增性高质量经济活动需要关税、产品标准、外汇管制等制度壁垒下一个相对一体化的国内市场,以保障“高生产率—高实际工资”的良性循环,达到杨格定理所描述的“报酬递增分工经济”与“普通民众购买力”相结合。
从经济史角度进行考察可发现,后发经济体实现赶超从来不是依靠“全球一体化”。恰恰相反,美国与德国的崛起均是借助高关税壁垒等措施形成的“国内一体化”,〔38〕由于外部产品很难进入,某些源于别国的创新反而在本国产生了技术应用上的规模经济,形成了“高生产率—高实际工资”良性循环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内需得以反哺生产,进入“技术创新—制度调整—结构跃迁”的良性演化通道。而彼时的头号发达国家英国则依然延续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自由贸易等“全球化”政策,最终被后来者赶超。
这就印证了聚焦于欠发达经济体利益的“新李斯特主义”学派的核心主张:一是要抓住价值链高端技术突变机会窗口(尤其是“共谋型”技术创新〔39〕);二是要以“国内一体化”市场保障中高端技术的溢出效应留在国内。“新李斯特主义”的政策主张正是技术创新引致结构跃迁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的有力保障。从这个角度讲,发达国家对我国采取技术封锁、高端工业资本品断供等措施是“危”更是“机”,有利于倒逼我国加大自主创新投入以实现进口替代和发掘技术突变机会,从而打破现有价值链高端成熟技术演化进程的锁定效应,实现路径创造;同时又天然形成相对封闭的“国内一体化”市场,使得创新及其级联演化溢出效应保留在技术演化体系内部、形成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通路成为可能。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路径
“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可以从经济角度来解释的现象”,就像生命是基因的表达一样,经济也只是创新的一种表达。这也是批判实在论深度机制原理以及涌现关系所揭示的“层级之间不可化约性”的体现。而创新的涌现是有内在发生机制的,创新也是有生命的。一个新奇不断涌现、技术不断生成、“技术—制度—结构”良性互动的经济体系能够不断进行路径创造,展现出勃勃生机;而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包括先前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造成“技术—制度—结构”演化通路受阻或新奇无法顺畅表达,经济体系便陷入僵化、锁死直至衰退,或者循环累积造成结构失衡引发泡沫与危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自立自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尽快实现进口替代,二是努力促成颠覆性技术涌现。前者是在现有技术生态体系下应对高端资本品断供和产业链断裂困境之举;后者则是打破现有技术演化路径锁定效应实现经济赶超的机会窗口,而核心环节就在于通过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打通从技术涌现到结构升级的良性、健康演化通道,不断创造增量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结合创新演化观的思想逻辑,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1.营造宽松自由的创新氛围
新奇创生是“技术创新—制度调整—结构跃迁”演化路径的源头活水,新奇创生的自主、自发、不确定性需要鼓励创新、宽容异端、自由无束、悦纳失败的社会氛围,需要多元互动、畅通交融、平等和睦、公正开明的文化环境,更需要低价优质的职住空间、精准专业的创投市场、周到体贴的政务服务。应当全方位营造宽松自由的创新氛围,确保新奇的不断涌现和顺畅表达。
2.提供灵活精细的制度供给
“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体”是创新演化生态系统的核心内容,技术与制度的协同共生理念也是演化经济学各流派(及相关流派)日趋形成的核心共识之一。〔40〕在技术创新与演化进程中,都需要时刻充分关注有关国家/区域/企业创新体系的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落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过程中与旧制度的矛盾冲突等问题,提供灵活机动、精准适度的制度供给,以破除路径锁定,确保技术与经济不断迭代升级。同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科技攻关中的关键作用,以更具调动力的制度能动性激发并适度引导技术演化与突变方向,在弥补原有“技术—经济”自然演化状态下“比较优势陷阱”的同时促进颠覆性技术的涌现。
3.突出民营科技企业在技术演化中的主体地位
民营科技企业(尤其科技类头部企业)是技术创新与演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市场机制参与基础科技研究的中坚力量。比如,华为“2012实验室”、阿里“达摩院”、腾讯“量子实验室”等机构,它们作为技术演化生态系统中最敏锐的触觉神经元,时刻感受并引领着技术演进方向和科技攻关靶向。应确立民营科技企业在技术创新与演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尤其要谨慎制定“反垄断”政策,充分认识技术演化过程中“收益递增”与“正反馈”机制造成垄断现象的必然性,以“确保市场自由进入”而非“是否一家独大”为原则裁定垄断判罚。
4.确立“科技自立自强”在“双循环”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充分认识当前去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疫情冲击等外部环境中的“危”“机”转化机会窗口,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落实“双循环”战略的核心抓手。利用产业链断供危机加快科技攻关步伐,探索打破技术演化路径锁定的颠覆性技术突变机会,促进“共谋型”技术涌现;在技术封锁下被迫形成的“国内一体化”市场中促进价值链高端自主创新型工业资本品的国内供应和消费;在“国内大循环”中促进新生技术的级联演化,形成产业间的系统协同效应;保持货币审慎适度供给,形成以内需反哺创新的“高生产率—高实际工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步入技术迭代升级与经济结构跃迁的健康演化通道。
5.夯实制造业根基,坚决遏制过度去工业化
产业转型升级绝不等于简单粗暴的“退二进三”,收益递增性高质量经济活动也绝不意味着去工业化,而是要向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各类产业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坚实的工业基础恰恰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和高附加值环节的依托。当前,我国制造业附加值低,随着土地、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产业脱实向虚形势严峻,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跃迁的演化通路受阻。应充分吸取美国等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失衡的教训,警惕过度“虚拟”的产业及经济(资本)结构对“技术—经济”演化进程的损害,出台系统性措施遏制过度去工业化。
6.注重幼稚产业保护,优化外贸结构
从新技术涌现到新产业形成并产生收益递增性经济效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期间难免受到来自演化体系外部(低价或高质同类产品)的竞争压力。应针对处于发展初期、基础和竞争力薄弱、具有发展潜力的幼稚产业适时出台补贴、扶持、关税及非关税等保护政策,以确保其正常发育和顺利演化;建立动态保护机制,研究退出条件和时机,避免过度保护(挫伤持续创新积极性)或保护不足。此外,至关重要的是“出口什么”而非“出口多少”,应反思单纯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出口,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中促进创新租金在我国技术演化体系内部生成、保留、扩散和积累,努力向内需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变。
注释:
〔1〕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贾根良:《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发展与当前的任务》,《政治经济学报》2020年第1期。
〔3〕〔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7-154页。
〔4〕Veblen,T.B.,“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898,12(4),pp.373-379.
〔5〕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8-361页。
〔6〕杨虎涛:《演化经济学的两种系统观》,《经济学家》2009年第8期。
〔7〕赵华:《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优越性》,《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8〕陶海青、金雪军:《技术创新的演化趋势》,《管理世界》2002年第2期。
〔9〕洪银兴:《科技创新与创新型经济》,《管理世界》2011年第7期。
〔10〕黄凯南:《制度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11〕贾根良:《演化经济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3页。
〔12〕Bednarz,M.,Broekel,T.,“The Relationship of Policy Induced R&D Networks and Inter-Regional Knowledge Diffusion”,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19,29(5),pp.1459-1481.
〔13〕Günther,J.,Kristalova, M., Ludwig,U.,“Structural Stability of The Research & Development Sector in European Economies Despite The Economic Crisis”,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19,29(5),pp. 1415-1432.
〔14〕Pariboni,R.,Tridico,P.,“Structural Change,Institut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Europe”,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20,30(5),pp.1275-1300.
〔15〕黄凯南:《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16〕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17〕Schumpeter,J.A.,“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2,3(4),pp.594-602.
〔18〕Arthur,W.B.,“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Economic Journal,1989,99(1),pp.116-131.
〔19〕Arthur,W.B.,“Complexity and The Economy”,Science,1999,284(5411),pp.107-109.
〔20〕David,P.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American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1985,75(2),pp.332-337.
〔21〕傅沂:《路径构造理论与演化经济学:分离还是融合?》,《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8期。
〔22〕〔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23〕Jimenez,P.,Ricardo,J.,“Mainstream and Evolutionary Views of Technology,Economic Growth and Catching Up”,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19,29(3),pp.823-852.
〔24〕Carrera,S.,Edgar,J.,“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Poverty Traps”,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19,29(2),pp.611-630.
〔25〕Paus,E.,“Trapped in The Middle?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for Middle-Income Countri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21,59(2),pp.663-665.
〔26〕〔英〕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27〕杨虎涛:《李斯特谱系:一再被强调的国家和逐步被重视的社会》,《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
〔28〕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29〕黄凯南、乔元波:《产业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分析——基于多主体的学习过程》,《经济研究》2018年第12期。
〔30〕杨虎涛:《高质量经济活动:机制、特定性与政策选择》,《学术月刊》2020年第4期。
〔31〕杨虎涛:《社会—政治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的耦合分析——兼论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政治范式》,《经济纵横》2020年第11期。
〔32〕贾根良、何增平:《现代货币理论大辩论的主要问题与深层次根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33〕贾根良:《财政货币制度的革命与国内大循环的历史起源》,《求索》2021年第2期。
〔34〕〔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贾拥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7页。
〔35〕杨虎涛、贾蕴琦:《产业协同、高端保护与短周期迂回——中兴事件的新李斯特主义解读》,《人文杂志》2018年第9期。
〔36〕〔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51页。
〔37〕这种技术或知识通常被传统的熊彼特意义的创新所忽视,即与发明进行了区分的创新,可总结为:生产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新原材料来源、采用新组织形式。显然,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创新的产生机制、组织形式,以及创新与科学发明、基础科学理论发展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早已今非昔比,熊彼特只局限于技术大规模商用和产品大规模推广为目的的静态创新观是狭隘的。复杂经济学的研究则相对重视发明及其背后的原理,并指出科学与技术“以一种共生方式进化着,每一方都参与了另一方的创造,一方接受、吸收、使用着另一方,两者混杂在一起,不可分离,彼此依赖”。这也是批判实在论深度机制原理和涌现关系的体现。因此,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环节也必须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创新体系。
〔38〕工业化起步晚于英法的美国从建国初期到二战前夕一直践行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思想,实施以开拓国内市场为主的“孤立主义”政策;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贸易保护、关税同盟等政策有效促进了德国的工业化转型和经济崛起。而在此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以及在此之后日本的古典发展模式也都得益于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等经济发展思想。
〔39〕赖纳特依据技术进步产生收益的扩散方式不同将技术分为两种:一是古典形式,即以较低价格或较高质量体现,往往使消费者受益而使生产者受损,如“索洛悖论”所描述的计算机作用随处可见但却无法从政府统计资料中显现;二是共谋形式(collusive form),即以雇主、工人及政府获得较高应税收入的方式体现,如“福特主义”提高工人货币工资的利润分配方式。
〔40〕比如,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老制度主义传统”的凡勃伦关于技术与社会习惯两个层次冲突与互动的描述,熊彼特企业家理论中将企业家创新根植于社会传统和历史基础,新制度主义“工具正当知识”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激励相关论述,“新熊彼特”学派“国家创新体系”及企业“惯例”理论,调节学派制度嵌入理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