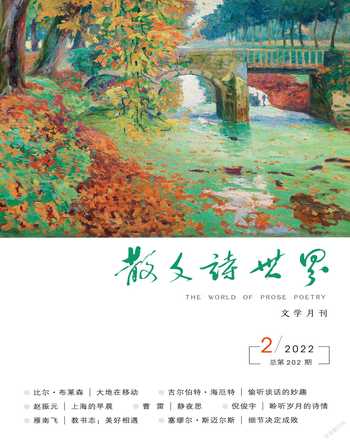看香港电影 外四章
葛希建(南京大学)
浪漫的想象是不可缺少的。晚八点,一些人在荧屏上说话,黑色的花椒树紧绷枝桠。
马六甲海峡的水气,手提箱里的美钞和军火,黑帮老大叼着一根雪茄。
逼仄的空间在来回的枪声中闪耀。当主人公的腹部溢出一摊黑血,
粤语歌曲在人的心坎上拨动,整个晚上是如此抒情,每个音调都合乎生活本该如是的样子。
单调的鼾声刻录丰腴的梦境,在血液的流动中,火红的罂粟花,随风招摇。
婚姻生活
又是一次开始。争吵的声音让心室收缩,房间的每个孔隙都蛀满偷窥者的眼睛。
家庭史已被历数,从结婚那天算起,内室置办的每件物什都铭写屈辱的记忆。
桌子上的课本瑟缩,好像音部已抵达肝火的界限,空出的一片休止。
他们被迫关注细节:窗上的冰花、雾中的烟囱、南方打工亲戚寄来的帷幔、沙发上硬壳状的指甲、过期的挂历。在一次次视角的叠加中,事物收缩为电视荧屏上的影像,缓缓移动起来。
省道302
省道302,车载的人口和货物从这里出发,交换城市的浮华。
黄昏,他从我家门口路过,新上季的仿制品包装得青春,格外亮眼,
摩丝固定的发型,好像火车道两边的山峦。
他在空气中和外界通话,剥玉米那般拿捏说话的腔调。可能是一桩大买卖。
他手机中的上海滩开到最大声,走远的脚步富有魔力,好像外面遍地都是黄金。
他有可能在维多利亚港抽雪茄,也有可能死在夏天的某个午后。
小白龙探母
天上的小白龙探母,再一次途经我的家乡。
过多的雨水降临,我变成一株吸水的植物,浸泡在河岸的凹坑里。
天气预报说接下来一周,安徽大部分地区会有强降雨。
我将一直呆在家中看电视,重复的广告,像咒语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播放。
我来回在屋中走动,像被上了满格的发条。
如果可以,我会穿过这个雨季。在路上,一边生锈,一边生长。
独立的统治
冬天,整个村庄被大雾包裹,天空好像生病了。
我在炉子前取暖,手贴到水壶上,热量传输我的身躯。
从地窖里挖埋藏的萝卜,从坛子里夹腌制的咸鸭蛋。
等两集电视连续剧播放结束,再用火钳换另一个煤球。那已经很晚了,我总怕死者在雾中显现。我插上门闩,向奶奶的屋里瞧上一眼,黑魆魆的,好像此刻她的生命是中性的。我掸掉裤腿上的雪片,走两步,试图完成一次独立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