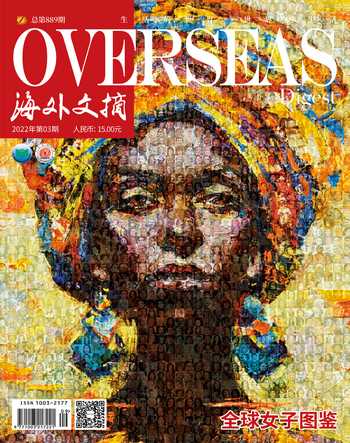古老牧歌唱出瑞典女性史
珍妮·蒂德曼–奥斯特贝里

这是一句让我感触颇深的话:“我们生来就要劳作,天生担负责任。二者伴随我们的一生,融在我们的血液里。”
那是2017年,我正在听瑞典达拉纳博物馆声音资料库的录音,说话的是瑞典妇女卡琳·萨罗斯。她来自达拉纳省穆拉市,生于1887年4月20日。
在卡琳13岁那年,她第一次被派到夏季牧场(fäbod)工作。她要为家里放牛,还要制作足够过冬的奶制品。村子里的妇女每年夏天都在牧场上过着没有男人陪伴的日子。那时,卡琳会给姐姐写信,把每天在牧场里的生活事无巨细地告诉她。在卡琳86岁那年,她对着麦克风读起了自己儿时写下的信。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出她已经没剩几颗牙了。她的嗓音低沉而嘶哑,但饱含伤感的回忆与对青春的憧憬。
卡琳不仅谈到了劳作与责任,还谈到了独立生活给牧场女工带来的自由感。虽然夏季牧场意味着辛苦劳作,但脱离受家长牢牢掌控的高压生活让卡琳体会到了舒适。在夏季牧场上,她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安排一天的劳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学会了如何用自己的声音召唤牛群。她满怀敬意地谈起了斯堪的纳维亚夏季牧场文化中十分常见的尖声呐喊,也就是古老的唱腔“库尔宁”(kulning)。

瑞典的夏季牧场
很遗憾,我没有听到卡琳·萨罗斯演唱库尔宁。她的声音只留存在了一个口述故事的档案中。
不过,另一位卡琳演唱库尔宁的声音还是把我迷住了。这位卡琳就是来自达拉纳省特兰斯特兰德的卡琳·爱德华松·约翰松。她生于1909年,是家里十个孩子中的老大。在她五岁那年,她妈妈和村子里其他几个年长的妇女开始教她唱库尔宁。卡琳的歌声成为了瑞典及其夏季牧场文化理念的代表性配乐。由于对库尔宁传统作出了不少贡献,她获得了瑞典的索恩金质奖章,还在广播、电视以及牧歌音乐会上表演库尔宁。1997年卡琳去世后,瑞典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刊登了卡琳的生平,介绍了她作为夏季牧场女工的种种事迹。
听完两位卡琳的故事和歌声,我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不仅要向两位卡琳致敬,也要向所有夏季牧场女工致敬。她们为了养家糊口,担起了如此繁重的工作。她们从牛奶和山羊奶中提炼奶酪和其他奶制品的方法沿用至今。她们贡献的知识让我们的食品制作工艺更精湛,让生活更美好。她们创作的音乐能召集牧群,使其免于落入狼与熊之口,后经小提琴手改编,又变成了舞蹈的配乐。
如今,我们能在许多现代语境下看到夏季牧场女工劳作与歌唱的痕迹。这证明她们不仅是瑞典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今日的一部分。她们在彼时与此时刻下的印记指引我们思考“遗产”一词的真正含义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在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社会里,每次表达文化只需要点一点鼠标或滑一下屏幕,于是我们发现自己总是在探索该如何自我定位。在动荡时期,比如陷入疫情、战乱、饥荒,以及面对气候危机等其他威胁稳定与安全的因素时,我们倾向于为自己寻找一个更纯粹的立足之地。在那里,本土社会比全球大局更具有存在感,农村没有被城市吞噬,我们也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改变自然以适应我们的需求。
而这一切都深嵌在夏季牧场文化中。这就是为什么对瑞典人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其他各国的人们来说,接受夏季牧场文化是如此重要,无论是将其视作遗产还是历史。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参与其中。对我来说,做夏季牧场女工的工作、学她们的手艺、唱她们的牧歌,这都是我與瑞典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有形联系的方式。这也是我向数百年来一直游离于书面历史之外的夏季牧场女工致谢、致敬的方式。为了找回这部分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库尔宁牧歌诞生的夏季牧场,重温那段时光,重现当时的工作情境。

牧场女工需要独自承担繁重的劳作,为全家越冬作好准备。
夏季牧场由贯穿瑞典中部的荒野地带构成,包括山地牧场和森林。这片荒野最终延伸到了挪威的山区。每到夏天,农民就会到夏季牧场放牧,时至今日依旧如此。一个家庭牧场包括农舍、小型乳牛舍、火炉房,还有牛棚、山羊棚和绵羊棚。有时,还会出现多个家庭群居的情况。妇女们会在周围绵延数公里的无围栏牧场上和森林里自由自在地放牧。
那么,为何夏季牧场体系能延续至今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研究一下瑞典人与自然及自然规律的关系。瑞典南部的土地,土壤肥沃但面积有限。中部荒野地带的冰碛土又十分贫瘠。农民需要一种既能养活人又能养活牧群的方法,那就是每逢夏季将牧群赶到青草成熟早且草地面积广的地方。

对村民和农民来说,夏季牧场文化曾是一种生存策略。直到20世纪初新的用地策略出台,将牧群赶往夏季牧场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规则。每个村子的村民会聚在一起,定下迁往牧场的时间。到了那一天,数百头牛、山羊、绵羊就会涌出村子,走向高山。
放牧文化存在于世界各地,但有一件事让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夏季牧场文化与众不同。在夏季牧场里,放牧的是一位妇女。她要保护牧群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要给奶牛和山羊挤奶,要保证家庭与房屋完好无损,还要制作奶酪和其他奶制品。她不能犯错。哪怕是死一头牲畜,也会造成严重的物资短缺。在制作黄油、奶酪、乳清制品的过程中,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害她全家在冬天忍饥挨饿。
村子里人力不足,所以妇女通常独自前往夏季牧场。她不能休息,不能睡懒觉,雨天也不能躲起来。即便如此,声音资料里的大多数女性说,她们每年到达夏季牧场后,立刻就能感受到独立与自由。比起身穿破衣烂鞋、独自待在黑暗中陷入极度的疲劳,以及独自在沼泽地埋头苦干,独立与自由的感觉压倒了她们内心的恐惧。
夏季牧场女工的生活意味着她们要树立自己的习俗与传统。数百年来,这套习俗与传统经母亲传给女儿。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创造了自己对女性的定义,也创造出了自己的音乐语言。
在原始语境下,库尔宁是一种劳动歌曲,其诞生是为了满足需求而非展现音乐。妇女们对牧群唱起库尔宁,为的是把它们赶进森林、叫牧群转移位置或引起它们的注意。妇女们也会对其他牧民唱起库尔宁,为的是打招呼和传消息,比如提醒别人警惕捕食者或森林大火等危险。对不同的牧群,库尔宁的唱法也不同。在部分地区,每个夏季牧场女工都有自己标志性的旋律,这样大家就知道谁在森林里了。
库尔宁总被人们描述成带装饰音的高音呐喊,通常属于小调。然而,很多录音显示,库尔宁也能用低音演唱,可见这种传统很是复杂。妇女们来自何方、受教于谁,决定了她们歌声的音调。库尔宁里最常见的高音呐喊声可达780—1568赫兹,而一般成年女性的说话声在165—255赫兹之间。

库尔宁流传至今。
库尔宁没有稳定而强劲的节拍打底,歌词创作通常比较自由随意,重音一般落在元音I和O上,常以辅音H和J开头,有时也以辅音S和T开头。库尔宁的旋律大多下行并缀有装饰音。
有关瑞典北部的中世纪资料中包含几段牧民的描述。她们说自己会用动物的角吹出乐曲,向自家牧群和其他牧民传递信号。16世纪,牧师奥劳斯·芒努斯向教会汇报瑞典农民的情况时,也提到了吹奏动物角的做法。不过,这一做法鲜少出现在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夏季牧场文化中。
17世纪80年代末,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约翰内斯·哥伦布写道:“瑞典山区女牧民的叫声很奇怪。”
18世纪末,学者们发起了旨在“重新发现”欧洲乡村音乐的运动。100年后,这个运动在民族浪漫主义时期达到高潮。在那时,长久以来一直作为牧民日常劳作的一部分且鲜少被称为音乐的库尔宁,不仅获得了人们的重视,还被赋予了新的文化价值。绘画、制作明信片、创作诗歌和举办小提琴比赛成了人们歌颂夏季牧场文化及其特色牧歌的标准方式。改编的瑞典牧歌作品也大量涌现。
或许,正是从那时起,库尔宁才真正从牧民之声转变成了放牧之歌。在那一时期,所有牧歌开始了文化“提炼”的过程,库尔宁更是如此。这一过程使库尔宁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既新颖又传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瑞典特色。
20世纪初的农业改革后,将牧群赶往高山牧场的需求减少了。突然间,庄稼收成和村内牧场足以养活人和牧群。20世纪中期更是实现了牛奶的工业化生产。到了20世纪后期,许多高山牧场都荒废了,女牧民的歌声也停止了。不过,仍有许多人沿袭着夏季牧场的传统。
如今,人们无需再遵循规则前往夏季牧场,即使去了也是麻烦多,收获少。然而事實证明,比起抱怨繁重的劳动,人们沿袭传统或继承“遗产”的意愿更强烈。19世纪中期,瑞典有3000多个夏季牧场。如今,仍有200—250个夏季牧场存在。
现在我渴望离开森林,前往山那边我的家。
黑暗渐渐笼罩这森林,夏日已离我们而去。
每只鸟儿都已飞走,每朵花儿都已死去。
草地失了肥力,如今已不见茂盛的牧草。
我数着过去的每一天,一周漫长得像一年。
不久我会回到父母家,我将立刻停止所有的渴望。
现在我渴望离开森林里的小路,我在那里迷失过方向。
我在黑暗的森林中,在沼泽里,在冷杉林、石楠丛和桦树林里误入歧途。
现在我渴望离开森林,也离开湖泊。
不久我就要告别,我将回到我的家。
在那里我能依偎在温暖的火堆旁。
表演库尔宁让她们觉得自己与本国文化遗产建立起了联系,也让她们觉得自己作为女人拥有了权力。
如今,夏季牧场女工的歌声从森林和高山牧场传了出来。演唱库尔宁成了仪式惯例,也成了表演项目。它带上了异国情调,进入了学术领域,走向了规范化,其文化意义得到了提升。人们认为库尔宁独一无二,难以学习,也难以掌握。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学院之类的高等院校还专门教授库尔宁。多位库尔宁传承人也开班授课。
在我研究库尔宁的第一年里,我采访了许多专业的女性民歌歌手。她们曾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表演过库尔宁。她们在斯德哥尔摩环球竞技场表演过,就在冰球比赛的中场休息时段;她们也在王室城堡里表演过,就在瑞典国王和外国贵宾的面前;她们还在盛大的汽车博览会开幕式上表演过。美国的玛莎·斯图尔特圣诞特别广播节目曾将她们演唱的库尔宁选为“冬日之歌”。当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的歌剧《生命》在东京上演时,她们演唱的库尔宁也是剧中众多传统歌声之一。
即使是迪士尼也需要库尔宁。在2013年的热门电影《冰雪奇缘》中,艾尔莎发现了自己的内在能量,发现了她冰雪魔法的真正力量,而那一刻我们听到的就是库尔宁。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能看出,库尔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受众人赞赏的声乐表达方式。如今,库尔宁游走在两极之间。它既属于城市,又属于乡村。表演的人既有老少农民,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歌手。这群歌手或是在皇家学院中学习过,或是师承自家祖母或者姨妈。如今,库尔宁既能呈现出歌剧的风格,又保留了传统的唱法;既可精心编排,也可即兴表演。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库尔宁远播万里,但受其影响最大的还是社区和家庭。我采访过的许多女性说,表演库尔宁让她们觉得自己与本国文化遗产建立起了联系,也让她们觉得自己作为女人拥有了权力。这种直爽而有力的声乐表达方式对她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她们的声音在地平线上回荡,占据了广阔的空间。在她们表演库尔宁并投资与之相关的文化时,她们既是在展现文化遗产,也是在将其概念化并与之磨合。她们对夏季牧场女工的歌声、手艺和劳作进行了彻彻底底的研究,里里外外都是学问。她们的研究既与过去建立起了有形的联系,也让瑞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清楚楚地显现在了世人面前。
像夏季牧场这样的文化遗产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地基,站立其上,我们就能更好地看待和理解当今世界。文化遗产让许多人与之共鸣,为之自豪,它也指明了我们最该保护什么,最该实现什么。定义文化遗产的过程应该是思想和活动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让我们与历史的邂逅更加迷人。参加与文化遗产相关的实践活动让我们渴望了解更多。一旦我们的求知欲熊熊燃起,文化遗产就能帮我们理解为何我们生活在现今的环境与社会结构下——因为文化遗产不在彼时,就在此时。
[编译自美国《史密森尼》]
编辑: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