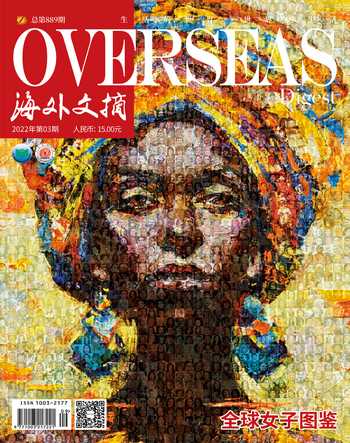全球女子图鉴:发声、掌权、改变命运、塑造未来
拉尼娅·阿布泽伊德

肯尼亚动物追踪者:正在放牧的梅帕雍·罗伯提贡23岁,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前往内罗毕谋生,却在那里不幸遇难。此后她只能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她另一份全职工作是为大象保护项目绘制象群活动路线图。为挣得每月薪金,她同另外八名妇女一起穿越丛林,来往于大象、狮子和水牛群之间。她手无寸铁,但身姿挺拔,性格刚强:“我做这一切,只为孩子不必饿着睡去。”
特蕾莎·克钦达莫托对自己终结的第一段童婚记忆犹新。在她成为马拉维南部恩戈尼族第一位女酋长几天后,在首都利隆圭东南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球场上,她看到一个正在和伙伴踢足球的少女停下玩乐离开,去给孩子喂奶。“我很震惊,并深觉心痛。”克钦达莫托回忆说,“小妈妈12岁,她还骗我说她13岁了。”她将此事告知族内长老,他们说:“这很常见。但现在你是酋长,就放手去做你想做的。”
所以克钦达莫托做了。她结束了这场童婚,并把女孩送回学校。校长垫付女孩的学费直到她中学毕业。她如今经营着一家杂货店,每次拜访女酋长时总会说:“谢谢您,酋长,谢谢。”
自此,女酋长在争取女性权益的事业上脚步不停。60岁的她已经取缔了2549个传统女性组织,禁止对入会女性施行夺走童贞的野蛮性启蒙仪式,并将少女们送回学校读书。“女性的声音是一场革命。”2013年,在开罗解放广场上,抗议强奸和性侵的游行者如此高呼。女酋长的声音亦是全球女性运动发出的众多声音之一。
当下世界仍属男性主导。然而,从政治到艺术,女性正在各个领域努力改变她们的处境。在政府机构、工作场所和家庭内,妇女们通过激进的街头示威和潜移默化的社群塑造推进着革命。
父权制根深蒂固,平权之路坎坷,无论男女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迄今为止,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性别平等。性别不平等不受地域、種族或宗教的影响。加拿大在世界经济论坛年度性别差距指数中排名16,而美国排在第51。
这些排名加深了我们对世界各地女性所面临的挑战和其影响力的理解,特别是在中东和非洲。这两片广阔地域的情况往往被统计数据所忽略,无视其内部的细微差异,只归于一个简单粗暴的概念下。
“中东不止有一种女性,”黎巴嫩女演员兼导演娜丁·拉巴基说,“有各种各样的妇女,她们中的大多数即便在困境中也十分坚强。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社会上,女性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与男权斗争。她们是如此强大,我从未设想过她们顺从软弱的姿态,一次也没有。”
突尼斯人权律师、民主妇女协会创始人宝荷拉·哈米达认为,妄断阿拉伯妇女权益少于西方是一种殖民思想的体现。阿拉伯妇女没有停止抗争,只是她们实现女性权利的方法或许和西方不同。
女性权益不是简单地由“穿什么”这样肤浅的表象决定,而是女性是否有自由选择穿什么的能力,以及选择和掌控她生活其他方面的能力。究竟该如何有效地追求性别平等?几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经验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
在卢旺达、伊拉克等国家,法律规定的指标确保议会中女性占有一定席位。在马拉维和其他没有立法保障帮助女性变革的非洲国家,女性酋长正在通过赋予女性权力推动变革。
2012年,乔伊斯·班达成为了马拉维首位女总统。尽管她没有政治家族背景,马拉维议会也没有规定女性议员比例,但班达还是冲破重重阻碍走向了成功。她将非洲的进步归功于女性领导人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她们尝试引领母系权力体系在西方父权殖民体系退出舞台后回归,对女权主义抱有更为宽和的态度。班达说:“(对抗性的)西方女权主义在这里行不通。我们不会照搬别处的模式实现平权。在非洲,女性曾是领导者,她们不会通过恐吓男性来获取权益。相反,吸引男性、说服他们接纳女性成为领导者才是非洲的传统。我们需要回顾我们的历史,照非洲的方式去实现平权。”
班达的平权事业和她个人的生活经历紧密结合在一起。好友因贫困失学的痛苦促使班达成立基金会,为贫困女孩提供免费受教育的机会。十年的受虐婚姻激励她成立全国女性商业协会,为女性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她说,经济独立能为女性提供更多选择。
2006年,班达担任马拉维性别事务部长,主导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2013年,马拉维颁布了《性别平等法》。在班达执政的两年时间里,孕妇死亡率显著下降。班达自己在生下第四个孩子时经历过大出血。此后,她十分关切马拉维女性的分娩问题。班达寻求男性部落酋长支持,说服他们鼓励族人前往医院生产。在班达看来,这是在男性支持下改变社会规范的非洲女权事业典范。
马拉维农村人口占多数,许多社区都异常保守,男性酋长中大男子主义倾向严重。班达说:“85%的人民住在农村,在这些保守男酋长的领导之下。你必须让他们参与到平权事业中来,让他们成为支持者,这就是我现在所做的。”
国际组织来到非洲试图解决女性问题,班达认为这些人“太天真”。国际组织工作人员可以在马拉维待上20年,但一旦撤离就会发现“收效甚微”,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打破根深蒂固的传统。班达表示,招揽有影响力的酋长,从内部改变文化传统会更有效。当女性担任酋长时,改变则愈发显著。
克钦达莫托就是一个好例子。她继承父亲的衣钵,管理着551个村庄和110万人。自2003年以来,她一直致力于改变部落陋习。即便面临手下和其他酋长的抵制和死亡威胁,她也从不退缩。她说:“在我的地盘,我不希望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无论你认同与否。”
早在2015年马拉维政府将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到19岁之前,克钦达莫托就已经禁止族内童婚,并安排女孩重新接受教育。最开始,人们不愿意接受她的观点,于是她组建了巡回演出的乐队,利用演唱会将人们聚在一起,宣传反对童婚,反对少女进入传统组织。随后,她制定了章程与反对派斗争,罢免了继续举行性启蒙仪式的男酋长,在族群里树立权威。与此同时,她打破传统,任命了约200名女性担任村长或附属酋长的职位。
克钦达莫托不是孤掌难鸣。萨利马地区67岁的姆万扎酋长掌管着780多个村庄和近90万切瓦族人。她也将改变马拉维社会现状作为自己的使命,维护女性权益,禁止性启蒙仪式和童婚陋习。在她管辖的区域,担任领导职位的女性数量高达320人。成为酋长15年来,她经手废除了2060桩童婚。
必须让男性参与到平权事业中来,让他们成为支持者。
突尼斯1956年頒布的《个人身份法》是中东北非地区最进步的法律之一。它禁止一夫多妻制,确保离婚双方平等,规定了法定结婚年龄,保证恋爱婚姻自由。1973年,突尼斯彻底实现堕胎合法化。在接下来几十年没有战争、别国制裁和民兵暴力的相对和平环境里,突尼斯妇女们稳扎稳打推进着平权改革的步伐。
“阿拉伯之春”给女性活动家带来了忧患,她们担心革命会阻碍女权运动。因此,出于对女性失去权益和社会地位的忧惧,她们加快了改革的节奏。
变化来得迅猛而彻底。2014年,新宪法进一步保障了《个人身份法》涉及的人权,规定男女平等。2017年,突尼斯妇女顶着巨大的压力,赢得了与非穆斯林通婚的权利,打破了这一地区的宗教禁忌。新的反家庭暴力法也已经出台,母亲可以在没有父亲许可的情况下独立带孩子出国。横向和纵向性别平等相关法律规定,在地方选举中所有政党必须拥有同等数量的男女候选人,增加国家统治阶层的女性代表。2018年选举中,女性由此获得了48%的市议会席位。在突尼斯议会的217个席位中,女性议员占据了79个席位,这一比例为阿拉伯世界最高。
2021年9月29日,突尼斯女权组织政治分析师萨拉·梅迪尼上班时无意间看到了手机上的一条新闻提醒,她一开始很吃惊,但很快兴奋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为我看错了。”她说,“我告诉同事们:‘他任命了一位女性!他任命了一位女性!’我们欢呼雀跃,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这天,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任命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部的高级公务员兼地质工程讲师娜杰拉·布登·鲁姆赞为新总理。她不仅是突尼斯的首位女总理,也是阿拉伯世界的首位女总理。消息一出,全球妇女为之振奋。赛义德说,这一任命“是突尼斯的荣誉,是对突尼斯妇女的礼赞”。
突尼斯的平权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哈米达与其他平权人士仍在为继承问题抗争。突尼斯继承法规定女性只能继承男性亲属一半的财产,这是阿拉伯世界普遍遵守的习俗。挑战它意味着与伊斯兰教法为敌。一些女性活动家支持大部分的改革,但一旦涉及继承权这个与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问题,她们的态度也是保守的。
女权活动家梅赫齐亚·拉比迪为突尼斯人在女性权益方面取得的进步和勇于讨论继承权这类核心问题而感到自豪。拉比迪视自己为后女权主义者,认为突尼斯女性甚至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女性必须互相倾听,她说:“我们要扭转超级世俗主义和极端宗教这两种倾向,恢复我们的声音。”
对拉比迪来说,女权主义的“普世遗产”是一座可以将不同倾向的女性团结起来的桥梁,西方女性没必要为她们代言。“她们说我们应该被给予自由,但又不允许我们发声。这是自由吗?是说女权主义吗?”拉比迪质问道。她明确告知西方女权主义者:“我求求你们,不要以我们的名义替我们说话。因为当你们替我们说话时,就扼杀了我们的声音。”
获奥斯卡提名的导演拉巴基也坚信女性叙事有其力量和必要性。在第一部电影《焦糖》中,她以黎巴嫩贝鲁特五位女性的生活为切入点,探讨了父权制和社会痼疾。拉巴基说,《焦糖》的创作灵感源于她对黎巴嫩女性刻板印象的审视。大众眼里“顺从、无法表达自我、担忧自己躯体、畏惧男人、受男人支配、活在恐惧中的女人”和她现实中遇到的女强人形成了强烈反差。“某种程度上我是在尝试寻找自我。”拉巴基说,“在所有这些刻板印象里,我究竟是谁?”
在拉巴基2018年获奥斯卡提名的电影《何以为家》里,她将目光投向了街头流浪儿童。“我们把孩子拖入战争和冲突中,给他们制造了这样的混乱、这样的‘家’。”2013年当她开始构思这部作品时,叙利亚受难儿童艾伦·库尔迪惨死在海滩上的照片带给她极大的触动。“我真的很想知道,如果这孩子会说话,他会说什么?在经历过我们让他经历的这一切后,他会有多愤怒?”观众告诉拉巴基,在看完她的电影后,他们感觉到镜头后有一位女性。拉巴基觉得这是一种恭维。“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视角比男性视角更好。”她说,“但这是一种不同的视角,一种不同的体验。”
我们怎样才能开始真正改变?拉巴基说:“有时候,我的声音比任何政治家都大,所产生的共鸣也比任何政治性演讲更为响亮。我需要更进一步,在我的领域以我的方式用我的声音实现目标。”
[编译自美国《国家地理》]
编辑:要媛

宝拉·卡洪布是肯尼亚环保组织“野生动物向导”的一员。她正向来到内罗毕国家公园参观的城市少年解释物种间的奇妙联结:蚂蚁怎样帮助金合欢树抵挡来自长颈鹿或犀牛等食草动物的垂涎。

在家人的支持下,伊丽莎白·潘托伦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博士学位,继而成为了女性保护组织的一员和女性独立运动的斗士。今天,她向小城女孩们展示一种可重复使用的卫生巾包并告诫她们:任何女孩都不应该因为经期而缺席课程。

喀拉拉邦一名修女多次向教会领袖控诉一位主教曾屡屡强奸她,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因此,她将目光投向了世俗司法。2018年9月,修女们在喀拉拉邦高等法院门外抗议示威两周。坚持宣称自己无罪的主教最終被捕。教会不但没有支持修女们维护自己的权益,反而向她们不断施压,要求她们保持缄默,别惹是生非,而且取消了抗议修女们的每月津贴。左起依次是:修女阿尔菲、妮娜罗斯、阿基塔、阿努帕玛和约瑟芬。

1950年的《印度共和国宪法》是这个英国前殖民地的建国总纲,确保每一位成年印度公民“无论宗教信仰、种族、种姓、性别和出生地如何”,均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利。换言之,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印度女性便拥有投票权,她们也正行使着投票权。班加罗尔的印度女性骄傲地展示被投票站工作人员涂上墨水的指甲,这是一种避免投票舞弊的国家惯例。眼下,印度议会中女性仅占14%的席位。然而,有报告显示,随着女性投票站在各选区的建立,在部分邦中,选举日参与投票的人数女性多于男性。
5.约旦无障碍捍卫者

约旦无障碍领域的偶像阿雅·阿哈比于2019年8月走完了短暂而精彩的一生。车祸导致的脊髓损伤使阿哈比丧失了站立行走的能力,却没有击垮她的意志。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在轮椅难以行动的地带,例如安曼的赫拉克勒斯神庙,她完全能够胜任全职出行顾问。阿哈比经营着“无障碍约旦”网站,为约旦残疾人和外来游客提供出行指南,帮助他们探索该国的大街小巷和珍贵的文化景观。

2012年,一名激进的穆斯林在家乡法国图卢兹展开了疯狂杀戮。第一位死在他手下的受害者也是穆斯林——法国伞兵伊马德·伊本·齐亚滕。母亲拉蒂法·伊本·齐亚滕将丧子的悲痛化为力量,发动了一场以她儿子为名的青春和平运动。这位来自摩洛哥的穆斯林女性奔走于法国各地校园与监狱,恳求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她在卧室为孙子女大声诵读绘本:“看着人们的双眼并微笑,他们会回应你。”

2014年,玛丽梅·塔玛塔瓦林参加耶布尔斯市长选举时,她的两个孩子遭遇霸凌,她本人则受到种族主义者和反穆斯林者的侮辱。身为毛里塔尼亚移民,她表示这是她人生第一次被贴上“异类”的标签。然而她赢了,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穆斯林女性市长。耶布尔斯市政厅矗立着象征法国共和政体的自由女神半身像。从这个庄严的地方起步,塔玛塔瓦林运用自己的才智,为建造新校舍和其他市政设施筹集到了丰厚的资金。

迪奥艺术总监玛丽亚·嘉西亚·基乌里和时装工作室负责人在争论一件披风设计时朗声大笑。基乌里于2016年出任迪奥艺术总监,这给时尚界发出了信号:此前迪奥从未让女性担任过这一关键职位。基乌里利用时尚促进平权事业,秀场模特的衬衫上写着“姐妹情力量大”和“我们都应成为女权主义者”。

普罗旺斯的圣保罗修道院始建于11世纪,还设有同样历史悠久的精神病院。文森特·梵高曾在此接受治疗并创作。艺术疗愈师阿尼克·波蒂奇奥负责该院的艺术工作室,为陷入困境、遭受身心创伤的女性提供帮助——“让她们认识自己,再让世界认识她们。”她说。

多米尼克·克雷恩是美国第一位获得米其林三星的女性厨师。诊断出浸润性乳腺癌后,她作出了顺应本心的决定:公开它。她在社交媒体上对着27万粉丝写道:“致同样经历抗癌旅程的所有姐妹们,我的心与你们同在。”粉丝们的回应满满都是爱与赞美。她回应道:“我很坚强。人生不可能事事如意,但我依然很感激。出现在公众视野从来不是我的主业,我最重要的事业是不停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