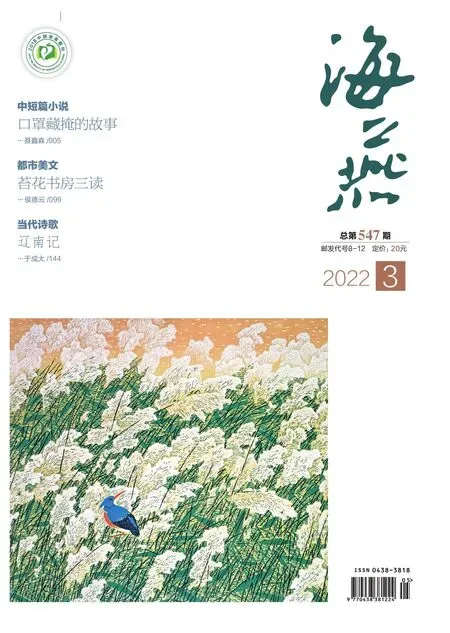楼顶的大象
文 丛 棣
一小时前他被人打了。
被拦下的黑色吉普野兽般喘着粗气,下来个壮汉把他从门岗里拎出来,左右开弓,一分钟也等不及的样子。他蒙了,事发突然,几乎没什么过渡,如果说之前从车窗飙出的那句脏话也算的话。赶来的同事把人拉开,也仅限于此,个个手足无措,倒像是过来陪绑的。打人者不是小区业主,长得就不好惹,一时间怼天怼地叫嚣把个大晴天给整阴沉了。队长也来了,那边赔着笑脸,这边紧递眼色,还使劲儿推了他两把,说,“放你假,赶紧走!”他很听话,真就像个贼一样溜掉了。
他的左脸火辣辣地疼,都走出老远了,还能听见身后不依不饶的叫骂声。他这才想起来忘报警了,队长也没报,谁都没报……他娘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他也没坐车,就那么闷着头走。太阳又出来了,马路明晃晃的,好像没有尽头,再抬头就发觉到家了。不回家他还能去哪儿?
家附近这一片都算是城中村吧。老红砖楼,临着条污水横流的小街。房子是租的,五楼,几乎是这一片的制高点。楼道阴暗逼仄,杂物堆积,过了四层迎面就是一道铁栅,最后一段楼梯给封死了,只留个小铁门供顶层的人上下进出。当初,他老婆一眼就相中了这个,说这样好,规矩。他倒是觉得多余,怪麻烦的,往上都给铺上了花花绿绿的地板革,这也意味着到此该换鞋了。怎么看房东大爷都不像个讲究人,住了这么久也没见对门邻居,想必也是搬走了,只剩下他老婆在这儿继续穷讲究,每天擦上擦下,将一些杂物搬来腾去,像是占了天大的便宜。

现在,他就被那道铁栅隔离在外面,手里攥着把钥匙,狠狠地攥着,钥匙齿几乎都扎进了肉里……
那把锁头虚挂在一边,这说明什么呢?
地上,除了他老婆的便鞋还多了双男鞋,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他忽然想起来就在一个多小时前,老婆曾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那时候他的左脸还没肿起来,他正坐在岗亭里百无聊赖地抚摸着一个大号的保温杯,杯口漂浮着几粒枸杞子。老婆问:“吃中午饭了吗?”他老老实实地回答:“刚在外面吃完。小区斜对面新开了家快餐店,挺干净的,菜味也不错,一荤两素才八块钱,饭管够添。”他没跟老婆说,他今天吃了十块钱,多要了一个荤的,是几块糖醋鱼,跟大饭店一个味儿。他吃过大饭店,一个月前,队长家的二胎办生日宴。他们是晚上去的,随了五百块的份子钱,五百块啊,老婆不争气,偏偏那两天闹肚子,没怎么动筷子,倒是把他撑得弯不下腰来。想到这儿,他不由得咂吧下嘴,老婆不会关注他的意犹未尽,在电话那头继续絮叨:“下午,德林又给我介绍个打扫卫生的活儿,还不知能干到几点呢,家里没什么吃的,你晚上在外边对付一口再回去吧……对了,顺便买瓶酱油上去……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他嘴上哦哦着,眼睛警觉地望向外面,还欠了欠身,一辆黑色大吉普在栏杆外咆哮着,一声高过一声……
那是一双懒汉鞋,又脏又烂,散发着恶臭。东一只,西一只,有一只几乎翻扣了过去,透出一种急不可耐的情绪。一张胡子拉碴的脸从他眼前一掠而过,是德林。德林平日就趿拉这种鞋,在老家时这样,出来还这样。也可以说穷时这样,有钱了还这样!老乡里面就属德林混得明白,领人干活儿,也帮人找活儿,听说马上就要在城里买房子了。这两年,德林没少给他老婆介绍零活儿,工地小工、家政保洁、医院陪护……甚至于他保安的工作都是德林托关系给找的。用他老婆的话说就是:“人家就是有‘章程’。”本地话里“章程”比“能耐”更甚,也更上档次,老婆说这话时总会捎带着剜他一眼,有时还是当着德林的面。德林曾不请自来地找他喝酒,人还没进屋就已酒气熏天了,也不跟他说几句话,眯缝着眼睛总往他老婆身上瞟,看得他心里那个不得劲儿啊。有时还会大着舌头胡咧咧,唠的都是裤腰带以下的嗑儿,他老婆在一旁赔笑,也不恼,事后反倒埋怨他小心眼。他现在算是回过味了,他的心足够大!这不,任那双烂鞋在胸口泛着臭味儿,抽口烟压压,再抽口烟压压……要不怎样?抄个家伙冲进去?像那些狗屁电视剧演的那样,捉奸在床,让一对狗男女跪地求饶……丢人呐!
终于,那把尖锐的钥匙被他揣进了裤袋,他又在外面把锁头挂好,扣死。转过身,像是想起了什么,目光顺着墙角往上梭巡,壁上现出一溜铁磴,出口是楼顶。在他眼里,那也是登天的梯子……
墙角有个倒扣的咸菜坛子,用来垫脚,高度正好。他还知道,中间有一磴活动了,不知怎么就活动了,还越来越厉害。他长得瘦小,脚下有轻重,不可能是他踩的,这说明还有别人上上下下,不过他一次也没碰见。也不可能碰见,他摔门而出的时间多是在晚饭后。有时正吃着呢老婆就又开始了,不可能有好气儿,从老人治病讲到孩子上学,又从当年可怜的彩礼扯到将来没指望的大房子。说一千道一万都离不开个“钱”字,怨够天怨够地只怨自己男人窝囊。那就继续窝囊,他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手上加快动作,嘴里塞满饭菜,直至将碗里的最后一粒米收了,这才起身摔门而出。
爬到楼顶,吹着凉风,心里会豁亮不少。

插图:杨博文
顶上也是磕磕绊绊的,堆积的什么在晚上看不真切。那就往远处看,这个地界,这个高度,视野还是很受限的。环顾一圈,半明半昧的灯火如同湿漉漉的井壁,往上看,很难找到月亮,星星更不可能看到。试探着走两步,抽两根烟,感觉有点冷了就下来。有时忍不住会往家里打电话,儿子睡了,就跟老爹不咸不淡地扯两句,问庄稼种没收没,也说这边什么都好,吃的住的,都好。楼顶就是清净,打电话都能听到村里的狗叫。当然,老爹嘶拉嘶拉的喘息听着也格外刺耳。一磨蹭就是个把钟头,有时还要晚,再晚老婆都会给他留门,其实他也揣着钥匙,而且每次出来都要回身把那道小铁门给锁上。老婆从来不问他去哪儿了,猜也猜不到,估计她也懒得猜。一想到自己曾经就在她头顶走来走去,有时他还会心生小小的快意。经常是屋里黑着,老婆早早躺下了,像个爷们儿一样把呼噜打得震山响,也是累了。等他摸索着上了床,老婆会条件反射般地翻个身,当然是背对着他。他就侧身顺势贴过去,偎着,再得寸进尺地搂一搂,这样就很踏实,很快就能进入梦乡……
出口不太宽绰,于他倒也无碍。上面还罩个小厦子,乍一出来,阳光刺眼,白花花一片……
好一会儿他才适应。那些黑黢黢的东西还在原地,渐渐显露出细节:一扇扭曲变形的木门平躺在那里,还有一扇斜搭在小厦子上;另一边,倚墙垛着些纸壳子,上面还压着木方和砖头;啤酒瓶和空易拉罐散落在角落里,还有几块碎玻璃,正钻石般闪烁着;中间明显被清扫过,晒着一大片咸鱼,覆着纱网;竟然还有个快锈透了的烧烤炉子,用来压住纱网的一边……
他没想到上面的状况这么复杂,一想到自己曾屡屡于夜里摸索至此,不禁心生后怕。
“呜呜……啊啊……”
他一哆嗦,回头发现是个人,没错,虽然正发出野兽的嚎叫。
四月的天气。阳光虽好,风还有些凉,尤其是在楼顶。那人却光着大膀子,跳着脚嘶吼,身上冒着烟,怎么会冒烟呢?不过他看得真切,突突的,甚至远远就闻到了一股油烟味,像是从饭店排烟管道冒出的。也是个膀汉,背对着他,嚎一阵骂一阵:“去你妈的!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呜呜……一个个不得好死……”他第一反应就是,精神病吧?那是一道楼沿,那人就叉着腰冲着虚空叫嚷,好像他面对的还不止一个人。
被发现时他已不知不觉地挪到近前了,那人回身死死瞪着他,他老老实实站住,两人相距五六步的样子。每个人都有标志性的特征,有的还是胎里带的,不知怎么,他差点喊出“大壮”来。没错,他认识好几个“大壮”,长得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儿,瞅着亲切。能有二百来斤吧?看上去很敦实,不是那种碍眼堵心的肥腻,相信再恶毒的人也不会直接把他叫成那种低等动物的,在他眼里,面前这个人更像是一头马戏团走丢的大象。不是像,就是!对视了几秒,他竟从大象的眼中看到了一只猴子……得,他也乖乖地认领了自己。
大象一点也没客气,“滚!离我远点……”那声音就像是从个大水缸里震荡出来的,嗡嗡的。
他没滚,皱着面皮挤出点笑,一边横向拉开距离一边暗暗往前探索,尽量不去瞅那头冒着浓烟的大象。楼沿很矮,刚刚过膝。他小心翼翼地往前探了探脑袋,还真有几个人,都在楼下仰着脸,比比划划,叽叽喳喳。他还看到了二楼那个老太太,老太太不光爱扒拉垃圾箱还爱管各种闲事。听说她儿女都挺有能事,可她死活不搬走,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潜伏着,为这一片儿的治安和卫生操碎了心。他收回目光,发现自己已与大象平行,相距七八步远。那道楼沿把两个人连在一起,从底下看,应该就是拴在一根线上的两个蚂蚱。
艳阳高照,清风吹拂……
他心里却乱糟糟的,看什么都失真,以前上来可从没这种感觉。
“你们来得倒挺快呀……哎,给我根烟!”没想到大象先开腔,后面还是命令的口气。
他摸索出一根烟,伸长手臂,挪着小步,脸上似有讨好的笑。
“站那儿,别过来!扔给我……”
距离有点远,那支烟被风吹落在地。大象捡烟时还恨恨地跟了句,“真他妈抠门!”
他朝楼下扫了眼,底下又多了几个人。这个高度,让他们竭力上扬的表情暴露无遗,其中几张皱巴巴的脸上爬满了嗔责和惋惜,他们的嘀咕和叹息也异常清晰,有个分明在说:“这警察不行,啥都不是,倒是抱住他呀……”
他正蒙着,却听见大象“嘁”了一声,“你们也抽这个,怎么混的!”
一个“你们”彻底点醒了他,心想,都什么眼神啊。不过,他还是挺了挺身子,还抻了抻制服的衣角,再往下看就觉得底下的人影小了不少。他们似乎也受到了鼓舞,有的在试探着喊:“好好劝劝他,那么年轻,想开点……”
见大象警觉地往一边平移,他忙伸出双手冲下面摆了摆又压了压,整个动作很随机很老练很行云流水,让他看上去重担在肩又成竹在胸。动作完成度之高简直出乎他的预想。
“那么年轻,想开点……”这是句现成的台词,虽然没什么创意,但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他也点上一根烟,这个时候烟是好东西,可以稀释内在的压力,可以缓解紧张的气氛,还可以瓦解对立的情绪……可大象抽得也太凶了,两口就见了烟蒂。他掏出有些干瘪的烟盒,犹疑了一下,还是整个扔了过去。
大象又续上一根,终于开口了:“你不懂,活得太累,太窝囊!”长吐一口烟雾后,又补充一句,“就像条狗一样……”
“那个……你是做什么的?”
“在底下‘鑫香园’干砧板,家常菜也能炒……对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有早餐,天不亮就得准备,”大象瞄向他,眼中闪过一星光亮,“你不可能看着我的,我一般在里面忙活,有时还得出去送餐……”
“都不容易,累死累活的,挣那么点钱还不够惹气的!”
大象一脸的难以置信,“别逗了,你们累什么呀?再说,谁敢惹你们啊!”
他反应还算快,“这不,有点事就得出来,你要是跳下去我这月奖金就泡汤了,还得挨领导骂,同事也会笑话我……”
他说得很动情,看看远处,叹了口气,连他自己都信了。
大象脸上竟有了羞愧之色,嗫嚅着,“苦点累点都能忍,可一天到晚被人哈唬得像条狗一样……你说,我不就是一下没腾出手来嘛,菜糊了再炒呗,骂两句就得了,还他妈的上手了,‘打人不打脸’知道吗。我都是快四十的人啦,不是人造的玩意儿……”
“谁呀?”
“老板呗,也是我表姐夫。两口子一个样。就看带我出来挣了他们几个钱,不看看我给他们出多少力,屈良心呐……”大象已明显带着哭腔了。
方才,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大象所挨的那两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左脸,还没完全消肿呢。见大象越说越激动,他赶紧把话岔开,“兄弟,听你这口音像是城山那边的啊?”
“对呀,城山二十里铺东李屯的,大哥你……”
“我是五十里铺的,五十里铺有个西房身你知道不?”
他没有胡说,他家就住在那个叫西房身的小村子里,对方所说的东李屯他也知道。二十里铺和五十里铺,字面上相距三十里地,具体下来也远不到哪儿去,正儿八经的老乡,俩人差点眼泪汪汪了。
烟盒把在对方手里,他又讨了一根,大象忙不迭地给他点上,此时两人几乎肩并着肩,头抵着头。大象也寻摸出一根,竟是最后一根,握皱的烟盒被他随手丢到楼下,底下有杂音升腾,像是轰起了一团苍蝇。
最后一根烟,两个人都抽得格外仔细。他眯起眼睛,若有所思,“想开点吧,兄弟,多大点事呀,你哥可比你惨多了……”
大象的烟夹在指间,就那么端着,怔怔地看着他,脸上竟满是期待。
“你说,你老婆给你戴过绿帽子吗?”他还用手比量了一下,却不是一个帽子该有的尺寸,“把人都领家里来了,大白天的,你说要点脸不?”
“哦……那你不宰了那男的,不,我要是你,就毙了那个王八蛋!”大象夹烟的手变化成一把手枪,还顿了顿,似有一缕青烟从指尖袅袅升起。
“我窝囊呀!”他咬着牙使劲儿跺了跺脚,他相信,那对狗男女一定会感受到他的愤怒,此刻就在他脚下,惊惧于大难临头般的地动山摇。
他的眼中闪动着泪花,转瞬,又凝结成冰,自顾自喃喃着,“没意思,真没意思,你说就我这熊样儿还活个什么劲呐……”
说这话的时候,他竟不自觉地往前挪动了两步,仿佛忘记了那是道危险的边缘。
“别,大哥,凡事想开点,你还年轻,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一个烟头划了道抛物线向无尽的深处坠去,溅起几朵刺耳的声浪:“快跳啊,寻思什么呢……”
“老子还有事呢,等不及了,快跳一个看看……”
“真他妈的磨叽……”
人越聚越多,其中不乏无所事事的小年轻,有的在打尖锐的呼哨,有的掏出手机又拍又录,好不热闹。之前,楼顶上的两个人光顾着抽烟唠嗑了,根本就没留意底下已乱成了一锅粥。
“呜呜……啊啊……”
一声声类于野兽的嚎叫,一下子把底下的人给镇住了。人们看到一头愤怒的大象,不,是好莱坞大片中的“金刚”在拍着自己的胸脯呼号,转瞬,阴云翳日,风沙骤起……
他也像是被噩梦魇住了一样,脚下生了钉子,一动不敢动。很显然,被激怒的大象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上前抱住并撂倒他,而是选择与他并肩而立,一副共拒来敌的模样。这不,刚刚嚎完,又开始往下吐口水,跳着脚吐,边骂边吐,一口接一口,也不知他哪来的那么多口水。一边吐还一边骂:“王八蛋,你们咋不去死呢,都该下去,扔油锅里炸一炸……”
正在兴头上的大象仿佛忘了旁边还有个人,又开始捡拾东西往下撇,一片片咸鱼,一个个空易拉罐……直到他伸出一只手。大象这才停顿一下,嘿嘿两声,递给他一个酒瓶子。他掂了掂酒瓶子,到底还是放下了,跟着大象往下扔半干不湿的咸鱼……
大象说:“看见那个哭天抹泪的胖老娘儿们没?就往她那儿撇……对,那是我表姐……这都是她家晒的咸鱼……”
大象又说:“我就是疯了,疯了好,看谁还敢再惹我!”
底下的叫骂声连成一片,这让两人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又抱来一摞摞的纸壳子,可劲儿抡,可劲儿甩,仿佛一片片乌云悠悠飘坠,没有遮拦的阳光越发的毒辣,刺眼。湿淋淋的大象不再冒烟,而是排着热气,赤裸的上身颤动出一片夺目的光芒。他也浑身湿透,最后瘫倒在那儿,几近虚脱。大象挨着他躺下,排出滚滚热浪,闭上眼,喘息着。老半天,他俩谁都没说话,后来都不约而同地转脸,相视而笑,开始是嘿嘿,后来就哈哈了,一个笑得喘不过气来,另一个笑得直咳嗽……
警笛声由远而近,大象挣扎着坐起来,说:“你们的人……他们怎么才过来?”
他也爬了起来,嘟囔着:“有人报警了吧,早就该来了,才到,这帮警察啊……”
见大象一脸的狐疑和警惕,他这才想起什么,有些难为情地抻了抻身上的制服,又指了指上面的标识。
警察再晚上来一会儿,他就要被大象压死了,大象骑在他身上扳着他肩膀,吼:“你个大骗子,亏我还一口一个‘哥’叫你,跟别人一样欺负我……”
他脸上还重重地挨了一拳,是右脸,这下对称了,看上去一定很饱满。
被警察带下去时,大象走在前面。他在后面饶有兴致地观察了一下,还别说,大象的身手还挺灵活,就是之前活动的那一磴差点被大象踩掉了,让他一阵心疼。下去后,大象第一时间是去穿鞋,他这才注意到大象原来一直光着脚,那双又脏又臭的懒汉鞋此时竟被主人践踏得服服帖帖。他脑袋嗡嗡的,脚一挨地就扑了过去,有那么点奋不顾身的意思,很像是一次自杀式恐怖袭击……
到底还是让警察给拉开了。大象一脸的惊惧和委屈,他倒是把脸憋成了茄子色,一张嘴,话没说出半句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自家的房门开了,他看见自己的老婆穿戴整齐一副要出门的样子,老婆也看到他了,就像看一只被逮住的猴子。没错,猴子和大象,双双被驯兽师……不,是被警察带走。
半个月后……
楼顶。天色将晚,夕光温柔……
他问:“正是饭口,你不干活儿偷跑出来,能行吗?”
“现在我愿意干就干点,谁也管不着我……这白酒不错,是我从吧台里顺出来的,肉串你再翻翻,别糊了……”
“我喝啤的。哎,我问你,你那天是真想往下跳吗?呵呵,整那么大动静!”
“狗屁!我就是想上来透透气,你要不上来,我嚎两嗓子就下去了,就怨你!”
“拉倒吧,一个大老爷们儿都快哭出来了,丢人不?没我你早就摔成大馅饼啦……”
“还说我呢,你好,你不也是紧着往前凑,也想比量比量,切,说到底你得感谢我才对!”
“不管怎么说,我认你这个老乡,不,是兄弟!走一个呗……呀,这烟咋恁大呢?”
“不是炉子的事,你弄得炭不好……来,整一个,大哥,咱俩是难兄难弟,嘿嘿……”
“我又找了个活儿,我不是有个朋友叫德林嘛,挺够意思的,今天他有事,要不也能上来喝点……”
“对了,兄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叫啥呢?”
“你就叫我‘大壮’吧……你笑什么呀,我真叫‘大壮’,李大壮!”
“哈哈……大壮……哈哈哈……我还是叫你‘大象’吧……”
“随你,反正也有这么叫的。你看,你又笑,还笑,喝傻老婆尿了你?”
他很久没有这么开怀大笑了,笑得肚子绞着劲儿的疼,蜷在那里老半天没直腰。笑一阵儿,咳一阵儿,大象,不,是大壮就稳坐在他对面,隔着滚滚浓烟,只剩下个轮廓……
过了一会儿,大壮紧张兮兮地问:“哥,你听见没?”
“什么?”
“ 好 像 又 来 警 车 了,拉 笛 了,你听……”
“你傻啊,那是救火车的声儿,哪儿着火了?”
说这话的时候,两人已靠近楼沿了,探着身子往下望。大壮看到了由远而近的救火车,而他看到了二楼的老太太,在众人中间,仰着脸冲他们这里比比划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