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心下一喊,群山呼应
李婷婷

王跃文
太阳从桃花岭的山头一点点往上蹦,又是一个新鲜的早晨。
有时,一场雨在天亮时收尾,岳麓山群峰间雾气直冒,作家王跃文会被妻子问到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为什么这些雾是一缕一缕的?不是一团一团的?”
卧室的窗对着桃花岭,客厅的窗对着梅溪湖。屋子正中间的书房三面环书,进门右手边,方方正正挂着一幅字:砚田丰登。
王跃文的家被红橡木和香樟木的气味包裹着。每天早上醒来,往鼻子里钻的木头香气,常常让他觉得恍惚,仿佛依然睡在童年那个木房子里,正从还没来得及结束的梦中醒来。
窗外,是稻谷,是河滩,是大水漫不到的漫水村,是洋洋洒洒铺向远方的、湘西连绵的群山。他只要在心里喊一声,群峰就来呼应。
2017年后的中国文化场,有关“官场”的描摹和呈现,经历多年的沉寂后,开始破土重生。而作为“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王跃文,一直不太喜欢这个被加诸于身的标签。这些年,他渐渐从“朱怀镜”(小说《国画》主人公)的世界走出,潜入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乡土。
不久前,王跃文的最新隨笔集《喊山应》出版。乡下人独自走山路,或在山间劳作,寂寞了,大喊几声,回声随山起落,此即“喊山应”。“心里灵空的乡下人闭上眼睛喊山,能从喊山应里听出山的模样。”王跃文说,“我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喊山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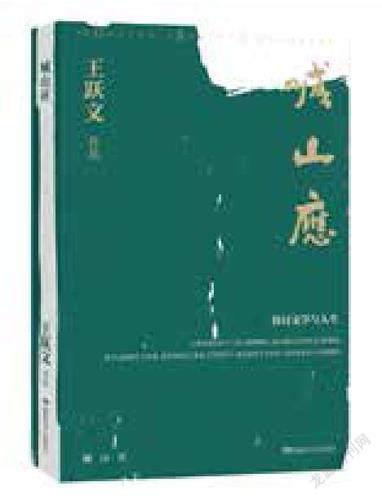
在《喊山应》中,王跃文讲到了“我的文学原乡”,那是漫水,一个他出生并度过童年生活的湘西小村庄。
近些年来,王跃文常会回乡小住。一个冬日的夜晚,大山缄口,万籁俱寂,但似乎总有不知从哪儿冒出的各种声音,让妻子张战机警地张着耳朵,一夜未眠。早上,她忍不住问丈夫,这些声音是什么?王跃文疑惑,哪有什么声音?她一一向他描述:
“唰唰唰……”“一只小野兽穿过树林。”
“噗噗噗……”“一朵很大的雪花砸向地面。”
“还有砰地一声……”“那是山那边的村子在放烟花。”
小时候,大山深处各种各样的声音包裹着王跃文的梦,久而久之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他想起无数个夜晚听松风,大风把天空刮干净了,把松林刮得哗哗响,把千针万线褐黄的松毛刮得纷纷扬扬。四面环绕的溆浦大山把漫水村轻轻托起,声音、颜色、气味,他觉得所有感官都是打开的,通往这个世界。
母亲总是在屋门前洗衣服、洗被子。她把稻草烧成灰,用水过一遍,捉一块自制的茶籽油枯,撸着袖子慢慢洗;洗好后,还要用米汤“浆”一遍,再在好太阳里抖开晾晒。被阳光烘热的衣服、被子,贴在身上,散发着迷人的稻香和米香。
还有割草的香气,烧松针的香气,春天插秧时青苗的香气,秋天收割时稻谷的香气,冬天山坡上马鞭草的香气……无数细腻的气味里,有王跃文的童年。
大山还赠予了他敏锐的触觉。上树掏鸟窝,下水捉泥鳅,他都是一把好手。“当你摊开手心,一把泥巴像花一样展开,就是最喜悦的时候。那个光溜溜、黝黑黝黑的背露出来,然后是灰白色的肚皮,一只泥鳅就展现在眼前。”
捉泥鳅要捉大的,越大越有成就感,“但吃泥鳅要吃小的,煎得香脆、进味”。王跃文说,“捡菌子也是,捡到大的菌子,像一把漂亮的伞;吃则要吃小的,小菌子像小扣子,圆圆的、亮亮的,吃起来香。”
来自童年的通感,直到今天依然作用于生活。比如一说到枞菌,气味就飘飘荡荡来到跟前。王跃文可以区分各种菌子的气味,那些细致入微的千差万别,扎根在他的感官深处。
再比如喝酒。白酒醉了,摊开身子躺着,慢慢睡就行;红酒喝醉,整个人开始弥散膨胀,无限扩大;最要命的是醉黄酒,“有点像晕船,身子不停打转,为了不转,我必须朝相反的方向去转,然后砰地一声滚下床来……”
这些不同的感官体验,也嵌进了王跃文丰盈的文学语言。
漫水村四面环山,东边的远山隔着溆水河。王跃文家的老屋在村子地势最高处,年年夏天的大水漫不到他家。“如果我们那个地方都淹了,整个漫水村会全部被淹掉。”他估摸着,这也是“漫水”这个名字的由来。
溆水最深处是一个叫蛤蟆潭的地方。老人们讲,蛤蟆潭下有个无底洞,一直通到龙宫。相传很久以前,有个姑娘在潭边的大青石板上洗衣服,青石板突然变成一只乌龟,把姑娘驮到东海龙宫,做了千年不老的龙王娘娘。孩子们比试水下能力,就往潭里扎猛子。记忆里,王跃文看见过潭底各色各样的彩色石头,至于龙宫和龙王娘娘,似乎没有谁见到过。
沿河是大片大片的自然河滩。一到夏天,王跃文就跑到河滩,看水面上飘飘飘荡荡的白帆船。中午或者黄昏,船上开始做饭,女人从河里舀一瓢水,炊烟从船上袅袅升起……他盯着眼前这一切,想象着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他对“外面的世界”最初的憧憬。
山村里,阅读条件几乎为零。王跃文印象中最早的读物是大哥床头的一本《红楼梦》,“已经翻烂得不成样子”。竖排繁体字,书中第三人称一律为“他”。他读了半天,依然分不清林黛玉到底是男是女。
那是八九岁的光景,再长大一点,他读过一本关于抓特务的短篇小说集、一本科幻小说集,“至于《林海雪原》《红岩》,都是上初中之后的事了,连《青春之歌》都没读过”。
第一次在写作上受到鼓励,源于小学二年级时的一次观影活动。学校组织看《红灯记》,要求高年级学生上交一篇观后感。不到10岁的王跃文积极性很高,第二天一早直接交到校长手上。那天广播体操结束后,校长让全体学生留下,把他的作文在广播里读了一遍。“现在回想起来,无非就是用了一些诸如‘大义凛然’之类的成语。”
至于这些成语的来处,他也不太清楚。可能来自某个读本,可能是火塘边听大人讲传奇故事时,那些偶尔火星般蹦出来的灼热、滑溜、活泼泼的语言。
对成语的迷恋一直持续到十七八岁。有一个夏天,王跃文的脑袋时刻处于飞速运转的状态,好像不断逼迫自己,只要见到一件事物,就要想到三个以上与之可能相关联的成语。他自己都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就掌握了这么多成语。
而真正的文学启蒙,来自中学一位姓向的语文老师。学校组织看电影,向老师陪他一起走,突然低头很亲切地问:“你立志了吗?”这是王跃文第一次听到“立志”两个字。他正慌慌张张不知如何回答,向老师接过话:“我看你作文写得好,长大以后可以尝试去当作家。”那天看的电影是《暴风骤雨》,向老师告诉他,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个作家的长篇小说改编,“他叫周立波,就是我们湖南人”。
“原来作家并不是那么遥远,写作可以离我们这么近。”王跃文想,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他并没有想过当作家,但对文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王跃文第一次真正坐船,已是1990年。那次出公差,从安庆到庐山,他要在船上睡一晚。

溆浦穿岩山。(王跃文 / 摄)

王跃文作品:《国画》《大清相国》《漫水》。
“刚开始好兴奋,哪知道,我晕船特别厉害。”在那条船上,他度过了翻江倒海的夜晚,但童年看着白帆飘向远方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
1984年,从湖南怀化师专毕业后,王跃文去了湖南省溆浦县政府。那年他22岁,一个从湘西走出的农家子弟,即将迈入社会的门槛,他形容那种复杂的感觉,“像是深夜熟睡的人突然滚到了一张硬邦邦的床上”。
王跃文像小说《新星》中的李向南一样,背一个黄书包,后来妥协随大流,换成黑色的人造革皮包,每天提着走街过巷,去县政府上班。
利用闲暇时间,他开始写作,用公文之外的另一套笔墨。他至今仍然记得,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叫《书房小记》,刊登在1989年8月8日的《湖南日报》上;第一个短篇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则在1990年的《湖南文学》露脸。
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职场、基层的小人物。他们刚从大学毕业,充满理想,却发现社会同书本完全是两码事,只能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地挣扎徘徊。
调入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后,办公室有了一台电脑,但没人会用,常年被一块深红色天鹅绒布整整齐齐地盖着。王跃文轻轻将它揭开,从启动开始,自学电脑操作,买来五笔打字教程,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他在电脑上敲下的第一篇文字是《桃花源记》。“我想着,等把《桃花源记》敲完,基本上就会打字,可以在电脑上写长篇了。”
小说敲到3万多字时,屏幕突然一闪,雪花点纷纷扬扬落下,紧接着,屏幕一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太难受了!当时跳楼的冲动都有。”他下决心,自己买一台电脑。
凭着记忆,王跃文将这3万多字“复原”,“但总少点感觉,也可能是心理作用,觉得后来写的不如前面。”这样敲下来,第一个长篇、也是让他名声大噪的作品《国画》出炉。
那是1999年,一个圆融老到、也深沉复杂的人物,走进王跃文的笔底。《国画》洋洋50万字,以主人公朱怀镜的视角,写尽官场百态:他一边讲排场,一边心疼浪费的饭菜;一边和情人云雨,一边对妻子充满愧疚;一边在官场钻营,一边和艺术家朋友打成一片,自谓“清流”。
小说出版后轰动文坛,有人说,“王跃文之于官场小说,相当于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琼瑶之于言情小说、二月河之于帝王小说。”虽然被媒体封为“官场小说第一人”,王跃文却一直拒绝这个封号,他的小说里,没有理想主义的英雄,也没有耸人听闻的黑幕,只是人性在权力蛛网中的变异和缺失。
在这之后,王跃文陆续写了《梅次故事》《朝夕之间》《亡魂鸟》《大清相国》《苍黄》……但对于自己的家乡,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敢轻易落笔。
最熟悉的,往往最难触及。
上世纪70年代,王跃文的父亲是家乡著名的养蜂能手。养蜂人要跟着花期走,父亲长年远行,去得最多的是安化、贵州和四川。每一次父亲出远门放蜂,母亲就会关注当地的气象预报。是晴天还是雨天?可否能收到好蜜?
1975年秋天,奶奶去世,父亲还在外地养蜂。王跃文在放学路上听到消息,飞快地往家跑,“只感觉到田野里各种小虫子打到脸上,生疼生疼”。到家时正值黄昏,妈妈告诉他,奶奶是听到哥哥把父亲的信读完才走的。“信一读完,她的喉咙响了一声,就落气了。”

2021年11月,王跃文与妻子张战参加《喊山应》《张战的诗》联合发布会。
2012年,王跃文发表小说《漫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那一年,他50岁,第一次真正地、直接地、深入地,用笔探入家乡深处。
《漫水》的结尾是这样的:“强坨爬起来,哭号着追上娘的灵棺。余公公腿脚酸酸的发软,人落在了灵棺的后面。他抬头望去,山顶飘起了七彩祥云,火红的飞龙驾起慧娘娘,好像慢慢地升上天。笔陡的山路翻上去,那里就是漫水人老了都要去的太平垴。”
2020年夏天,王跃文的父亲去世。当父亲的灵棺抬上太平垴时,他抬头望去,山顶飘起七彩祥云,火红的飞龙架起父亲,好像慢慢地升上天……他心下一震。世间之神秘,又怎能在十年前的落笔处预料并与之呼应呢?
铺展在溆浦大山的自然风物,发生在溆水河边的故事和情感,扎根在童年记忆里的色彩、声音、氣味,依然在任何时刻拥抱他、抚慰他。那是他的文学原乡,也是他的精神原乡。
在《喊山应》的序言里,王跃文写道:“我写过的那些人和事,那些时间和空间,那些实和虚,那些真和幻,都是人世的回声。透过我的文字回声,或许能看出人世的模样。”
孩童时,住在一个木房子里,觉得童年漫长,他总是想,为什么还没有长大,对大山外面的世界,萌生最初的想象。
以笔为帆,乘着文字的扁舟驶进中年。他依然住在一个木房子里,卧室的窗对着山,客厅的窗对着水,仿佛关于漫水村的一切还围绕着他,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安全地陷入童年。
心下一喊,群山呼应。
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1962年生于湖南溆浦,1999年发表长篇小说《国画》,代表作有《朝夕之间》《大清相国》《苍黄》等。2021年末出版最新随笔集《喊山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