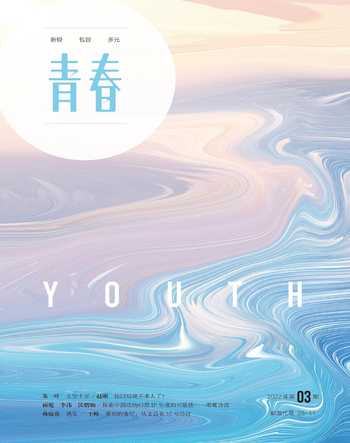在边城
赵小明
走出去,也许能更好地归来。
有人说,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骏马能像一页跳跃着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往远方。是的,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总是能把我带向远方,带到那牧歌式的桃源之地,走出自我之地,走近边城,感受边城。
边城,茶峒。一个古怪的地方,一个封建统治者镇抚与虐杀苗族戍边屯兵之地,开始有城关的种子,才有边城的雏形。岁月经年,城堡与民居,街坊与作坊,军营与民防,贸易与往来,店家与客栈……这个湘西的小码头,于湘川黔三省交界处悄然兴起。
茶峒——边城,边城——茶峒。茶峒是边城的茶峒,但边城已不仅仅是茶峒的边城。眼前的边城,房屋以二三层砖木建筑为主,清一色褐色木质外表,岩石路面随行随势而走,凭水依山而成的街道,并不是那种整齐的井字型,有平行线,有三角形;古城墙经风沐雨,仅留剩江边一截断壁残垣,墙缝间偶尔冒出的小花小草,像是要证明些生命特征的存在;剥落的青砖墙体,滄桑疲惫,再也不见雏嫩的吹号手,在朝霞初露中站立城关吹号的画面;满街巷飘拂着翠翠和边城元素的旗幡和灯笼,使得这个与其他山水模样相仿的古镇,有了翠翠的故事,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内容和含义。
蜿蜒的江边河街,岩石高高垒起的墙基,古朴的吊脚楼,见证着这方曾经兴衰起落之地。敞开的店铺前有人在修补渔网;有人在整理照相装饰的苗族服饰和头帽;有人在“一锅吃三省”的招牌下捡拾蔬菜;江边石台阶上有人在捶衣洗菜;一对青年男女站在江中浅滩石块上,俯身躬腰用手把江水洒到对方身上;几条红布蒙尾的篷船靠岸停泊,有人在小篷船里候客乘船,划船大嫂招呼:“二十块钱一位,边城上下之间游个来回”;有人在江中放鸬鹚叼鱼,时不时地把吐出的鱼放进竹笼;近岸的水边一群鸭子悠闲畅游,不时地把头扎进水深处,撅起屁股,在水中寻找新鲜美味;一只小鸟在滩石间敏捷地飞来飞去,从这个岩石尖忽闪到那个岩石顶,伺机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水里逮到小鱼儿一口吞肚;两只白鹭脚腿蹬起,扑闪着翅膀抬起身子,向白塔那边飞去。白塔下的水车碾坊停息已久,长满荒草的碾坊,不再转动的水车沉默了,成为勾起念想的物件。
沿河街边,五棵大杨树弧形拱布在江边近岸。说不定是多少年前,防风挡浪打桩的杨树树梢复活生长而成;说不定是多少年前,洪水泛滥飘浮的树枝落根新生。看那树的腰围,一个人是合抱不来了,树干底端布满疤痕,是拴船的绳索勒痕,还是碰撞的伤疤?终没影响它们长高长大,远望这一小排树,像几个哨兵伫立,风儿吹拂摩挲作响,飞快地把外边动静,翻窗越墙透露给河街的人们。
白塔、绿树掩映中立于江边,不知倒塌几回、重修几次,简约清瘦,黑白分明,虽不高大挺拔,但终归是边城不可或缺的标志物象。
临近白塔,街道尽头,一户苗族大娘的家,一个简约的民宿,屋后石块垒起的庭院,种满辣椒、茄子、青菜、莴苣、豇豆、芫荽,寄居大娘家的上海姑娘,饶有兴趣地侍弄蔬菜,捉拿昆虫,在庭院和房后的小门里进进出出,用几句生硬的苗家话搭腔,装扮得像个主人,让人误以为是个边城姑娘。她说,她是不愿意日子如复印件一样重复着过,瞄上这里小住,想在这边城寻清静,白天寄情于边城山水间,夜晚可以趴在窗棂看星星、看月亮,也可能半躺着翻阅那本随身携带的《和伊壁鸠鲁一起旅行》,在都市另一端发现城市的美好,也发现城市的病痛。
在庭院里那棵老榆树下,我们聊起两种边城:一个是地理上的边城;另一个是内心里的边城。地理边城在消弭,心中边城在垒起。自然的边城在消退,空间的隔阂在消融,山高路远不再形同天堑,世界都可以说是一个地球村,而身相近心却远,高大的城墙没挡住人们同质化的生活,人与人往往被一层玻璃隔开了,看得见图像,听不见声音,更捉摸不透对方下一步的举动。人们心上的一道道坎,把原本同城化的人们隔开,垒起一座座边城,每个人可能成为一座边城,跨一步就滑向了边城!我说,在这繁华而喧嚣的都市,我有时像一只没有灵魂的躯壳,很空洞,似乎在透明的空气里孤独地生息,在人流如潮中竭力地游弋,不由自主地成了某条流水线的附属产品,似乎拥有了平凡而舒适的生活,却又焦虑着美好和幸福,有一种迷失自我置身于孤岛的感觉。姑娘说,这不是现代和城市的过错,也许是我们没做好同步。
茶峒的边城世界,有着可以理解和想象的,有着追求和向往的,享受那段时空,可以让我们放逐心扉,自在逃遁,以此为引线,随心打开自己的记忆,回到记忆深处。
从过去流向未来的清水江,是边城的母亲河。来了去,去了来,一波又一波,一轮又一轮,故去新来,丰枯交替,汩汩依旧,生生不息,就像每日度过的生活,在平淡中流淌。
这清澈见底的清水江,曾是边城走出大山,走向外面世界的重要通道。清水从云贵高原走来,翻山越岭融入酉水,跌宕起伏在沅陵并归沅江,再一路奔波注入洞庭湖,然后顺长江流向海洋。这漫长东流的行程中,尤其是凤滩水库没修建之前,沅陵以上的河道极为险峻,这水道不像江南河沟那样平坦笔直,更没有都市河流的胭脂粉味,江水不断东流,不停跌宕碰撞,消解落差。江水或跌落冲入深潭,或激情昂扬,溅起堆堆浪花;或埋头前行,波光粼粼;或左摇右摆,在山垭口转身东张西望;有时打着滚儿翻过峭石,有时在弯曲的滩边扯住大树伸入水中的脚根,细说徘徊,像是在讨论什么渊源。这里行船走筏,滩多险急,峰回水转,悬崖前面挂绿水,船行其间,人在船中,时不时地险象环生,让人胆战心惊,似乎生命悬在呼吸之间。那里人把行船叫“走船”,行船的“船拐子”,走船人的艰辛和安逸是没得选,他们只能以此为生,以此为乐,无论滩怎么陡、江怎么窄、浪怎么激,总得像马哈鱼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追溯洄游。一江水,一帆船。这一江水,清早太阳水中出,傍晚太阳水中落,船行几天又几夜,两岸青山能记住?没人去问两岸高大的珙桐、鹅掌楸、光叶榉、重阳木;没人去问那一簇簇珊瑚冬青、中华石楠、南天竹;没人去问攀跳的猕猴、奔跑的野兔、麂子和灵猫;也没人去问水里的大鲵、小鲵和水獭。这一帆船,承载了边城那方地域的传奇:苗家接龙的传统场面,面目丑陋或美貌能干放盅的“草鬼婆”,椎牛祭祖苗老司,土家跳“毛古斯”的把戏,还有边城江边吊脚楼里对唱山歌的那人那事……
绕过白塔,沿石阶下山坡,渡船到江中的翠翠岛,岛上翠竹幽幽,峭石嶙峋。中央广场上,黄永玉先生用汉白玉雕塑的翠翠和她的大黄狗就在那儿。边城,沈从文播撒的种,他那缠绵而又纯洁的文字,仿佛从天上飘下来,从水里长出来,怀着细密绵长、软到好像化掉所有杂质的情意写边城、写生命、写爱情。
翠翠,沈从文先生精心创造和呵护的人物形象。她是美的化身,“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她是爱的化身,边城世界充盈着爱,青年男女的纯洁情爱,爷爷护着孤雏孙女的祖孙挚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人们常说,无爱的人生如同一潭死水,而翠翠生活在一个博爱的世界里,边城所有的人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爱着她,她也许曾经站在这水边凝望遐想,面对缓缓流淌的江水,她不仅感觉到有歌要唱,而且也能感觉到另一条深情的长河。尽管翠翠和二佬傩送的爱情并没有尽情地激情释放,但他们的爱情应该是一块石灰放在屋里,自然吸收空气,慢慢氧化熟成,而非生石灰丢进水里,吱吱冒泡,不一会儿就成了糊状的石灰水,他们的爱是有筋骨的。沈从文先生对翠翠形象的关爱一直没淡化。《边城》首次出版于193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84年将其改编成电影。沈从文对文学电影剧本评改,只提了简短的四小点建议,其中一条特别提道:“翠翠应是个尚未成年的女孩,對恋爱只是感觉到,其实朦朦胧胧的,因此处理上盼处处注意到。”足见他对翠翠这一形象疼爱有加,害怕艺术家们把翠翠描绘得太成熟了,失去了她应有的新鲜和清纯。
跟着肩背竹篼头戴斗笠的大娘,在“茶洞古码头”界碑的地方登上拉拉渡,每个过渡人在一只木箱盖上,自行放上两块零钱,尚不支持微信支付,仿佛与摩登时代隔着一层,仍延续着传统的惯性。船在艄公牵引下向前,第一次见到这样行船,商量着从艄公手中接过尺数长的木棒,试着把木棒缺凹口按上跨河的缆索,双手紧紧握住木棒,向后倾斜着身体,使劲把木棒拉向自己,渡船便一寸一寸向对岸挪去。在清水江的水面上,从湖南花垣茶洞摆渡到重庆洪安,摆渡就是一边在远去,一边在到来。我们的生活不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摆渡之中,在晴朗和阴雨中摆渡,风雨以后见彩虹;在山水和古镇间摆渡,在自然和人文间寻觅本真;在喧闹和寂静中摆渡,寻找静谧佳境;在熟人和陌生人中摆渡,学着善良,布施善良;在清醒和孤独中摆渡,孤独但不茫然,在孤独中醒来,在清醒里排解;在都市和边城间摆渡,身处喧嚣浮躁的都市,发现被忽略和被隐没的纯净,回归简单静寂,整理和化解被冲突和裁剪而产生的孤独,抵达关乎命运的彼岸;在拥有和梦想中摆渡,实现人生通达。
边城临别,随意走进一家饭店,端几把矮小的杂树靠背椅,坐到有年头的杉木圆桌边,透过木栅栏、木轩窗凝望江边,一条龙舟向下游划去,与另一条上来的龙舟相会。此刻,周围的云雾褪去,天空放晴,对面“三不管岛”上的树木,黑白分明的房屋灿烂了起来,远处群峰越发青翠靓丽,像水洗过一样。饭店墙角贴着一张边城的旅游宣传图片,一幅高空拍摄的古镇全景,配文写着:古往今来,茶峒令人神往,这里风光独特,风情浓郁,苗汉土家和睦相处,文学大师沈从文年轻时随军入川,曾在此小住,后来以此为背景,创作了惊世名著《边城》,自此,寻梦人纷至沓来,翠翠和她的大黄狗一直在等待,欢迎你到边城来,触摸翠翠初恋情愫的那个人,也许就是你。
忽然,河面上传来清脆的鼓声,咚咚咚,咚咚咚……节奏欢畅洒脱,撼动有力,沿着水面,顺着暖风,阵阵跳跃而来,像是鼓舞,像是召唤,像是诚邀,像是归纳,像是奋进。错落有致的鼓点,咚咚地敲在心坎,整个神情像是被感染起来,不仅仅是那种瞬间的激越,更像是一种萌芽已久的冲动,似乎有股共同捕捉生命共振的力量,似乎有什么觉醒的激动,在沉默已久的豪爽瞬间被唤醒,被激活,被点燃。连续几天借故避酒,此刻兴奋起来,像踩上咚咚的鼓点,自觉地开怀畅饮,以至于不知不觉醉入梦乡,竟然不知如何上的车,何时离开边城,仿佛在一帘幽梦中远离了那方山水。直到凤凰古城,华灯初上,簇拥进场,观看大型场景剧《边城》,才算彻底清醒过来,才感知:边城无边!
边城,是一个符号,人们心中的符号。
责任编辑 苏牧
实习编辑 谢温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