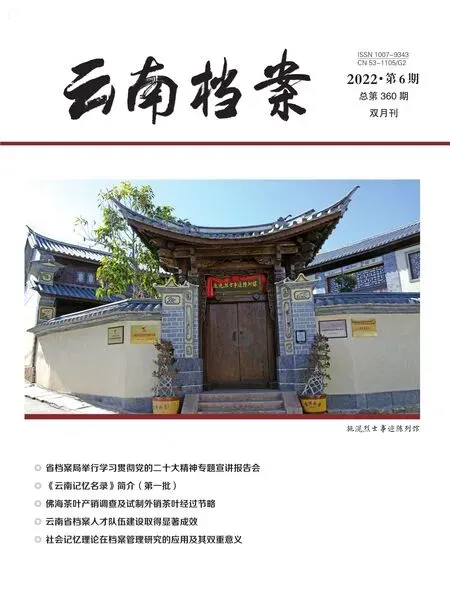社会记忆理论在档案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双重意义
■ 杨 霞
一、社会记忆理论在档案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记忆理论发端于法国的年鉴学派,20世纪20年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开创性地提出“集体记忆”概念成为这一理论的开端。1989年美国社会学家康纳顿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用社会记忆代替集体记忆理论,成为集体记忆理论之后又一具有深刻学术影响的理论范式。[1]
社会记忆理论一经提出,西方学者就意识到该理论对档案领域的冲击。特里·库克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社会记忆理论对档案领域的影响,在观念上要“坚持多元化的叙述,而不是主流叙述,要关照整个社会和人类全体的历史经验而不只限于充当国家和公共文件的保管者”;在档案管理鉴定工作中,更注重从后现代档案管理和社会记忆建构的角度来强调档案鉴定工作应该摆脱传统鉴定的束缚,采用宏观鉴定模式;[2]同时扩大档案概念的域,在档案学上认为档案是动态的、虚拟的概念,档案积极的体现了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档案产生于现代网络中那种动态的平衡体制,从而改变档案产生于稳定的、垂直的行政体系中。[3]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弗兰克·阿普沃德等人提出文件连续体理论,社会记忆、机构记忆、活动凭证和行为轨迹依次构成四分之一的价值表现轴,将社会记忆理论的印迹深度嵌入档案学理论维度。[4]布罗斯曼瞄准社会记忆对档案工作者的冲击,提出“记忆档案工作者”,其工作职责是促进完整知识、社会认同和集体意识的形成。[5]
中国学者关于社会记忆理论对档案工作的研究要迟于西方学者,现有的研究亦是以西方社会记忆理论为重要基础,1997年冯惠玲教授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使得“记忆”引起档案学界关注,[6]进而拉开国内研究的序幕。
(一)社会记忆理论推动档案工作的变迁
赵彦昌认为“集体记忆构建中档案的开发利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档案的编纂、编研,更侧重于如何将档案融入社会,发挥反映集体记忆变迁和记录历史进程的重要作用,使档案具有‘生’”。杨安莲从社会记忆建构特点来强调现代档案工作变迁的必然性。[7]在档案鉴定工作中,刘东斌先生认为,档案鉴定应当挑选反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社会记忆”,特别是对边缘群体社会记忆要着重关注。[8]丁华东认为受到社会记忆理论影响,档案工作者的角色更多了,即是社会记忆的传承者、建构者、控制者,更是社会记忆的守护者,社会记忆建构的中介者,这一新的观念将影响档案未来从收集到鉴定到利用等各个环境工作。[9]
(二)社会记忆理论对档案记忆观的分析
丁华东、张燕在其论文《探寻意义:档案记忆观的学术脉络与研究图景》中论述了社会记忆理论专注于记忆的生成、传播、保存,这对肩负记忆使命的档案工作者而言,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和强大的吸引力。档案记忆观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记忆理论在档案管理研究这一具体语境的体现。[10]谢巍宏从“记忆”理念在各类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特殊作用角度阐释了老字号声像档案对城市记忆构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11]
(三)社会记忆理论对档案记忆理论范式形成的阐释
王佳佳以社会记忆理论为指导,通过社会记忆理论构建的“主体一中介一客体”分析框架,阐释了档案研究由“证据”范式转变为“记忆”范式。[12]丁华东强调要在社会情景中理解和分析档案活动与档案文献,在档案记忆范式中探讨了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13]丁华东在分析用社会记忆(包括历史记忆、文化记忆、集体记忆等)的新视野和新思维来探视档案现象,对档案的社会功能、档案工作的社会意义进行重新思考、阐释所获得与凝练的基本性认识的基础上,认为档案记忆理论范式已形成并作为档案学的前沿范式之一。[14]
综上所述,社会记忆理论在档案管理已有研究的视角主要是从社会记忆的本质出发,来探讨社会记忆理论与档案工作、档案记忆观、档案理论范式形成等方面的关联,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现代档案形成本身因为受到权力影响,其所记录的信息并非客观的历史真实,所以它在建构的历史记忆时会出现“失真”或者“异化”的问题,该问题如何解决需要进一步思考。其次,社会记忆理论将促使档案具有动态性,改变以往的束之高阁的命运,参与到集体记忆变迁和社会历史记录的过程,使档案融入到社会之中,使档案具有“生”,但是这种情况下如何落实到具体实践之中,在具体操作中如何保障档案的安全性也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社会记忆理论在档案管理研究的理论意义
(一)社会记忆理论促进档案记忆理论的发展
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载体和工具,在社会记忆理论的影响下,其传承社会记忆的功能受到关注,档案记忆理论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由社会记忆理论衍生的档案记忆理论,从记忆、认同、社会结构等深层社会意义出发,将档案和档案工作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场域,注重档案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结构解读,已逐步演化为档案学界的新兴理论范式。[15]同时社会记忆理论将社会记忆的思维模式引入到档案学之中,一是促进档案真正价值和社会作用的发挥,二是将档案学理论与社会科学联系起来,扩大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促进档案记忆理论的诞生,扩大了档案学的研究视角。
(二)社会记忆理论引发多元档案价值观的探讨
社会记忆理论认为,社会记忆是人的一种感知实践,是人们以信息的方式对在生产劳动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进行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过程。从社会记忆视角审视档案价值使得档案价值发生转变,不再唯一信奉‘证据的神圣性’的档案信条,认识到档案除了证据价值之外的记忆功能,档案成为建构社会记忆不可替代的要素。在社会记忆理论引入到档案管理研究后,引发研究者以不同的研究视角来重审档案价值,档案价值的研究需要回归复杂的社会系统来全面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视角首先扩展了档案的价值域,在建档观念中,既要体现“国家”的理念,同时更要兼顾以民为本的本心,在档案体系的建立中,建立以全体人民群众为主的档案体系,档案的收集范围既包括国家政权性信息,也涵盖社会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的信息,使档案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历史政权的记载,还体现在人民群众在档案中找到回忆和怀念的载体。[16]
社会记忆理论认为社会记忆受权力的影响,社会记忆是多元权力和多元价值观长期复杂博弈的结果。在现有社会语境下,国家权力一定程度的让渡于公共权利,档案形式多元化、档案服务大众化、档案管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要求以保密和服务领导为中心的档案理论和价值观以及档案实践体系必须做出改变,档案多元价值观应运而生。2008年米歇尔·卡斯韦尔和萨米普·马利克共同创立南亚裔美国人数字档案馆的实践项目,该项目作为独立的国家性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通过记录、保存和分享代表南亚裔美国人独特和多样经验的故事,从而提供给他们发言权,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同时该项目的出现成功促进了档案多元价值观的发展。
(三)社会记忆理论创新档案价值鉴定理论
社会记忆的作用与反作用、社会记忆的选择与遗忘问题对档案鉴定工作构成了挑战,档案鉴定应该从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这一重要属性出发,判别文件的“保存价值”。首先,档案鉴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确立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记忆”建构目标和指导思想,制定鉴定政策制度、综合标准、技术规范、范例汇编等,从而把档案记忆理论渗透到明确、具体的鉴定依据和规则之中,使其成为档案鉴别的尺度和文件选择的依据。[17]其次,鉴定规则能够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留存和传递公民的社会记忆(表现为鉴定规则的覆盖范围和透明度)。最后,档案鉴定工作的内容转变,“由国家模式转变为建立在公共政策利用决定论和宏观职能鉴定论的社会模式”。保留更多反映社会方方面面的档案,如将房地产档案、山林权属档案、婚姻登记档案纳入到档案收集范围之中,同时为了保证档案鉴定的结果是使档案既能全面反映社会记忆又能使社会公众共享档案信息资源,档案鉴定工作要在社会监督下运作。[18]
三、社会记忆理论对档案管理研究的实践意义
社会记忆理论被引入到档案管理研究后,得到相关专家学者的肯定和重视,在影响档案学理论的同时,拓展了档案工作对象范畴、凸显了档案机构“记忆宫殿”优势,突破了档案工作者自身角色定位。[19]
(一)拓展档案工作对象范畴
社会记忆理论引入到档案领域之后,档案工作对象的范畴不断扩展,从政府文件、官方档案到私人档案、社群记录再到社会组织自治档案(Autonomous archives),档案工作不再是政府组织、档案馆的分内之事,社会大众、特殊社群、各类行业组织均可参与到保存自身活动记录,管理自身档案的工作中。
1.创建均衡化档案资源建设方案
档案资源作为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社会记忆与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资源对于组织和个人了解历史、展望未来以及完善社会记忆体系等方面作用显著,所以用社会记忆和全覆盖、均衡化的理念引导档案资源建设,编制以社会记忆为主体的档案资源建设方案是社会记忆理论在档案资源建设中的重要启示之一。
2.重视地方档案资源的收集与保存
大部分的地方特色档案资源都被保存在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或者是图书馆等场所,能被国家公共档案资源体系系统收藏的是极少数,但是正是这些地方特色档案资源蕴藏着“大量正史所未言的、细致入微、具体详尽、生动逼真的历史信息”。在档案工作实践中,群体自发收集与本群体情感表达及记忆续写相关的记录以留存自身群体历史及身份认同。
(二)凸显档案馆“记忆宫殿”优势
在社会记忆理论引入到档案领域之后,档案馆作为保管档案文献的重要场合,在社会记忆构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更加凸显其“记忆宫殿”的职能。一方面档案馆利用丰富馆藏,进行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另一方面,档案馆在档案收集中突破以往的为统治阶层服务理念,为了重构社会记忆,将处于社会边缘群体但是能凸显社会记忆如农民工档案收集到档案馆。
(三)突破档案工作者自身角色定位
传统的档案工作者的主要职责是保管好档案,常常被当作“看门人”,随着我国地方档案机构实行“局馆分立”模式,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机构的职能愈发凸显,其也相应承担着留存人民群众社会记忆的功能。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构建社会记忆的过程中作为能动的主体,其自身角色定位发生变化。这种职业赋予的“特权”要求档案工作者将“保存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记忆”作为历史使命与社会职责,勇敢承担起“社会记忆积极建构者”的角色。[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