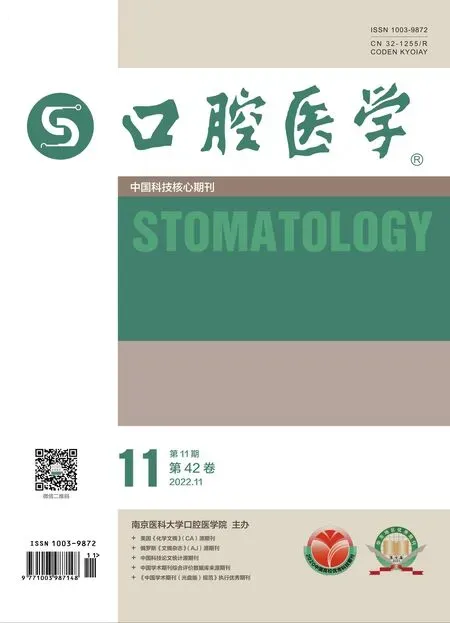WTAP在肿瘤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林旭阳,韩 笑,张成婉,张双越
RNA转录后修饰在生命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确认有>160种的RNA修饰[1],分别存在于信使RNA、转运RNA、核糖体RNA、核小RNA(small nuclear RNA,snRNA)、核仁小RNA(small nucleolar RNA,snoRNA)以及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在RNA修饰中,N6-甲基腺嘌呤(N6-methyladenosine,m6A)是真核生物mRNA中一种最普遍、最丰富、最保守的修饰方式[2]。RNA m6A修饰主要发生在3′非翻译区(3′-untranslated region,3′-UTR)和终止密码子附近的RRACH基序([G>A]m6AC[U>A>C])上[3-4]。研究表明m6A修饰是一个动态可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甲基化转移酶(Writers)包括METTL3/14、Wilms肿瘤蛋白1相关蛋白(Wilms′tumor 1-associating protein,WTAP)和KIAA1429等,通过催化RNA上腺苷酸发生m6A修饰;去甲基化酶(Eraser)包括脂肪量和肥胖相关蛋白(fat mass and obesity associated protein,FTO)和AlkB同系物5(AlkB homolog 5,ALKHB5)等,通过对已发生m6A修饰的碱基进行去甲基化修饰;而阅读蛋白(Reader)包括YTH结构域家族蛋白1/2/3(YTH domain-containing family protein 1/2/3,YTHDF1/2/3)、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 mRNA结合蛋白(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2 mRNA-binding proteins,IGF2BPs)和不均一核糖核蛋白A2B1(heterogeneous nuclear ribonucleoproteins A2B1,HNRNPA2B1)等,主要功能是识别发生m6A修饰的碱基,从而激活下游的调控通路,如促进RNA翻译、降解以及剪接等过程[5]。在RNA m6A修饰过程中,WTAP与METTL3、METTL14组成复合物(WMM复合物)发挥催化功能[6]。在WMM复合体中,METTL3作为主要的催化亚基发挥作用,而METTL14与METTL3形成稳定的异源二聚体以增强甲基转移酶活性[7]。WTAP 则将METTL3和METTL14招募到目的mRNA上[6]。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WTAP作为RNA m6A修饰的关键分子,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总结WTAP在肿瘤中的潜在作用机制及相关靶点治疗。
1 WTAP的生物学功能
1.1 WTAP定位于核斑中参与m6A甲基化过程
WTAP首次于2000年通过酵母双杂交实验被发现,被认为在功能上与Wilms肿瘤蛋白1(Wilms′tumor 1,WT1)密切相关,因此得名WTAP(WT1-associating protein)[8]。WTAP在拟南芥中的同源蛋白AtFIP37与METTL3的同源蛋白MTA存在相互作用[9],而在酵母中WTAP的同源蛋白Mum2也同样与METTL3相互作用[10]。随后,通过免疫共沉淀进一步证明了METTL3、METTL14与WTAP存在相互作用,以WMM复合物的形式作为甲基转移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作用[6]。现有研究表明METTL3、METTL14和WTAP共定位在核斑点中[6,8,11]。通过在细胞中敲低WTAP,METTL3和METTL14在核斑点中的信号大幅度减弱,而METTL3和METTL14的蛋白表达水平没有发生变化。此外,敲低METTL3和METTL14并不影响WTAP在核斑点的信号[6]。因此WTAP在WMM复合物中起到重要的定位作用。
不同于METTL3,WTAP本身不具备催化活性,且不影响METTL3的催化活性,但通过液相串联质谱发现敲低细胞中的WTAP表达能显著降低多聚腺苷酸RNA中m6A的富集水平[7]。此外,通过斑点杂交实验同样表明敲低WTAP不影响WMM复合物其余的组成部分,但可使细胞中的m6A水平显著降低[6]。因此,在m6A甲基化过程中WTAP不可缺少。
1.2 WTAP调控可变剪接(alternative splicing,AS)过程
AS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基因表达调控机制,可以使得单个基因产生多个独特的mRNA种类[12]。20世纪90年代,有研究发现果蝇WTAP的同源蛋白FI(2)d是性致死(sex lethal,SXL)中AS所必需的,其中SXL是果蝇中决定性别通路的主要调控因子[13]。近来有研究者发现WTAP与一些剪接因子共定位,并且已经在人类功能性剪接体中被发现[14-15]。通过PAR-CLIP发现WTAP所结合的mRNA中有很多与RNA的剪切相关,同时,敲低WTAP会产生大量RNA剪切异构体[6]。最新研究显示,WTAP能抑制富含GC的短内含子的剪接,从而对AS过程进行调控[16]。
1.3 WTAP影响胚胎组织发育
研究者们发现人和斑马鱼的WTAP有81%的序列一致性,且N端保守性更高[6]。通过原位杂交发现WTAP在斑马鱼胚胎中广泛表达,敲低WTAP会使斑马鱼表现出发育异常,包括头部、脑室偏小,小眼畸形,细胞分化延迟和细胞凋亡增加等[6,17]。另外在小鼠胚胎中,WTAP突变体存在着中胚层和内胚层的损伤[18]。
2 WTAP在肿瘤中的作用
2.1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肝癌是全球患病率排名第六,致死率排名第四的恶性肿瘤,原发性肝癌分为HCC(占75%~85%)和肝内胆管细胞癌(占10%~15%)以及其他较少见的亚类[19]。通过分析TCGA数据库中365例HCC患者和50例正常对照的mRNA数据,发现在HCC患者中WTAP的表达要明显高于正常人。此外,在分析ICGC数据库中的232例HCC患者的mRNA和生存期后,发现WTAP的表达水平与HCC患者的生存率呈负相关[20]。
研究表明在HCC中WTAP介导的m6A可以抑制转录后ETS原癌基因1(ETS proto-oncogene 1,ETS1)的表达,从而促进HCC的发生和发展。WTAP还可以通过ETS1-p21/p27通路,对细胞周期进行调控[21]。Chen等发现,WTAP介导的m6A可降低肝激酶B1(liver kinase B1,LKB1) mRNA的稳定性,通过LKB1-AMPK通路减少p-AMPK的表达,导致细胞自噬能力下降[22]。此外,WTAP为抑癌基因miR-139-5p的靶基因,miR-139-5p的表达降低,使得WTAP的表达上升,促进EMT通路,因此HCC的增殖和侵袭能力增强[23]。
2.2 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
AML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血液恶性肿瘤,其特征是髓系母细胞增生或原粒细胞无法进行正常分化,有着很高的致死率[24]。在WTAP被证明是m6A甲基转移酶复合物的亚基前,已有研究表明WTAP是热休克蛋白90(heat shock proteins 90,HSP90)的下游蛋白并在AML中高表达,可以促进AML细胞增殖并可阻滞细胞分化[25]。AML细胞中高表达WTAP不仅导致不良预后,还可增加AML细胞耐药性[26]。
微小RNA通过RNA m6A在AML的调控中起到关键作用。miR-550-1是一种肿瘤抑制因子,通过调控WTAP影响m6A的表达水平,从而影响WW结构域转录因子1(WW-domain containing transcription regulator-1,WWTR1)的稳定性进而对细胞周期进行调控[27]。在AML细胞中,METTL3对WTAP的内稳态起到关键作用,敲低或过表达METTL3都可上调WTAP的表达。但是下调METTL3所导致的WTAP表达上调并不会影响AML细胞的增殖能力,其原因可能是缺乏METTL3导致m6A水平下降所致。因此在AML中WTAP的成瘤机制与m6A甲基化转移酶复合体密切相关[28]。
2.3 骨肉瘤(osteosarcoma,OS)
骨肉瘤是最常见的一种原发性恶性骨肿瘤,年龄分布呈双峰状,高发于儿童、青少年和60岁以上人群[29]。在人OS组织和OS细胞系中WTAP的表达上调,从而促进骨肉瘤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转移。敲低WTAP减少同源框蛋白1(homeobox containing protein 1,HMBOX1) mRNA中3′-UTR处m6A的水平,增强HMBOX1的稳定性,抑制PI3K/AKT信号通路的激活,最终影响骨肉瘤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转移[30]。
2.4 胃癌(gastric cancer, GC)
GC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种重点疾病,患病率排名第五,是第三大癌症致死因素[19]。一项基于TCGA和GEO数据库的研究显示,相较于正常组织,GC组织中WTAP的表达上调,高表达WTAP与不良的预后密切相关[31]。在GC细胞中WTAP通过与己糖激酶2(hexokinase 2,HK2) mRNA 3′-UTR 的m6A结合,增强HK2 mRNA的稳定性,加速GC细胞的瓦博格效应(Warburg effect)促进GC细胞增殖[32]。此外,在GC中WTAP的高表达可以减少癌症相关T细胞的浸润,抑制肿瘤免疫,促进GC的发展[33]。
2.5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
CRC是一种致死率很高的疾病,发病率排名全球第三,是第二大癌症致死因素,且人数呈上升趋势[19]。在CRC中WTAP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的争议。CRC分为结肠癌和直肠癌,基于TCGA、GEO、HPA数据库以及组织芯片免疫组化相关数据得出,在结肠癌中WTAP的表达要高于正常组织,而在直肠癌中却没有此现象[34]。虽然在低分化CRC中WTAP呈现高表达,但是有研究表明WTAP的表达与患者的预后无相关性[35]。同时,Wang等发现,在不同分化程度的CRC细胞系中,低分化的细胞系WTAP的表达显著高于中分化和高分化细胞系,而中分化组与高分化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6],其相关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2.6 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PC)
PC因其极差的预后,受到人们的重视[19]。通过RT-PCR发现在PC细胞系中WTAP mRNA的水平要明显高于对照细胞[37]。免疫组化结果也显示在PC组织中WTAP的表达显著高于周围正常组织,并促进细胞的侵袭转移以及对化疗药物吉西他滨的抵抗[38-39]。在PC中,WTAP能结合并稳定黏着斑激酶(focal adhesion kinase,Fak)的mRNA,Fak反过来激活Fak-PI3K-AKT和Fak-Src-GRB2-Erk1/2信号通路促进PC的发展与药物抵抗[39]。此外,lncRNA DUXAP8在PC中高表达,通过miR-448/WTAP/Fak信号通路影响PC的侵袭转移[40]。另外,Wilms肿瘤蛋白相关蛋白假基因1(Wilms Tumor 1 associated protein pseudogene 1,WTAPP1) RNA会与WTAP mRNA的对应部分结合,招募更多的真核起始因子3(eukaryotic initiation factor 3,EIF3)翻译起始复合物促进WTAP的翻译,高表达的WTAP激活Wnt信号通路加速肿瘤恶化[41]。
2.7 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EC)
EC的发病率和相关病死率正逐年上升,已成为导致女性死亡的重大风险[42]。WTAP在EC中的表达被发现要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增强EC细胞的增殖,侵袭转移能力,抑制凋亡能力。在EC细胞中,降低WTAP的表达会导致微囊蛋白1(caveolin 1,CVA-1)的表达上调,同时 CVA-1 3′-UTR处m6A和METTL3的富集水平下降,进而抑制NF-κB信号通路,从而抑制EC的进展[43]。在EC细胞中过表达WTAP促进β-连环蛋白(β-catenin)入核,增强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β,GSK3β)在Ser9位点的磷酸化,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增强EC细胞顺铂耐药[44]。
2.8 膀胱癌(bladder cancer,BC)
BC是全球第10常见的恶性肿瘤,估计每年有549 000新增病例和200 000死亡病例[19]。WTAP的表达在BC中要显著高于正常组织,与癌组织的分化程度和复发密切相关[45]。一项研究表明,WTAP以依赖m6A的方式提高肿瘤坏死因子α诱导蛋白3(TNF alpha induced protein 3,TNFAIP3) mRNA的稳定性,从而提高TNFAIP3的表达,抑制BC细胞自身凋亡,降低对化疗药物顺氯氨铂的敏感性。而在上游部分,Circ0008399被发现与WTAP结合,促进METTL3,METTL14与WTAP结合形成m6A甲基化转移酶复合体,提高BC细胞抗凋亡能力以及降低对顺氯氨铂的化疗敏感性[46]。
2.9 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RCC)
恶性肾肿瘤占全球癌症总数的2%,并且发病率正在上升,RCC是肾癌中最普遍的一种类型,约占85%[47-48]。在RCC中,WTAP在癌组织中表达显著升高,不同表达水平与患者的预后有显著相关性[49]。在RCC中,WTAP通过调控周期素依赖性激酶2(cyclin dependent kinase 2,CDK2)的表达调控RCC的增殖。WTAP通过与CDK2 mRNA 3′-UTR 位点结合,稳定CDK2转录物,提高CDK2的表达,促进RCC细胞增殖。而降低CDK2的表达可以抑制细胞由WTAP介导的增殖能力[49]。此外还发现,miR-501-3p在RCC中高表达并参与上述过程,通过miR-501-3p/WTAP/CDK2信号通路调控RCC进展[50]。
2.10 头颈癌(head and neck cancer,HNC)
HNC通常在大量吸烟和饮酒的老年患者中确诊,由于近年来烟草消费的减少,其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正在缓慢下降[51]。基于TCGA数据库的研究表明,在头颈鳞状细胞癌(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HNSCC)中,肿瘤组织中的WTAP表达要显著高于正常组织,并且与肿瘤的分化程度、分期,特别是T分期密切相关[52];此外,WTAP似乎在m6A甲基化调控因子交互网中扮演着中心枢纽的角色[53]。另外,有研究者指出m6A与HNC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细胞浸润相互关联。通过对TCGA与GEO数据库中876例HNC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其进行m6A评分,研究者认为m6A分数低的样本在TME浸润亚类中属于炎症表型,此类患者有着低肿瘤突变率、高生存率,同时对抗PD-1/L1免疫疗法反应增强[54]。
由于在流行病学、病理学、自然史和治疗方面的差异,HNC又分为鼻咽癌和非鼻咽癌[51]。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点,主要分布于东亚和南亚地区[55]。在鼻咽癌中WTAP呈现高表达,WTAP高表达与不良预后也密切相关。WTAP的上调被发现是由CREB结合蛋白(CREB-binding protein,CREBBP,又称KAT3A)介导的组蛋白H3K27位点乙酰化所致[56]。而WTAP介导lncRNA DIAPH1-AS1的m6A修饰,通过IGF2BP2增强其稳定性,提高DIAPH1-AS1的表达。DIAPH1-AS1作为分子适配体促进异黏蛋白(metadherin,MTDH)与LIM和SH3结构域蛋白1(LIM and SH3 protein 1,LASP1) 形成复合物MTDH-LASP1,从而提高LASP1的表达,最终促进鼻咽癌的形成和侵袭。因此WTAP可作为鼻咽癌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和诊疗靶点[56]。
在非鼻咽癌中,HNC主要包括口腔、鼻腔、咽和喉四个部分[51],具体相关机制还待后续研究。
3 WTAP与肿瘤治疗
WTAP已被发现在多种肿瘤中表达上调,参与并调控肿瘤的发生和进展,这给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目前,WTAP的靶点治疗研究正在兴起。Zhang等人研究表明,在结肠癌中碳酸酐酶Ⅳ能通过多聚泛素化诱导WTAP蛋白降解,通过WTAP/WT1/TBL1轴抑制Wnt信号通路,从而实现对结肠癌的抑制[57]。此外,在非小细胞肺癌中西达本胺通过抑制WTAP和METTL3的表达,降低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receptor,HGF receptor,又称c-MET) mRNA的m6A水平,下调c-MET的表达,进而通过c-MET/HGF依赖的方式提高非小细胞肺癌对克唑替尼的药物敏感性,从而治疗非小细胞肺癌[58]。
4 总结与展望
在本篇综述中,我们总结了WTAP的生理作用以及在不同癌症中的调控功能及相关分子机制和靶点治疗。WTAP作为m6A甲基化转移酶复合物重要的成员,对WMM复合物的形成和稳定以及细胞m6A表达水平起到关键作用。此外,WTAP还发挥AS功能,调控基因转录过程,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胚胎发育。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肿瘤细胞WTAP表达上调,并与不良预后密切相关。机制方面,WTAP主要影响靶基因mRNA上m6A的表达水平,从而调控靶基因的表达,激活或者抑制相关通路影响肿瘤进程。值得注意的是,WTAP介导的m6A的表达水平变化在不同靶基因中呈现出不同的调控结果,其中的分子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有必要更深入研究WTAP介导的m6A在不同肿瘤中的作用机制。目前将WTAP作为靶点治疗癌症的研究也在不断进行,为治疗癌症提供了新的方向。此外,WTAP所介导的m6A与其他修饰之间的关联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