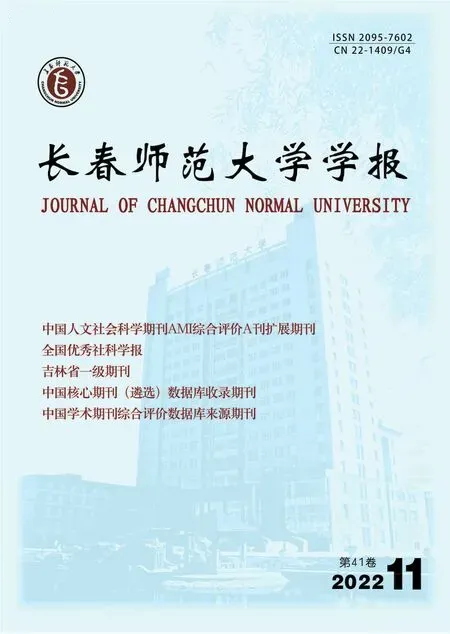对镜不识现象在中日文学语境下的流传与变异
宋 旭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人类对自身形象的印象大多模糊而主观,在遇见的所有面孔中,对自己的脸通常是最缺乏了解的。在镜出现之前,个体的自我形象不被任何人据为己有,“我”在“我”的世界里散漫游离,人们望见世界,唯独除却自身。镜出现以后,人们也并非立刻接受那镜中人与自我的关系,这个从“我”走向“我”的过程在文学的源脉里呈现为笑中含泪,诉说着自我认知的艰难。
一、对镜不识之闹剧
人们第一次在镜中看到自己的映像时,极有可能发生困惑和误判,而这种错位经过文学的处理和渲染后往往呈现出趣味纷呈的效果。钱锺书先生就曾援引一些人在镜中见到自己却无法认出的趣事[1]643。如《笑林》中的故事《不识镜》云:“有民妻不识镜,夫市之而归。妻取照之,惊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妇归也。’其母也照曰:‘又领亲家母来也。’”①
人人不识镜中己,皆以为是旁人,而这误认又看似有理有据,都被认成照镜人的同龄人,由此引发的误会令人哭笑不得。丈夫买镜赠给妻子,妻子将自己的镜中影误认为丈夫的小妾,由此闹出的一系列乌龙情节还被冯梦龙编入笑话集中。
对镜不识的故事传到日本,在佛教、神道典籍以及各种曲艺门类里开始出现类似的传说。《宝物集》,《神道集》第四十五“镜宫事”,狂言中的《镜男》《土产の镜》以及室町时期的物语绘卷《镜男绘卷》中都有相关记载。
《镜男绘卷》的另一传本《镜破翁绘词》记载了和《笑府》所收十分类似的故事。很久以前,生活在近江国片山里的一位老人进京,在四条町路看到一个稀罕物件,见里面有美女和宝物,便买回家放到柜子中。妻子看到,以为他从京里找了女人回来,哭喊不休。经过一番折腾,老人认定该物件是灾物,便将其弄碎,却发现每个碎片中都有一张脸。故事到这里,和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情节无甚差别,但后来却朝着怪谈方向发展。老人担心这东西是妖怪,便带着它向深山行进,最终到了一处白老鼠甚多的隐秘之地,并在那里取了长生药和砂金带回来,从此长生不死。[2]187
这个故事将两国的民间笑谈与传说结合在一起。而在多数情节类似的日本昔话中,最后会出现由比丘尼解决的情况。和经卷中的故事一样,绘卷和昔话都是与起倡导作用的本缘谭相似的存在。总体而言,日本这类笑谈脱胎于佛教典籍和中国笑话集。
类似情况又有《启颜录》中关于买奴的记载。鄠县一老父让儿子到集市上买奴,儿子“付钱买镜,怀之而去”。“至家,老父迎门问曰:‘买得奴何在?’曰:‘在怀中。’父曰:‘取看好不?’其父取镜照之,正见眉须皓白,面目黑皱,乃大嗔,欲打其子,曰:‘岂有用十千钱,而贵买如此老奴?’举杖欲打其子。其子惧而告母,母乃抱一小女走至,语其夫曰:‘我请自观之。’又大嗔曰:‘痴老公,我儿止用十千钱,买得子母两婢,仍自嫌贵?’老公欣然。”未见奴出,遂寻求帮助。“老父因大设酒食请师婆,师婆至,悬镜于门,而作歌舞。村人皆共观之,来窥镜者,皆云:‘此家王相,买得好奴也。’而悬镜不牢,镜落地分为两片。师婆取照,各见其影,乃大喜曰:‘神明与福,令一奴而成两婢也。’因歌曰:‘合家齐拍掌,神明大歆飨。买奴合婢来,一个分成两。’”[3]16-17
在镜中见自身,却误以为是奴与婢。不仅一人有如此想法,众人都被蒙在鼓里,全村人的“傻气”共同促成了这场啼笑皆非之景。可见对镜不识并非个例,而是一个普遍现象。
钱先生认为这类笑话滥觞于《杂譬喻经》。总体而言,经书中故事的目的性要比笑话集明确得多,即解世人之愚惑,使其分清虚实,打破承装虚幻的容器,唤醒混沌中人。因讲经说法、道德规化的需要,《大智度论》《维摩诘所说经》《楞严经》等佛教典籍中有不少类似的故事。《百喻经》中有一则记载,一人将一面镜覆盖在箱中珍宝之上,他人见之以为有人在其中,无人看管的宝物遂得守护。
江户时代的笑话集《笑眉》中有《佛前的宝镜》[4]31,记载了与《百喻经》同样情节的故事。《百喻经》等佛教经典传自印度,可知印度早就有此类故事的传承,而中国和日本的同类故事应从印度传来。
世界范围内亦不乏类似故事。弗洛里昂的寓言《孩子与镜子》中,一位母亲借助小孩子不识镜中人的情况控制了他的情绪。她把正在生气的小孩领到镜前,告诉他:“你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生气他也生气,你高兴他也高兴,若想幸福就不要再闹脾气。”与前面以镜中的自己为他人的情节一样,小孩子也真的以为镜中是另外一个孩子[5]73。
除了认己为人,亦有认人为己者。《大庄严论经》中记载了一则故事,一婢女去池中打水,恰好有另一面貌端正的女子在附近树上藏身。婢女见水中清丽倒影,以为是自己,顿时为自己的处境和遭遇愤愤不平,得知真相后满心羞愧。佛陀借此希望人们对自己有清醒正确的认识。钱先生借但丁之言论此种现象:“误以影为形与误以形为影,两者同病。”[1]645不自知的情形甚至可以达到“爱镜中头眉目可见,瞋责己头不见面目,以为魑魅,无状狂走”的地步。
在经书中,对镜不识的笑谈往往被用作宣扬某种正确行为的教化工具。但之所以会被如此使用并经久不衰,根源在于人类意识深处普遍承认认识自己是困难的。尽管读者读到这样的故事会感到荒唐而发笑,但笑过之后往往陷入思索。人们的确不会像故事里的主人公那样认不出镜中的自己,但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似乎并不能称得上真正认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每个人与故事中的镜前痴人并无本质不同。
二、对镜不识之悲剧
对镜不识的故事并没有停留在笑谈层面,它在古典文学中也往往以悲剧面貌登场,而悲剧故事的主角多为动物。张华《博物志》记载:“山鸡有美毛。自爱其毛,终日映水,目眩则溺。”[6]4074刘敬叔《异苑》言:“山鸡爱其毛羽,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帝欲其鸣舞而无由,公子苍舒令人取大镜着其前,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遂至死。韦仲将为之赋,甚美。”[6]4074起舞至死的因由从鸾鸟的典故中可清楚得知:“琤蚌王结罝峻祁之山,获一鸾鸟。王甚袄戤,欲其鸣而不能致。乃饰以金樊,飨以珍羞,对之逾戚,三年不鸣。夫人曰:‘闻鸟见其类而后鸣,可悬镜以映之。’王从言。鸾睹影,感契慨焉,悲鸣哀响中宵,一奋而绝。”[6]4059
朝鲜半岛名儒李穑曾咏“谁吊镜中鸾”;文豪李詹言:“镜里孤鸾,独低徊以顾影。在中鸣凤,已寂寞而呑声”,典出于此。以为镜中影像为同类故而鸣舞,又有庾信《镜赋》:“山鸡看而独舞,海鸟见而孤鸣。”《西游记》第十五回中,土地与山神向悟空讲述的“鹰愁涧”来历,亦与飞禽误认自己的影子为同类而掷身于水有关。
印度尼西亚有动物将水中影误认为是本体的寓言。老虎和山谷里的野兽发生争斗,猿爬上池塘旁边的树,老虎追来,在池中发现猿的影子,扑入水中抓猿,结果死掉。[5]74人不识镜中影会闹出笑话,而对禽鸟而言,则需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也警醒我们,不识己会引发严重的悲剧。故事至此便不限于教化或消遣的范畴,因为主角是动物,作者和读者均没有嘲笑的立场和资格,反而多了些无能为力。在这种无能为力的感受里,我们进一步意识到自己不仅与那些痴人无异,甚至在对自己的认知程度上与禽鸟相仿。
有人类的地方便少不了对自我认知的探求,因而禽鸟的悲剧不会仅仅存在于东方古典文学中。钱锺书将其与西方同类例证联系在一起,戏称这类禽鸟的表现为“山鸡症”,同“水仙花症”。“水仙花症”的典故出自古希腊神话中一则传播甚广的不识水中己的故事。钱锺书将其概括为:“美少年映水睹容,不省即己,爱慕勿释,赴水求欢,乃至溺死,化为水仙花;自爱成痼,如患心疾者,世即以此名其症(narcissism)。水仙花亦由无自知之明,然爱悦而不猜嫌,于《杂譬喻经》、《笑林》所嘲外,又辟一境。”[1]645
河神肯皮修斯和仙女雷伊奥派的儿子纳西索斯是罕见的美少年,被众多少女追逐爱慕,可他不为所动。仙女艾可对他一见钟情,亦被冷然拒绝。艾可失恋忧苦,消失于世间。曾经被纳西索斯伤过心的仙女们愤而向复仇女神涅墨西斯请求处罚他,让他也体验一回永远无法得尝所爱的滋味。有一天,纳西索斯狩猎疲惫,在泉水边喝水,突然惊奇地发现水中有一个人影,满头秀发,眼眸闪烁,非常漂亮,对其一见倾心。惩罚生效了,纳西索斯陷入一种无法实现的恋情中不可自拔,如同其他仙女爱上他。他凝视虚像,每日顾影自怜,极尽相思之苦,最终耗尽精力,化成岸边一朵水仙花。
钱先生说纳西索斯无自知之明,但换个角度考量,这些患有“山鸡症”与“水仙花症”的主体更珍贵之处似在于其对自我的执着关注。尽管这份关注并未参透正确答案并以悲剧告终,但恰恰证明了自知之难之险。无法实现的恋情,也是无法认识的自己。通过无止无休的自我凝视,纳西索斯、山鸡、鸾鸟们与群体性阿谀、社会性模仿划清界限,只试图讨好自己。讨好自己比讨好他人更加危险,收获的惟孤独而已,注定不会得到集群部落的理解。尽管是主观的无意识,但却是自我认知过程中客观的必经之路。米开朗基罗曾画过一幅纳西索斯画像,画中的他用双臂拥抱自己的倒影,形成一个圆环,网住了自己,也排斥了世界。他人的目光可以打破局面,而他并不想跳出这种迷惑。这背后的吸引力并非来自那个他以为的另一个美少年,而是美少年的本相——自我。
这些照镜故事不仅暗含镜的起源和发展形态,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一个看似荒诞的框架内探讨自我认知。人们认识自己是从不认识自己开始的,故事中的主角并没意识到镜中影像是自己。因不自知而引发纠葛、误解和伤害的过程,都是追索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反讽和自省接踵而至。从成像原理看,反射镜所成的是虚像,这意味着针对自我的探求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或者说无解命题,是佛教譬喻故事中的“空”。镜非常“狡猾”,提供给人观察自身的途径,激发人们认清自己的好奇心,却迟迟不揭晓答案,直到照镜者付出代价去寻找。
大抵因为如此,在水镜中凝视自己倒影的意象,多哀伤难以自持,充满悲凉的危机感。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四幕第一场中,忧郁者雅克朝水中俯下身去,连连哭泣。理查二世像放弃因装满水而沉重的桶一样放弃王冠,跳入映出自己的井中,眼中噙满泪水。夏尔·德·奥尔良将“深井”冠以“忧郁”的形容。马拉美笔下的水镜寒彻骨髓,甚至能将面孔冻伤,将人影照成幽灵②。天鹅在水镜中看尽忧郁,看尽流亡的自我,也看尽“比石头还重”的“珍贵的回忆”③。某种意义上,这些意象均为纳西索斯姿态的变体,是西方文学中的“山鸡起舞”与“鸾鸟悲鸣”。
这些相似情形的演化,其根源无一不是面对镜时自我迷乱、自我期许、自我追索引发的认知混沌和意识模糊。形与影纵横交叠,拨动着自我反映的维度。对镜沉思带来的,未必是通往出口的解决途径。但行在眼下暂时看不清远方的路上,总比原地踏步要乐观许多。探寻自我的深井,虽黑却明。
三、松山镜
在日本,不识镜中己的悲剧以另一种特色鲜明的脉络流传下来,其形态多以落语、能、谣曲、狂言等艺术形式呈现。孝子孝女在镜中对着自己的影像,以为看到亡故父母的灵魂显现,十分怀念。例如落语《无镜村》,谣曲和落语《松山镜》等,情节大略相同,细节则各有差异。这是将古代中国戏谑故事情节加以改写,于教化与逗乐的初衷里增添了对亲人的追思和对孝道的推崇,不断诉说着无人能抗拒生死与无常的真相。故事基调由喜入悲,表现出日本独有的神佛习合印迹。
江户末期刊行的《续鸠翁道话》对狂言《镜男》进行改动,讲孝子买了镜子,见镜中有人,以为是父亲,与之对话却不见回答,以为阴阳有隔,故而听不到声音,但思量父亲去世三年后尚能以此种方式重逢亦是难得,便携镜回家④。谣曲与落语《松山镜》中,女儿在镜中看到自己,认其为过世的母亲,怒斥父亲竟然连心爱的人都视而不见,殊不知她口中因父亲的变心而满面泪水的母亲正是她自己。日本的民俗学者将这类故事称为“松山镜”,因为最初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出身越后松山的女子。
松山镜的故事在日本各地区都有流传。在岩手县花卷市流传的版本为:有位孝子因父亲去世而十分悲伤,和村人共同前往伊势,为父亲祈愿。有天晚上思念父亲,他便独自一人出町步行至一家店铺,见镜中映出的自己的面容,以为是父亲,非常高兴,便要店主把镜卖给他,带回家早晚观看。妻子发现他会发出奇怪的笑声,好奇之下跑去瞧,在镜中看到美丽的女人,妒火中烧,夫妻二人大吵一架。当他们一起拿着镜子,发现里面既有所认为的父亲又有年轻女子,方才安下心来。[5]69
故事的总体框架与先前所述的笑话无异,但加入的思念去世亲人的情节直接翻转了故事本身的基调。同为悲伤,却不似山鸡与鸾的悲壮凄美、令人痛惜,反而有一种欣慰和温情弥漫在冲突里。这也贡献了一个缓冲——不认识自己似乎在某些特定情形之下并非一件百分百的坏事,这大概是求真道路上东洋独具一格的通融和宽慰。
后来松山镜的线索交织穿插在小说中,发挥着特别的魅力。《手镜》(《ふところ鏡》)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日本桥万町松云堂的老板娘性格温柔,她有一个叫阿雪的女儿,是她和前夫的孩子,丈夫利平对她就像亲生孩子一样。一年夏天老板娘卧病在床,到了冬天情况越来越差。但有一天突然恢复了意识,同阿雪聊天:“不会让你一个人的,会一直陪在你身边。”[7]193次年春天,老板娘病逝,利平将她的手镜给了阿雪。阿雪闲暇之时就盯着手镜看,起床的时候自不必说,连睡觉也要放在身边。利平很奇怪,问她为何如此,阿雪笑言母亲住在镜子里。最开始她只在镜的一角看到人影一闪而过,映出脸的一部分。后来这种情况屡屡发生。有一天,因为遭受了长屋小僧的恶作剧,她跑到屋子里哭,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仔细辨认,声音从手镜中传来,近前一看,镜中竟是母亲微笑的脸。“那时寂寞就缓解了许多。从那以后二十年,直到现在也经常拿着手镜。”[7]194但是最近阿雪有意不用那面手镜,亦能看到母亲的姿容。“托神明庇佑,今年与母亲同岁了。如今看向任何一面镜中,好像母亲还在。”[7]194
一方面,此篇可依照前章逻辑进行阐释。去世的母亲住在镜中陪伴寂寞的女儿,镜是一扇时光窗,提供了一处灵魂安居的空间,一种生命延续的介质,一个供母女重逢的条件。另一方面,当阿雪在镜中母亲的陪伴中长到母亲去世的年纪,她看任何镜都仿佛看到母亲。因为当阿雪长到母亲永远停留的年纪,便可以触发这项功能。或者有另外一种解释,即这里面隐藏的是松山镜的线索:镜中一直只有阿雪自己的影子,镜中母亲的音容笑貌一直都是一种因思念和容貌相似性而引发的心理幻象。当阿雪长到与母亲当年同样年纪时,两代人在镜中更是不可区分,任意一面镜中的阿雪都像极了母亲。也就是说,阿雪自始至终都将自己误认作母亲。故事中亲情、孝女的元素也承袭了传统松山镜的故事。
山鸡、鸾鸟、纳西索斯用尽生命诠释着自我认知道路的艰险漫长和需要付出的代价,而日本松山镜的脉络使不识镜中人的故事在荒诞笑谈、教化讽喻和哀戚悲壮之外有了一个温情的分支和转向。悲剧无可躲避,但悲剧本身也是一种应对和安慰。
这种献以生命迈向自我的源头悲感在后世作品中亦成为反写、颠覆与重释的基点。文学家们似乎试图在叙述空间中将镜根除、拒绝,却有意无意放任镜的替代物蠢蠢欲动、伺机出场。归根结底,镜永远不会缺席,它可以假意隐身,以被替代的狡黠方式存在,使“我”不断看见“我”,不断迷醉,不断重温原初那份无可规避的阶段性壮烈——无视悖论与解构的永恒在场。
四、结语
古代不识镜中人的故事往往归在笑话集中。在现代関敬吾编写的《日本昔话大成》中,松山镜这个母题故事也被归类于“笑话”中,这种因不清楚成像原理而造成的误认在传说中被赋予夸张的维度。但某种意义上,它可彰显孝、爱、乌龙、神秘,却唯独不应简简单单付之一笑旋即结束。分不清镜中人是自己还是他者,看似是艺术手法上的夸张,实则有意无意。这些故事都在不断追问同一个问题:你真的认识自己么?“上帝创造了梦魇连绵的夜晚/也创造出了镜子的种种形体,只为让人自认为是映像幻影,也正是因此,我们才时刻惊悸。”[8]159
关于自我的探索,人们的确经历了一个朦胧而混沌的起步。镜看似使人对自己产生混淆和误认,但实际上,自我起源于误认,误认是必经之路,人们需要通过镜的指导跨越虚实、他我的路障。如果没有镜,人类不知何时才能遇见自己。在古代西方,镜象征着智慧、哲学;而在东方,镜以一种看似曲折笨拙的方式帮助人们自省,将“我”带到另一个“我”的身边,使人们在与自己面对面的浑然不知里窥见本质,这是镜在东方文学中蕴含的特殊魅力。通过镜中映像抵达自己的灵魂,这是一切人与镜终极对话的回向所在。尽管柏拉图认为镜中是些毫无实质的东西,但他承认镜在精神和哲学层面的用途是不可替代的,即便触摸不到,也不代表无。映像虽非现实,却是一种表征和显露,通往隐蔽的事物,比如自己。就像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神谕所言,也是苏格拉底的一贯主张——“认识你自己”。
在现代社会,这种动摇和迷惑仿佛愈演愈烈,只不过曾经存在于笑话集和劝导篇中的情形换了种方式存在而已。盯着手机屏幕,被电子产品支配的我们有时候就像全然认不得自己似的。
[注 释]
①钱锺书指出,俞樾《俞楼杂纂·一笑》中“渔妇不蓄镜”皆由此来。本文所涉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部分例证根据钱锺书《管锥编》“不识镜”条目札记追索原典。
②典故出自马拉美《镜子》:“啊,镜子/那寒彻的水/竟可恶地将你冻伤的面庞蒙掩。……你显出我的身影/犹如徘徊在远处的幽灵。……嗬,可怕啊!多少个夜晚,/在你无情的镜面上/我看清了纷乱梦幻的赤条条的本相!”
③典故出自波德莱尔《天鹅》。
④未见《续鸠翁道话》原书,此据王晓平《唐土的种粒》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