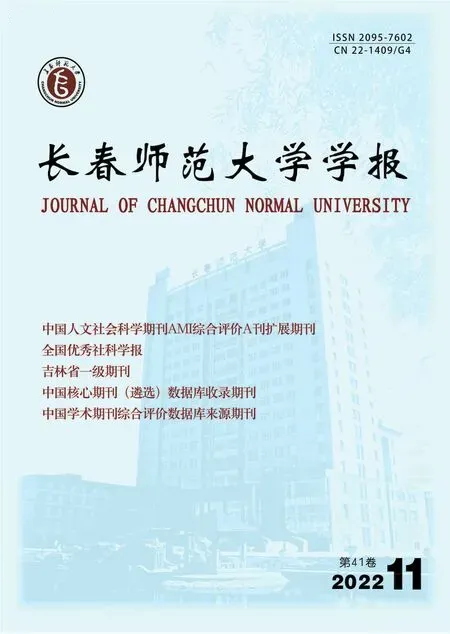东汉陈宠的司法实践和法律思想探析
王玉洁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1)
陈宠(?-106),字昭公,洨县(今安徽固镇)人,先祖世习律令。陈宠幼承家学,明法通经,年轻时曾担任郡吏,后历任辞曹、尚书、太山太守、广汉太守、大司农、廷尉、司空等职,执法宽平,政绩斐然,是东汉章和时期著名的执法官和律学家,其事迹见于《后汉书·郭陈列传》《东观汉记》《晋书·刑法志》等历史文献。本文从陈宠的家世入手,结合时代背景对其司法实践活动和法律思想进行研究,以求正于方家学者。
一、陈宠的家世和籍贯
陈宠出身于著名的律法世家——沛国陈氏家族。陈氏家族起自西汉陈咸,绵延五代,世代传习法律,掌管刑法,其中有三人因明法通经而位至尚书,号称“一门三尚书”。
陈咸为陈宠曾祖父,西汉成哀年间因精通律令而官至尚书。他性格仁恕,经常告诫子孙:“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1]卷46《郭陈列传》,1548后世子孙皆奉以为法。后来,他不满王莽掌权,愤而辞官,只专心整理家存的律令文书。
陈咸的三个儿子陈参、陈丰、陈钦在王莽辅政时均在朝为官,王莽篡权后跟随父亲一同辞官返乡,具体仕历不详。现在只能通过史书零星记载得知陈参曾教授过王莽《礼经》。
陈钦之子陈躬,东汉建武初年任职廷尉左监,早卒。其子为陈宠。
陈宠字昭公,明习法律,兼通儒家经典,是陈氏家族的杰出代表,也是东汉闻名的执法官和法律学家。汉章帝初任尚书,深受器重。章帝赏赐其宝剑,并亲自署名“陈宠济南椎成”①。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陈宠代郭躬为廷尉。永元十六年(公元103年),任司空。汉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卒于相位,号称“任职相”。《后汉书》称赞陈宠“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1]卷46《郭陈列传》,2458;“居理官则议狱缓死,相幼主则正不僭宠,可谓有宰相之器。”[1]卷46《郭陈列传》,1567其子为陈忠。
陈忠字伯始,明法通经,也是陈氏家族的优秀子弟,东汉时著名的执法官和法律学家。陈忠于汉安帝永初年间被征辟到司徒府为官,迁为廷尉正,后担任主管刑狱的三公曹尚书,又历任仆射、尚书令、司隶校尉,复为尚书令等职。
陈氏子弟世代传习法律,且大都担任司法职位。习法与务法相互结合,巩固了其作为法律官僚世家的重要地位。程树德曾言,“东汉中叶,郭吴陈三家,代以律学鸣”[2]《汉律考》,175-176。这里所说的“陈”便指以陈宠为代表的陈氏家族,足见陈氏一门作为法律世家地位之隆。《后汉书》对陈氏家族有很高的评价:“赞曰:陈、郭主刑,人赖其平。宠矜枯胔,躬断以情。忠用详密,损益有程。施于孙子,且公且卿。”[1]卷46《郭陈列传》,1567
《后汉书》记载:“陈宠字昭公,沛国洨人也”[1]卷46《郭陈列传》,1547,也就是沛国洨县人。洨县的设置最早可追溯到汉初的洨国。西汉高后元年设洨侯国,吕产为洨侯,治垓下,今安徽固镇濠城集。洨国的封地范围应在今固镇、泗县、灵璧、五河一带区域。②清光绪《宿州志》载:“汉尚书陈咸墓在州东南八十里故洨县城南。乾隆初土坍见石门,有汉篆曰:陈公咸墓。”“汉司徒(应为司空)陈宠墓在阳城故址南,俗呼凤凰古堆。”[3]卷4《舆地志》,109据《后汉书》等史料记载,陈宠生前担任过司空,未曾任司徒。唐代李贤等注《后汉书》:“洨,县名,故城在今泗州虹县西南。”[1]卷46《郭陈列传》,1548清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载洨县故城在“今凤阳府灵壁县南五十里。”[4]卷46《郭陈列传》,543现代考古对固镇、灵璧一带进行遗址发掘时发现濠城镇周边存在大小墓群,这些墓葬群应是洨国即后来的汶县中官僚及民众的墓群,陈氏家族的墓葬区可能就在此处。
二、陈宠的司法实践
(一)撰写《辞讼比》七卷
陈宠初为州郡小吏,后被司徒府征召为属官。陈宠勤于政务,表现出众,被司徒鲍昱提拔为辞曹,“掌天下狱讼”,负责处理地方上报的诉讼案件。不同于廷尉主办刑事案件,司徒府负责的诉讼多涉及民事纠纷,事类庞杂,“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1]卷46《郭陈列传》,1548-1549为了改变诉讼案件事类混杂、积案日久以及司法审判轻重失当的种种弊端,陈宠潜心研究,将案件分类整理,撰写了《辞讼比》七卷,使得“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后被鲍昱上报皇帝,获准颁布施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执法混乱的局面,有利于司法的澄清和法律体系的健全。
(二)上疏革除酷刑苛法
陈氏家族一贯主张议法从轻,陈宠秉持家训,反对烦苛的法律和酷烈的刑罚,主张轻刑宽法,曾上疏汉章帝痛斥司法暴虐,“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1]卷46《郭陈列传》,1549他认为,“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1]卷46《郭陈列传》,1549他建议汉章帝“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箠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1]卷46《郭陈列传》,1549汉章帝采纳了陈宠仁政宽法的主张,多次下诏减轻刑罚,史书称:“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绝钻鐕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1]卷46《郭陈列传》,1549酷刑的革除促进了法律的文明进程,妖言罪的解除得到了官僚士大夫的拥护和支持。
(三)支持孟冬论处死囚
依照汉朝旧规,孟冬十月、仲冬十一月、季冬十二月都可以执行死刑。汉章帝时改变这一传统,规定只在孟冬十月论刑。元和二年(公元85年),天下大旱,粮食减产,长水校尉贾宗等上书皇帝,认为此次大旱是因为决刑时间更改所致,使得阴气微弱、阳气发泄,引发旱灾,请求恢复旧律。汉章帝收到上书后,召集大臣进行讨论。陈宠从阴阳五行和通三统的角度出发驳斥了贾宗等人的观点,又引用《月令》论证十月行刑的合理性,指出《月令》“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1]卷46《郭陈列传》,1551,表明处决罪犯应在孟冬十月执行完毕。汉章帝最终采纳了陈宠的意见,不再恢复旧律。这一刑制改革影响深远,成为清代秋审制度的重要来源。
(四)主张删定律令条文
汉朝法律自汉武帝增修之后愈加繁密,内容大量增加,体系十分庞杂,刑罚也相当严苛,到西汉后期“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5]卷23《刑法志》,1103。汉元帝、汉成帝时期都曾减省刑罚,议定律条。东汉光武帝也曾对律法进行修订。但这几次改革仅进行了部分删改,“律令烦多”问题依然严重,加上当时汉儒注律成风,使律法更加庞杂。陈宠作为执法官对此深有体会,便上书皇帝请求重新修订,指出:“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1]卷46《郭陈列传》,1554但是,这项建议还来不及施行,陈宠就因事论罪了。两汉时期律令庞杂,关于法律的解释杂乱、繁多。因此,陈宠删订律令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有利于法典体系更加完善。
三、陈宠的法律思想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汉朝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产生了显著变化,之前约法省禁的黄老思想逐渐被德刑并举、礼刑结合的新儒学思想代替,开始了法律儒家化和儒家经典法律化的进程,在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方面主要表现为德刑并用、礼刑结合、顺天应时、春秋决狱。这些思想特征在陈宠的法律思想上均有所反映。
(一)德刑并用
汉朝统治者汲取秦代“尚刑而亡”的教训,奉行“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针,兼采儒法两家学说,以维护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和大一统的局面。汉代政治家、思想家在谈到治国理政时也往往主张文武并用,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如汉初陆贾提出的“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6]《至德第八》,13,反映了德刑相济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强调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和德主刑辅,促进了法律儒家化进程。东汉以后法律儒家化进一步发展,德刑并用思想已经根深蒂固。陈宠曾在上疏中提出:“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眚灾肆赦’;周公作戒,‘勿误庶狱’;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圣贤之政,以刑罚为首。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1]卷46《郭陈列传》,1549由此看出,陈宠秉持的是一种宽严相济、德刑并用的法律思想。他继承了西周“明德慎罚”和“以德配天”的思想观念,同时受到新儒学思想的支配,其思想立足点在于如何更好地维护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体现了法自君出和官本位的典型特征,代表了东汉官方正统的法律理念。这种儒法杂糅、德刑并用的法律思想在汉武帝时逐渐形成和确立,东汉时期进一步得到巩固,是汉代法制的重要结晶,为后世封建王朝所沿袭,成为立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礼刑结合
汉代统治者鉴于秦朝任法专刑、蔑礼用强的弊端,在修订完善汉代法律制度的同时,非常重视礼义教化对维护统治的重要作用,逐步确立了礼和法并用的施政方向。汉初著名思想家贾谊提出要以礼义教化万民。司马迁提出:“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7]卷130《太史公自序》,3976。东汉时期礼与法的关系日趋紧密,形成了以礼入律现象。汉章帝时陈宠请求皇帝删定律令时提出:“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1]卷46《郭陈列传》,1554陈宠关于礼刑关系的阐述表明他秉持的是一种礼刑结合的法律思想。礼不仅仅是一种等差性的社会行为规范,还被赋予了法律效力。出礼入刑使得法律道德化,而以“应经合义”为标准制刑议法,则使法律进一步儒家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成为对礼刑关系最本质的概括,揭示了中华法系融合伦理、道德、礼仪的内核特征。
(三)顺天应时
如前所述,汉章帝时曾下诏大臣讨论秋冬行刑问题,大臣们各抒己见。陈宠引用《礼记》中的《月令》一文进行阐述:“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1]卷46《郭陈列传》,1551他提出“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1]卷46《郭陈列传》,1551,即孟冬十月论处囚犯正是顺应天道,合乎四时。陈宠所依据的《时令》即《月令》记录一年十二个月气候、生物和农作物的生长变化,且“以时系事”,记述一年十二个月朝廷的祭祀礼仪、政务、法令、禁令等,体现了古人遵循自然规律安排生产生活并将政令施行和自然变化联系起来的天人合一的理念。由此看来,陈宠秉持的正是一种天人感应和“司法则时”的思想,即将司法审判与四时变化、阴阳五行等理论结合,说明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形成的“司法时令说”的理论已经成为司法的指导原则并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法律制度中,反映了儒家思想在东汉不断向法律领域渗透,并开始逐步法律化、系统化、制度化。
(四)经义决狱
在汉朝法律儒家化进程中,儒家思想对法律的不断渗透的表现之一就是用儒家经典来指导司法审判,使儒家五经逐渐法律化,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案依据,这一现象一般被称为“经义决狱”,又因为主要援引《春秋》及其注释,又称为“春秋决狱”。这一传统经董仲舒大力倡导,成为两汉时期比较常见的司法现象。东汉时期汉章帝曾召集诸儒考订五经异同,并整理编纂了《白虎通义》,使经学著作完全法典化。儒学大师纷纷以经典解释律法,律令章句学十分盛行。在儒学繁荣的东汉,明习经典成为每一位政府官员的必备素养,司法官吏也自然地征引儒家经典来审判案件。史书载陈宠“虽传法律,而兼通经书”,“及为理官,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1]卷46《郭陈列传》,1554。陈宠还曾建议汉章帝“稽《春秋》之文,当《月令》之意”,支持秋冬行刑制度。这些充分展示了陈宠对儒学经典的深入掌握和熟练运用,其中蕴含的“经义决狱”司法观念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大融合,也是东汉法律儒家化、儒家经典法典化的显著标志。
四、结语
陈宠凭借家传法学入仕,多次担任司法官职,深入参与了东汉的司法改革活动,推动了当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也为后世法制改革和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其法律思想展示了汉代法律逐渐儒家化的重要进程,代表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法律思想适应了地主阶级稳固君主专制政权和统治人民的需要,为后世封建王朝所沿袭,成为立法指导思想,对中华法系的发展和中国独特法律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 释]
① 尚书令韩棱、尚书郅寿、尚书陈宠皆以才能见重,为一时名臣。汉章帝十分赏识这三位重臣,恩赐三人宝剑,并亲手题名:“韩棱楚龙渊,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见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5《袁张韩周列传》,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后汉孝和皇帝纪》,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等。
② 洨侯国、洨县情况具体参考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8页;《安徽通史》第二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8·光绪宿州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3、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