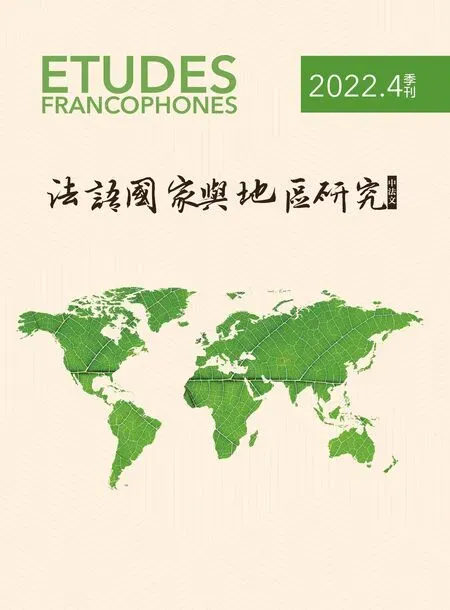布瓦洛论“诗与真”
王 夏
内容提要 “诗与真”是文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布瓦洛诗学的焦点问题。17世纪法国文学理论家布瓦洛的文学思想关于“诗与真”的论述包含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基于理性的“像真性”“自然本真”和“内心的真诚”是布瓦洛尚真诗学的核心术语,它既体现了以理性为纲的古典主义诉求,又集中代表了布瓦洛在法国君主专制的特殊历史时期对古希腊以来“摹仿说”的诗学传统和文艺复兴以来由于人性解放所致的自由风发的文艺思想的综合考量,这也是布瓦洛以“真实”为核心的人格理想与法兰西国家发展的历史使命相融合的必然结果。因而,布瓦洛的尚真诗学是历史使命,是时代精神,亦是其人生哲学。重读布瓦洛,全面揭示其尚真思想成为评价其意义与价值的首要任务。
引言
长期以来,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作为“古典主义代言人”被定格于人们心中,“古典主义老夫子”的标签①由于《诗的艺术》被誉为“古典主义的法典”,布瓦洛也被公认为“巴那斯山的立法者”(圣伯夫.《布瓦洛评传》,见:布瓦洛.《诗的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2),“新古典主义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朱立元.《西方美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71),“法国古典主义至高无上的指导者”(冯寿农.《法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2019:46),“巴那斯山的摄政王”(Pascal Debailly.«Nicolas Boileau et la querelle des satires».Littératures classiques,2009,68(1):131—144.)布瓦洛也成为当之无愧的“古典主义的代言人”。国内对布瓦洛的研究大多为西方文学史、美学史教材围绕“古典主义”所做的概略式评述,研究素材也主要依据于《诗的艺术》,布瓦洛自然被贴上了“古典主义老夫子”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和遮蔽了布瓦洛诗学的真正内涵,其尚真诗学也被视为古典主义老旧的翻版②学界将布瓦洛等同于古典主义的这种普遍认识决定了对其尚真诗学的认知情况,即认为其尚真诗学派生于古典主义思想,甚至是古典主义的老旧的翻版,没有任何新意。笔者认为,对于布瓦洛的尚真诗学,应该深刻洞察其社会历史语境和作者的文学认知,全面领会“真实”的思想内涵。。自18世纪以来,打倒古典主义和淡化以至埋没布瓦洛“普遍之真”的趋势,成为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现代、后现代主义一贯推行的口号,布瓦洛的尚真诗学受到巨大的冲击。更有甚者对布瓦洛的“惟上”因素大加谴责③Voir:John Richardson Miller.Boileau en Fr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Paris:Société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1942.«On l’accusait d’être un vil flatteur du Roiet des nobles...».,认为他所倡导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④Voir:Michael Nerlich.«Il faut devenir contemporain de Corneille:Réflexions sur le rapport Boileau-Stendhal». Etudes littéraires,1990(223):59.«Boileau s’est fait le porte-parole de la bourgeoisie commerçante contre la noblesse féodale guerrière,plaidant pour les principes cartésiens-jansénistes de la pensée (Kortum,p.133—135),et démolissant à tous les niveaux des normes néoaristotéliciennes fondamentales de la production artistique qui auraient pu servir les intérêts de la caste guerrière,d’un roi absolutiste conquérant et d’une église dogmatique,réactionnaire et belliqueuse.Cette orientation politico-idéologique de Art poétique n’était nullement extérieure à la dimension esthétique de ses réflexions sur la poésie.»的真实观。这些现象都存在忽略或无视布瓦洛诗学的历史语境、理论渊源及其核心思想的问题,对布瓦洛尚真诗学缺乏全面而整体的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布瓦洛尚真诗学的“真实”内涵不但与17世纪法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而且与布瓦洛的人格理想关联甚密。它既体现诗学的传统与发展、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又体现生命个体与历史潮流的互动与融合问题。本文的分析不局限于大家熟知的《诗的艺术》,而是在对布瓦洛主要作品⑤在国内,除《诗的艺术》之外,布瓦洛的其他作品《论蒙娜丽莎》(Dissertation sur Joconde)、《讽刺诗》(Satires)、《唱经台》(Le Lutrin)、《诗体书简》(Épîtres)、《讽刺短诗》(Épigrammes)、《传奇英雄的对话》(Dialogue des héros de roman)、《读朗吉努斯感言》(Réflexions sur Longin)、《论崇高》(Traité du Sublime,法语译本)以及致友人的信札等作品并无完整的中文译本,这种译介情况影响了布瓦洛文学思想的全面研究。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将“诗与真”的诗学母题置于17世纪的特殊语境中进行综合考量,并将其纳入文学演变的历史潮流中客观审视,尤为关注布瓦洛尚真诗学的生成环境、时代因素、诗学传统以及“真实”对于布瓦洛的特殊意义,以期挖掘布瓦洛尚真诗学的思想文化内涵。
一、思想内涵
“真实”(le vrai ou la vérité)是布瓦洛诗学的核心字眼。他对“诗与真”的理解与阐释贯穿其所有作品,集中体现于《诗的艺术》(L’Art poétique)、《诗体书简》(Épîtres)和《论蒙娜丽莎》(Dissertation sur Joconde)等作品中反复强调的概念,诸如“像真性”(la vraisemblance)、“真实”、“自然”(la nature)和“内心的真诚”(le cœur sincère),它们互为补充,共同诠释了布瓦洛的理性文学观。紧扣这些术语,剖析其深层思想,是理解布瓦洛论述“诗与真”的锁钥。
1.“像真性”与“真理”
何为“像真性”?顾名思义,“像真性”即像真情的事实。这里涉及文学作品与创作客体之间的契合度和相似度问题。在布瓦洛的文艺理论代表作《诗的艺术》中,他告诫作家:“切莫演出一件事使观众难以置信:有时候真实的事很可能不像真情。我绝对不能欣赏一个背理的神奇,感动人的绝不是人所不信的东西。”(布瓦洛 2010:33)很明显,此处的“像真性”包含合理、使人信服的含义,很自然地指向古典主义以理性为纲的文艺标准。判断是否符合真情,主要依据是理性。只是在布瓦洛的世界里,比起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思辨理性,即“正确地作判断和辨识真伪的”所谓的“良知”⑥笛卡尔.《谈方法》.载《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62.,理性更像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它还包括对行为的控制力和约束力,讲究适度(la bienséance)与节制,与当时社会理想的意识规范或从经验所得出的常识常理密切相关。在《论蒙娜丽莎》中,布瓦洛以“像真性”作为批评布雍(Boüillon)与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的标准:
但是除了布雍先生在这里所追寻的荣誉之外,我发现这种恭维相当无礼,因为一个奉承者对一个自称是他那个世纪最英俊的国王说,“我有一个比您更英俊的哥哥。”这种意图是徒劳的。这并不像真的。拉封丹先生很好地避免了这些,只是简单地说,这个奉承者乘机赞扬他哥哥的英俊,但并未抬高到国王的高度。⑦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Œuvres complètes de Boileau. Paris:Société les Belles lettres,1942:27.
布雍的“恭维”之所以“不像真的”,原因在于它超过了“国王的高度”。布瓦洛的这种判识表明,文学的真实有限度,但凡超出常情常理、伦理规范之外的描述都不像真的,是不真实的。在将阿里奥斯托(Arioste)、布雍与拉封丹《故事新诗》(Contes et nouvelles en vers)中对蒙娜丽莎的故事情节的比较分析中,他多次提到“像真性”,并以此作为批评准则。这些所谓的“逼真”结论都依据常理和经验得来,正如德尔菲娜·和吉格(Delphine Reguig)所言:“‘真实’的定义对于布瓦洛来说,就像对于许多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关系,而是某种属于他自身经历的思想。”⑧Delphine Reguig.Boileau poète.Paris:Classiques Garnier,2016:166.
对于布瓦洛而言,文学不是完全照搬现实的摹拟,他深信绝对的真实只能引起憎恶,这一点也被布霍斯特(Brossette)后来的记载所证实(2010:30)。“绝对没有一条蛇或一个狰狞怪物/经艺术摹拟出来而不能供人悦目:一支精细的画笔引人入胜的妙技/能将最惨的对象变成有趣的东西。”(2010:30)“经艺术摹拟”意味着可以对作品进行加工,但这种加工只可能是适度的、符合“常情常理”的摹拟标准的美化和虚构,并不等于赋予想象和虚构绝对自由的空间。在《论蒙娜丽莎》中,布瓦洛说道:“一个诗人兼伟大的批评家曾经说过,我很清楚有许多东西是诗人和画家都允许创作的。他们偶尔能任意想象,不应该总是将其限制在狭窄和严峻的理性范围内。”⑨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op.cit.,p.11由此可看出,布瓦洛的文学世界里不是只有理性,他也容许给予想象一定的空间。但对于想象,他认为把它让位给“开玩笑的小说一切还情有可原,它不过供人浏览,用虚构使人消遣”(2010:38)。而作为生活的摹拟的戏剧,却必须比小说更注重与理性结合。因此,在处理想象在文学(主要指戏剧)创作中的地位时,他不像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刘勰那样重视想象,强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神思,而只是依据“常理”和经验来约束想象,因为在他看来,“在任何的虚构里那种巧妙的假象/都只有一个目的:使真理闪闪发光”(2010:103),虚构的宗旨在于揭示真理。换言之,布瓦洛所允许的虚构必须服从理性的管辖,必须揭示真理。何为“真理”?对于布瓦洛而言,理性即真理,这是他的文学之真的最终旨归。
2.“自然本真”
与布瓦洛尚真诗学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词是“自然”。布瓦洛所谓的“自然”与今天我们所指的自然风光、事物的本然迥然不同,它指的是普遍的人性,强调的是一般的真,与个别的真相对,说透彻,就是自然的本真。在《诗体书简九》(Épître IX),布瓦洛将“自然”与“真”勾连:“只有自然才是真,一接触就能感到:一切里面只有它能得人喜欢、赞美。” (2010:105)他告诫作家“唯一钻研的就该是自然人性”(2010:53),他论及人性的“陆离光怪”,“每个灵魂的不同特点”,但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他承认特殊的真实,而恰恰成就了他与贺拉斯(Horace)相仿的“年龄论”(2010:53)。他一面说着“每种情感都说着不同的语言”,告诫作家不能使“创造出来的英雄个个和他一样”(2010:39),一面又规定创作不同情感应有的语调和模式。确切地说,他所谓“个体的真实”是类真实,是“充满人性的典式”。在《诗的艺术》中论及喜剧时,布瓦洛描绘了一幅具有普遍特征的“严父”与“情郎”的画面:
你看特朗斯写的是怎样一个严父/看见儿子讲恋爱痛骂着小子糊涂;小情郎听着严训又怎样恭敬有加,一跑到情妹身边就忘了那些废话,这不仅是一幅画,一个近似的小影,却是真正的情郎,是活的父子真形。(布瓦洛 2010:55)
这种对普遍之真的钟爱,事实上与基于理性的“真实”如出一辙。二者都指向了纯粹的事物本质。正如安东尼·亚当(Antoine Adam)所言,受到拉穆瓦尼翁(Lamoignon)学院的文学思想沾溉的布瓦洛所谓的“模仿自然指的是作家以真实为准则,严禁无根据地游戏和追求形象。这种真实,不是我们日常的经历所能达到的物质的、特殊的真实,而是‘观念的完美’,是事物纯粹的本质。”(Boileau-Despréaux 1966:XVII)
3.“内心的真诚”
除了以“像真性”和“自然本真”为准则对诗歌创作做出严格的规定之外,布瓦洛对“真实”的思考还包含对诗歌创作主体的要求。在《诗体书简九》中,布瓦洛写道:“如果内心不真诚,才易使人厌倦。”(2010:106)。“内心真诚”包含多重含义。布瓦洛要求作家对自己真诚,有自知之明,正确衡量自己的才华和实力;在接受批评时不能做执迷不悟,为自己辩护的“傻子”;要求作家要摒弃虚荣与矫饰,表达“真正自己的感情”,避免“违心之论”(2010:107)。除了对自己真诚,表达真实情感之外,布瓦洛提出的“内心真诚”事实上明显包含了善和美的杂糅。
在《诗的艺术》第四章中,布瓦洛写道:“处处能把善和真与趣味融成一片。一个贤明的读者不愿把光阴虚掷,他还要在欣赏里能获得妙谛真知。你的作品反映你的品格和心灵” (2010:62)在布瓦洛看来,内心真诚的作家必定是具有崇高品格、良好趣味的作家,唯有这样,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令“贤明的读者”收获“妙谛真知”。在《诗体书简九》中,布瓦洛反复强调“没有比真更美的了”(2010:102),“只有真才能算美”(2010:106),所谓的“内心真诚”即真善美的合一,寄托了布瓦洛对作家品性和境界的最高要求。
虽然“像真性”“自然”和“内心的真诚”这三个术语最初具有各自不同的意义,但事实上最终都似乎指向了同一种文学之真,或者说它们互为补充,共同指向了古典主义的理性与德行并举、以真善美为最终旨归的文学之真。
二、理论依据
任何观点的产生大都有其思想依据。布瓦洛诗学肇始于法国古典主义时期,这一时期是西方诗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上承文艺复兴,下开启蒙运动。这种历史的定位为我们考察布瓦洛诗学的理论渊源提供了参考的视角。布瓦洛尚真诗学与前古典主义的诗学传统、17世纪笛卡尔开启的理性哲学风潮和朗吉努斯(Longin)的“崇高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剖析其思想渊源,有利于更深入地把握布瓦洛尚真诗学的理论内涵。
1.摹仿说
“摹仿说”探求的是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也是西方自古希腊时期以来对“诗与真”这一命题的集中表述。文艺摹仿现实,是人们对文学真实性的最初认识。从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最早提出“艺术摹仿自然”论,经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柏拉图(Platon)、贺拉斯、亚里士多德(Aristote)等人发展为自成体系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Léonard de Vinci)的“镜子说”,直至古典主义时期布瓦洛的“摹仿自然”观,我们不难发现在“摹仿说”的嬗变中,文学的真实问题始终是古代思想家们共同探讨的核心议题。尽管对文学如何反映现实以及何为“自然”的问题存在不同认识,但在柏拉图将艺术视为“最高理式”“与真理隔着三层”的“摹仿的摹仿”的影响下,亚里士多德基于“一事物的真相就是这事物的本身”⑩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58.这一朴素唯物论的“摹仿艺术”以及贺拉斯摹仿社会生活的文学“合式”论,都无一例外地注意到了“摹仿说”的社会和理性的维度。
布瓦洛对“诗与真”的理解既沿袭了自古希腊以来崇尚“摹仿说”的诗学传统,又扩展了“真”的含义。首先,同“摹仿说”一样,“像真性”反映的是作品与创作客体之间的关系。在《诗的艺术》第三章开篇,布瓦洛提出经艺术摹拟的蛇令人悦目。虽然他关注的是如何将丑和恶的现实描摹得令人赏心悦目。但不管是丑陋的蛇也好,还是狰狞的怪物,布瓦洛都承认它们是文学艺术应该描摹的对象。这是古希腊以来承认艺术反映现实的“摹仿说”的延续。其次,“像真性”“自然”强调的是文学作品与创作客体之间的契合度和相似度,这就必然与“摹仿说”一贯体现的理性思维方式相吻合。概而言之,布瓦洛的尚真建立在古希腊以来的“摹仿说”的反映论和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既是西方诗学传统的延续,又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段。
2.笛卡尔哲学
作为古典主义的思想基础,笛卡尔理性哲学同样为布瓦洛的诗学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截至17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法国封建君主专制的最终确立和加强,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掌权,“首先要解决无知的问题”⑪笛卡尔.《 谈谈方法》.王太庆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即从思想上动摇建立在迷信、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之上的封建统治的根基。继17世纪初英国的培根(Francis Bacon)率先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之后,法国的笛卡尔于1637年发表《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从方法论上以理性主义对抗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和形式主义。继而在1641年发表的《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中,笛卡尔详细论述了他的基本哲学思想,从此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近代哲学时代。
笛卡尔哲学的出现则为痴迷于古代文学的布瓦洛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论所确立的“思想”与灵魂的主体地位,“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决不把它当成真的东西”的信条,以及从简单到复杂、从特殊到一般,分析与归纳结合,注重次序和“正确地运用才智”⑫同上,第9页。的方法成为17世纪中叶法国作家研究文艺现象⑬朱立元.《 西方美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69.和处理题材的方法⑭朗松.《 朗松文论选》.徐继曾 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271.。这种思维方法表明思考的过程须经过分析、解剖、排列、综合四个步骤。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笛卡尔提出对真与善的理解:真理是凭借理性而获得的明晰的认识;善行是在理性支配下的意志对生活的指导。真与善的灵魂就是笛卡尔哲学的核心所在—理性。“真即美”,真是美的根本条件,所以艺术在相当范围内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美的条件存在于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条理、秩序、均整、统一、对称、简洁、明晰和规律。⑮朱立元,前揭书,第169页。
这种注重分析和条理的科学方法和怀疑的精神影响了布瓦洛,为他更巧妙地把“真善美合一观”与“崇高论”相连提供了依据。“在1650年出生或者受教育的人,则在正当年的时候接受了笛卡尔的影响。”⑯朗松,前揭书,第253页。对于在笛卡尔哲学的润泽下度过青年时代的布瓦洛来说,虽然他对理性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常理、经验和道德要求等形而下的基础之上,尚未到达笛卡尔的形而上的思辩层面,但笛卡尔哲学的方法却成为他研究文艺的思维方法,而在此基础上所衍生的“真善美合一观”最终成为布瓦洛的诗学信条。他把自古希腊以来柏拉图所推崇的真的“理式”和贺拉斯的“判断力”进一步确定为“那种正确地作判断和辨识真伪的能力”和“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即“理性”,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尚真诗学的内涵。
3.朗吉努斯“崇高论”
朗吉努斯之于布瓦洛,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论崇高》(Traité du Sublime)之于布瓦洛,更如思想的富矿。布瓦洛翻译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并在其法译本序中极力赞赏其君子的人格和崇高的才思。他对朗吉努斯“崇高论”的高度认可在《读朗吉努斯感言》中历历可见。无疑,朗吉努斯的“崇高论”为布瓦洛的诗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向。
崇高是言词的某一种力量,专能提高灵魂,夺去灵魂,它或则来自思想的伟大与情感的高贵,或则来自词语的壮丽,或则来自表达的那种和谐、活泼而生动的圆转;也就是说,它来自分别看待的这三件东西中的一件,或则,为构成完美的崇高,来自合在一起的这三件东西。(布瓦洛 2010:184)
布瓦洛推崇崇高,并把“思想的崇高”视为根本的、完美的崇高,这就为提倡文章道德合一找到了理论依据。“你的作品反映着你的品格和心灵”(2010:62),“一个有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诗品。”(2010:63)文学作品反映创作者的内心,这是传统的“摹仿说”与道德的结合。对矫饰文学、粗俗文学的批判⑰这里主要指布瓦洛对17世纪沙龙文学中的矫揉做作之风以及诙谐文学中低俗滑稽风格的批判,他对斯居德里小姐(Madame de Scudéry)的作品多有批判,并在《诗的艺术》中嘲讽了低级的滑稽。,对作家伦理的要求则变成了追求崇高的首要任务。再往深处想,提倡“思想的崇高”,这意味着认可创作内容的思想性,而根据理性裁决创作内容也是古典主义理性文学的题中之义,归根到底这就意味着“崇高论”与古典主义诗学观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崇高”建立于神学本体论的基础之上,并表示旧约中“上帝说:要光明形成,光明就形成了 ”这句话“把造物界对造物主的那种服从,标示得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崇高,并且有点神的意味呢。”(2010:195)最终,布瓦洛将文学思想的终极目标落在了“崇高”上,即让灵魂获得一种神奇而高贵的提升。这种“灵魂的提升”经由理性所获得的启迪和教育更具超越性。在此意义上,真与德合一,与理性的创作标准相通,布瓦洛的尚真诗学也具有了理性、伦理和神性的多重特征。因此,朗吉努斯的“崇高论”扩展和深化了布瓦洛的尚真诗学,并为他更好地奉行古典主义文学观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历史使命与人格理想
布瓦洛尚真诗学的理性、伦理和社会属性披露了其不容置疑的历史使命,承载了法兰西民族国家崛起的文艺诉求,也体现了文艺理论家布瓦洛的人格理想、诗学信仰与国家意识和历史潮流的自觉融合。这使布瓦洛的尚真诗学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
1.历史的遗留与诗学的整合
布瓦洛崇尚理性和真实的文学思想是对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与诗学思想全面整合的必然要求。14—16世纪在欧洲各地发生的、以反抗中世纪政教一统的压迫为主要任务的文艺复兴反天主教、反禁欲主义,主张个性解放,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这种摒弃神为中心,拥护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欧洲掀起了文学革命,引发了自由风发的文艺思潮。首先表现为文学作品中对现实和人性的真实诉求以及作家通过作品表达内心思想的愿望愈加强烈。
先是意大利人文主义先驱但丁(Dante Alighieri)在《神曲》(Divina Commedia)中揭露了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昧,表达了对拉丁语文化及其教会权威的挑战和抗议。这一创举在当时社会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16世纪法国诗学的灵感主要是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诗学,而不是本国中世纪的民族传统。”⑱陆扬.《文艺复兴诗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147.16世纪的法国同样可以被称为受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最大的欧洲国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法国文艺领域出现了新的图景:加尔文(Jean Calvin)大胆的释经理论,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自由风发的小说和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充满哲思的散文体出现。这些作品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题材和体裁上,无疑都是对中世纪文学的革新和挑战。尤其以《巨人传》(GargantuaetPantagruel)最为突出,拉伯雷用粗俗的语言表达了人性解放的狂欢,这是它与教会文学和骑士文学截然不同的一大特征。
一方面,这种粗俗的文学表现形式恰好地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广大民众试图冲破中世纪以来的压迫和禁锢的真实诉求;另一方面,它是中世纪以《列那狐传奇》(Le Roman de Renart)、维庸(François Villon)的抒情诗和小故事诗为代表的市民文学的延续,寄托了市民阶层表达自身思想和情感的现实愿望。
到了17世纪,法国文学艺术经历了文艺复兴200多年的洗礼,反对教皇极权主义(Boileau-Despréaux 1966:XXIV)和反禁欲主义的诉求更加强烈。从社会层面来看,压抑太久的人性渴求情感宣泄,社会的攀比、拜金等不良风气盛行,思想混乱;从文艺领域来看,自由风发的思想在法国文坛进一步蔓延,渐渐形成以反映苦闷颓废的情绪和形式主义的趣味为特征,语言上强调雕琢和矫饰,表现手法极其夸张的巴洛克风格,这种浮靡颓废的文风腐蚀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迷失了理性,不利于专制国家的思想统一。
在这些社会现实的面前,法国文艺的规范化显得尤为必要。那么,文学是否要如实反映现实的混乱与黯淡?是否要真实再现人性假、恶、丑的一面?作家是否要口无遮拦,尽情倾吐内心情感?这些文艺复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17世纪混乱的现实冲击下更加凸显,成为布瓦洛所生活的年代文艺发展首要面临的一大难题。在理性主义盛行的17世纪法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从路易十三(Louis XIII)统治时期的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到路易十四(Louis XIV)时期的《诗的艺术》,社会与文艺领域都发出了抵抗放恣的文学之真的声音。路易十四英明地意识到,他的国家不需要,也不容许这种无节制的文学真实。为了巩固和加强专制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他需要用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作为古典主义的法典,引领理性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文艺之真,从而使作家在理性的指引下进行创作,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扫清文艺复兴以来混乱的文艺局面。
布瓦洛的尚真诗学披露的是一种节制、典雅、高尚并举的理性主义文学观。它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的全面整合。具体而言,它是当时对茫然失控的人性救赎,是对纵脱不羁的文学思潮的矫正,更是社会转型时期有利于专制国家发展和民族文学繁荣的必然选择。
2.国家政治与古典主义
任何一种文学思潮与诗学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反映时代需求。17世纪的时代精神是“古典”这一术语所包含的思想,它以理性为圭臬,视古人为典范,反映宫廷趣味,维护君王的统治。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君主专制的统治地位,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黎世留 (Armand-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建议和支持成立法兰西学院,并组织编纂《学院词典》以规范法语和扩大法语的影响力。在这些文化措施的基础上,“太阳王”以规范文艺增强其政治统治的野心愈加强烈,他把专制集权和“荣誉”至上的意识形态渗透于文学艺术中,最终于1674年授权布瓦洛撰写《诗的艺术》。这部“古典主义的法典”规定了文艺创作的标准和要求,从此,以理性、均衡、简洁、明晰、秩序为特征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得以最终形成。
毫无疑问,诞生于古典主义的布瓦洛诗学⑲布瓦洛与古典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作为“古典主义的代言人”,布瓦洛在“古典主义的法典”—《诗的艺术》中总结了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标准和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瓦洛定义了古典主义;另一方面,古典主义先于布瓦洛诗学(布瓦洛作品中所蕴含和所揭示的文学理论)存在。严格说来,古典主义指的是从文艺复兴后期到17世纪在法国达到极盛,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走向式微的,在全欧洲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文艺思潮。但通常意义上,西方学界的“古典主义”指的就是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因为这一时期古典主义发展极盛,形成了高度典型的精神气质。布瓦洛诗学诞生于古典主义的环境中,它很大程度上与古典主义的旨趣是一致的,但也包含一些与古典主义思想不完全一致的地方(这一点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体现了17世纪的时代精神。其文艺真实论与古典主义的理性宗旨表现出高度的趋同性,二者都追求理性与道德的合一。
这种将真善美与理性同一的真实观是与布瓦洛同时代的很多作家的共识。拉罗什福科(Duc de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在《道德箴言录》(Réflexions ou sentences et maximes morales)中写道:“真实是完善和美的基础和根据:一件事情,不管它是什么性质,假如它不是它所应是的那样完全真的,假如它没有它所应有的一切,它就不会是美的和完善的。”⑳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何怀宏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25.所谓“应是的那样”和“应有的一切”表明“真实”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直观而自然的真实,是应然的,符合理性的,与美和善同一的“理想的真实”:
在布瓦洛的时代,所有作家都赞同某些普遍原则,这是真的。所有人都相信那些规则。所有人都坚信一部作品必须服从于理性的某种要求。所有人都引用像真性的观点,也就是说,一种理想的真实,符合事物的主要性质的真实。(Boileau-Despréaux 1966:XVIII )
布瓦洛对文学真实性的总体认知与当时这种“真善美理”一体的文艺观如出一辙。他还将它与朗吉努斯的“崇高论”勾连,并上升为作诗的制胜法宝:
因为我诗里真实战胜了谎言,它处处昭然在目,处处扣人心弦,因为我诗里时时善与恶鉴赏分明,因为我诗里庸人从来不僭居上品;还因为我的心灵永远领导着智慧,它绝不告诉读者自己不信的东西。(布瓦洛 2010:104 )
而这种“扣人心弦”的标准,指向的正是那种被朗吉努斯称之为“崇高”,“在言词里,能感动人,使一个作品能震撼人心、夺人之魂、移人之情的那种非常的、神奇的东西。” (2010:194)
这种以理性、崇高为原则,对“诗与真”做出种种规定和调和的诗学观,寄托了布瓦洛对文学代表真善美的美好希冀,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布瓦洛的诗学观点的集大成者《诗的艺术》是在国王的授意之下写的,它必然代表了路易十四时代君主专制集权国家在文艺领域的意志,即代表的是有利于君主专制统治的文艺思想。这种政治意图和历史使命使他不能宥于传统诗学的“摹仿说”,而是使文学之真的概念更具有民族化和时代性特征。它体现政治对文学的规训,但又远远不能简单地说它是一种唯上的生存智慧,或是一种政治文学观。因为理性的号角已经在17世纪法国的上空吹响,古典主义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说它是一种无可为而为之,与国家命运共存亡的睿智也不足为过㉑笔者认为,结合布瓦洛自小树立的“改善道德风尚”的文学理想以及他批判文坛不良风气的诗学实践来看,布瓦洛对国家在文艺领域推行古典主义是支持的,这也可以看作他与国家命运相统一的诗学立场。。
3.与历史使命融为一体的人格理想
以上两个维度明显披露了文艺理论家布瓦洛的历史使命和伦理使命。17世纪法国作为君主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要求文艺必须承担起强大的社会功能。文艺反映政治需求,服务于国家发展。这是“古典主义的代言人”布瓦洛难以规避的历史使命。然而,与其说布瓦洛的尚真诗学是法兰西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不如说是他将其人格理想、诗学信仰与历史潮流融合的自觉选择。
“自由的真理是我唯一的追求”(Boileau-Despréaux 1985:188),正如诗人在致德吉列拉格(De Guilleragues)先生的《诗体书简五》(Épître V)中写下的这句话,在所有人都在为国王“荣誉”讴歌的17世纪,布瓦洛却积极践行“真实”的内涵,并将之扩展为一种为“为自由真理”奋斗的精神追求。对于布瓦洛而言,“巴那斯”是崇高、神圣的,这是他为之奋斗终身的诗学信仰。在此信仰的感召下,他敢于运用手中的笔,奋笔疾书,以辛辣而尖锐的讽刺诗嘲讽和抨击虚假的道德与社会伦理,并由此确立了“改良社会道德”的理想。面对矫饰文学泛滥、低俗文学抬头的不正之风,布瓦洛秉持“真与善”融合的文艺方针,恪守高尚的职业操守,顽强抵抗和批判,为法兰西文坛树立起良好而坚固的诗学典范。在“太太学堂之争”中,他致信并鼓励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这一兄弟般的慷慨相助事实上表明了布瓦洛保护理性和真实的坚定立场,因为那些矫揉造作的可笑之人赋予观众嘲笑的对象浪漫气质和矫饰的术语。《太太学堂》的争论在于很好地表明真实的反对立场。反对莫里哀的不单单是国王的喜剧作家和伪君子们,还有那些爱好浪漫悲剧,一种英雄主义的虚幻文学和虚假的文雅人士。这是为什么布瓦洛在致莫里哀的讽刺诗中,攻击基诺(Quinault)、斯居德里(Scudéry)和梅那热(Ménage)的原因所在,也是他在诗中所表达的观点。这是理性,也是真实的意义(Boileau-Despréaux 1966:XIV)。
在《讽刺诗十一》(Satire XI)中,他写道,“世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剧院。在那儿,每个人都在大庭广众之下,彼此互相欺骗,他们所演的角色通常和自身相反”(Boileau-Despréaux 1985:143)。面对虚伪的世界和爱慕虚荣的人们,他呼吁“唯一坚固的荣誉就是始终以真实作为向导,就是对一切事物都重视理性和法规,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就是完成所有上苍启发我们的善行,总而言之就是保持公正。”(Boileau-Despréaux 1985:146—147)
这种对社会伦理之真的体悟和捍卫诗学的崇高信仰加深了布瓦洛对自我的要求,“真实”成为他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哲学。面对自己的才能,他向国王坦言自己没有写颂诗的才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讽刺诗;在与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同为国王的史官期间,他深知“真实难求”,放弃为国王写史诗,选择“只忠实于他唯一的天赋—作诗”㉒Roger Zuber,Micheline Cuénin.Le Classicisme.Paris:Flammarion,1998:267.;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统治下,他坚定地保留对冉森教派的好感,与拉辛、阿尔诺(Antoine Arnauld)等冉森教徒保持了交往和联系。正是这样,布瓦洛通过辛辣的讽刺痛骂和直率的性格成为“他那个时代真实气质的证明”㉓Roger Zuber.Histoire de littérature au XVIIe siècle.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3:98.,在文学上保留了相对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堪称在王权至上的社会中“极其艰难的坦诚”(Boileau-Despréaux 1966:XXVII)。
由此可见,“真实”在布瓦洛诗学中呈现出多种义项,它并非本体论层面的“真实”,它是“艺术的摹拟”,是“像真性”,是“自然”、是“内心的真诚”,也是善行、公正和自由。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表层背后隐藏着统一的诗学逻辑,即真善美合一。这就是“真实”的力量。提倡文艺作品的“不真实”(虚构和加工)是为了“使真理闪闪发光”;呼吁作家的内心“真实”是为了有“反映品格和心灵”的作品;反对社会的虚伪是为了“保持公正”和“求善”;追寻真实的内心,是为了“追求自由的真理”。由此可见,布瓦洛尚真诗学观秉持以“真善美”为信念的古典主义诗学逻辑,披露了布瓦洛对国家文艺政策和社会伦理之真的深刻反思,也体现了其历史使命与真诚的人生哲学的自觉融合。
结语
布瓦洛尚真诗学的文化内涵极为深刻。它既体现了对古希腊以来诗学传统的继承和民族国家发展的特殊时期的古典主义诉求,又集中反映了对文艺复兴以来所遗留的诗学问题的全面整合,同时体现了布瓦洛将历史使命与自身人格理想自觉融合的决心和担当。“摹仿说”、笛卡尔哲学和朗吉努斯“崇高论”为布瓦洛的尚真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养分,使它不囿于“摹仿说”的反映论,与理性、崇高的古典主义的文艺诉求结合,扩展和深化了“真实”的社会和伦理维度。布瓦洛的尚真,是历史的必然,亦是其人生哲学。对于布瓦洛而言,这是一种渗透于文字与生命中,对自由真理的追求与践行,寄托了人类心灵深处对文学的最高期许和守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将对文学之真的推崇内化为一种真诚的人生哲学。他对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和内心真诚的重视,对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那份坚守和担当,对于现当代文坛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诚然,从文学的本真需求来看,这种真实观过于理想化,但于那个特殊的时代而言,却具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它也确实促进了古典主义文学的繁荣,对社会的整体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综上所述,将布瓦洛的尚真诗学仅仅视为“普遍、恒常的真实观”和“意识形态文学”而大加谴责,显然有失偏颇和公允,全面的反思和审慎的提炼,是对待这一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也是诗学领域古为今用的建设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