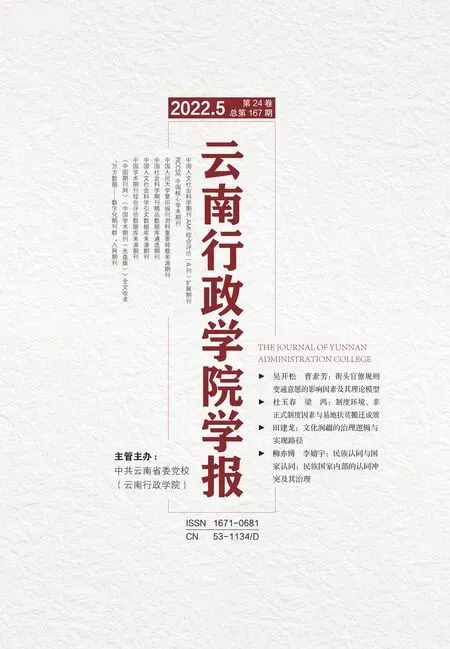从古典到早期现代:立法者科学的传统与继承*
张 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29)
近代以来,世界经历了一个民主化(其核心是身份的平等化)过程,这让人们似乎淡忘了政治思想史上的立法者传统。这一传统起于古典,我们能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之后的罗马作家们那里清晰地看到关于立法者科学的主张①(英)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M].卢华萍,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及至早期现代(earlymodern),马基雅维里依然保有这种对于“立法者科学”的关注,而之后的孟德斯鸠、卢梭和亚当·斯密等也都表达了此一取向,甚至美国立宪本身也被视为“立法者科学”意义上的行动——只不过其立宪内容意味着向现代政治的转向。立法者科学不同于对“立法”的方法所作的技术性讨论,作为古典政治“科学”的组成部分,它关涉的是人的行动与其生活秩序之间的关系,它的内容所涵括的是根本生活秩序之建构、维系、变革过程中人的处境。“人”的行动最集中地体现在“立法者”身上,而立法者所面对的是“政治的”秩序。故而我们先要回到古典政治科学来审视“政治”的意涵,由此明确立法者在政治秩序中居于怎样的位置、他(们)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所在,以使传统立法者科学的特质更为清晰。
一、“政治科学”的古典意涵:探究人的存在秩序
古典政治科学有着与当代颇不相同的意涵。在古典思想家们的眼中,“科学”并非现代自然科学,而是从对自然(physis)的思考中发端,进而以寻求不易之则(即理,logos)的态度所展开的对于人事问题的探究,它所依凭的是理性。而政治科学则基于这样的理性探究对生活秩序的安排。它“谨慎乃至一丝不苟地遵循对政治生活及其对象而言自然且固有的清晰阐述”①(德)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M].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67.,从而表现出对政治秩序的整全把握,以及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整体性关注。
相较于现代科学,古典思想家所坚持的“科学”并不指向特定(如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像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对于真理的探索,它关涉各个存在领域的本性”②Eric Voegelin.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AnIntroductio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4.。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的“洞穴隐喻”中描绘了一个从洞穴中走出最后看见太阳的过程,这是一个哲学家的养成过程,他所需要的是将灵魂转向,“从变易的世界转向存在世界”③(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 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19.,直视那最真实的“善的型”(Form of the Good)。而算术、几何、声学、天文等的学习以及辩证法的使用,能够促成这种转向,使哲学家得以观察最普遍、最纯粹的实在,获得真正的知识或科学。相较其师,亚里士多德当然更加从经验着眼,但是他眼中的科学也绝非技术性的,而同样是对真实世界的整全认知,其中最重要的依然是那个最高的实在(ultimate reality),“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理型’(eidos)不是抽象存在于观念界的实体,而是‘蕴含于’每一个物体之中”④陈思贤.西洋政治思想史(古典世界篇)[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11.。他在《物理学》的开篇便说:“如果一种研究的对象具有本原、原因或元素,只有认识了这些本原、原因和元素,才是知道了或者说了解了这门科学,因为我们只有在认识了他的本因、本原直至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了这一事物了。那末,显然,在对自然的研究中首要的课题也必须是试确定其本原”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
这样的研究方法自然也用在了对政治事务的观察与思考中。他说,“我们在政治学的研究中,也要分析出每一城邦所由组成的各个要素而一一加以考察”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所以他以男女的结合与主奴的结合这两种关系共同组成家庭为起点来研究城邦的起源(家庭联合成村坊,村坊组合为城邦),从组成城邦的公民的性质来研究城邦的本质。这些研究所处理的要素归根结底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恰恰是政治学的前提与题材”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除了行为,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政治家“需要对灵魂的本性有所了解,就像打算治疗眼睛的人需要了解整个身体一样”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2.。之所以要了解灵魂的本性,在于政治的目的是“最高的善”,也即最高的幸福,而“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这当然是一种德性政治观的视角。然而也正是这样的视角才使得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思想家能够更深入地触及人的根本生活状态,从人的“存在”(being,ousia)层面来思考政治秩序。亚里士多德以“四因说”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50-60.来处理“存在”问题,而“人为何要以‘政治’的方式存在”亦可归入这一阐释框架。相比于当代的“行为主义科学”而言,这样的努力试图关注“完整的人”。“完整的人”是难以量化的,确定人在世界乃至宇宙中的位置,由此彰显了施特劳斯和沃格林所说“科学”的真正内核②See Jed W.Atkins.Cicero on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Reason:The Republic and Law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84.。
相较之下,“罗马人不像希腊人那样爱思索,希腊人正是通过思索才了解科学……但罗马人显然很快就成了好学生,尤其是在政治领域”③(法)菲利普·内莫.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M].张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5.。古罗马的政治科学主要体现在其史学论述和法学实践中(拥有哲学主张的西塞罗是例外),这在波利比阿、普鲁塔克、塔西陀以及罗马法学家那里有充分彰显。在进行历史写作时,史学家们把人事置于视野的中心,他们所展开的并非仅仅对人的行为的观察,而是将人事作为整体世界的体现,以“人的存在秩序”的眼光来打量历史之中人的政治生活。在《历史》中,塔西陀所书写的是罗马“政治”,他指出这是一段“充满了灾难的历史”,其中有恐怖的战争和激烈的内讧。然而仅仅是描述这些还不够,他认为“我们应当回过头去,考虑一下罗马的情况、军队的情绪、行省的态度、整个世界上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理解多半出于偶然的事件及其结局,而且可以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④(古罗马)塔西陀.历史[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这其中透露出的是沃格林的洞见:“人在社会中的生存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它拥有一种超越纯粹动物式生存的精神和自由的向度,是因为社会秩序是人与存在秩序的调适,也是因为这种秩序能被人所理解。”⑤(美)沃格林.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2)[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6.
与希腊人不同,罗马人所面对的是一个世界共同体(world community),罗马史学家所书写的是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从中所要确立的是“关于世界社会的学说”⑥(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83.。但这也只是他们对于环境变化所作的应对,而在“试图以整体的眼光来描绘人的整全本身”这个层面,罗马史学家看待政治的态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无本质不同。比如,使波利比阿享有盛名的混合政体理论,作为政体科学意义上的政治科学⑦J.G.A.Pocock.Virtue,Commerce,and History: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42.,是被置于“整个世界何以落入罗马统治之下”这一历史视阈中来展开的,它所关注的不只是政治人物、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更是生活在某一政体之下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存在状态。正是从这种眼光出发,波里比阿在判定何为恰当的民主政治形态时,注意的是“其传统及习惯是去崇拜神明、照料双亲、尊敬长者、遵守法律”以及“确保大多数人的意志能被普遍接受”⑧(古希腊)波利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M].翁嘉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96.。而在普鲁塔克那里,政治书写的“科学”品质同样在于对人的整体存在秩序的理解,《道德论集》中所涉及的内容广泛,有道德、政治、宗教、哲学、文艺等诸多方面,然而其中政治具有突出的地位①G.J.D Aalders H.Wzn.Plutarch's Political Thought[M].Amsterdam:North-Holl and Publishing Company,1982:5.。与他所批驳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不同,普鲁塔克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政治,认为逍遥遁世的生活使幸福成为不可能,“因为生命本身……都是神明为了他被人知晓而给他的礼物”②(古希腊)普鲁塔克.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M].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0.,能够带来荣誉和伟大的公开的行动是值得欲求的生活方式。《道德论集》被认为是《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珍贵无比的前奏”,从其中的观点出发,我们知道普鲁塔克所“考虑的不是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的生平,而是人们的全部生涯”③(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M].陆永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而这全部的生涯在《名人传》中显然是以“政治”的形式展现的。
相比史学写作,古罗马的法律实践同样基于对人的根本理解,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这样一本罗马法教科书的开篇便称:“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④(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M].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5.。无疑,“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包含了人所能涉及的最为广阔的面向;而作为罗马法总原则的“正义”⑤(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M].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5.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它内含着对于人本身以及人所处的关系世界的根本理解,以之为核心而在国家中所作出的整体性法律安排,也就是共同体意义上的政治安排。罗马法的内容看似琐碎,但正如现代德国法学家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所言,罗马法学家“有着把关注点从当时的日常问题转向整体的勇气,而且在思考特定情势之狭小状况的时候,他们也把其思想的焦点转向了整个法律的一般性原则,亦即实现生活中的正义”⑥转引自(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7.。在罗马法学家中,最具有政治哲学思维能力的毫无疑问是西塞罗。他承袭了古希腊以降的政治科学传统,“对‘人类整体社会’与由此产生的义务、对社会与诸神之间的关系、对城邦这样的诸多小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指导”⑦(法)菲利普·内莫.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M].张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33.。在西塞罗的眼中,政治具有核心的地位,“那些可以使我们对国家有用的技艺的知识……是智慧的最高贵的功用,是美德的最高义务,而且也是拥有美德的最好证明”⑧(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M].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2.。美德关涉灵魂,它被西塞罗纳入到了政治的视野中。虽然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这是带有鲜明的德性政治观的特点,但也更加体现了西塞罗对于整全的人性以及对于人的根本存在状态的关注。
斯宾格勒(Spengler)曾在《西方的没落》中指出,“一直以来有待我们去发现的是,在世界图像中存在着何种活生生的相互依存关系(与无机的、自然律的相互依存关系全然不同),从整体的人而不仅仅是(如康德所认为的)从人的认知部分辐射出来的是什么”⑨(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 卷)[M].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48.。古典政治科学正是在“活生生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审视人的生存秩序的,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则承载着这些相互依存的关系。国家建立在法律之上,即使是像柏拉图这样期待哲人王统治(ruleofphilosopherking)的思想家,到晚年也转向了务实的法律之治。制定法律是立法者的任务,但这也只是立法者奠立和维续政治秩序的体现而已①(德)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M].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70-71.。在古典政治思想传统中,立法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与之相应的立法者科学可谓是政治科学的首要议题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94.。
二、立法者科学:古典政治科学的首要议题
在古典思想中,政治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人类事务的认识和安排是政治“科学”的内容,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角色是立法者。古典作品中多有对立法者(可以是君主、贵族或人民)进行教育的知识——比如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古典思想家可谓是“立法者之师”③(德)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M].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71.,他们从立法者如何产生和如何行动等视角来进行对话或书写。古典传统中的“立法者”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订立法律者”,更是政体的奠基者、风俗的改进者、法律/政策的制定和调节者、国家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者。不过,这些活动大抵以立法作为途径或目的,所以法律仍是关键。从根本上说,“立法者”是那些深刻影响乃至决定政治共同体整体状态的行动者,他(们)可能是最初的奠基者,也可能是后来的政治家,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集团,但他(们)始终是以权威领导使政治秩序得以奠立和维续之人。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例,苏格拉底是以立法者自居并围绕“如何建立理想的城邦”来进行对话的,而在这个理想城邦中哲人王是统治者,他(们)以强迫的方式被培育而成(即实现了灵魂的转向),通过制定习俗和法律来管理城邦,使之繁荣昌盛,给民众带来最大的福利。此间,无论是创建理想城邦的苏格拉底,还是统治城邦的哲人王,都是广义上的“立法者”。与之对应,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二卷的最后谈及立法者时说道,“这些实际立法家有些只为某一城邦拟订法典,另一些则既订法典,又兼定政制;例如莱克古士和梭伦就都完成了两项大业”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03.。而除了立法者在其发挥作用方面的区别(即创建城邦抑或维持城邦)之外,在立法方式上也能够辨别出两种模式。波利比阿曾将莱克古士和罗马人并立,他指出,“莱克格斯(即莱克古士)凭借他理性的能力,可以预见事件自然发展的方向以及使它们何以如此的因素,于是得以构建他的宪法,而无需去学习不幸遭遇所带来的教训。另一方面,罗马人虽然就其政府形态也得到相同的结果,但并非以抽象理性而得到结果,反而是从许多斗争以及困难中所习得之经验及教训而来。最后,借助从灾祸中所学习到的经验,他们经常选择较好的路径,他们与莱克格斯(即莱克古士)一样到达相同之终点,亦即所有现存之政体中最优良的”⑤(古希腊)波利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M].翁嘉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03.。
而无论是理性的构建还是渐进的改良,“立法”所突出的都是人(不论是个人还是集团)的意志与行动在实现秩序过程中的作用,而“立法者科学”正是一套关于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奠立与维系的“科学”。它不否认某些立法者具有超凡的能量,也不排除某些立法者本身可能资质平凡⑥(英)N.G.L 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M].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036.。但肯定“立法者”都拥有特别的政治权威,通过以立法为核心的行动来确立、维持或改变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存在条件。立法者科学就是将立法者行动的诸多方面包括条件、方式、目的、内容等,纳入到论述视角中的一套知识体系。
立法者科学是政治科学的首要议题,因为在古典时,国家是政治的中心(甚至全部),“就职业的品德来看,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行当比建立新国家或维护那些现存国家更接近于诸神的庄严职责了”①(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M].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8.。“建立新国家”或“维护现存国家”都是实践,所以古典的立法者科学拥有一种实践的特质,它指向政治共同体的秩序安排。这一安排体现人的意志与能力,彰显着一种有为的、行动的政治取向。当然,最有力量的政治行动是“立法”。
柏拉图对立法的看重是毋庸置疑的,这从他晚年专门写作《法篇》便可见得②刘玮.公益与私利: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62.。在其中,来自雅典的异乡者与克里特人、斯巴达人一起探讨立法的基本原则及立法者的工作应该如何展开。法律被凸显到一个极高的位置,正如睿智的雅典人所指出的,“法律一旦被滥用或废除,共同体的毁灭也就不远了;但若法律支配着权力,权力成为法律驯服的女仆,那么人类的拯救和上苍对社会的赐福也就到来了”③(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 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75.。而立法则不只是偶然性和无限多样的环境起作用的结果,就像航海者在暴风雨中需要行船的技艺那样,共同体必须出现一位真正的立法者,“除了他自己的技艺外,他不需要进一步依赖任何东西”④(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 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7.。立法的起因在于人和人类立法者,它旨在使城邦获得完整的善,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实际上早在《理想国》中,那位直接看到了太阳本身的哲学家,在重新回到洞穴从而成为立法者之后,他“关心和卫护其他公民”的活动便是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实践活动。
柏拉图曾说,“立法或建立一个社会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顶峰”⑤(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 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6.。关于善的理念的知识只有通过政治实践的方式才能在城邦中普及,从而促使城邦公民实现幸福。亚里士多德指出,“实践就是幸福,义人和执礼的人所以能够实现其善德,主要就在于他们的行为”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53.。就个人而言,“有为”,以思想作为行为的先导,并且抓紧时间积极行动,才能获致最优良的生活;而就城邦集体而言,只有立法者“有为”,才能使全邦人民获得最优良的生活。正是由此出发,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一个完美城邦所必须具有的配备,因为“有如其他的制造家那样,政治家和立法家也得有他们所需要的原料,而且这些原料也应该符合他们的要求”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56.。在亚氏看来,原料主要是人民(包括数量和品质),次要的则是人民所居住的土地(也要考虑量和质)。不过,“质料是一种相对的概念,相应于一种形式而有一种质料”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9.。对于政治共同体来说,形式便意味着政体。在《政治学》中,“务实”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绝对至善的政体和适于特定城邦的良好政体,而“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77.。
立法者行动的核心在于政体建设,因为“法律的起因是政制”⑩(德)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M].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25.。在波利比阿看来,“对于所有政治局势,造成成功或失败的主要因素是这个国家宪政的形式。正是来自这一源头,就如水来自水源一样,所有行动的设计及计划不仅由之而起,也在其中完成”①(古希腊)波利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M].翁嘉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94-395.。立法者的政体建设行动是这“所有行动”中最关键的,它关涉科学和艺术,前者意指无从避免的因果关系和以共同体为对象的整全考虑,后者则意味着“明智地运用可使用的手段使各种事务达致一种颇具价值且可欲的结果”②(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50 页。。与此同时,因为政体决定着统治权的归属,所以它的确立过程便是立法者疏解政治共同体中的冲突和斗争的过程。亚里士多德曾通过《雅典政制》展示了立法者梭伦在解决城邦冲突过程中的枢纽作用:“他以仲裁者身份,代表每一方以与对方斗争,而后劝告他们共同停止他们之间方兴未艾的纷扰。”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而具体的状况,亚氏则通过引用梭伦的诗句予以说明:“我使这样的事情普遍流行,调整公理和强权,协和共处,这样我应允的事都已一一完成。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如果是别的人代表我执着鞭策,他,这不智与贪婪,又那能抑制人民!因为如果我有时让敌对的两党之一得意,而有时又令另党欢欣,这个城市都会有许多人遭受损失。所以我卫护两方,进退维谷,有如孤狼在一群猎狗之中!”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16.
克服共同体中不同群体的力量与利益分化为基础的对抗和平衡,是古典“政治”的重要内容。正是以此为内容的“政治”过程,使雅典作为政治共同体从根本上免于专制,得享法治。而从亚里士多德对梭伦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法治的实现需要立法者的推动,并且法治的确立表明城邦公民开始拥有一套进行政治权利分配的体系,这也就体现了立法者对于政体的抉择——虽然他(们)并不一定对此有所意识⑤张新刚.友爱共同体:古希腊政治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41.。在梭伦立法之时,“雅典的领土上有多少不同,全邦就分成多少派别。山区的人主张采行极端民主制;平原地区的人主张采行极端的寡头制;海滨的人组成了第三派,主张采行一种中间性的混合制,……而且在那个时候,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⑥(古希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M].陆永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78.。梭伦拒绝了许多人让他实行僭主政治的建议,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调解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为雅典民主政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04-105.。
施特劳斯曾说,“古典政治哲学的根本就在于:共同体内部的不同集团为权力而拼搏,这种不同集团间的论争就是政治生活的特征”⑧(德)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M].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77.。而“共同体内部的冲突,即便不是源于最基本的政治争论,起码也与之有关:关于何种类型的人应成为共同体统治者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妥善解决,看来是优秀立法的基础”⑨(德)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M].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71-72.。这寥寥数语便道出了古典传统中作为论争的“政治”与立法、政体之间的关系。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论争的解决不只是共同体中普通立法的基础,更是伴随着根本的立法而实现的,而根本的立法则意味着政治共同体基本秩序(也即是政体)的确立。正是由此着眼,我们看到“立法者”在古典政治生活中的位置,以及以立法者为对象的“科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古典政治科学的首要议题。
三、古典立法者科学的继承
古典时代的立法者科学致力于政治共同体的整体幸福,而幸福以德性为内核,意味着走向自然所规定的完善。这体现了德性政治观的基本取向:立法者所进行的政体建设,在最终的意义上所指向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人的培育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2-33.。
在马基雅维里那里,这样一种以自然目的论为基础的德性政治观受到了决定性地颠覆:道德和政治实现了分离。而除了马基雅维里外,其他继承了传统“立法者”话语的早期现代思想家们,比如孟德斯鸠②(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69.、卢梭、亚当·斯密等人,也都延续了这种道德与政治分离的做法。但需要明确的是,所谓“分离”指的是政治不再以道德为目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把道德纳入政治行动的考量范围。也即是说,政治并非一个被独立区分出来的领域,而是依然保有古典共同体的视野,不论是道德,还是宗教、文化、经济等,都事关政治秩序的确立和维持。当然,这些思想家在继承了立法者科学的古典传统之时,都融入了自己时代所存在的政治问题的思考,但这并不妨碍将他们归入同一谱系之中加以考察。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欣赏那些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创立新秩序的“新君主”们,例如摩西、居鲁士、罗慕路斯、提修斯等。在《论李维》中,他同样指出,“共和国或王国的创建者值得赞美”,而且他认为这些人应该大权独揽,甚至不惜采取暴力等非常手段③(意)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罗马史[M].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8-39.。马基雅维里有关“立法者”的论述是政治现实主义式的,像自然法和自然正义这样的理念并不在他的“立法者科学”中占据任何位置④(美)哈维·曼斯菲尔德.驯化君主[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147.。但是,马基雅维里的“立法者”并未丧失整全的视野,所谓的“建制”“奠基”“立法”,都是在试图为共同体确立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说“所有受到赞美的人当中,最值得赞美的是宗教领袖。其次是(笔者注:以法律和制度)缔造共和国或王国的那些人”⑤(意)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罗马史[M].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1.,因为宗教塑造人们的道德和精神,规定人们的存在状态,是共同体政治秩序的重要构成部分。与罗慕路斯相比,马基雅维里似乎更推崇驽马这位立法者,后者“发觉罗马人民性凶残,想用和平的技巧培养公民服从的精神,于是取宗教为维护文明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手段”⑥(意)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罗马史[M].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7.。波考克曾评述说,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先知的地位也许高于立法者,因为他的成果无论如何是最持久的,但先知的目标是要成为立法者,提供一种能够作为公民生活基础的宗教”⑦(美)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M].冯克利,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204.。立法者需要审慎地面对共同体中的质料(即人),通过法律、习俗、宗教等手段赋予质料以特定的形式(form),这和古典传统是一致的。
对卢梭而言,立法者也是“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⑧(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0.。但与马基雅维里不同,卢梭的立法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他们处在更加超脱的地位,“缔造了共和国,但绝不在共和国的组织之内”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1.。这个立法者“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能够“认识到人性的深处”②(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9.,他“规划全体的秩序”,“赋予公共事物以最好的可能形式”③(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9.。作为致力于复兴古典思想的作家,卢梭也是把政体的建设放在首要位置的。他说:“一个健全有力的体制乃是人们所必须追求的第一件事;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一个良好的政府所产生的活力,而不只是看到一个广阔的领土所提供的富源”④(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1-62.。不过,立法者的目光却不应仅盯着那些建构政体的法律,因为他的工作是要确立起政治的秩序,这要求人们能够心甘情愿地服从法律,也即“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所以宗教成了立法者的手段,通过“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⑤(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4.。与此同时,立法者要关注为之立法的人民的自身状况(在这一点上他举了柏拉图的例子),这包括人民的性情、政治体的幅员与人口、土地的质量及气候的影响,等等。在卢梭以立法者的姿态写就的《科西嘉制宪意见书》和《论波兰政体》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对共同体整全状况的细致考量。毫无疑问,在立法者的问题上,卢梭以孟德斯鸠为榜样。他引用了《罗马盛衰原因论》中的话来强调立法者建制的突出重要性,而且他用《论法的精神》来支撑其“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并使它的立法只能适合自己”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8.这一主张。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立法者要致力于对第四种法律(即风尚、习俗和舆论)的塑造,这是政治秩序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就这一点来看,卢梭和孟德斯鸠有着显然的一致。甚至之前的马基雅维里也有如此观点,即“如同好习俗得要有法律加以维系,法律也得要有好习俗才能贯彻”⑦(意)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罗马史[M].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69.。在这些继承了古典立法者科学的思想家们看来,立法者要凭靠自己的智慧和行动来塑就根本的政治秩序,他(们)就不能囿于法律和制度,所有构成人们生活方式的存在物都应在其关照的范围内。
与马基雅维里和卢梭相比,亚当·斯密似乎与古典传统的距离更远,毕竟他一直以来被视为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开创者。然而,在这位颇具现代样貌的思想家那里,却出现了古典色彩的立法者的身影。只不过,在古典立法者的形象中,亚当·斯密有着自己的取舍。他欣赏梭伦那种“尽力去建立人们所能接受的最好的法律体系”的立法者⑧康子兴.社会的“立法者科学”——亚当·斯密政治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254-261.,而拒斥“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的立法者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1-302.。在亚当·斯密看来,立法者要“尽可能使自己的政治计划适应于人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偏见,如果不能树立正确的东西,就要致力于修正错误的东西”⑩(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2.。不能不说,斯密的立法者思想着实是温和而保守的,这与他的自然法理学特质相关。但即便温和,立法者也是在塑造政治秩序,只是在方式上要适应立法对象们的需求,从而在正义与现实环境之间实现平衡⑪See Ryan Patrick Hanley.Enlightened Nation Building:The“Science of the Legislator”in Adam Smith and Rousseau[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8(2):219-234.。通过立法者的形象来凸显人的行动之于其生存秩序的创造能力,并且将人的审慎、道德、偏见和激情等纳入秩序建构的整体视野,这与古典思想家关于立法者科学的主张离得并不远。
不同于以上所述及的思想家,美国的建国之父所展开的是一场“立法者科学”的实践。将一种全新的政体赋予新大陆上年轻的美利坚民族,这场立法实践创造了一个叫作“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秩序和美利坚民族共识进一步积累的基础。1787年制宪会议所做的既是改制也是建制,它所出台的联邦宪法应对的是“社会缺乏秩序这一根本问题”,而社会的失序表现为“信任的缺失、权威的瓦解、债台高筑、行为堕落及民风日下”①(美)戈登·S·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1776-1787[M].朱妍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437.。所以,仅有七条内容的简洁的联邦宪法,虽主要规定的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等机构和制度,但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方方面面都被统摄其中,新的秩序规定的是美利坚人新的生活方式。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三十八篇中,麦迪逊历数了古代希腊罗马的立法者,并将美国的制宪者们与之作比。虽然他也指出,和古人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智慧超常、人格出众”的公民手中不同,“在筹划和建立常规政府方案的古典模式基础上,美利坚作了进一步的改进”,采取了“一群公民相互切磋,体现更多智慧,更安全”的制宪会议的形式。但是二者之间所承担的任务实质上是相同的,即都是确立整全秩序的实验,所以都“容易引起风险和困难”②(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M].尹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244-246.。
相比之下,孟德斯鸠的“立法者”更为普通,他(们)不一定如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大权独揽”,也并非卢梭所要求的那样好似“神明”,亦或亚当·斯密眼中的“无偏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在孟氏看来,“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的”③(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46.,而且立法者所订立的法律可能是细微而繁琐的,比如禁止亲属间婚姻的法律、关于妇女继承遗产的法律、限制宗教团体的财富的法律,等等。在某些时候立法者甚至并不制定法律而是进行劝说(conseils)④(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55.。由此看来,孟德斯鸠对“立法者”的定位不限于“建国/创制”阶段,国家的维持同样有赖于立法者,而且维持的方式是多样的。之前有言,马基雅维里、卢梭、斯密等眼中的立法者与美国制宪者都是出现在政治共同体的重大关头,或者为政治秩序奠基,或者为共同体完成改制。而对孟德斯鸠来说,某些政治家或者像中国皇帝这样的专制君主也被看作立法者。但之所以把孟德斯鸠和前述思想家及美国的实践者一起归入立法者的古典传统,乃在于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并不局限在权力、制度、法律等层面,而是从对人的深层认识出发,关照整全秩序的建构或维持。虽然立法者的“光环”似乎不足(伟大的立法者除外),但孟德斯鸠是从共同体的存在秩序角度对他(们)予以审视和劝告、教导的。立法者的审慎和明智事关政体的走向,他(们)制定的法律与国家的自然状况和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故而要在构成“法的精神”的复杂关系中考量法律的影响,由此才能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秩序,为共同体中的人们提供宽和的生活方式。
四、结语
对古典政治科学传统(立法者科学属于这一传统的核心部分)的回望,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现代政治传统,从而更清晰地思考笼罩在现代性中的西方乃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阿兰·布鲁姆(AllanBloom)曾在《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指出,“政治的消失是现代思想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并对我们的政治实践有很大影响。政治逐渐退化为亚政治(经济)或所谓的高于政治(文化),这两者都在逃避整体均衡的技艺,即政治家的精明”①(美)阿兰·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44.。布鲁姆所说的“政治家”,承当的正是立法者的角色,因为他所举的例子便是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所设想的立法者②(美)阿兰·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45-146.。立法者是具有高度(甚至最高)权威的政治主体,拥有审慎(prudence)的德性③(法)耶夫·西蒙.权威的性质与功能[M].吴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6.。古典“立法者”与现代的“立法者”不同,前者更具有主动性、根本性、创造性,后者则更类似于制定法律的“官僚”。面对当今时代的问题,我们更需要的是主动性、创造性的立法者,他(们)的合法性虽然是源自人民的——这与古典传统有不同,但却能洞察并且避免人民所固有的激情、短视和偏见,以理性和明智展开构建、维系和改革根本政治秩序的行动。
当今世界,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方兴未艾,作为其表征的右翼民粹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问题,都在不断对原有的生活秩序构成着挑战,消耗看社会的凝聚力。我们要致力于建立真正“政治的”共同体,以应对根本共识的危机,就需要立法者通过考量政治共同体中出现的变化(比如政治力量分布的变化,以及风尚和习俗的变化等),围绕着法律(特别是确立政治权力格局的宪法)的调整,重新使共同体的成员们获致共识,使“社会契约”得以修复。在此特殊时刻,柏拉图的立法者“通过调解重建友谊与和睦,使公民们把注意力投向外部的敌人”④(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 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70.的话,很值得我们反复回味。法治是通过不同群体/集团间力量和利益的分化、对立和妥协平衡来实现的,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立法者的“调解”过程。而惟有以此为基础,共同体的持久的“友谊与和睦”才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