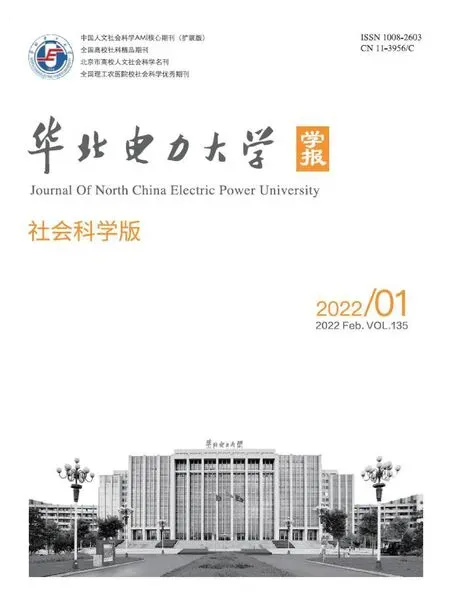汉语二语学习者个体量词加工及教学研究
牟 蕾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语言教学中心,北京 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量词是汉藏语系特有的语言现象,现代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量词,这也是留学生学习的难点之一。量词与名词的组合关系复杂,同一个量词可以与不同的名词组合,同一个名词也可以与不同的量词来搭配,这些都造成了学习者的困扰。个体量词是汉语名量词的一个子类,是表示人和事物数量的单位词,如“颗”、“粒”、“张”、“块”、“片”、“枚”等[1],个体量词是汉语学习者较早接触的一类量词,而且其习得模式同其他量词有所差异,具有理据性的同时也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
鉴于教学中的这些情况,本研究旨在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汉语个体量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有哪些?这些成果能否推及二语学习者个体量词习得?
2. 汉语二语者的个体量词加工和习得过程是怎样的?
3. 根据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教学实践,汉语学习者初级阶段学习的个体量词可以分为哪几类,针对不同类别的个体量词采用哪些教学方法?
二、汉语个体量词研究回顾
英语中“a book”,汉语要说“一本书”,从信息的传递来看,两者没有差异,量词“本”好似冗余信息,那么现代汉语中量词有何存在意义?关于量词的功能性作用,以及名量词的组合关系,学界早期有“三论”,分别为量词限制论(量词用于对名词加以限定)、名词决定论(量词的选用由名词决定)、量词辅助论(量词辅助名词特征的表达),但更为主导的观点是名词和量词的组合是约定俗成的。[2]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认知理论和语义学理论的引入,人们开始探寻名词和量词组合的理据性意义。邵敬敏提出“双向选择网络”,认为名词在个体量词和个体名词组合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能否组合还取决于个体量词和个体名词的语义选择,并且是双向选择。[3]Tai & Wang、Tai & Chao认为表形状的个体量词的认知基础在于物体形状的维度[4][5],石毓智进一步指出形状量词的首要认知基础是维度之间的比例,而非维度。[6]这些研究理论也对量词习得研究有很多启示。
目前,对汉语个体量词习得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外汉语教学领域针对量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使用状况的描写,通过语料收集、描写、分析,展现留学生汉语量词学习存在的偏误、使用的学习策略等。[7][8][9]但这些研究多流于静态的描述,而缺少对加工过程的探究。
三、汉语二语学习者个体量词加工模式
前文回顾了学界关于量词及名量词组合的理论及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母语者的量词加工,而对于汉语二语学习者来说,汉语作为一门外语,与学习者母语的文化、思维、认知特点等都有一定的差异,二语学习者学习个体量词的过程是否也同汉语母语者一样?他们在脑海中构建的个体量词模式和母语者的是否相同?下面根据量词加工理论,总结出汉语二语学习者量词加工的三种模式——“双系统加工”、“名词主导的双向选择组合加工”、“语块加工”,结合教学实际提出更为贴合留学生学习经验的“特征附着加工模式”。
(1) 双系统加工
张积家等人根据对母语者量词通达的研究,认为个体量词和名词是“双系统”[10],即在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词典中,“量词系统”和“名词系统”是单独存在的,量词和名词的组合相当复杂,一个量词可以对应多个名词,一个名词也可用多个量词来修饰,而两者联系的紧密程度取决于语义的重合度和使用的频率。根据这一理论,我们设想在汉语二语者的心理词典中,也是存在两个系统的,个体名词系统是概念系统,按照分类学的语义特征来组织,个体量词系统也按照语义特征来组织,但这些特征是事物的形象特征、主体的情感特征和交际的语体特征。[11]
例如对量词“张”的加工,除了基本的形、音、义之外,其外围线索按照语义特征编码,“张”与扁平事物或具有扁平平面事物相联系,包括“纸”、“名片”、“照片”、“床”、“沙发”等等,这些概念在分类学上并不是同一范畴,但是在特征层面有相似性。在名词系统中,“纸”、“名片”、“照片”按照语义联系在一起,“床”、“沙发”也是处于同一范畴内。量词系统和名词系统进行语义特征的匹配,匹配成功表现为可组合,而组合出现的频率越高,学习者心理词典中的联结就越牢靠,也就越容易提取。
按照这一加工模式,语言使用者已经具有丰富的个体量词和个体名词知识,并且能够依照量词对概念进行重新分类,宗守云曾指出量词在语义上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各种各样不同的名词归为一类[12],也就是说量词具有范畴化的作用,量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的认知和思维。但是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他们学习的量词知识有限,只能通过有限的量词知识做出归纳,这是借助普遍的认知能力,而不能反映民族和文化背景,因此他们做出的范畴划分会不同于汉语个体量词所划分的语义范畴。从这点来看,汉语学习者难以通过双系统进行名词和量词组合的加工。
(2) 名词主导的双向选择组合加工
针对个体量词和个体名词的组合关系,邵敬敏提出了“双向选择组合网络”[3]。该理论强调名词的主导和制约地位,即名词的语义决定了个体量词的选择。而且这一选择过程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为组合的可能性,名词的语义主导哪些量词可供选择,例如,“水”决定了个体量词只能是“滴”、“点”、“汪”等量词。第二个层次为组合的现实性,这是个体量词所决定的。例如,现实表明水很少,与“水”有关的个体量词中只有“滴”和“点”是合适的。
按照这一理论,学习者首先要习得名词,对名词的加工除形、音、义外,同时也需要习得可组合的量词,如对“水”的加工,不仅对其字形、读音、字义、附带的感觉等进行编码,还要对其可组合的量词“滴”、“点”、“汪”等依次习得,最终形成“水”的量词网络。然后在具体提取和表达的阶段,会根据表达的实际需求和语境做出选择。
从这一推论能够看到语境所起到的作用,学习者在进行二语表达时,对量词的选择要根据语境和实际表达的意念。因此学习者在加工时不仅要进行语义加工,还要对其包含的功能意义进行加工,例如量词“位”是称量人的量词,其附带意义是尊敬的表达,我们可以说“一个老头儿”,但很少说“一位老头儿”,因为要与“老头儿”的色彩意义相符。但是这一理论与实际不符之处在于,学习者量词习得过程是渐进的,在最初阶段,他们无法建立起“水”的量词系统,他们不知道“水”可以有如此多的表达方式,因此这一模式或许可以适用于高级阶段的学习者,但对于大多数汉语学习者来说是难以适应的。
(3) 语块加工
以上两种推论都是依照汉语母语者对语言的理解来解读的,母语者本身已经建立起丰富的个体量词和名词搭配范例,在既有的丰富的量词和名词范围内进行解释,并非解析从其接触语言之初到语言成熟的阶段量词和名词的习得及组合关系的建立。若从儿童母语习得的视角出发,儿童语言习得经历了初始阶段、原型阶段、成熟阶段。[13]儿童在最初的阶段并没有意识到量词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整个短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将其视为一个语块,随着其语言发展,逐渐知道量词的功能性,但用来指一些原型物体,在成熟阶段,他们能够将量词延伸到原型物体之外的一般物体。
若以此理论推论到二语学习者,二语学习者在最初阶段也可能将名量短语以整体的形式进行加工,例如“一张纸”、“一座桥”,因为在这个阶段,所学的量词数量有限,可以视为语块,进行整体加工记忆,并不对其进行深层的特征归类和加工,随着示例增多,特征得以突出,从而进行归纳,得出量词的特征概念。但是这一加工理论与二语学习者实际不符之处在于,一般接受课堂学习的二语学习者都是先建立量词的语法和功能概念,他们会同其母语进行对比,知道在数词和名词之间存在量词成分,其掌握的量词数量有限,会出现过度泛化的情况。而不是在最初阶段就完全依赖语块加工。
(4) 特征附着加工
以上三种推论是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对二语学习者个体量词加工过程进行预测,其中有合理之处,但也有与事实相左之处。鉴于此,并根据教学实际,我们认为汉语学习者个体量词的习得过程是名词特征附着在个体量词之上的过程。具体过程可见图1。

图1 汉语二语学习者量词特征附着加工过程图
量词是汉语学习者在初级阶段就开始学习的一类词,但其习得顺序要晚于名词。也就是说学习者先学习某一名词,然后接触到量词,在课堂学习中会了解到量词作为汉语的特色有别于其母语。但是“条”、“本”、“张”这些量词对学习者来说并无实际语义,仅仅是充当着“河”、“书”、“纸”的限定词,学习者只知道其作为量词存在,对应不同的名词实物。
随着个体量词和名词组合示例的增多,学习者逐渐建立起量词一对多的概念,即同一个量词可以对应不同的名词,这也是教材和教学中常见的做法。学习者能够对相同量词组合的名词特征进行归纳、整合,得到该量词所指称事物的特征集合,如一张“纸”、“照片”、“名片”,这时归纳出的特征为“薄而平整的物体”,对于学习者来说,这是量词“张”修饰事物的原型特征。
下一步学习者就会利用归纳出的特征尝试进行验证,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名词为“报纸”、“车票”,学习者可以利用“张”来指称,学习者归纳出的特征得到验证;第二种名词为“布”,符合“薄而平整”的特征,但却极少用“张”,这时可以进行自我解释,并对特征进行修正,“布”的特征并非是平整,因此不能用“张”来称量;第三种名词为“桌子”、“板凳”,这些事物不符合“薄”的特征,为什么也可用“张”,这时会进行进一步修正,具有一个扁平的平面也可称之“张”。而“板凳”一词,也可称“一条板凳”,这时“板凳”一个名词可以对应多个量词,名词一对多的概念也就建立起来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不断经历、不断修正、不断完善。
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之后,量词实际上也被赋予了所指称事物的特征,例如,“张”与扁平的概念相对应,“块”与三维的方正概念相对应。所对应的名词中,有些是原型名词,有些处于边缘地位,这就与前文所说的量词和名词的语义匹配相类似,原型名词所具有的概念和认知意义更为典型,也就不容易被替换,而边缘性名词的量词则容易被他者替换。[14]量词所具有的信息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学习者所理解的,而是在名词和量词的组合过程中,名词语义特征信息附着在量词之上的,随着深入的学习而不断加深的,这也可以解释汉语二语学习者量词通达既能直接通达,也可通过名词间接通达的原因。
有些量词本身具有实义,只是在历时的演变过程中充当了量词,随后的学习过程中,当学习者再次习得含有该量词的其他词汇时,量词所具有的概念就被激活,有利于学习者对含有该量词词汇的掌握。例如“糖块”、“面条”。于是该量词的特征概念在学习含有该词的词汇过程中被强化,更有利于其推演到其他量词指称物。
四、汉语个体量词的分类及教学
上一节对汉语二语学习者个体量词习得过程进行了解读,但是在教学中要如何帮助学习者建立起量词模式,使其有效地提取相应信息,将是本节要讨论的问题。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模式是大脑神经机制对外界刺激信息的一种摄入反应。它把不同感觉神经传人的信息综合起来,建成酷似于外界刺激物的模式,这就是编码、贮存的过程。[15]而一个完整而有效的语言模式,是由核质(模式的核心)+外围线索所构成。所谓的“核质”,是由语言信息的主要线索编码而成。所谓的“完整模式”,是由环绕核质的外围线索再编码而成。[15]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如何帮助学习者建立量词的模式?
接受课堂教学的汉语学习者,往往是遵循教材安排的顺序来学习,在此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础汉语40课》[16]为例。该教材中出现的个体量词包括“个、本、块、位、条、座、张、把、支、件、辆、部、家、所、封、片、幅、根、栋、棵、只、匹、顿、头、门、颗、顶、枝”。这些量词对名词分类的能力是不同的,根据Gao& Malt的研究[17],他们将个体量词分为三类:
(1)定义明确(Well-defined)的量词。量词的语义特征对其后的名词做出明确的范畴定义。例如,“棵”后面的名词只能是绿色植物,“本”后面名词也只能是外型上具有“本子”形状的物体。这些量词的语义特征可以从与之搭配的名词的类别特征中推论出来,讲话者对“量词-名词”之间搭配的知识非常清晰。
(2)原型(Prototype)量词。在名词和量词的组合过程中,常常有一类典型的、具体的名词与量词搭配,这类名词与量词的语义特征总能联系起来,更为典型,而其他的名词虽在语义上有联系,但并不十分典型。
(3)任意(Arbitrary)分类量词。这种量词在语义特征上没有清晰的定义特征,也无相应的类别原型。量词没有提供清晰的分类特征,量词与名词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需要通过记忆来学习。[11]
根据这一分类,我们将《基础汉语40课》中的个体量词做如下分类:
(1)定义明确的量词:本、位、辆、封、棵、枝、头
(2)原型量词:块、条、座、张、把、支、家、所、片、幅、根、栋、只、颗、顶
(3)任意分类量词:件、部、门、匹、顿
定义明确的量词和名词组合的理据性比较充分。(参见表1)首先体现在意义的对应性,除了上文提到的“本”和“棵”之外,“位”原指一个人站立时的专属空间,由此引申为礼貌性地称量人的量词,“辆”对应的是各种车辆,“封”是“信封”的形状,转而称量“书信”类的物体,“枝”是指植物枝干长出的东西,如“一枝花”。“头”则是指称大型的动物、牲畜。这些量词都从其历时的演变原初而来的。第二,从该量词作为实词的角度考量,这些词往往能够组成其他名词,这些名词也会随着学习者学习深入而接触到,例如,“本”可组成“课本”、“书本”、“本子”等,通过这些名词的意义,同时加深了量词的概念义,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第三,从汉字的理据来说,多数定义明确的量词其汉字本身就能体现出其部分含义。对于留学生来说,汉字和语音都需要学习,汉字的意义、量词的意义、组成实词的意义三者结合起来,对于学习者来说外围线索更为丰富,便于提取。在教学中有这样的情况,提问学生:“老师的量词是什么?”同时提供线索:“老师是一个人,站在教室里”,线索是对量词“位”的汉字解读,学习者能够更迅速地加以提取。

表1 定义明确类量词的理据意义
原型类量词所组合的名词可分为原型名词和非原型名词,但是依据上一节的习得过程,对于学习者来说,他们心理词典中的原型也许不同于母语者认为的原型。这一方面与教学干预有关,教学从最初阶段,提供有限的、和量词组合的名词,学习者会依据这些有限的名词归纳出语义特征,而随着其他组合实例的增多,他们对其归纳出的语义特征进行修正,他们提取的特征也许会和母语者所认为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学习者心中的原型名词是动态变化的,因为随着学习词汇的增多,他们的心中的原型可能会有改变。例如,在教材《基础汉语40课》中,量词“条”最早出现是和“河”组合,“河”的形状就是原型,几课后又出现“一条裤子”、“一条路”,才会对其原型意义加以修正。
教学中首先要根据各民族普遍的认知思维来区分原型,而不能依照母语者的语感来判断。其次,要利用学习者体验性,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正是体验性假说,通过对客观事物和世界的体验性感知,学习者才能更好地对语言进行加工。例如,在教材中量词“把”出现时是“一把椅子”,根据“把”的含义,“把”同“抓、握有关”,可引申为有把儿的东西,学习者则难以理解“椅子”和“把”的关系。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将量词“把”对应的简单的“原型名词”提供给学习者,如“勺子”、“刀”,这些西餐常用的餐具,学习者能够体验到手握把手的感觉。然后,再扩展到“椅子”,课堂上教师手扶椅子、或手握椅背提起椅子,这些动作会使学习者自然领悟到“一把椅子”的组合理据。
五、结语
本研究从汉语个体量词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出发,总结出二语汉语学习者的三种量词加工模式,分别是双系统加工、名词主导的双向选择组合加工、语块加工,而这三种模式都是基于母语者个体量词习得和量词知识推演的,汉语学习者的量词知识是有限的,而且其思维模式不同于母语者的思维,这三种加工模式与实际学习过程有不符之处。根据汉语学习者渐进的学习特点,我们提出了“特征附着”的模式,即汉语学习者首先建立量词的功能概念,随着名量组合的范例增多,学习者对名词特征进行提取,并进一步将这些特征附着在量词之上,并在语言实践中加以验证,最终形成其心理词典中的个体量词模式。
学习者自身的加工处理固然关键,但是汉语学习者是在教学的干预中建构自己的知识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不同的个体量词特点帮助学习者构建量词模式。量词可以分为定义明确的量词、原型量词、任意分类量词。定义明确的量词理据性充分,教学中充分利用其理据意义,帮助学习者建立量词的外围线索。原型量词对应的名词有原型名词和非原型名词,教师要根据学习者的思维和认知来建立原型,而非依据母语者的原型,任意性量词和名词组合并无充分的理据意义,则要依靠示例来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