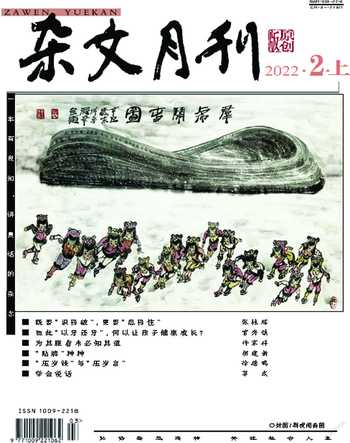编纂《四库全书》伴随着文字狱
沈栖
清代乾隆帝從三十七年(1772)二月,决定汇聚天下群书后按经、史、子、集编目,并定名为《四库全书》。历时12年,于四十九年(1784)基本告成。其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凡7.7亿字。它堪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我们在充分肯定《四库全书》系统、全面总结中国古典文化,形成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的同时,还应当从另一个视角看到它在编纂过程中,伴随着惊世骇人的文字狱。
乾隆帝下诏搜辑古今群书,说是旨在“稽古右文,聿资治理,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但各省督抚奉谕后心存迷惑,观望不前,上交书单寥寥无几。乾隆帝再次下谕限定半年为期,“速为妥办”,除江浙一带略见成效外,其余省份依然敷衍塞责。三十九年八月初五的一道谕旨,乾隆帝直接挑明了此事的目的:“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并宣布: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一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乾隆帝“寓禁于征”,在搜辑古今群书的华丽招幡下查缴禁书且销毁的祸心昭然若揭。
在乾隆帝亲自督催课责下,各省督抚才闻风而动,大批古今群书汇集京城。伴随着搜求、整理遗籍,查办禁书、严惩“笔墨妄议者”的文字狱拉开了帷幕。60余年的乾隆朝发生了142起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就占五成。据《清代文字狱档》载:从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短短六年间,竟发生了49起文字狱。限于篇幅,兹仅略述两案:王锡侯的《字贯》案和徐述夔的《一柱楼诗》案。
先说说《字贯》案。王锡侯系江西新昌乡举,《字贯》刊行于乾隆四十年。因他陷入宗族纠纷,与人结怨而被告:“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与叛逆无异。”乾隆帝下谕称:《字贯》凡例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伸国法而大快人心”。《一柱楼诗》作者徐述夔早已故去,事发于其孙徐食田因置地与蔡某纠缠,遂成讦讼。蔡某呈诉状中摘出《一柱楼诗》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判为“悖逆之词”。乾隆帝很快得知此案,望文生义地斥责:“借朝夕之朝,代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继而勃然大怒:“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
乾隆帝口口声声称“毁书而不罪及其人”,貌似怀柔,其实并非如此。因文字贾祸的文字狱,不止是全然销毁禁书,而且罗织罪名,株连家族,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如大学士九卿会议王锡侯比照大逆律拟极刑,奉旨从宽斩决,其子孙7人斩监候,秋后处决;而《一柱楼诗》案,除了徐述夔剖棺尸身被凌迟,抛撒郊野,其孙徐食田、徐食书等家属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编纂《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始终步步推进查办、销毁禁书,屡有以笔墨失检、文章微疵而获罪的文字狱。据统计:《四库全书》在编纂全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万部,销毁书版8万块,数量惊人!诚如著名清史学家王锺翰所说:“《四库全书》的编纂和禁毁,都是严格按照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的意旨进行的,既不是自由的学术活动,也不是文化历史长河自然演进的结晶。”这是因为乾隆帝意识到:倘要从根本上解决威胁清朝统治的反满思想,亟需拔本塞源,彻底查办并全然销毁一切蕴含反满思想的书籍。因此,查办、销毁禁书,严惩“笔墨妄议者”的这一政治运动便以编纂《四库全书》的堂皇粉饰而强劲推向全国,收到了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所不具备的政治功效。黄遵宪云:“其文字之祸,诽谤之禁,穷古所未有。由是葸懦成风,以明哲保身为要,以无事自扰为戒,浸淫于民心者至深。”(《黄遵宪致梁启超书》)龚自珍所痛斥的“万马齐喑”局面即源于此。
光大文化与毁灭文化的行为集于一身,看似悖谬,实为同质:宣扬道统,使顺从者尽为笼络;文化专制,对不顺从者严加惩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显然,今人从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盛举中可以清晰地窥见其封建专制主义的斑斑劣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