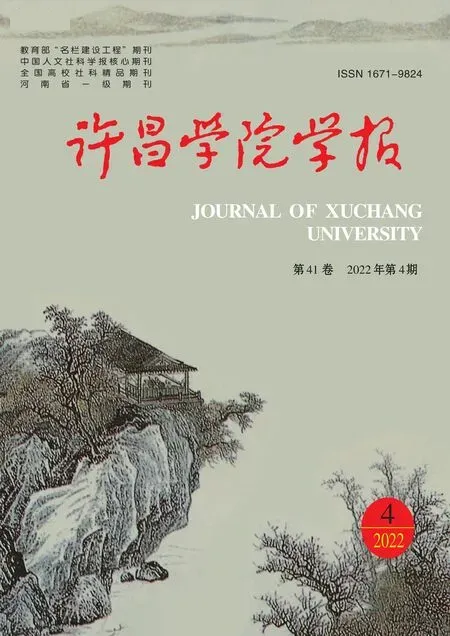论《元亨释书》的成书背景与撰述动机
胡 照 汀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元亨释书》,成书于1322年,为日本五山文学前期的代表禅僧虎关师炼所撰。该书仿中国纪传体史书编撰体例,设“传”“表”“志”以及“赞论”,是日本首部汉文纪传体佛教史籍。国内外学者多从佛教史与思想史方面考察《元亨释书》十科僧传及其十科分类的作用;或从历史层面对个别高僧生平事迹做考证;或将僧传作为反映僧侣思想与生平的历史文本;或从佛教发展史的角度,将《元亨释书》僧传作为佛教史料,借以考证佛教史的发展特征。关于《元亨释书》成书的外缘内因,学界至今尚无考论。故本文从成书背景(外缘)及撰述动机(内因)两个方面考察这一问题,以期为更深入的《元亨释书》研究奠定基础。
一、《元亨释书》的成书背景
(一)镰仓末期政局与公武崇禅
承久三年(1221),镰仓幕府攻陷京都,屠杀倒幕大臣,并将后鸟羽、土御门及顺德三代天皇流放边地,是为后世所称“承久之变”。自此之后,天皇的继承权被牢牢地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京都朝廷与镰仓幕府之间的对立矛盾不断积累加深。幕府严密监视怀有倒幕意图的天皇与贵族,天皇也暗自组织武士和义军积蓄倒幕力量。至虎关师炼执笔撰述《元亨释书》的镰仓末期,朝幕矛盾已经发展到冲突爆发的边缘。这一时期,皇室内部也逐渐分裂为大觉寺统与持明院统两派,两派围绕皇位继承权斗争激烈。
先看这一时期京都皇权的更替。德治二年(1307),师炼发愤著述《元亨释书》。是年当后二条天皇七年,为后宇多上皇行院政之时。后宇多院于此年七月出家,并于东大寺受戒。翌年(1308)八月,后宇多院将院政之位让于伏见天皇。同年,后二条天皇退位,花园天皇即位。再看镰仓武家政权。师炼执笔撰写《元亨释书》的德治二年(1307),镰仓幕府将军由后深草院之子、伏见院之弟久明亲王担任。执权为北条贞时之后继者北条师时。
无论是京都的公家贵族,还是镰仓的武家政权,都大力崇佛兴禅,极大地推动了新兴禅宗的发展传播。龟山、后宇多和花园三代天皇皆倾心佛门,修禅崇佛。龟山法皇极为崇佛,其本人不仅于嘉元元年(1303)在东大寺受戒,同三年就了圆受密教灌顶,更是将其寝宫龟山殿改建为后来的禅林寺,并命规庵祖圆常侍左右,咨问禅要。后宇多天皇出家后住大觉寺,醉心于密教修行。花园天皇在退位后,于持明院出家,晚年于花园御所修行禅法。镰仓幕府北条氏更是极力地推动禅宗传播。建长元年(1249),五代执权北条时赖迎兰溪道隆并为其营造建长寺,入住讲法。弘安二年(1279),八代执权北条时宗迎无学祖元于镰仓,并于弘安五年(1282)为其建造圆觉寺。正安元年(1299),元代禅僧一山一宁赴日,受到九代执权北条贞时的尊崇,并应幕府之请住持建长寺、圆觉寺,后又移住京都主南禅寺。不惟临济宗,五代执权北条时赖亦请曹洞宗开祖道元赴镰仓说法并就其授菩萨戒。可以说,日本禅宗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公武政权的大力支持而兴起并发展起来的。
(二)宗教文化背景
1.新旧佛教对立
旧佛教,是指以天台宗延历寺和真言宗金刚峰寺为代表、以显密佛教为修学内容、以强大的庄园经济为依托、以天皇和公家贵族为檀越的位于南部北岭的体制寺院。因这些显密寺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拥有巨大实力,多被史学家称为“权门体制寺院”[1]10。由这些权门体制寺院以及他们所倡导的以天台止观、真言密教和华严唯识为主要修学内容的佛教诸派被统称为“旧佛教”。旧佛教寺院倚仗权势,豢养大量僧兵,多次以“嗷诉”的形式干涉朝廷的政令决断,并脱离民众逐渐流于世俗化和贵族化。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日本社会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日趋增强,至镰仓末期佛教信仰已深入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与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教以及生活习俗融为一体。为了满足底层民众的信仰需求,也为革新旧佛教的腐败与堕落,一些日本本土僧侣创造出符合本民族信仰特征的新的佛教信仰,如源空的净土宗,亲鸾的净土真宗,一遍的时宗和日莲的日莲宗。相对于旧有的显密佛教,这些新兴佛教教团被称作“新佛教”。不容忽视的是,构成新佛教的另一宗派禅宗也随着荣西、道元的入宋留学及宋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的渡日被传入日本。禅宗以其简明易行的修行特征受到镰仓幕府武家政权的欢迎,首先得以在镰仓流行开来,而后在荣西、圆尔辨圆等人的努力下又逐渐在京都的公家贵族间渗透传播。
从新佛教成立伊始,新旧佛教就始终处于激烈的矛盾对立中。旧佛教寺院利用特权地位在竞争中长期处于优势,通过干涉朝廷政策的手段时时挤压以净土宗和禅宗为代表的“新佛教”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如对净土宗的打压。元久二年(1205),由于净土宗的发展损害旧佛教的利益,兴福寺僧贞庆起草《兴福寺奏状》上书朝廷,请求“停止一向专修”。建永二年(1207),朝廷宣旨严禁一向专修,将源空等人流放至土佐,并处住莲等人死刑[2]226。如应安元年(1368)延历寺与南禅寺“嗷诉”事件。贞治六年(1367)六月,三井寺僧徒烧毁南禅寺所设两处关所,南禅寺僧祖禅作《续正法论》大加贬斥显密诸宗及山门寺门。以此为导火索,应安元年(1368)六月,三井寺联合延历寺及兴福寺,奉神舆入京要求朝廷拆毁南禅寺,并流放祖禅及春屋妙葩。是年十一月,朝廷不得已将祖禅流放边地。翌年(1369)四月二十日,延历寺众徒再度奉舆入京,要挟朝廷拆毁南禅寺楼门,朝廷不得不再次妥协,拆毁南禅寺楼门,并令京都五山以下诸禅寺住持全部退院。八月,延历寺僧徒归山[3]289。这次事件可谓显密佛教(延历寺)与新兴禅宗(南禅寺与天龙寺)的直接交锋,以朝廷及禅宗寺院对延历寺的妥协而告终。可见,在师炼撰述《元亨释书》的镰仓末期,新兴禅宗时刻都面对着旧佛教显密诸宗的敌对与竞争,必须时刻保持警醒与危机感。这构成了《元亨释书》撰述的重要历史背景。
2.禅宗诸派竞争
就《元亨释书》成立的镰仓末期的禅宗诸派,依禅宗修学内容可将日本临济宗大致分为“纯粹禅”和“兼修禅”两大流派。所谓“纯粹禅”,也叫“镰仓禅”,是指中国渡日禅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以镰仓建长寺和圆觉寺为据点,依宋代禅林清规将宋代禅院的修行方法原样“移植”并推广的禅修风格。其修行具浓厚的华严宗教学的性质;所谓“兼修禅”,亦名“京都禅”,是指京都建仁寺荣西和东福寺圆尔辨圆,迫于南都北岭显密诸宗打压新兴禅宗的外在压力,大力倡导“禅教合一”,强调禅宗与显密诸宗的融合,并在各自开山的寺院中推动真言、止观和宗门三教兼修。故其修行带有浓厚的密教色彩[4]37。镰仓末期,也同样是日本禅宗二十四流大部形成的时期。除大鉴派(派祖清拙正澄)、竺仙派(派祖竺仙梵仙)、别传派(派祖别传明胤)、东陵派(派祖东陵永玙)、愚中派(派祖愚中周及)和大拙派(派祖大拙祖能)之外,二十四流中其他十八流派皆已形成[5]25。二十四流中,除道元派(派祖道元)、东明派(派祖东明慧日)和东陵派(派祖东陵永玙)属曹洞宗外,其余二十一流均属临济宗。临济宗二十一流中,除千光派(派祖荣西)传黄龙派法脉,其他皆燃杨岐派法灯。这一时期业已形成的十八流派中,佛光派(派祖无学祖元)、大觉派(派祖兰溪道隆)、圣一派(派祖圆尔辨圆)和一山派(派祖一山一宁)等主要宗派皆具强有力的外护势力(贵族或武士)和固定的修学寺院(五山禅刹),形成了稳定的传承系谱和教派组织。随着禅宗各派蓬勃发展,受法禅僧数量亦急剧增长。各派因扩张势力,争夺信徒,经常产生摩擦与冲突。如佛光派三世法孙梦窗疏石,为与大觉派争夺幕府的信仰与支持,极力扩充自门派势力,以致两派间的对立摩擦逐渐升级,至南北朝时演变为必须由朝廷幕府出面才能调解的政治问题[6]975。
3.宋元文化传入
《元亨释书》成立的镰仓末期,同样是宋元文化大规模传入的时期。入宋、入元禅僧除禅籍之外,亦将大量儒家典籍、诗文集等带回日本。如俊芿在建立元年(1168)归国时,其所携书籍除律宗、天台宗和华严宗经论章疏之外,亦有儒书256卷,杂书463卷,碑文76卷。以荣西、圆尔辨圆为代表的渡宋日僧在传播禅法的同时也携带大量禅籍语录和儒家典籍回国。据《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记载,当时传入日本典籍除经论章疏170余部,合370余卷册之外,还有《周易》《孟子》和《扬子》等外集,共计230余部,合960余卷册[7]352。东福寺丰富的藏书,为师炼博涉内外之学,饱读儒家典籍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早期渡日禅僧,如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西涧子昙、无学祖元和一山一宁等皆学通内外,知识渊博。一山一宁更是通晓儒道百家之学,能赋诗,善书画。师炼出入一山门下十数年,博学多闻的一山对师炼教诲极深,为其编撰《元亨释书》给予了有益的指导。
二、《元亨释书》的撰述动机
(一)忧患意识
师炼撰述《元亨释书》的动机,首先源于其本人对日本“僧史”撰述水准的低下与僧团腐化堕落的忧患意识。
1.“无通史”
在《释书·序说志》中,师炼说明撰述主旨曰:
佛法入斯土以来七百余岁,高德名贤不为不多。而我国俗醇质,虽大才硕笔,未暇斯举矣。其间别传小记相次而出,然无通史矣。故予发愤禅余旁资经史,窃阅国史洽掇诸记,日积月累已有年矣。远自钦明,迄于圣代。补缀裁缉为三十卷。仅成一家之言,不让三传之文。名曰《元亨释书》。[8]448
在七百余年的日本佛教发展史中,虽然产生过诸如思托《延历僧录》、宗性《日本高僧传要文抄》和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等佛教史传类作品,但从体例和规模来看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史籍,从内容上也不能超越宗派之见完整地、体系性地总结记载日本佛教各派的发展演变。这正是师炼痛感“无通史”的原因。中日佛教史籍撰述水准的巨大落差以及通过吸收儒家史学思想撰述日本佛教“通史”以弘道辅政的使命感,构成了师炼撰述《元亨释书》的又一动机。
2.戒律衰颓
虽身居禅院,但师炼时刻保持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在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同时,师炼也时刻对日本禅林与佛教诸宗表面繁荣之下所隐藏的内部危机保持着清醒的反思和深刻的忧虑。至《元亨释书》成立的镰仓末期,佛教传入日本已逾七百年,从以东大寺、兴福寺为代表的奈良佛教最初确立,经天台和真言为股肱的平安佛教,至镰仓末期净土宗、禅宗等教派兴起,佛教发展盛况空前,蔚为壮观。七百余年间,僧团涌现出大量高僧,堪为后世释子之楷模。但滥竽充数、徒具虚名者亦为数不鲜。针对当时的禅林时弊,师炼痛加批判:
近代丛林之浇漓,尤甚矣。主宾相欺,局务不正。非权则贿,非党则谀。负贩户籍,间不容发。惜乎!少室正脉,大雄遗砚,流为市井之习俗。可悲!可痛![9]205
师炼犀利地批判那些欺上瞒下、有名无实的禅门“宗师”,对贪慕名利、扰乱宗风之徒深恶痛绝。在贬斥僧团时弊的同时,师炼亦在思考如何中兴佛法。高僧的德行与道德榜样,对于提振宗风、凝聚僧团尤为重要。无论是对弘扬佛法,还是于整饬日益衰弛的戒律,整理和总结祖师先贤的高德伟业都极为必要和紧迫。有鉴于僧团的腐败堕落和出于自身著述弘道的强烈责任感,师炼决定绍续伟业,以儒家史学的“鉴戒”史观指导《元亨释书》的编修,在历史叙述中寄寓褒贬,以“彰善瘅恶”的精神警诫僧侣恪守戒律、专心修行,实现佛法久住、释门永兴。
(二)禅教兼修
师炼的佛教修行特征可以“禅教兼修”来概括。首先,宗门方面。师炼为临济宗圣一派下禅僧。圣一派素以“兼修禅”为其修行特色,派祖圆尔辨圆在建立东福寺时,就与檀越九条道家约定当寺以“显密禅”三者兼修为宗旨。如《圣一国师年谱》中记载:“当学显密性相大小权实等教,以祈国家安宁。复诸君臣寿福。”[10]52荣西以及圆尔辨圆在推行新兴禅宗的时候,以一种“折中”的方式与旧佛教传统“妥协”。即以最澄所倡天台宗“圆密禅戒”四宗相承为旗帜,在主要推行临济禅法的同时,兼修天台止观与真言密法。师炼正是在圣一派浓厚的诸宗兼修传统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修行特征。在教门方面,弘安九年,师炼十岁于比睿山登坛受戒。永仁五年,弱冠之年的师炼于仁和寺习广泽之秘法。嘉元二年,二十七岁的师炼再度于醍醐寺习学密教。师炼一方面于东福寺、建长寺和南禅寺等位列五山前列的禅宗寺院中参禅问道,既受东福寺圣一派“兼修禅”传统之濡染,又于建长寺和圆觉寺,在习得“纯粹禅”等宋代禅法精要的同时,汲取宋元儒学文化;另一方面,亦于延历寺、仁和寺和醍醐寺等显密寺院修习天台、密教和律法。禅教兼修的信仰特征也令师炼熟悉佛教各宗要旨与经典教义,为其在审视佛教诸宗发展的宏观立场上组织材料撰述日本佛教“全史”创造了条件。
三、结语
晚年的师炼在《自赞》中如此回顾自己的一生:“曲禄之床,斑驳之服。偷禅者名,欠禅者实。这般孟浪无方,也有恶称可腼。若非语心论师,即是僧史修撰。”[9]72“偷禅者名,欠禅者实”“孟浪无方”“恶称可腼”,师炼自嘲的口吻中暗含对自己沉溺于儒学修习与著述弘道,而疏于修禅悟道与心性参究的反省和愧疚。“若非语心论师,即是僧史修撰”之句,足见师炼对十八卷《佛语心论》与三十卷《元亨释书》是何等的推重与自负。师炼将二书视作明道载道的最佳载体,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佛语心论》的撰述是从祖述并阐释禅宗经典,即四卷《楞伽经》,来强调禅宗于诸宗中的正统。《元亨释书》则是通过记叙梳理佛教史和禅宗史的发展演变轨迹,以揭示日本佛法与王法融合统一的历史本质和佛法传承流衍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