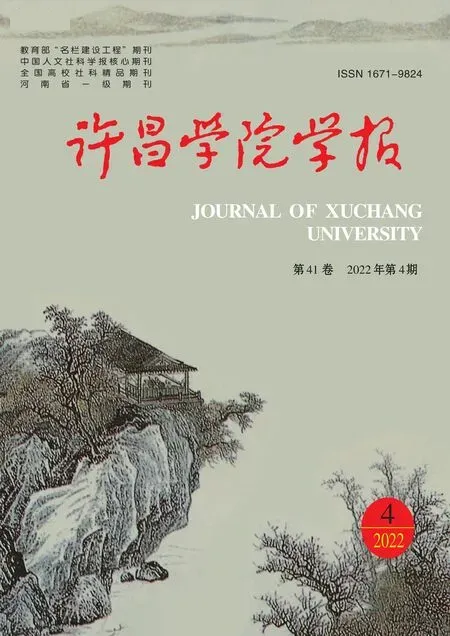论四十年代公孙嬿的“色情小说”
高 姝 妮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1940—1942年公孙嬿在《中国文艺》发表了六部中短篇爱情小说,这些小说因对肉欲的大胆描写引起了北京文坛的关注,一些批评者称其为“色情文学”。然而,沦陷时期北京特殊的政治语境与“建设新文艺”路线的现实主义创作需求,使得抒发私欲的浪漫主义“色情文学”成为一股文学启蒙的逆流,于是1942年北京文坛掀起了“色情文学”的讨论热潮。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色情文学”这股逆流并不是公孙嬿随性而为。这些“色情小说”描写了人病态的情欲与异化的肉欲,表现了畸形社会对人精神的压抑和阉割。可见,欲望的书写并不止于感官上的娱乐消遣与堕落腐化,溯其创作根源,它还暗示着笼罩在“沦陷”阴影之下北京文人苦闷、彷徨、无力、愤懑、自责的复杂心态。
一、公孙嬿与“色情文学”的创作
查显琳(公孙嬿)毕业于辅仁大学西语系,是北京文坛颇有影响的诗人,外文专业的教育背景使他深得西方文学思想的熏陶,其中对他文学创作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流派。以济慈、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强调个人情感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倡导自然的审美理想以及个体精神的解放,因此,在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影响下,查显琳的诗歌表现出对自然意趣和生命性灵的关注,注重个人欲望的表达。尽管查显琳一直致力于诗歌创作,但论其在北京文坛的影响力,还要从他署名为“公孙嬿”的“色情小说”谈起。
如果说对欲望释怀、追求自然之美的浪漫主义诗歌构筑着查显琳的诗学观,那么“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创作理想,以及主张客观真实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想则构成了他创作“色情小说”的理论基础,在此王尔德、莫泊桑、劳伦斯的作品无疑为公孙嬿的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秉持着生命自然性与自为性的创作观,公孙嬿的小说创作在追求诗美理想的同时,也关注主观精神的表达。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语境里,严苛的政治统制造成了个体精神的压抑,于是主观情感的表达尤为放大,无以抒发的苦闷情绪在欲望的书写中借以渲染。然而公孙嬿并不满足于直抒情感,他以夸张、丑化甚至扭曲的欲望书写揭示了畸形社会对人造成的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公孙嬿对肉欲的书写,遭到了批评者的道德谴责,在“道德”的“歧途”上,他的小说被贬抑成“色情小说”。
1940年11月《中国文艺》发表了公孙嬿的处女作《海和口哨》,然而他并没有想到这部在“暑假百无聊赖中”[1]41创作的“狭窄与粗浅”[1]41的小说,竟使他“背负色情文艺作家罪名”[1]41。之后公孙嬿在《中国文艺》又相继发表了《镜里的昙花——韶华不为少年留》《北海渲染的梦》《流线型的嘴》《解语花》《卸妆后的生命》五部中短篇小说。此外公孙嬿还在《新民报》(半月刊)发表了《红樱桃》,在《国民杂志》发表了《珍珠鸟》,它们与《中国文艺》刊载的六部小说同时被划为公孙嬿“色情小说”之列。为了重振民族精神,复兴华北文艺,1940年北京文坛提出“建设新文艺”的文化路线,积极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呼吁作家要创作表现民众生活、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然而,公孙嬿却以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深入挖掘人复杂的精神世界,以生命原欲的书写反观社会现实对个体心灵的压迫,在一定程度上“违逆”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主流,甚至僭越了传统道德观的底线,于是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一些批评者的攻击,“淫秽”变成了公孙嬿“色情小说”的注脚。一方面,对于“色情”的评价,公孙嬿无奈于一些批评者将“色情”与“淫秽”的概念相混淆。他认为,“色情”表现的是男女正常的生理与情感的欲求,而“淫秽”则“以描写性交的动作声音”毒害青年的思想。在此,“色情”强调对欲望的释怀与精神美感,表现出公孙嬿对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然而,“淫秽”却指涉着身体描写的低俗与不堪。于是,一些批评者借此将公孙嬿小说的“色情”描写定性为散播“淫秽”思想的“烂俗”文学,可见批评者指涉的“色情”与“淫秽”有着等同的意义。面对众人的指责,公孙嬿并没有为自己辩解开脱,但也无意接受“色情文艺作家”的称谓,他将“色情”视为对文学的亵渎,为此重新诠释了“色情”的含义,极力为“色情文艺”正名。故而另一方面,公孙嬿又表现出对“淫秽”臆断者的否定与反击,他说:“我们不要只记忆住‘色情’二字而忽略了原作的本意和内容,与他好含蓄,一个表现时代,或对某一方面自己主观见解的怨尤地方……‘色情’二字的成立当非绝对性的捕逮,有时候是技巧增加以后文章的力量,有时候是渲染增加文章的美妙。”[1]41
从其作品也可见出,公孙嬿并不着意于“色情”的描写,而是将“色情”描写作为表现美、渲染美的创作方式,而情感的困顿、欲望的释怀、时代的忧郁、青春的易逝、个人的迷惘才是“色情小说”要表达的真意,其潜藏的复杂情感和创作心绪是值得关注与思考的。可见,以“淫秽”定义“色情小说”是不甚妥当的,容易造成对小说主题的误读和曲解。
公孙嬿的小说以欲望的放大指涉着异化的非理性世界,展现了异变时空下人们挣扎、疏离、隐忍、盲从的心态,这是公孙嬿从劳伦斯的创作中得到的借鉴与启发。劳伦斯通过性心理和性描写表现人性欲望的放大,强化肉欲突显了灵与肉的撕裂。《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即是在生命本能的驱动下保持着个体意识的自觉,丈夫克里福德的性无能使康妮的肉欲受到压抑,而麦勒斯强健的性能力使康妮的自我意识在灵与肉的交欢中得到释放,在此劳伦斯以性的方式确证了自我身份的认同,建立了人的生命本能与社会意识的内在关联,人性的复归在灵与肉的和谐状态下得以实现。公孙嬿从劳伦斯对灵肉关系的思考中得到启发。沦陷的时空使日本的殖民意识形态挤占了民众的个体意识,精神的解放与人性的复归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自觉,因此生命本能的肉欲激发了人对自我的认知,劳伦斯对欲望自由的书写表达了他对生命美学理想的追求,而公孙嬿却以审丑的立场放大了人性本能的欲望,使得欲望呈现出异化的样态。无论是西方文学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对色情文学审美理想的建构,还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对色情文学启蒙意蕴的拓展,不同的创作理路都打通了色情文学中个体意识与社会现实的分界,使主观抒情的色情文学在社会现实的观照下呈现出作家的现世焦虑。公孙嬿的“色情小说”即是在多元文学思潮的融合中形成的,不仅得益于劳伦斯、王尔德等西方作家的创作理路,还借鉴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技巧,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私下喜欢读沈从文与老舍二人的小说,对于穆时英的新感觉派,有了更深的偏爱……我受到另一本劳伦斯的《查特莱的夫人》影响不少。”[1]41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深刻影响着公孙嬿小说的叙事模式和情感结构,也因此构成了公孙嬿“色情小说”的思想资源。
与此同时,北京沦陷,特殊的政治语境也促成了公孙嬿对主观情绪书写的自觉。国破家亡的悲哀、日本人统治的耻辱、亡国奴的无奈、寻求自救的挣扎、生存危机的窘迫呈现出沦陷区民众复杂的精神图景,进步文人思忖民族精神的崛起,沉默的知识分子无声地坚守士人的道统,浸在生活苦难中的百姓在麻木与盲从中求取自保,曲意逢迎的投机者趁机钻营谋权。日本的“胁迫”更替了“北平”和平时代的气象,“北京”使无所适从的“北平人”变成了屈从的“北京人”,于是在“屈从”的状态下便显现出不同价值立场的选择,或是潜隐地挣扎抵抗,或是沉默地坚守自我,或是被迫行事,或是投机谋权,或是软弱无力,或是盲目自保,总之“屈从”使每个人在压抑的精神空间里凝神屏息。他们的表里不一,最终导致了异化的生存状态。在这一意义上,公孙嬿的“色情小说”即是将人们异化的生存状态凝缩至欲望的书写,他的目的并不是找出病因,而是列出病状。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人的精神“病因”无以解除,但“病状”却能间接揭露“病因”之恶,从而间接表明作者的写作立场和排日态度。
二、欲望书写的多重阐释
公孙嬿的“色情小说”以两性关系开掘欲望的深层意蕴,无论是摩登女郎与懵懂男性之间异化的肉欲,还是青春韶华的女性与成熟男性之间压抑的情欲,复杂的人性欲望在人伦关系与社会环境的面向上有了多重的文学阐释空间。公孙嬿的欲望书写意在表现人在非理性意识下的异化状态,人成为欲望的囚徒,而欲望对人的奴役也导致了人格的异化与分裂,由此深刻地反映出病态的社会对人精神的挤压,以及沦陷区民众无以摆脱的精神困境。
公孙嬿的小说以男性的叙述视角为主,且男性的形象是颇为单一的,他们多为在校大学生,良好的家境与教育背景让他们更关注个体意识的表达,当个体意识在现实的阻碍中无以释怀时,便异化为欲望对现实的疏离与反拨,因而公孙嬿笔下的男性在欲望的蹂躏中不安、压抑与痛苦。《海和口哨》中的“我”爱上了在海滨偶遇的少女,她的妩媚妖娆紧紧绑缚着被欲望撕裂的“我”,于是在欲望的驱使下“我”甘愿臣服在她的脚边任凭她戏弄,“爱”让“我”学会征服与占有,因此即便“我”得到了肉欲的满足,也无法摆脱情欲的折磨[2]。从“邂逅”到“离开”,从相识到相恋,少女一直控制着感情发展的主动权,而“我”也随之陷入少女的爱情圈套任凭她摆布。在此,传统的“男强女弱”的两性关系逆转为“女强男弱”,女性不仅是欲望的操纵者,同时也是男性情感的引导者,她们一改传统女性清纯、良善、软弱及贤淑的性格特点,以摩登女郎的魅惑、成熟、随意和性感触动着情欲懵懂的“公子”和“少爷”,而这也成了公孙嬿笔下女性形象的共同特点。无论是《海和口哨》《流线型的嘴》,还是《解语花》《卸妆后的生命》,摩登女郎对男性欲望的魅惑构成了公孙嬿既定的叙述模式,男性压抑自我而变为女性的仰视者,在此公孙嬿在文本中强化了女性的主体地位。这种叙述视角的改变突破了传统爱情小说的创作理路,于是传统的两性关系表现出一反常态的畸形与裂变,而两性关系的异化则构成了欲望异化的动因。寡妇(《卸妆后的生命》)将“我”视为泄欲的工具,她通过性的满足遮蔽情感的空虚,她需要“性”却漠视“情”,于是肉欲对于寡妇来说即是极端化的生命本能的需求[3];“莓”(《流线型的嘴》)换衣服时要求“我”留在她的房间,她肉体的倩影不断触动着“我”,继而“我”又邀请她去我的房间等“我”换衣服,欲望在换衣者与观望者间流动,也在理性的压制下变得焦灼与不安,换衣者的撩拨与观望者的冲动展现出人欲的丑态[4]。“肉欲”的膨胀不断放大男性的生命原欲,女性“鲜红的唇”“桃杏色的双颊”“长细的头发”“修长的肢体”“高凸的胸”“白玉的皮肤”等无一不是代表肉欲的能指符号,它们促使男性在欲望的灼烧中寻求两性关系的主导。然而在公孙嬿的小说中,男性的占有欲不止于肉体的满足,他们还有内在的情感需求,但对于女性来说,对爱情的藐视与不屑导致她们放浪形骸,于是女性对欲望的亵渎钳制了男性的情感欲求,两性爱情观的失衡导致男性欲望的压抑,继而在占有欲的驱使下使其做出非理性的行为,诸如跪在女人的皮鞋上、吻女人的脚、把女人的脚托在腿膝等。公孙嬿笔下的两性关系摆脱了传统道德观的束缚,女性的征服欲与男性的占有欲在爱情的角逐场上暗中较量,女性摆出胜利者的姿态,体味着“征服”的喜悦。在此男性变成女性俘获的战利品,他们为逢迎女性而减缩了个体的精神空间,他们被欲望驱使,既要疯狂地占有,又无从排解情感的苦闷,虚无、彷徨以及患得患失构成了他们复杂的心绪,他们的性格特质和情感困惑都是同一的,就连他们的名字也都是相同的——燕。
男性情感的忧郁和迷茫并不意味着女性在两性关系的博弈中占据上风,无论是摩登女郎(《流线型的嘴》)、妓女(《解语花》),还是名门闺秀,她们藐视伦理道德但又无法挣脱既定的命运,内心葆有的人性良善与放荡不羁的行为构成了灵与肉的错位,于是她们陷入情感与道德的双重困境。《海和口哨》中的摩登女郎曾在早年遭到男人的欺骗,为了报复男性,她戏弄男人的感情,然而她并未体验到报复的快感,却背负着道德的罪恶感,她越是放大欲望,越是陷在罪恶的深渊中无以挣脱,唯有死才能救赎她心灵的负罪,也只有死才能让她的内心找寻到久违的平静与安宁,死亡铺筑着她既定的归途[3]。《解语花》中的妓女深深地吸引了“燕”,然而“燕”的软弱迫使他放弃了心底的情感,他的逃避与疏远对痴情的妓女造成了伤害,妓女的主体身份随着爱欲的失衡而褪去,当她发觉爱欲无法弥补她卑贱身份的原罪时,非理性的“疯”成为她与现实对抗的自觉,妓女不堪的爱情被歇斯底里的“疯”搅碎,而“疯”又给予她重生。感情的退潮使她更为理性地感知到婚姻与情欲的现实差距,她不甘成为男性情欲的玩物,因而断然拒绝了“燕”,拒绝了与“燕”的一切过往[5]。无论是死亡还是疯狂,这些女性以决绝的方式对现实施以反抗,在这一点上,女性比男性有着更为冷静的自知,而男性则在欲望的压抑下表现出逃避而又无所适从的懦弱。同样是面临精神困境,男女不同的应对方式间接反映出异化的政治语境下人们复杂的心态与不同的选择路向。
在公孙嬿的“色情小说”中,青春与欲望有着莫名的关联,摩登女郎触动着男性青春的欲望(《海和口哨》《流线型的嘴》),成熟的男性对正值青春的女性爱慕不已(《镜里的昙花》)。在此,青春代表着情窦之初的韶华记忆,它懵懂、纯粹、青涩、短暂又美艳,不仅牵动着人对青春最真切的向往,还引发了爱之初欲的迷思。“我”(《镜里的昙花》)在山间认识了“小原”,她的“淳朴”“自然”“纯净”深深吸引着我,让我产生了爱欲,然而作为有妇之夫的“我”断然拒绝了这样的感情。无论是“妻子”还是“小原”,她们的青春记忆里都熔铸着“我”的爱,与其说“我”贪恋青春,不如说青春复苏了“我”的爱欲,让“我”的生命重新得到洗礼[6]。《海和口哨》中摩登女郎的青春时代被一个欺骗她的男人消磨殆尽,痛苦的青春记忆使她产生了报复心理,她戏弄这些男人的感情,通过这些男人的爱欲确证自己的青春,最终她选择以死来祭奠青春、救赎自我,通过死亡永恒地驻留她的美与爱的记忆。易逝的青春带走了青涩的年华,情欲最初的萌动迸发出生命的激情与活力,公孙嬿的小说往往带着青春的感伤,无论是男性对青春少女的迷恋,还是女性对青春的怅惘,失落、惆怅、忧郁,恰恰留驻着感伤的心绪。然而青春的意义不止于此,它还关联着作者的民族意志。短暂的青春年华不应在碌碌无为中消磨,人的青春应贡献于民族与国家,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沦陷区需要青年力量的支持以重振民族精神。因而公孙嬿对于青春易逝的感伤充满了焦虑,甚至将这种心态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诸如,中年男人对青春少女的迷恋,以及女人以死保留青春的决绝。可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公孙嬿的内心变得焦灼与急迫,在此青春不再逡巡着爱的萌动,它背负着更为深沉的民族使命,于是青春不仅有了来处,还有了归途。
公孙嬿的“色情小说”以欲望的书写呈现人非理性的精神裂变,由此公孙嬿的色情小说不再是坦露欲望的抒情小说,而是反映畸形社会与异化人格的精神小说。不仅如此,其“色情小说”的叙述结构也表现出“异化”的创作形式,不仅故事情节颠覆了传统“男强女弱”的叙述模式,就连“色情描写”也不同于以往作品“淫秽”的身体描写,它以人的主观精神为中心展现隐秘的心灵世界。此外,公孙嬿诗化的语言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提升至美丑共融的境界,无论是融合多元的创作方法,还是寻求自然的审美艺术性,公孙嬿的“色情小说”都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
三、个体意识的边缘化写作
公孙嬿的色情小说以欲望化的书写突显人的个体意识,然而他想要表现的个体意识并不是个体精神的解放,而是肉欲与情欲二元对立下个体精神的压抑。如果说个体精神的解放表达了人挣脱束缚的快感,确证了人的主体性,那么个体精神的压抑则显示出人无以摆脱的现实困境,深刻反映了沦陷区异变时空下对人的主体性的阉割,于是个体意识的边缘化使人的心态变得盲动与扭曲。所以说,公孙嬿的小说着眼于人的精神危机,通过个体意识的陷落展现了作家更为深刻的社会思考。对于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的北京文坛来说,公孙嬿主观抒情的欲望化写作悖逆于新文学建设的发展要求,不仅如此,肉欲的描写还颠覆了传统文学的道德观。因而他的作品一经发表就遭到了反对者的攻击,一方面是对色情小说道德立场的批判,另一方面则是民族启蒙的集体意志对个体私欲的排斥与否定,由此强调个体意识的欲望化写作面临着边缘化的文学危机。
公孙嬿的“色情小说”打破了个体欲望的平衡,肉欲与情欲的分离使欲望主体呈现出异化、分裂的状态,由此暗示了人孤独无着的生存状态。小说往往以“欲”的名义寻求“爱”的可能,然而,“爱”的虚无造成了“欲望”的空洞,男女主人公相识却不能相知,相惜却无法相爱,不同的精神欲求和情感结构使他们“理应”具有的亲密关系变成了陌生化的疏离。《海和口哨》中的摩登女郎与“我”互生爱意,肉欲并不能使“我”的情欲得到满足,反而促使“我”增强了对摩登女郎的依赖,“我”真诚的爱增加了她道德的重负,于是她选择逃离,逃离她对“我”的爱,逃离罪恶的情欲,逃离现实的苦闷。“筠”(《北海渲染的梦》)是“燕”的恋人,他们彼此相爱并“私订终身”,然而家庭背景的悬殊让“燕”变得自卑,“筠”纯洁的爱让他无以面对甚至深感愧疚,于是他对“筠”的爱被融贯在无尽的罪恶中,怯弱使他选择了逃避[7]。《解语花》中的浪荡公子“燕”与痴情的妓女许下婚约,但家长的反对动摇了“燕”对爱的坚守,于是他有意疏远妓女甚至与她断绝了来往,爱的等待使妓女的希望变成了绝望,最终她以“非理性”的“疯”向“理性”的社会秩序发起宣战。可悲的是,在理性的现实世界里,妓女对现实的疏离招致了现实对她的遗弃,抑或是她从来都是时代的弃儿,只不过她一直沉浸在自我编织的谎言中寻梦[5]。人情冷漠、门第观念以及传统婚恋观将摩登女郎、大学生、浪荡公子禁锢在现实的枷锁中,他们无意妥协,却又无计可施,于是他们逃避无解的感情,以妥协求得短暂的安宁,他们反抗残酷的现实,以沉默挣扎在世的苦闷与精神的束缚,于是两性关系在守望、期许与疏离、逃避的对抗下呈现出错位的样态。摩登女郎的自杀、妓女的“疯”、“筠”的死极端地表现出在现实的压抑下人对自我的确证。公孙嬿的小说往往通过个体意识的边缘化反映人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于是在欲望的驱使下人以非理性的方式反戈现实的压迫。在此,欲望的异化指向了社会价值观的畸形。
在沦陷区,似乎没有人会在畸形的社会中保持愉悦,日本殖民意识形态的统摄剥离了中国人的主体地位,亡国之辱、生存之苦、现实之痛使沦陷区文人的心态变得忧郁而复杂。日本的殖民统治越是严苛,这些文人的挫败感便越是强烈,他们为时代哀悼,更为自己的不堪感到失望和痛心,灵肉的分离构成了生活常态,沉默或是言说的背后潜藏着沦陷区文人对人间的悲悯与精神的负罪。公孙嬿极力表达的并不是才子佳人式的“男欢女爱”,而是将爱的魅惑、忧郁内化为现实对个体意识的异化和扭曲,压抑的自我唯有在现实的虚妄中才能得以释怀,“虚妄”恰恰反映了人的现实悲剧,因此小说常弥漫着哀伤、忧郁、凄怆的情绪。
公孙嬿的小说往往以诗化的语言使小说流动着诗性之美,为情感的表达渲染了美的氛围,与诗歌的“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
漫步在月下,之间一颗微黄的大星座在天上陪月亮摆摇着,和流水一般澄澈的蓝空,可显得有点儿空洞。[4]40
水波粼粼,静听,有一种单调而孤单声韵,自远处来,流向不知名的地方去……[2]65
无论是海边的月夜、水中的碧波、蝉声的聒噪,还是孤独的白塔、凄冷的西风、昏黄的天地、荒芜的原野,忧伤的心绪始终融贯在公孙嬿的文字中,使全文流动着阴郁的感情基调。诗美的“意境”烘托出人物淡淡的哀伤与忧愁,渗透着时代的忧伤,由此呈现出个体意识边缘化的现实困境。
公孙嬿不仅从小说的主题上开掘人的精神困境,还着力从小说的叙述方式上表现内容的主题结构。公孙嬿的色情小说淡化了情节结构,突破了传统历时性的叙述模式,以人物的情绪推动情节的发展,人物心态的变化构成了小说的内在逻辑。如《北海渲染的梦》中,“燕”和“筠”的关系通过身体描写、语言对话和场景转换来推进,而对“燕”的退缩、“筠”的生病以及二人关系的转变,文中并没有详细的描述,只是通过“燕”的主观情绪的变化才得以展现[7];《流线型的嘴》则以男女情欲的变化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碎片化的情节被人物的欲望整合,于是欲望的异化形态构成了非理性的叙述模式,突显了个人的主体经验[4]。此时,大后方、解放区将“抗战”作为主流文学的创作面向,然而在政治语境严苛的华北沦陷区文坛,民族启蒙话语被异化为“隐言”的叙述方式。沦陷区特殊的政治语境不断地挤压文学启蒙话语的建构,于是文学的社会效用在文学启蒙话语建构的过程中被放大。在此,以理性精神为主体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因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直接暴露和书写而得到北京文坛广泛的关注与认可。一方面,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社会现实对民众生活的压迫,具有对现实社会批判的力度;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文学暴露的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反映民众普遍的生活困境,体现了社会集体意识。因此,为了凸显文学的社会效用,以重振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复兴华北文艺”运动,需要现实主义文学开辟文学启蒙的新路径。然而,公孙嬿的“色情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欲望书写批判社会对人的主体性的压抑,在体现社会集体意识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冲击下,个体意识被边缘化,于是体现个人私欲的欲望化写作走向了非主流的文学创作。可见,在倡导理性精神的文学启蒙呼吁下,大胆描写人欲、表现个体意识的色情小说,注定了它饱受争议的“文学身份”。
当沦陷区的民众在殖民意识形态下备感压抑时,屈辱与愤懑形成了一股反抗的暗流,于是民族精神的启蒙成为沦陷区有识文人共同的追求,而公孙嬿的“色情小说”则着眼于个体意识的表达,一定程度上与倡导民族精神的集体意识相疏离,由此遭到反对者的贬抑。另一方面,色情文学的道德立场遭到反对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公孙嬿的“色情小说”散播不良思想、涣散人心,不利于文学启蒙话语的建构,因此公孙嬿的“色情小说”在北京文人的质疑声中被边缘化,这意味着个体意识的书写也随之被边缘化,甚至在冷遇中退场。
四、结语
特殊的政治语境压抑着人的主体性,个体意识被边缘化,于是公孙嬿的“色情小说”借鉴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以欲望化的书写极力表现个体意识。这不仅是一次文学创作的实验,也是一次创作理路的革新。公孙嬿的小说试图通过两性异化的情感关系表现人与人以及人与现实的疏离,以非理性的方式表现欲望主体的空虚与压抑,力图展现沦陷区民众的精神危机。然而公孙嬿的创作理路遭到了反对者的质疑,欲望写作不仅悖逆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符合文学启蒙话语的建设要求,因此公孙嬿的“色情小说”在北京文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和接受,于是表现个人欲望的“色情文学”遭到了民族主流话语的冲击,从而成为边缘化的存在,最终悄然退离了北京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