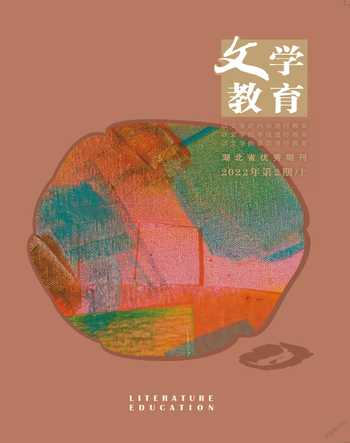《伶仃》:中年女性的心灵成长史
温凌慧
内容摘要:本文以蔡东短篇小说《伶仃》为研究对象,关注面临社会与家庭双重危机的现代中年女性,在失去另一半陪伴,被迫出走家庭之后如何以自洽、向上的努力重建自我生存秩序,透视以卫巧蓉为代表的现代中年女性的生存境况与情感成长之路。
关键词:蔡东 《伶仃》 中年危机
蔡东自发表《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后经过一年多的休整期,2018年年初起接踵发表了五篇小说,主要关注个体自我价值的进化与确认,肯定人的抗争性与成长性,作为女性作家,她又从身边出发,为现代生活中的女性群体觅得一个发声的渠道,这系列中的《伶仃》典型地体现了这样的关注视角。《伶仃》接续了中国文学对于弃妇群体的关注,所描述的正是一个被家庭所抛弃的中年妇女形象,但她不同于过去在文本中常见的蓬头垢面一蹶不振的弃妇形象,而是一个在社会与家庭失去平衡后,短暂地迷茫,又努力达成心灵自洽的“弃妇”,在自我放逐中回归确认自我。
短篇小说《伶仃》讲述了年过中年的卫巧蓉因丈夫出走,婚姻而被迫失败,不甘失落于丈夫的离去、家庭的分崩离析,从一路跟踪、窥视前夫到与自我和解,接受一个人独自生活的事实,重建个人的生活秩序的故事。小说展现出现代快节奏生活下女性不仅面临社会普遍的生存压力,并且作为弱者遭受着来自家庭的中年危机;显示出一个丧失了习以为常的情感寄托的顽强生活者,如何在“隔膜”丛生的现代人际关系中重建自己的安全领域,以女性的敏感感知温暖,从中国女性惯于忍与熬的传统美德中汲取自洽、向上的力量,适应作为个体而存在的生活,重新觅得心灵的平衡。
一.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失败
現代都市在带给人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取消了许多人与人获得无间交往的机会,日渐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情感困扰。自现代都市进入文学写作视野起,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就成为写作者乐此不疲探讨的话题,鲁迅的《故乡》首次注意到人与人之假冒“可悲的厚障壁”i,叶圣陶的《隔膜》通过主人公“我”在各种逃离不开的日常生活片段中与某某兄等人看似熟稔实则无意义的交谈,写出了人际交往的敷衍。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下,现代人越发察觉到人是以一座孤岛的形式存在,不仅面临着延续千百年的乡土中国的分崩离析,现代都市又未能建立起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们越发难以获得心灵的零距离温暖。当生长在城市的卫巧蓉逃离城市,来到尚未沾染现代社会浮躁生气的小岛时,她发现地域已经无法隔绝“隔膜”的蔓延,“隔膜”不仅存在于城市,也存在于远离都市生活的小岛,对过往人际关系的放弃并不意味着能够毫无负担地开始与人建立新的联系;“隔膜”不仅横亘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间,也在自以为亲密无边的枕边人之间划出鸿沟。“隔膜”以它无处不在的存在,宣告了卫巧蓉在社会与家庭的关系上的双重失败。
过去卫巧蓉在城市中常常能捕捉到看似相处自然的同事、亲友和服务员脸上“一闪而过的游离和厌倦,那种实际上对你不感兴趣的疏远,那种掩藏不住的对周围人事的漠然”,对于这些人来说,交往的目的并不是与人相交、建立联系,并不是渴望能够获得温情,而仅仅是为了勉力完成交谈的任务以获取一些便利与利益。这样的境况在卫巧蓉尾随前夫来到小岛后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隔膜”不是城市独有的,它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到来早已席卷了小岛。哪怕是看似熟稔的房东兼茶友,卫巧蓉也没能与他们坦诚相见。这并不是个例,现代人已经习惯这种透明屏障一般的“隔膜”的存在。老吴两口子随和的口吻下也藏着现代交际的准则——保持距离:两口子对待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亲切自然,然而在等距离亲密背后是不动声色的疏离情感。卫巧蓉在都市中随处可感受到他人对她的拒绝接纳,来到小岛之后,老吴两口子作为她日常接触最密切的对象,也依然如此,只不过罩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现代人际关系中的“隔膜”是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议题,过去卫巧蓉将家庭视作情感的港湾,而忽视了这个始终存在的人际危机。当“隔膜”蔓延至她的家庭,浮现至生活的表层,在她与丈夫之间划出一道鸿沟的时候,她被迫正视这无处不在的“隔膜”,追问这“隔膜”怎么会将自己丝丝缕缕地缠绕、捆绑、束缚,将自己隔绝于家庭、社会之外。
假如说和他人的联结被阻隔,给卫巧蓉带来的是无处不在的陌生感,那么丈夫的出走则彻底打破了她的美梦。她失去了自以为牢固的家庭。丈夫毫无负担地离开家庭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徒留她在臆想和谣言中过活。波伏娃的“第二性”理论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尴尬地位:“她是家庭主妇,妻子,独一无二而又模糊的母亲。”ii卫巧蓉作为女性因家庭获得了一定的社会价值,又难以脱离家庭寻找独立生活的意义。她的女性身份限制了她在家庭与社会中角色的转换与扩张。当丈夫在孩子长大后认为自己已对家庭尽到了应尽的责任与义务,随后执意抛下家庭去选择自己新的人生时,卫巧蓉不愿相信:熟悉的爱人不仅带走了爱情,且使家庭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支撑。家庭束缚了卫巧蓉,且以它的坍塌促成了卫巧蓉人生信仰的坍塌:“曾是彼此在世上最亲近的人……怎么突然走远了?”当卫巧蓉走到了自以为人生的绝境处,她也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一条救赎的路。
二.绝境处的自我救赎
救赎的完成无非是两个途径,一是他人伸出援手;一是自我努力实现救赎。当卫巧蓉面临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危机时,社会以真实存在的“隔膜”拒绝了援助,所撒播的温情不过是隔靴搔痒式的安慰。她最主要的人生信仰——家庭业已崩塌,母亲去世,丈夫出走,女儿也已独立。家庭不再能够给予她生活的信心与支撑。但她并没有一味向下沉沦,而是以自己敏感的心性去感知陌生人与亲人赋予的温暖,在个人与周遭风景无声的沟通与浸润中治愈伤口,以不惊动他人的努力生活来促进伤口的愈合,从而实现了自我的救赎。卫巧蓉的一系列努力,显示出她作为一个普通人在生活泥淖中痛苦、无助、挣扎、前进的痕迹与成果。
正如叶圣陶给好友顾颉刚的信中所说:“人心本是充满着爱的,但给附生物遮住了,以致成了隔膜的社会。”iii“隔膜”隔绝了卫巧蓉与他人亲密无间的交往,但卫巧蓉并不是在“附生物”面前畏葸不前,她没有被交际的距离感所阻隔,也没有因此放弃与他人的沟通与交往。要摆脱困境也不是只有强硬地除去“附生物”,打破“隔膜”这一条途径。有距离的相处反而为她提供构筑自我舔舐伤口空间的机会。在被无处不在的“隔膜”阻隔了畅快的交往后,卫巧蓉将“隔膜”视作自己的保护伞,小心翼翼地划出一片安全区域,在此区间内重建自我生活的秩序与对他人的信赖:在保持距离的邻里关系中祝福赞叹吴氏夫妇的幸福与没满,在过往数十年家庭信仰分崩离析之后重建并保持自己对美满家庭存在可能性的信任与追求,并从吴氏夫妇身上认识、学会另一种夫妻相处模式;虽然没有办法即刻习惯将同床共枕多年的丈夫从自己生活中剥离,但也改变了以往歇斯底里的态度,仅仅隔着人群的距离从出走的丈夫身上汲取温暖,将远距离的追随与陪伴当作是家庭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以获取成长的过渡期;而乐高老人作为被卫巧蓉帮助的对象,实际上也成为她的治愈剂,乐高老人酷似亡母的相貌拉近了她对乐高老人的心理距离,得以试探性地放下戒备与乐高老人交谈、相处,从中获得了另类的家庭温暖,让她在小岛上仿佛得到了另一处家庭的根系养分。与乐高老人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的身份关系使得卫巧蓉毫无负罪感地筑起保护自己的藩篱,将与她的相处时光当作是难得的放空、放松。在这一过程中,来源于周遭人的温情瞬间都被卫巧蓉精准捕捉,并从中汲取能量。
卫巧蓉逐渐明白,家庭破碎不等于幸福破碎,不仅丈夫就在触手可及之处,女儿也始终将她牵心挂念,已经逝世的母亲仿佛以另一种身份、另一种形式陪伴于她。卫巧蓉捡拾着散落各地的家庭成员的情感碎片,以寻找新的情感寄托。她在养老院里遇见同样被家人遗忘的乐高老人,相似的遭遇使卫巧蓉卸下心防,来自母亲的力量温柔地包裹着她,令她再次交付出柔和的情感,并在付出的过程中重新感受到自己对于家人、对于他人的价值。在她忍受腿脚不便的病痛折磨,且不能再以追踪丈夫作为精神寄托时,得以将乐高老人视作暖源来进行愉快的幻想。卫巧蓉身体里还有女性与生俱来的爱的能力,她将乐高老人当作母亲一样耐心陪伴,又以爱的目光注视女儿长大,不仅爱女儿一如既往秀气的脸庞,也爱女儿“眼角的一小簇皱纹”,用始终如一的包容与耐心去对待亲人。女儿长大后,又从这传承里接棒了亲情的力量,用陪伴抚慰卫巧蓉。卫巧蓉从这一系列事件中提取温情,感受到亲情的支撑以及家庭对自己的需要,因而决心要“磨”过难熬的日子,用“做女儿的帮手”这一理由来重建她对于家人的意义。
小岛单纯的生活环境不仅为卫巧蓉提供了现实意义上的避难所,卫巧蓉同样以自己坚韧的习性将小岛上的风景过滤为自己精神上的养料。正如柄谷行人所说的“风景”也属于意识形态,是有意义的,它始终与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相连,是“作为人类疏远化了的风景之风景”才得以存在。卫巧蓉在被迫与外界相阻隔的境地之下,得以将更多的心绪投入到身边的景物之上。对这些景物,卫巧蓉不仅是简单的“观看”,而将自我的情感投射到其中,且以小岛的景色治愈自己的心疾。初来到小岛时,卫巧蓉“背负着一座地狱”,小岛上不同以往的人文风情也不能引起她丝毫的震颤。但是三个月的小岛生活让她理清了思绪,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事、景的美消融了附在她心上的“附生物”,万物的色彩重新进入她的视野。就连小岛普通的清晨,卫巧蓉也努力从中感受生命的苏醒,不管是光线、树影还是林间的小动物,在卫巧蓉眼里都鲜活生动,最是吵闹平常的菜市场也集结了世间所有明丽的色彩。
三.独立生活的自主选择
卫巧蓉三个月的小岛生活不仅是她对过去习以为常的家庭秩序的告别,也意味着她从依附到独立的成长过程的完成。成长源于旧秩序的打破,卫巧蓉被迫甩出常规生活,这为人到中年的她提供了新的成长契机。对于人过中年的卫巧蓉来说,丈夫的出走不仅使她失去了爱人,还失去了过去数年她视作归宿又辛勤供养的家庭。“家”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并规定着家庭成员的主要行为模式。即使历史车轮迈进家庭观念薄弱的现代社会,“家”也仍然是重要的社会组织,被视为是一种稳定的集体性的结构。因此当卫巧蓉意识到与自己联结最紧密的组织已经崩塌,第一反应是拒绝接受这个现实,并开始义无反顾的追寻之路。即使这样日复一日的跟踪并不能得到什么结果,她也没有上前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勇气,只敢畏畏缩缩地在背后观察丈夫的一举一动。以窥私欲的满足,来制造岁月静好的假象。
卫巧蓉以窥私来治愈自己失去家庭的不甘,又不仅仅沉溺于这样畏首畏尾的生活。在卫巧蓉的身上有着中国女性固有的坚韧与敏感,她的处世哲学也显示出与百年前的尚洁“破网”哲学的共通性:当她(们)走到“绝路”时,承认并接受命运,但又以“化动为静的,呼呼又生气的‘沉默’来对待命运”。卫巧蓉看似脆弱的精神状态与神经质的行为背后,实际上贯彻着儒家的传统思想。她既不敢违抗命运的轨迹,又不愿意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在面对生活带给她种种苦难时,以内在的顽强与韧性重新建立生活的种种可能性。在家庭信仰崩塌的时刻,卫巧蓉仍然努力生活,认真地在她和徐季构成的真空小世界屏障内观察世界、和他人相处。卫巧蓉的接受和沉默,蕴含着坚强与洒脱。她的窥私行径,矛盾地呈现了她质疑的勇气和害怕得不到理想回答的懦弱。在努力汲取来自外界的温情的鼓励下,卫巧蓉完成了由犹疑、求而不得到反求诸己的转变:她学习承认分别,也学习承认生活破碎的必然,用“熬”的方式宽慰自己曾经的纠结。最终卫巧蓉放弃了潮湿但适合窥私的北居室,在南居室里任由丰沛的阳光驱赶去潮气,将自己的灵魂与躯体重新放置于阳光之下;接受自己寡居人的身份,不再强求家庭的圆满和亲人的陪伴,将拐杖随身携带聊以作伴,坦然承认与丈夫缘分已尽。种种选择,显示出卫巧蓉由执著于丈夫的陪伴到甘于一人的积极生活,宣告了卫巧蓉个人成长的完成。她终于放下了过去背负的沉重的情感包袱,决定去探索未知但充满了希望的未来。
卫巧蓉的小岛之旅,显示出她作为普通人是如何不断与生活抗争的,她通过努力对抗生活的崩塌与不幸,使自己摆脱了生活与情感的双重困境,呈现出一个失去家庭信仰和情感支撑的中年女子救赎自我的过程。她以心灵的成长宣告了自我秩序的重建,展示了在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家庭危机下,以女性的韧性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危机。
参考文献
[1]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08.
[2]刘悠扬,蔡东.“自甘退步者”群像正浮出水面——蔡东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9,06.
[3]李俊国.方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家族的命运书写[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5.
[4]雷锐.一尊闪耀着圣洁光辉的瓷像——析《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形象.名作欣赏[J].名作欣赏.1986,02.
注 释
i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7页。
ii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58页。
iii叶圣陶:《<火灾>序》,《叶圣陶集》第一卷,第353页。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