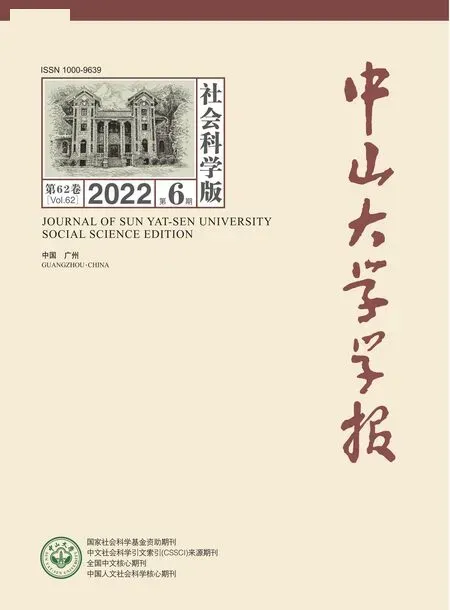编 后 记
本期含“名家特稿”“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亚欧文化研究”“打造新时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专题专栏,相关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19篇。
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民歌,其地位和价值虽有尊卑与高下的变化,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歌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还是相当强势的。所以以民歌或半民歌的方式作为传播手段,也就成为一种古代文人比较自觉的选择。汉乐府名篇《陌上桑》便堪称这一方面的典型。作为美丽、智慧、忠诚的采桑女子的形象代表,秦罗敷承载了民歌诸如身份、职业、题材等的若干重要因素,由此而深入中国人的记忆深处。但一如称《云谣集杂曲子》为民间词集而带来阅读上的诸多困惑一样,若秦罗敷其实也是融合了多种身份的一个复合体。采桑似乎并不构成秦罗敷的主体身份与生活来源,“罗敷喜采桑”,这个“喜”字已经委婉写出秦罗敷采桑的娱乐和消遣意义。而且“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又岂是农村女子的日常妆扮?而行者、少年、耕者、锄者的反应,也足以见出秦罗敷的出场因为带有偶然性,才能一时惊艳如此,近乎扰乱了社会秩序。故而关于《陌上桑》的诗歌的定位在民歌的基础上,也颇有如游国恩等提出不同见解者。赵敏俐此前就发表过关于此诗的专题文章,本文则从汉代“流行艺术”的生成,进一步探讨其娱乐和表演等特征,推进了相关学术史的发展。
作家都有自己的籍贯,或有流寓之地、临居之所,而创作无论如何“心游万仞”“精鹜八极”,也终归要落于一定的地域,这是地理学能够介入文学研究的背景之一。但这种背景实在是有着强与弱的不同,强者固可以不论,弱者则也近乎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所以,以地理学的视角介入文学研究注定是有层级、有限度的,如果因此而过于放大地理的影响力,也是不客观的。只有精准地把握好文学与地理关系的“度”,才能使相关问题的解决更为到位而彻底;一旦过犹不及,则容易遮蔽了文学的自身意义。换言之,要考察作家作品的文学地理意义,必须有充足的地理文献支持、明晰对应的历史文化对勘与独特地域性感情的加持,只有此三者能深度而自然地结合,才能彰显作家作品的深层意义和特殊价值,否则就流于地理与文学的简单叠加而已。王兆鹏、肖鹏深得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理念、方法与路径,他们近年围绕若干诗词经典联袂做了不少有深度的现场勘查,同时紧密关联带有地域特性的历史掌故与创作传统,因此他们的考论结果往往能一新世人耳目,他们的研究也因此在诗词研究上带有一定的范式意义。本期刊发他们考论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一文,便是在这一理念之下的最新成果。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专栏在本刊刊出多年,影响日甚。但冷门绝学,每推进一点也委实不易,这大概是其之所以“冷”“绝”的原因所在。本期刊出关于商周“作册”、岳麓书院藏秦简以及周家寨汉简日书《五龙》的三篇研究文章,或源流梳理,或文字考订,或理论分析,各擅胜场,值得关注。
现今的珠江三角洲,大致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空间重合,是世界级的经济文化建设湾区,也是现代文明的集中发力区和展示区。但是往前追溯一百多年,珠三角的工商业此时得以长足发展,政治变革也一度在此风起云涌,这都是明面上可以清晰观察到和深刻感受到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引领全国的格局和气度。但暗地里的珠三角却也延续着盗匪横行、地方武装势力对基层社会恣意妄为的行为。作为盗匪的主要组织形式,“堂口”一度在珠三角林立,盘踞一方,也称霸一方,实际上正是当时不稳定的政治社会为他们的非法地域势力提供了空间。本期刊发何文平梳理清末民初珠三角的堂口的分布、源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势力情况,可见百年之前曾经留下的历史痕迹。历史的物理印记或许会被雨打风吹去,但氤氲在历史深处的记忆却是不可磨灭的,历史总是在记忆中复活,在复活中再成为历史。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有循环的历史才是富有生命力的。
宋明理学的阐释空间虽然有大致的维度,却难以直达边际,这种恍惚有尽头却又行走无尽时的状态,可能正是理学的魅力之一。王阳明近年很热,热到仿佛有一点逢人不谈王阳明、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感觉。其实如果王阳明真的人人似乎触手可及,甚至稍翻卷页,便敢信口开讲,那大家遇到的很可能是假的王阳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哲思的浩瀚从来是需要专业来摆渡的,岂有缺乏哲学根底而能直截本源的。这种极高的悬格倒不一定是出于哲学的傲慢,而是哲学的底蕴以及在阐发、接受中意义的丰富与流失,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换言之,哲学上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带有极大的普遍性。王阳明思想的变与不变,就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尤其是在传承中形成的与王阳明思想的离合之处,就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了。但无论怎样的纷乱,走向本质的努力总是需要坚持的。王阳明心目中的“至善”就是无善无恶,消除了善与恶的现实界限,而以本性的至善来一统善恶,就成为方以智思想的新境,当然这一新境也部分地承传了朱熹与胡宏的思想。廖璨璨将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说作了历史的梳理,并以更富有学理性的认知串联起从王阳明到方以智的思想脉络。
“亚欧文化研究”专栏在本刊设立三年以来,发表了一批中外学者关于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文章,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研究格局。这大概也是综合性大学学报开设的第一个这方面的专栏,形成相关的学术合力则是本刊的初心所在。数字人文研究近年在国内似有风起云涌之势,虽然“数字”与“人文”在传统的观念里似乎不无相隔之处,但作为新时代人文研究的新范式,“数字人文”还是多少让人充满了期待。郝岚结合谱系与文学、发生学与新谱系学三种人文研究方法,对当代数字人文研究范式作了一定的批判性思考。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在创办之初也曾经历过普及一般性学术还是研究高深学问之争,当然,最终在王国维等人的坚持下,高深学问成为国学研究院的发展方向。知识与学问当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叶隽以严复、辜鸿铭、王国维与陈寅恪为对象寻绎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及其制度依托,在反思民国学术的过程中,展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若干复杂面相,其视野和眼界带来了不少新人耳目的地方。
本期推出的“打造新时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专题,讨论的核心是人类学视野下的全球健康治理。在持续了三年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背景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实已经充分呈现在眼前,构建这一共同体的紧迫性也充分显露。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不只是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巨大威胁,还包括对经济与文化等全球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本专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中国经验和行动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