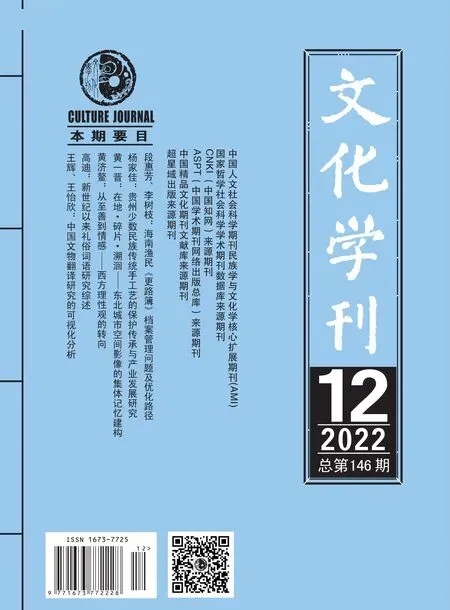双雪涛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阐释
刘瑞林
一、引言
双雪涛从2009年开始发表影评,2011年双雪涛的处女作《翅鬼》获得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这标志着双雪涛正式开启了他的小说创作之路。2016年,双雪涛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和《飞行家》。2017年成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最具潜力新人。他的小说《北方化为乌有》在2018年获得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猎人》在2020年获得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论家谢有顺在第十五届 “华语传媒大奖” 的授奖词中评价双雪涛为 “有北方的声口、气息, 语言也像北风般的简净、峻峭。城市的历史,个人的命运,自我的认知,他者的记忆,见证的是一代人的伤感和宿命、彷徨和执着”。
二、意象叙事彰显人民情怀
(一)湖
意象是双雪涛在进行情感诠释的时候经常使用的一种载体。双雪涛文本当中的意象阐述是想要“表达”和“暗示”一定的“看不见的东西”。意象叙事的目的是呈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借助“意象”这一象征将作者的内心情感实现串联。看过双雪涛作品的人都知道,在双雪涛的艺术作品当中湖与湖水是时常出现的,湖与湖水被作者幻化成了一个得以逃离现实或者摆脱固定叙述的空间。例如:在《天吾手记》当中,湖成为李天吾回忆摆渡的载体,在神秘的湖里有台北解答密语的场景,也有东北抓捕罪犯的场景。在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中,庄德增和傅东心在人工湖相遇,庄树和李斐在人造湖结束情感纠葛。人物不同、情感线条不同,却最终落点都在平静的湖面。结尾烟盒在水上飘着,烟盒上的塑料在阳光下泛着光,北方的微风将它吹向远方,又以看似平静的湖面做结尾,将整体的小说故事感情线实现了巧妙的循环。在《光明堂》中,湖的出现是最为密集的,廖澄湖疯后掉在湖里淹死了。“我”梦里的父亲和廖澄湖也是反复在湖边出现,一直到结尾处湖中出现的怪异的大鱼,仿佛“我”一下子看到了湖底的众多景象,解开了迷惑已久的事件的谜底。这里的湖不再是湖,是一定程度上“我”的情感寄托,“我”摆脱情感牢笼的钥匙[1]。
(二)雪
除了湖之外,雪也是双雪涛常用的意象。在《光明堂》中,如同粉末的雪象征着父亲的离开,傍晚磅礴的大雪渲染着林牧师布道的氛围,雪花纷飞之下,林牧师被捅,他鲜红的血液与洁白的雪花交相呼应,情感尤其突出。作者用雪的变化完美地诠释了情感的转折。文章最后,我和姑鸟儿(原名李淼)去寻找真相,时大时停的雪与文章叙事交相呼应,最终,雪停了,天晴了。
(三)破败的工厂空间
作者在《天吾手记》的后记部分曾经写到“我感谢我家乡每年提供的寒冷本身,因为寒冷使我更坚定地去接近温暖的东西。”东北的老工业区虽然没有了原有的生产功能,也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对于在东北的老工厂当中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工人来讲,他们对东北的老工业区有着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来自于他们曾在这里奋斗,曾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集体生活。所以,在双雪涛的作品当中,他所诠释的工厂空间是工厂区域范围内工人的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力量。所以,在双雪涛的记忆当中冰冷的工厂空间是有温度的,那里有他美好的记忆,在他的记忆里“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是他与自己的祖辈和父辈具体的三代人的生活。工厂的破败与曾经的美好记忆形成鲜明的对比,强调着记忆的美好和在记忆当中工人群体的团结、奋斗和拼搏,呈现的是一种生存的自信和勇气[2]。
(四)火车
在双雪涛的作品当中,火车是威严的,因为火车是舶来品,火车的出现寓意着我们国人富强的梦想。火车又是承载着巨大的想象空间的。因为火车可以打破人的空间想象,带领人“离开”或者是“逃走”。于是,《跛人》中火车带“我”和刘一朵逃离了北京。《光明堂》中林牧师死后,三姑信仰崩塌,随绿皮车离去。《大路》中女孩儿自杀后,“我”艰难地活着,是火车将“我”带到了“最远的地方”。火车的出现寓意着“离开”,也代表着新的希望。“我”虽然时刻都想着能够乘坐火车出逃,但是“我”的精神寄托在火车的另一端,那里是“我”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故乡,是“我”的灵魂和肉体能够得以稳妥寄托的复归之地。
意象叙事明在写实,实在抒情。双雪涛就是使用这种朴实的写实方式表达着对于普通老百姓和底层平民的关怀。在虚与实的不断交错当中,寄托着对东北的深情和敬仰。
三、以幽默的谈吐传播东北文化
(一)调侃式幽默
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幽默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喜好自夸,很坦诚地自嘲,用自身独有的幽默方式与这个世界打着交道。一定程度上调侃式的幽默既是作者自我保护的一种意识,又是化解和缓和个体与现实矛盾之间的润滑剂。例如:《平原上的摩西》当中,从李斐的自述我们可以知道李斐有着非常悲惨的童年经历,在李斐的记忆里是幼儿园严酷的管训和一个又一个挨不完的巴掌。但李斐在看到别人有妈妈接的时候,调侃道“你要是倒霉,回家也是这一套。”童言无忌,看似幽默,却让人莫名的心酸。也体现着李斐作为一个东北人的坚强和乐观。在《聋哑时代》当中“我”遭受了校园暴力,被欺负得很惨,回家还要生火做饭,“我”很委屈,流了眼泪,作者描述到“我的眼泪冲坏了我脸上完整的鞋印”,这也让“我”又委屈又觉得好笑。调侃式的幽默好像让暴力下的肉体也没有那么委屈和疼痛了,这是东北人骨子里的乐观和坚韧。老师说“我”“扶不上墙”,我反驳道“老子从小翻墙就不要人扶”,作者三言两语看似简单地描述着自己童年的经历,看似“鸡同鸭讲”,却是用简洁和幽默默默地对抗和消解着伤人于无形的语言暴力。东北人天生自带喜剧因子,但却是一定程度上自我保护的行为,在幽默的躯壳下,是东北人坚韧和乐观的心态。
(二)好坏颠倒式的冷幽默
冷幽默指的是在社会环境里对于常规价值观和道德观异化而产生的一种幽默,而这种幽默反而常常引发人的深思。与现实的好坏、美丑、正常与不正常相悖的审美逻辑,看似“非主流”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着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预示着新东北人对未来的展望和期待。《无赖》当中,“我”家被迫拆迁举家投奔无赖老马,在母亲的眼里老马就是一个喜好酗酒的无赖,还喜欢当着孩子的面讲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他还将自己曾经偷盗的事件常常拿出来说,仿佛这是他足以炫耀的“资本”。老马粗俗却也有着温柔的一面,就是这个常常令人瞠目结舌的无赖,却给过“我”从未有过的温暖。老马被“”误会,却用酒瓶敲碎脑袋的方式帮“我”拿回了台灯,守护“我”一个少年求学的梦。老马看似好色、大胆,实则是他不被世俗常规接纳;老马虽有偷盗的前科,那却是在当时社会不偷就要饿死的无奈之举。“我”也“期望”“我”成为“无赖”,因为“我”不想去坚持无所谓的坚持或者成为百害而无一利的人类。除了老马,作者还创作了许多“无赖”的边缘人形象:戏痴吕东、棋痴父亲、疯子等等。对于这些人的描写作者完全打破了常规的审美,真实却是在褒奖东北人的真性情[3]。
(三)斥拒式幽默
斥拒式幽默就是利用人物之间的关系冲突,幽默地呈现温情与对峙的局面。《聋哑时代》当中,“我”的父母下岗了,要去学校门口卖苞米,“我”感到很恐惧,因为生活条件的急速下跌,让“我”很恐慌,对生存的恐慌。父母会因为“我”的一句客套话与“我”抱头痛哭。“我”的客套话,反而让父母觉得“我”懂事了,这让“我”很莫名其妙。还有在《跛人》中,“我”落榜了,父母问“我”有什么计划,“我”搪塞地说要去肯德基,父母却说是不错的计划。父母希望“我”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是现实却让“我”对未来迷茫且不知所措。父母的艰辛付出给“我”莫名的压力感,也增加了“我”与父母之间的隔阂。这是老一代与新一代的矛盾冲突。作者表面用幽默的语言在诉说,其实是一种冒犯式的叙事风格,也将父与子之间的隔阂和冲突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很抗拒这种混沌的生活状态,但“我”也关切着东北个体的困境和无奈。
四、独有的小人物的“罗曼蒂克”
(一)小人物的浪漫主义气质
双雪涛所塑造的人物一般都有相对独特的一面,而这独特的一面大都是小人物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们或许生活得并不如意,但却有着自我的偏执和信念。在《大师》《平原上的摩西》《剧场》这些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当中,从时代的角度看他们可能是失败者,但对于作者而言,其意图并不在于从道德的层面去评判这些小人物,而是从另一面去彰显这些小人物的信念,从而引发读者对生命生存价值的思考。在《大师》中父亲是个棋痴,他在下棋时“看淡胜负,不贪图名利”,在棋外也总是讲究双赢,给足对方退路。看似父亲是生活中的“异类”,但这也让父亲与和尚之间的生命哲学又多了几分诗意与暧昧,父亲对于自我的坚守是父辈留给我们下一辈不竭的精神动力。我辈日益平庸,是对上一代精神的缅怀,也是对理想主义信念的挽歌。在双雪涛的作品当中大多数的“现代人”都是孤独且失意的,游荡于社会,一事无成,但精神世界很丰富,有理想,有抱负,爱思考,虽不是社会主流,但是他们积极努力地生活着,生存着,却又总是会掉进无尽的深渊,令人感慨,却又充满无力感。一定程度上这是人的生存与现实的抗争,本身我们人类就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体。作者探寻着理想主义者想要寻觅的隐秘角落,又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光和热,小人物浪漫主义情怀的消逝,也是现实悲剧性的胜利[4]。
(二)虚与实的奇幻游弋
双雪涛的作品采用了别样的透视方式。他善于挖掘那些隐蔽的,不被关注的角落,采用破碎的叙事方式在虚构与想象中发人深思,彰显艺术的浪漫气质。《跷跷板》中,“我”和病床上的刘庆革以交谈展开回忆,在回忆里“我”想要寻找埋葬在跷跷板下的尸体,却意外地发现尸体“死而复生”,跷跷板下埋葬的究竟是谁,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尸体身上破碎的工作服却将“我”的思绪拉回了那个机器轰鸣的时代。《火星》当中,小说的前半部分很常规地叙述魏明磊的生活及魏明磊与高红的相识,两年后两人相见,寒暄中高红拿出一封信,信中的内容又在虚与实之间让人难以分辨。小说看似平淡无奇,却在虚与实之间突出了人物面对现实的无力感。虚与实的矛盾冲突让平庸的故事带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五、对于梦想的坚持与自由
(一)为被损害的故乡人重塑形象
双雪涛曾自嘲自己喜欢无休止地写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双雪涛出生在东北,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所以,他的作品绝大部分也与东北有关。双雪涛的创作根据地就是东北,再具体一点就是东北沈阳的艳粉街。双雪涛笔下的艳粉街就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带。但很多人从这里走出去,很多人又把这里作为自己的退路。双雪涛在小说当中明面上在描述东北的艳粉街,实际上在阐述这里的人情世故。在东北这群人里浪漫中又带着悲观,冷峻中又体现着无尽的温柔。有很多人和事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遗忘了,被忽视了,但是他们却是现实存在的,挣扎过,努力过。那些籍籍无名的人也有着无尽的精神力量和抱负。在《平原上的摩西》中,作者“就是想反映一点东北人的思想和习惯”,书写一些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屏蔽的事物,作者颇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揭开历史的迷雾,还原真实的人与事,将很多无名者公布于众,这些无名者的精神也感染和感动着更多人。《聋哑时代》当中的父辈们是那个时代生命的缩影,在历史的洪流中,除了权与势,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努力地生存着,他们坚毅、勇敢且隐忍[5]。
(二)让爱与梦想在卑微中重生
在双雪涛的作品中有为故乡的人和事正名的意味,还有对心灵世界的尊重与关怀。虽然那些在现实中坚持了自我的人大都沦为了失败者,但是每一个人还是应该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这是在正义匮乏的世界,失败者努力寻找正义的依据。《聋哑时代》里,李默不辞而别,他在短信里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去生活,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灵魂交出去,它就会消灭你的肉体。”艾小男坚定地信奉一生只有一个爱人,但她离开了自己唯一的爱人李默,她希望他幸福,好好活着。这是对爱的诠释,也是对尊严和自由的向往。双雪涛也曾说“在我的小说当中有很多执念,可能是关于人的,比如尊严和自由。”但是在他的笔下那些被城市所抛弃的人,是没有尊严和自由的。尊严和自由的缺席也是对那个时代人性的凸显。张扬尊严和自由,正是双雪涛作为一个作家一直担当的使命。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双雪涛的作品看似在描写一个一个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在大众的眼中可能是失败的,边缘的,“非主流”的。但是他们也勇敢过,隐忍过,为自己努力过,他们是那个时代生命的缩影。双雪涛用东北人独有的幽默和虚与实的交错纠葛,重塑了一个一个鲜活的东北人形象,让爱与梦想在卑微中实现了重生,发人深思,引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