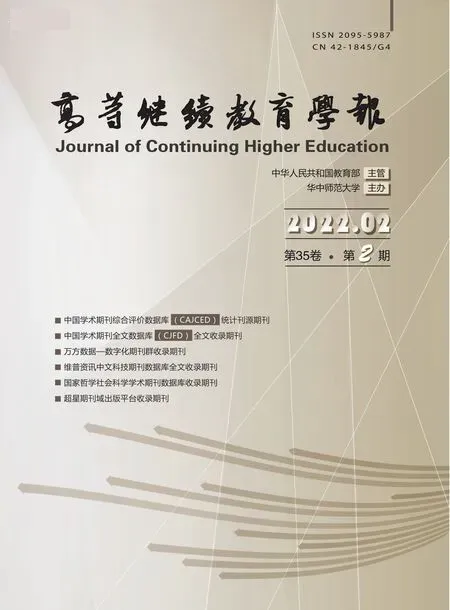发达国家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特点及启示
刘凤存,董菲菲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图书馆,山东 滕州 277599)
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现代社会,国家之间的竞争愈发体现为知识、科技、创新尤其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特别是高精尖工匠型人才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大小的重要标志。
“职业教育是培育工匠精神的摇篮,作为职业教育中坚力量的高职院校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培育工匠精神的重任”。[1]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经济腾飞对工匠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先导,开始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高职教育。与之相适应,相关专家学者也逐渐将研究关注点转向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研究得以全面展开,在价值定位、培育环境、培育目标、培育课程、培育模式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构建了特色鲜明的工匠精神培育体系。
一、发达国家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特点
(一)赋予工匠精神培育的特有价值
大多数发达国家认为,工匠身上具有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企业行业制胜的法宝。这是因为,所生产产品如果没有匠心、匠技、匠艺和创新元素的有机融入,就不可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很快被淘汰。
严肃、规范、细致有时甚至近乎刻板的敬业态度和专业精神养成了德国工匠的责任意识,成为德国企业生产设备之精密、制作之精良、生产过程之精细的秘诀,这种长期专注于某个领域某个产品使之获得国际市场“隐形冠军”的称号[2],有力保证了所生产产品成为高质量品牌,助推德国制造业成为世界翘楚。日本工匠素来就秉承卓越匠心的态度和对工作执着热爱的精神,日本企业一向信奉精益求精和追求细节理念,使所打造的精巧产品向来以精致的机械结构、精湛的技工技艺、精密的生产工艺而闻名于世。他们认为任凭质量不过关产品流通到市面上是一种耻辱,与收入金钱多少没有关系,从而有力塑造了日本技术“高精尖”、日本产品“品质一流”的国际形象[3],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领跑者。瑞士工匠以满腔热情、极为用心、坚定执着的匠魂精心打磨、细心雕琢机械表每一道工序和每一个发丝小的构件,精心提升零件精密度和复杂度,专注产业创新和升级,专心研发复杂的新工艺和新产品,精益求精地对待产品质量,使瑞士钟表成为世界钟表行业领跑者,能够傲视群雄而成为世人追捧的奢侈品牌。
(二)营造工匠精神培育的和谐环境
发达国家大都认识到只有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和谐氛围,将个人荣辱与产品品质挂钩,给予工匠相应的社会地位,才可以有效提升学生敬业、乐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才能使工匠精神在全社会发扬光大,提升工匠精神的培育效果。
一是社会舆论环境。以严谨著称的德国早就把“匠心”渗透于国民内心之中,将成为大国工匠作为最令人羡慕的荣誉;美国让工匠的工作有舞台,生活有尊严,使之常年活跃在全球工业创意、商业模式创新最前沿[4];在日本,“匠”常常被看作是荣誉的象征,工匠会得到令人敬仰的社会地位。二是法律制度环境。德国建立起严格的行业标准和规章制度,并能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有效实施;美国法律严格规定不准进口有坏点的产品,让诸多国家加大了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管理力度;日本从法律上明确工匠在技艺上要精益求精,保障产品质量。三是校企合作环境。德国规定企业和高职院校同时对学生进行教育,但是实习必须按照程序操作的严格要求在企业完成;美国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专项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有效吸引了企业优秀员工加入校企合作队伍;英国明确规定高职院校必须与企业深度合作,在开设课程之前高职院校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调研,企业也会派人在行业技能委员会任职,确保了工匠精神培育质量。
(三)厘定工匠精神培育的特色目标
发达国家均强调只有从“德”的工匠品质和“才”的工匠技能这两个维度来强化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才能够圆满完成工匠精神培育任务。因此,发达国家大都以树匠心、立匠德、励匠技为培育目标。由于各国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关注侧重点不同,工匠精神培育目标也必然表现出各自特色。
德国为了保持制造业精度高、质量优、技术超前等优点,以纵横交织的“职业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目标。从纵向上来看,包括基本职业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关键能力);从横向上来讲,基本职业能力包括与具体职业相关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而综合职业能力(关键能力)包括超越了具体职业、专门职业技能与职业知识范畴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5]美国制定了以“综合能力为中心”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不仅掌握专业知识、动手操作能力,还应该具备交流合作的能力、探索创造的能力等,具体来说由知识(相关行业的专业理论领域)、态度(职业动机、情感和理想领域)、经验(实训活动领域)、反馈(测评、评价领域)等四个维度所组成。日本政府认为,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高职院校必须以“职人精神”为目标来培养未来建设者,要求所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精湛的技艺,坚定的理想信念,爱岗敬业、精益求精、专注极致的职业道德,完美的个性人格、独立自主的品质以及善于创新、勇于挑战、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意识。[6]
(四)开发工匠精神培育的特定课程
发达国家普遍将确定课程内容作为工匠精神培育过程中的最关键环节,课程开发的质量和水平既决定了工匠精神培育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工匠职业素质的高低。课程内容的确定大多以未来工作岗位为导向,瞄准特定的工作岗位需要来实施。
为了增强工匠精神培育实效性,德国开发了基于工作过程的系统化课程,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领域为根本原则组织与职业相关的教学内容”,注重工作行动的整体性,在系统化的基础上将学习内容和教学情境有序化,强调典型工作情境中的解决实践问题能力。在美国,由若干资深从业人员组成专门委员会,将某一个特定职业目标进行工作岗位和工作职责两个层次分析,分别得出综合能力和专项能力,形成能力汇总表。然后由教学专家来确定具体教学单元或模块,将教学单元按照知识和技能的内在联系进行顺序排列,将若干相关单元组成一门特定课程。[7]日本既通过“道德教育”(“爱国心”教育、“心”的教育、个性教育、劳动教育、国际化的日本教育)来影响“职人精神”,也采取寓于“专门德育”(“德育课程”和“德育活动”)中的“职人精神”培育和寓于各学科中“职人精神”培育方式进行,还利用“职业生涯教育”课程来对学生进行“职人精神”培育,其指导思想、内容、措施均与“职人精神”紧密相关。
(五)打造工匠精神培育的有效模式
发达国家广泛认同面对国际市场需求多样化背景,在企业产品已由单品种、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多品种、小批量的精益生产转变的外部环境下,只有采取合理有效的工匠精神培育模式,才能适应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
德国“双元制培育模式”是以企业和高职院校为主体,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高职院校、学生紧密结合,形成了“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而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观念,学校理论教学和企业实践紧密相连,学生具有学徒和学员的双重身份,技能养成的重心更加侧重于企业,由行业协会建立公共实训平台,为德国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具有卓越匠心的技能型人才。“校企合作培育模式”由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次推出,随之出现了并列式、交替式、双重制、底特律契约、企业与学校契约等模式,强调能力培养和训练、具有个别化教学性质的CBE职业教育模式,又在许多社区兴办“工匠工厂”,有针对性开展“工匠运动”,提出“今天的DIY,就是明天的美国造”口号,重振了美国制造业。瑞士采取由培训中心、企业行业和高职院校所组成的三方协作的“三元制现代学徒制培育模式”,以产教融合为理念,由企业行业牵头,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特色的不同类型校企合作方式,实现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零距离对接,展现出学徒培育的高效性,为企业“量身”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严谨意识的工匠型人才。[8]
二、对我国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启示
(一)把工匠精神理念融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
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大多存在“重技术、轻素养”的倾向,注重了学生职业技能的提高,忽视了职业道德素质的养成,导致学生在很大程度上缺少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的精神。随着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高职教育培养出更多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另外,企业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也会重点关注综合素质,不仅对学生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进行考核,还要对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创新能力进行评价[9],所以,高职院校需要将工匠精神渗透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二)用工匠精神内涵引领高职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具有潜移默化的立德树人功能,当前校园文化建设既没有体现出高职院校的办学特色,也没有体现建设主体的多元化特点,突出技术性而缺乏人文性特征,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高职院校要深化校企融合理念,通过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良性互动,以工匠精神内涵来引领校园文化转型,打造校园文化的职教特色;构建由学生、教师、校内管理人员、学生家长、行业企业专家能手等共同组成的多元化校园文化建设主体格局,共同致力于校园文化建设;将工匠精神元素有机融入到校园文化中,使学生在校园中随处可以感受到工匠精神文化气息。
(三)以工匠精神为指导,确定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
尽管众多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分解中,都明确列出了人才的职业素质,但是分类的依据和标准不够明确。工匠精神是匠心、匠技和匠魂的统一体,其内涵特征也必将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从知识结构上讲,主要由科学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知识组成;从能力结构上说,应当具备与从事职业相匹配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从素质结构来看,一般包括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身心素质等方面。[10]
(四)以工匠精神为核心,打造高职院校课程体系
课程作为重要载体,在工匠精神培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更多关注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忽视了综合职业素质的培养;过分强调学科体系,淡化了职业教育的综合性和实践性;过多关心知识结构的形成,忽略了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应该将工匠精神融入到高职院校课程体系中,既要用好思政课程,又要在专业课程开发中渗透工匠精神意蕴,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工匠精神要素和专业特征有效开展课程思政,通过实践教学环节践行工匠精神理念,将专业实训教学有机融入地方经济产业链中,使工学结合市场化。
(五)让现代学徒制成为工匠精神培育首选模式
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模式应该随着外部环境和时代主题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由于当前对工匠精神最佳培育模式尚未定论,所谓的校企合作也只是流于形式,导致学生在企业实习过程中难以体会到工匠精神的实质,综合素质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现代学徒制将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与传统师傅带徒弟培养模式相结合,通过校企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知识学习与工作情境”相结合[11],应该成为工匠精神培育的首选模式。需要通过完善校企合作机制来构建工匠精神培育平台,通过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来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通过引入教考分离、第三方评价的多元化考核机制来提升工匠精神培育质量。
得益于对工匠精神的重视,大多数发达国家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本文通过对发达国家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的价值、环境、目标、课程和模式等方面的诠释,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对我国的相关启示,这些对策与建议必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育工作的开展。发达国家除了在以上五个方面呈现出显著特点,在其他方面肯定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而且,工匠精神培育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多元的过程,这个过程还体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需要我们持续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