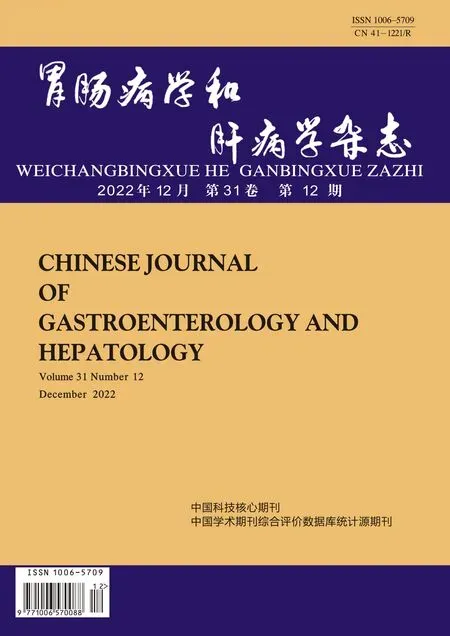肠道菌群和炎症在疾病中的作用及其研究进展
刘 娜, 金 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江苏 连云港 222000
肠道菌群是指在宿主胃肠道内定植的有机微生物群,广泛参与体内的营养代谢、免疫系统调节和自然防御感染等。体内某些细菌可能与导致身体组织炎症的介质有关。炎症是许多慢性多系统疾病的基础,包括肥胖、动脉粥样硬化、2型糖尿病、炎症性肠病等。炎症可能是由细菌的结构成分引起的,如涉及白细胞介素和其他细胞因子的级联炎症通路。同样,细菌代谢产物,包括一些短链脂肪酸,可以在抑制炎症过程中发挥作用。本文就肠道菌群与炎症分子的关系进行综述。
1 肠道菌群
人体肠道内有10万亿个细菌与人类共生,它们能影响体质量和消化能力、抵御感染和自体免疫疾病的患病风险,还能控制人体对癌症治疗药物的反应[1]。肠道菌群按一定的比例组合,各菌间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在质和量上形成一种生态平衡。肠道菌群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当肠道益生菌数量减少,致病菌数量增加,其正常生理平衡被打破,便会引起肠道菌群失调[2],近年研究[3]表明,肠道菌群具有营养和代谢功能,此外,还参与宿主免疫系统发育、成熟、神经信号传导、肠道内分泌等多种重要的生理活动。
2 肠道菌群在免疫和炎症中的作用
细菌具有粘附与定植能力,同时对宿主产生多种效应[4]。由于缺乏分解和利用碳水化合物能量所需的酶,人类无法消化膳食纤维的成分[5]。某些特定种类的微生物产生的酶,使营养物质分解为可吸收的形式,包括不消化的碳水化合物转化为短链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可能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作用[6]。此外,细菌自身的成分,包括脂多糖等内毒素可能被释放出来,损害人体健康。除了营养代谢外,肠道菌群也影响药物代谢动力学的多个方面[7]。肠道黏膜具有屏障作用,形成抗致病细菌的自然防御。肠道菌群通过刺激免疫系统的调节细胞而抑制炎症[8]。另一方面,由于细菌调节肠道的通透性,某些种类的细菌透过肠上皮细胞而进入血液,引起机体产生细胞因子等介质,导致机体炎症产生[9]。同样,肠道上皮组织内的细胞将细菌代谢物传递给免疫细胞,促进局部和全身的炎症反应。
3 肠道菌群与炎症之间的作用机制
3.1 脂多糖脂多糖也被称为内毒素,形成革兰氏阴性菌的主要细胞壁成分。在肥胖和其他代谢紊乱、脂肪组织炎症和胰腺β细胞功能障碍中可以观察到脂多糖明显升高[10]。正常情况下,肠道屏障包括肠上皮层和黏膜层,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脂多糖从肠道进入人体,由于饮食或致病菌等因素破坏肠道屏障,可能导致脂多糖移位,并进入血液循环,激活巨噬细胞,产生细胞因子,导致局部炎症[11]。此外,脂多糖可与免疫细胞上的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4, TLR-4)结合,从而激活肠道局部和远处的促炎级联反应[10]。有研究[12]发现,高脂饮食喂养的小鼠血液循环中有大量的脂多糖,但使用抗生素时,脂多糖水平明显降低。由此表明,高脂饮食诱导的肠道菌群释放脂多糖,应用抗生素时,可以阻止脂多糖的下游效应。
3.2 短链脂肪酸肠道细菌能够将宿主未消化的复杂碳水化合物分解代谢为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在饮食、肠道菌群和下游炎症级联反应的激活等相互作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3]。短链脂肪酸的类型和浓度不同,它们对炎症的产生作用也不尽相同[14]。有动物研究[15]表明,丁酸短链脂肪酸与多种对抗代谢紊乱的作用有关。丁酸盐通过表观遗传相互作用促进脂肪细胞的脂解、增强线粒体功能,从而使能量消耗增加,防止肥胖的发生[16]。在一项对13例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研究中,发现9例口服丁酸盐患者的症状得到缓解[17]。此外,丁酸盐也可通过改善胰岛素信号传递,降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18]。
3.3 胆汁酸胆汁酸在体内有多种作用,使脂类发生乳化从而被机体吸收。初级胆汁酸转化为次级胆汁酸是由肠道细菌完成的。肠道菌群的变化会影响合成的次生胆汁酸的种类,而次生胆汁酸又会影响肠道分泌的激素[19]。法尼醇X受体(Farnesol X receptor,FXR)是胆汁酸合成中最重要的调节因子,可作为转录因子启动多种下游靶基因表达,对胆汁酸的合成进行负反馈调节,胆汁酸通过激活肠细胞和脂肪细胞中的FXR信号通路导致炎症[20]。研究[21]发现,与正常小鼠相比,缺乏功能性FXR的小鼠,其脂肪组织明显较少,提示肠道菌群可能通过二次胆汁酸的形成促进肥胖的发生。
3.4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CRP是一种与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和肥胖相关的急性期反应物。有研究[22]表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肠道菌群与健康人群中类杆菌及双歧杆菌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能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先天就存在类杆菌及双歧杆菌减少情况,导致肠道黏膜免疫系统不成熟,使机体出现免疫缺陷有关,或是后天多种因素导致类杆菌、双歧杆菌数量减少。有研究[23]显示,血浆CRP水平升高的肥胖小鼠考拉杆菌属成员的丰度与较低的CRP水平有关。同样,类粪杆菌的丰度与CRP水平呈负相关[24]。对BMI>25 kg/m2的健康受试者基线血清和微生物群数据的评估显示,CRP水平较高的受试者乳酸菌属和双歧杆菌属的丰度明显较低,而大肠杆菌和拟杆菌属的丰度较高[25]。因此,CRP是一种下游炎症标志物,可通过特定肠道微生物的抗炎代谢产物的作用而下调。
3.5 细胞因子细胞因子是免疫原、丝裂原或其他刺激剂诱导多种细胞产生的低分子量可溶性蛋白质,具有调节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血细胞生成、细胞生长以及损伤组织修复等多种功能。细胞因子可被分为白细胞介素、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集落刺激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等。众多细胞因子在体内通过旁分泌、自分泌或内分泌等方式发挥作用,具有多效性、重叠性、拮抗性、协同性等多种生理特性,形成了十分复杂的细胞因子调节网络,参与人体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26]。
3.5.1 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TNF-α是一种关键的炎症驱动因子,现已证明TNF-α水平的升高与胰岛素抵抗和葡萄糖耐受不良有关,TNF-α能够激活多种信号通路,包括mTOR通路,使其成为促进代谢紊乱的关键分子[27]。有研究[28]报道,TNF-α在女性中高于男性,提示TNF-α可能存在性别相关差异;在肥胖患者中,TNF-α由脂肪组织中巨噬细胞分泌[29],并参与肠道菌群的失调。研究发现[30],青少年双歧杆菌丰度较高的人TNF-α的产量较低。
3.5.2 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IL-6属于机体中一种重要的细胞因子,研究[27]表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炎性病变可能是因为IL-6过度表达造成的,由于巨噬细胞的浸润增加,巨噬细胞释放细胞因子IL-6。这种分子通过促进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失调来促进炎症产生[31]。有研究检验了IL-6与2型糖尿病的关系,发现IL-6可以预测2型糖尿病的发病[32]。此外,IL-6与乳酸杆菌种类的丰度呈正相关。有研究显示,粪杆菌属的丰度与IL-6的水平呈负相关,可能因为丁酸盐的产生增加及其抑制NF-κB信号通路[33]。同样,一项针对肥胖人群的研究显示,在糖尿病和非糖尿病人群中,粪杆菌属与IL-6水平呈负相关[34-35]。
3.6 氧化三甲胺-N-氧化物(Trimethylamine-N-oxide,TMAO)膳食中的胆碱、肉碱等化合物存在于鱼类和其他动物中,它们被肠道微生物代谢为三甲胺(trimethylamine,TMA),然后在宿主肝黄素单加氧酶的作用下转化为TMAO[36-37]。产TMA的细菌包括梭状芽胞杆菌属、变形杆菌属和大肠杆菌属,肠道微生物产生TMAO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至关重要,Koren等[38]已揭示肠道微生物代谢物TMAO及其前体三甲胺是小鼠和人类的致动脉粥样硬化的物质。大动脉粥样硬化性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表现出明显的肠道菌群失调,血液TMAO水平明显升高[39]。在前瞻性队列研究[40]中,血浆TMAO浓度可以预测主要心脏不良事件的风险。研究[41]发现在小鼠和人类细胞培养中,血清TMAO水平升高可通过NF-κB信号通路诱导IL-6和TNF-α的产生增加。此外,研究表明TMAO水平与TNF-α呈正相关[42]。
4 肠道微生物群、炎症和疾病的相互作用
不断升高的炎症介质可以导致多重慢性病的发生。全身性炎症可引起多种疾病,包括代谢综合征、炎症性肠病和癌症,这些均与肠道菌群失调有关[43]。
4.1 代谢综合征及相关疾病胰岛素抵抗、葡萄糖耐受不良、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和肥胖等危险因素均与微生物群组成的变异相关,这些疾病的统称为代谢综合征[44]。对动物和人类的研究发现,血液循环中较高水平的脂多糖与肠道菌群共调、炎症介质的产生密不可分。脱位的脂多糖可通过激活脂肪细胞上的TLR-4受体和上调NF-κB来刺激促炎通路,进而促进胰岛素抵抗,与健康人相比,2型糖尿病、肥胖和葡萄糖耐受不良患者循环中的脂多糖水平更高[45]。血清脂多糖水平的升高也与包括TNF-α和IL-6在内的促炎细胞因子相关[46]。血液循环中的促炎细胞因子可能抑制胰岛素信号,促进胰岛素抵抗[47]。研究[48]发现,IL-22能提高小鼠的胰岛素敏感性,并引起2型糖尿病小鼠IL-22水平降低。
4.2 癌症研究[43]表明,胰腺癌、胃癌、结肠癌、肝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与慢性炎症相关的菌群改变有关,肠道菌群会影响胃肠道局部肿瘤的形成以及对癌症治疗的效果。一项对结肠癌小鼠的研究发现,使用抗生素可减少肿瘤的发展,这表明肠道菌群发挥了关键作用[49]。另外,促炎微环境通常与癌症的发展有关[50]。这可能阐明了为什么炎症性肠病患者结直肠癌的发生要比正常人高[51]。与健康人相比,结直肠癌患者的微生物多样性有减少的趋势,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可以影响产生促炎细胞因子的免疫细胞的存在,进而促进促炎微环境的产生,促进肿瘤细胞的产生[52]。
5 结论与展望
炎症是许多疾病的基础,包括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炎症性肠病和癌症。在动物和人类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和炎症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作用,这可能为这些疾病的治疗干预提供依据。目前,一些炎症标志物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慢性炎症性疾病[53],通过进一步了解肠道菌群与炎症的关系,可以描述疾病发病或进展及预后,以便更好地研究肠道菌群与炎症的相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