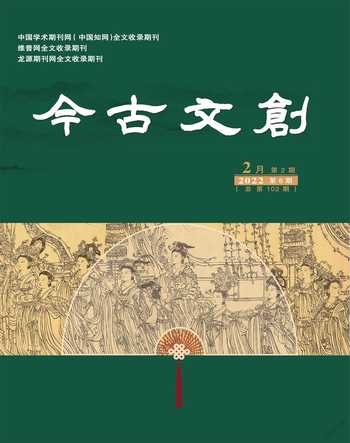蒙古族祭火仪式与文化记忆的变迁

【摘要】蒙古族的祭火仪式历史悠久,同时随着时代的变革其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迁。以往以家庭为单位的祭火仪式当前有了逐渐过渡向集体祭火仪式的倾向。家庭祭火仪式向集体祭火仪式的转变,同时也让文化记忆的传承机制及相关知识的性质产生变化。
【关键词】祭火仪式;变迁;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6-0092-03
火,是人类最原始的自然崇拜对象之一,很多民族都有与火以及火神相关的民间信仰。对生活在北方偏冷地区的蒙古族来说,火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腊月二十三日是蒙古族“送火神”的重要日子,蒙古语称之为“Gal Tahih”(祭火日)。传说在这一天,平时居住在每家每户炉灶中的火神会返回腾格里(天府)汇报过去一年的人间诸事,为了让火神开心,在天上说点好话,人们就在各自家里准备丰盛的祭品并祭拜火神。
至于蒙古族祭火习俗最早何时何地如何产生,目前还没有定论。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信仰习俗与原始万物有灵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蒙古人称火神为“Odkhan Galaikhan Eke”,意为“最小的火之女神”,德国蒙古学家海西希由此判断祭火习俗是在母系社会中产生的。布里亚特蒙古学家道尔吉·班扎罗夫认为蒙古人祭火习俗是从古伊朗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文也称拜火教)中的仪式演化而来的。[1]十三世纪的柏朗嘉宾和威廉鲁布鲁克等人的游记中均记载外来者见蒙古可汗必须先用火来净化。[2]
不论如何,蒙古族祭火习俗延续至今,不可否认的是其祭祀仪式在过去受佛教等宗教的影响,如今受现代化、城镇化的影响而随着时代变迁,其内涵——对火的崇拜、“期望火神保佑”这一素朴的愿望却一如既往,由此也可窥见民间信仰的包容性、功利性、世俗化等特征。变迁是文化现象永恒的话题,内蒙古地区的祭火仪式在近几年也经历了一些新的变迁。具体来说就是原本以家庭为单位的祭火仪式正在逐渐过渡成为以地区(例如旗、苏木等)为单位的集体祭火仪式。
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从2014年开始到2020年,旗政府在每年腊月二十三日举办集体祭火仪式,相关新闻报道称“集体祭火仪式已成为巴林右旗广大群众固化的活动形式,逐渐成了巴林右旗又一重要的民族节庆文化品牌。”[3]
巴林右旗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政府所在地为大板镇,全旗总面积10256平方公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巴林右旗常住人口为155027人,其中蒙古族人口为72259人,占46.61%。这里是契丹辽文化的发祥地,有辽代释迦佛舍利塔、辽庆州遗址、辽庆陵三个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及清代康熙行宫、巴林亲王府、荟福寺等自治区级重点保护文物。巴林右旗先后被命名为“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全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好来宝之乡”,有巴林婚礼、巴林祭火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余项。
一、祭火仪式:一种文化记忆
为何将祭火仪式称为一种文化记忆?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回答文化记忆是什么。记忆,这一原本属于心理学和医学范畴的概念首次出现在社会学理论中,是在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1925年发表的《记忆的社会框架》 (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一书中。
作为迪尔凯姆的弟子,哈布瓦赫承袭了其师关于集体意识的思想,并提出了集体记忆理论。哈布瓦赫首先指出记忆的社会性,记忆不只是一种生理心理现象,无论是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都是通过社会的框架来进行建构的,正如他所说“……我们的回忆总是集体性的,并竟有他人重新从我们的记忆中唤醒,即便它涉及的是我们独自经历的事件和独自所见的事物。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在物质形态上与我们有所分别的他人是否在场并不重要:因为在我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些记忆得很清楚的人物一直在那里陪伴着我们。”[4]
其次,他指出记忆并不是原封不动的“昨日重现”,而是通过当下的社会滤镜——“社会框架”去建构过去的,社会框架发生变化,记忆则被重建或被遗忘。
但哈布瓦赫在20世纪初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被很长一段时间被学界所遗忘了,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才在法国学界重新受到重视。这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皮埃尔·诺拉,1984年至1996年间他组织一百多名学者编纂出了3卷7本的巨著《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记忆之场”是诺拉生造的词汇,在此书英文版的前言中,他说“如果非要对记忆之场给出一个官方定义的话,那么我希望通过这一概念表达任何一种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象征元素,凭借人的意志或时间的积累成为某一共同体的记忆遗产。”[5]
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紧接着延续了记忆研究的脉络,在历史人类学框架下研究“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s Gedächtnis)。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为集体记忆进行了分类,提出有“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两个子类别。交际记忆指的是发生在个体生平框架内的历史经验,它的形式是非正式,通过日常生活的交际产生,载体是普通的回忆集体的时代见证人。而文化记忆是发生在绝对过去的事件,它是一种被缔造的高度成形的庆典性交际,这类记忆的存储需要通过特殊化的传统载体完成。[6]
根据以上关于记忆的理论,不难推导出,传统民间信仰仪式是属于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以及阿斯曼所说的文化记忆的。台湾人类学家黄应贵认为仪式活动同语言文字、物質文化一样,都是属于社会记忆机制。[7] 事实上,近年来在国内文化研究中,“传统节日”“民俗文化”“博物馆”等研究对象也都开始与“集体记忆”“记忆之场”理论结合。[8] 祭火仪式的变迁也意味着其深层有关祭火的文化记忆也在不断地经历变迁。
二、祭火仪式之变迁
(一)家庭祭火简介
祭火仪式在集体祭火仪式出现之前,都是在各个家庭内部进行的,虽然整体步骤相似,但每家每户在细节上却各有不同。整体流程大致为祭火前的准备工作、正式祭火以及祭火后的相关事项。祭火仪式之前的准备工作从祭火日当天的早晨开始,先将熬好的奶茶及奶豆腐,黄油等奶制品一同向火神和自己的祖先敬献。之后将家里每个角落的灰尘打扫干净,这一过程蒙语称为“Toos Shuurdeh”,意为拂尘,比日常的打扫更彻底,也象征着将家里打扫成洁净神圣的地方。
下午准备祭品,开始煮羊的胸叉骨(蒙语为Evchuu),煮熟后在其汤里焖大米,加黄油、红枣、羊肉做成稠粥,蒙语名为“Amas” ,又称作“Galiin Budaa”(祭火饭),两种名称经常混用。祭火饭的量通常要足够吃几天。准备好后,祭火仪式在傍晚日落时正式开始。将备好的酒、祭火饭、茶先后放进火里(炉灶或火撑子)献给火神,之后将祭品洒向天空献给祖先,献上祭品后一起跪拜火神,并向火神祈祷家人安康、万事如意。仪式完毕后家中小辈向长辈敬酒,之后全家人一同享用羊肉和祭火饭。之后的七天为“无主日”,火神不在家里,期间不能向外借东西,并将剩余的祭火饭在这几天内吃完,不得扔掉。
(二)家庭祭火的变迁
在近代之前,佛教的流传对祭火仪式的影响较大。16世纪佛教传入内蒙古地区,原本具有萨满教特色的蒙古族祭火仪式有了佛教色彩,一些细节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根据记载,佛教传入之前在祭火日当天(腊月二十三日)要杀全羊来供奉火神,佛教传入后由于佛教主张不杀生,供奉全羊變为供奉羊胸叉骨,并且特意留一些皮毛来代表活羊。[9] 18世纪伊始内蒙古地区自然社会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蒙古族逐渐开始定居,进行农耕,祭火仪式也随之受到影响。不再“逐水草而居”,住进砖房之后,祭火的场所改变了。
原本在蒙古包中,火撑子(蒙语称Tulga)位于正中央,祭火时全家人围绕着火撑子进行祭拜,而定居之后很自然地在厨房进行祭火仪式,有了炉灶之后也不再用火撑子。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祭火仪式步骤变得简单,宗教色彩也越发稀薄。颂词的内容从歌颂佛教神变为祈求家庭幸福美满,有些家庭甚至不再念颂词。原先还会在祭品中加入蓝、白、黄、红、绿五色绸缎,分别代表蓝天、白云、喇嘛教、红火、绿色的生命。而现在很多家庭略过这一步骤。
当人们以回顾的目光看待祭火仪式不难发现其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传承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一种微妙的连续性。采访多名当地人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一直是这样祭火的,别人家可能不一样”。女性结婚之后遵循男性家庭的祭火习俗,颇多人回忆跟自己娘家的规矩不一样。由此可判断出,每个家庭对过去仪式的保留和遗忘的部分都不一样,且每个家庭中的父母通过向子女言传身教的方式将这种不同传承了下来。
(三)集体祭火仪式
自2014年起,巴林右旗每年举办集体祭火仪式。纵观2014年至2020年有关巴林右旗集体祭火的报道,不难发现集体祭火仪式的流程是固定的。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在巴林右旗大板镇大板蒙古族中学举办祭火仪式。仪式由巴林右旗民间文化艺术联谊会主办,政府领导也会出席仪式。参加仪式的大多为旗政府所在地大板镇的蒙古族居民,人数在500人左右。政府领导发言完毕后当地非遗传承人向青少年讲解祭火的相关知识。随后由当地巴林祭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净化火撑子(Tulga),伴随着主持人的颂词,巴林右旗集体祭火仪式正式开始。在现场主持人引领下,几位领导作为代表,负责起火、点燃火炬以及旺火,之后将香、黄油、酒、羊胸叉骨、祭火饭、枣、茶叶等祭品洒向火撑子,供奉火神。身着蒙古族节日盛装的人们围着“Tulga”,带着对新年的美好憧憬用各自带来的祭品祭祀圣火,祈祷家人及亲朋在新的一年幸福安康,全旗风调雨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10]
三、祭火的文化记忆之变迁
祭火仪式在近几年发生了由家庭向集体过渡的转变,同时关于祭火的文化记忆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总结如下。
(一)记忆传承机制的转变
以往的祭火仪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传承下去的,而近几年的集体祭火仪式是以旗为单位的大型文化活动。这种文化记忆的传承不是由一代一代的家庭来完成,而是由参加仪式的集体来完成的。因此人们在回忆祭火仪式时,出现的画面也是集体活动的景象。
(二)有关祭火记忆的知识性质的转变
在集体祭火仪式前,主持人向青少年讲解祭火知识。家庭祭火仪式中的知识的传递,是在家中成员口头教育以及耳濡目染中产生的。并且每个家庭的祭火仪式并非完全相同,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特色。而集体祭火仪式的知识,是通过指定的主持人向学生讲解产生的,具体知识的内容也是较为综合性的、去差异化的内容。
参考文献:
[1]Atwood, Christopher P., “Buddhism and Popular Ritual in Mongolian Religion: A Reexamination of the Fire Cult” (1996).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12.
[2]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许小莉.巴林右旗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活动丰富多彩[EB/OL].http://www.blyq.gov.cn/jrbl/show-48024.html,2019-7-10.
[4](德)阿斯特莉特·埃尔著,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7-48.
[5]Pierre Nora. From Lieux de Mémoire to Realms of Memory (preface). Realms of Memory [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6](德)阿斯特莉特·埃尔著,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46.
[7]胡林莉.国内集体记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基于CSSCI数据库的知识图谱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21,12(02):134-135.
[8]贺·孟和吉日嘎啦主编.珠拉沁文史[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261-267.
[9]宝力尔,宝忠.巴林右旗举行集体祭火活动[EB/OL].http://www.blyq.gov.cn/jrbl/show-51794.html,2020-01-17/2021-11-1.
作者简介:
艾嘎,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