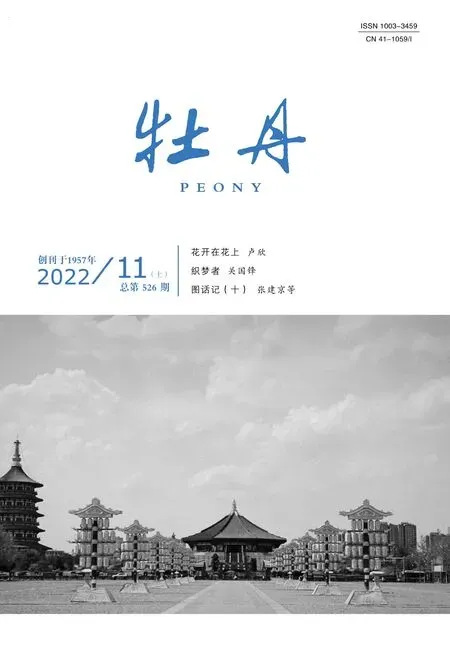秋之蛰庐
佩之
立罢秋,又过了处暑,天气才越来越像个秋天了。
雨淅淅沥沥,不断从天空中落下,地上聚起深深浅浅的水潭,雨点落在上面,泛起此起彼伏的小小的涟漪,同时冒起不大的泡,瞬间便又消失了。
蛰庐花园中那座石屋的外墙上,前几日还茂密青翠的爬山虎的叶子,此刻也稀疏了不少,并在雨中倔强地散发着生机。一阵风吹过,窸窸窣窣,叶子与叶子间的厮磨,也难以挽留那些无奈的飘零。
原本在夏日里满壁的叶子中隐约可见的“谁非过客,花是主人”的刻石,此时已经真切地展现在眼前,似乎在向人们昭示它那耐人寻味的哲理。
一九二三年九月,康有为来到蛰庐,写下那幅著名的对联:“丸泥欲封紫气犹存关令尹,凿坏可乐霸亭谁识故将军”,他那圆浑苍厚、恣肆开张的书法和这石屋的风格倒是相得益彰。如今,这副对联在这石屋上已经静静地守望了百年之久。物是人非,时过境迁,无论关令尹,还是故将军,抑或康有为,还有这石屋的主人张钫,都已成为匆匆过客,而这座石屋,以及这石屋上的这副对联和一岁一枯荣的藤蔓,或许还要继续守望下一个百年吧。
石屋那朱红色的门,在雨中愈发鲜亮,在墨绿色叶子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抢眼,而门上那斑驳的痕迹,在无声中难掩岁月的沧桑。
在沉重的吱呀声中,推开这扇门,尘封的岁月便同时被开启。门内不大的空间里,陈设古朴简洁,一如旧时。桌椅、条几、书案、文房……墙上的一帧书法是后来悬挂上去的,细细看来,居然是张钫先生的旧藏、唐代徐浩所撰书的《崔藏之墓志》拓片,墓志不大,但字里行间尽显大唐气象,宽博之中透出森严的法度,《墨池编》卷一云:“欧阳询传张长史,长史传李阳冰,阳冰传徐浩,徐浩传颜真卿。”如此说来,徐浩还是颜真卿的老师呢。
石屋确实由石头所建,高近两丈,面积虽小,但并不觉得逼仄。墙壁很厚,有二尺余,有固若金汤之感,进得门来径直数步,便是后门,两门相对,而后门略小。透窗而望,藤蔓在窗外随风摇曳。张钫先生就是在这石屋中运筹帷幄,落墨挥毫的。恍惚间,康有为、于右任、王广庆……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在这石屋里运笔泼墨、谈诗论艺。
这石屋便是千唐志斋主人张钫先生的书房——听香读画之室,书房是蛰庐花园的一部分,也是园中最早的建筑。室名由原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关葆谦以隶书所题,既有汉隶之拙厚,又有清人之逸气。秋风秋雨,读画听香,单是看了这个名字,便能生出几分情趣来。
有时我们在想,一个戎马倥偬的将军,一位带兵打仗的武人,却能于政务之余,留心翰墨,醉心金石,并且有如此之成就,真是令人钦佩。一千余方唐代墓志得以妥善保存,大唐风云千余年后凝聚在这窟室之中,让后人能够一脚踏进大唐王朝,与唐人对话,何其了得!这不仅显示了张钫先生卓识远见,更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功莫大焉!《梁文炳墓志》《戒子女书》《楷书孙子兵法》等书迹,不仅文采斐然,情真意切,更是楷、草、行,诸体兼善,骨力洞达,展示了张钫先生在文学及书法方面的修养。
秋风湖上潇潇雨,自古逢秋悲寂寥。自古文人都有悲秋之慨,秋气肃杀,秋雨连绵。宋玉曾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当年,张钫先生蛰居铁门时,不知是否生出过此等感慨呢?估计康有为最能洞察张钫先生当年的心情吧。康氏小住铁门期间,曾作《宿铁门·赠伯英将军兄》诗二首以赠张钫,其一曰:“窟室徘徊亦自安,月移花影上阑干。英雄种菜寻常事,云雨蛰龙犹自蟠。”英雄种菜,云雨蛰龙,一位变法失意的落魄文人,一位护法未成的热血壮士,相叙悃诚,同病相怜,如若不然,张钫怎么能让南海先生为其花园题写“蛰庐”的斋号呢?蛰,潜藏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雨,断断续续下了几天,书房前的青砖地面上,已经长出了些许青苔,使得这个园子显得更加深邃和幽静。园子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一阵微风吹过,书房两侧那几株树上的倔强的花又凋零了几朵,留在枝头上的,也已经枯萎,不复盛夏时的柔嫩。
雨中,一位撑伞的素衣女子飘然而至,在书房前短暂驻足后,又缓缓移步至书房西北侧的窟室,那窟室门楣的上方,章太炎以古篆题写的“千唐志斋”若隐若现,室内的墙壁上,镶嵌的正是那千余方唐代的墓志铭。每一方墓志的背后都是一段鲜活的人生,每一方墓志的背后都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这不同的人生和历史,便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大唐风云。
风吹过,雨丝拂过脸颊,一阵寒意随风而生,秋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