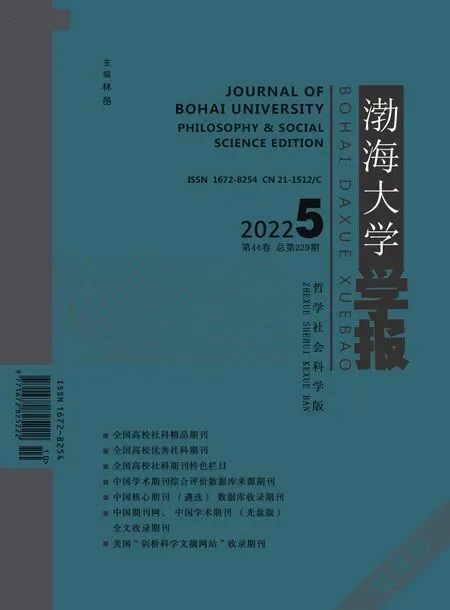当代工业文学的一次成功写作
——谈李铁长篇小说《锦绣》
张祖立 陈镜如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辽宁大连 116622)
当代中国,能一贯、执着地进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人很少,李铁则是其中一位。他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锦绣》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锦绣》叙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新世纪的不同时期,东北一个金属冶炼厂的变迁和工厂工人命运的变化及精神面貌,充分描写了富有魅力的父一代子一代人物形象和工匠形象,使作品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向度得以全面展现。
一、“全景观”式的工业史
《锦绣》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家园”以20 世纪50 年代为背景;第二卷“山河”以90 年代为背景;第三卷“前程”以新世纪开端为背景。从故事发生的时间看,小说跨越和覆盖了70 年的历史岁月。在当代工业文学叙事诸多文本中都有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相对应的叙事,但这些作品都是“断代”性的,像《锦绣》这样跨越如此长时间的叙事似乎没有。显然,《锦绣》具有更大的景深和更丰富的内涵,客观上具有了一种史诗气质。
第一卷冠名为“家园”,凸显了新中国工人以厂为家,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边努力创业一边进步成长的过程。“家园”有双重含义,一是工厂这个家,另一个是工人建立自己的家。此时的工人绝大多数是新招来的,多数正值青春年华,恋爱、成家、生子。以往的这类小说,大多突出前一方面;《锦绣》却花费不少笔墨写后一方面,这部分基本属于私人空间,最能写出人物的真实情感和心理。因此,这样的书写方式是个亮点。建立家园,表面注重的是家的外观和物质材料,其实最重要的是家中成员的成长和塑造。20 世纪50 年代,虽已有“斗争生活”的意识,但毕竟与后来的60 年代至70 年代不同,此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是主要任务。作品没有过多添加阶级矛盾、政治斗争元素和相关情景。作品中的张大河们以厂为家、学习技术、积极工作,体现了那个年代工人们特有的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作品笔法朴实,故事情节波澜不惊。作品在侧重叙事的内容上和追求的风格上,与草明等“十七年”作家的工业题材创作有着一定的相似,可以说,是向“十七年”写作的一次怀旧和敬礼。这一卷竭力突破将工人、劳模形象塑造为“高大全”式人物的模式,在充分描写人物闪光点的同时,真实表现出人作为人所可能具有的缺点。在通常的文学想象中,张大河等人要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才能成为一个近乎完美无瑕的典型形象。但这部作品并没有把当时政治话语、政治生活细节、宏大叙事因子过多地堆砌在张大河和其他人物身上,反而在有意识强调他和工厂领导、工友们作为普通人的真实想法和心理。张大河有虚荣心和功名思想,想做技术大拿,也想着“要让大家都跟我学”,在得不到提拔时焦虑。小说对他描写的真实性还在于他成家后有时放不下古小闲,在他的34 篇日记中古小闲共计出现过12 次,这与他心系工厂的心理常常显出矛盾,他没能抵住诱惑,偷摸了古小闲的乳房,但一直不敢承认(退休多年后才坦白),让好工友姜连子一生为其背黑锅。张大河即使退休到了晚年,也没有成为那种理想的、完美的、成熟的典型形象。但他的确是个令人喜爱的工人形象。张大河的不成熟,反倒是作品的一种成功,这是与许多作家关于那个时代的写作对比后显出的新意和不凡。
第二卷名为“山河”,联系作品叙事内容,这个题目容易让人产生“山河破碎”和“重整山河”的复杂情感。相比第一卷的简朴,此卷显得深沉和悲壮。工厂政策性破产,工人下岗、上访,企业转轨,寻求合资,投资钛白粉项目,企业改革以失败告终……这些内容和情境,每每都会让读者想起谈歌《大厂》《车间》等“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但《锦绣》仍有自己在叙述上的独特考虑,即虽然仍重视描写在艰难中挣扎、拼搏的企业家形象如薛立功,但在笔墨运用上,注意向其他方面转移,呈现出“散点透视”的特点。企业领导薛立功不再是绝对的核心人物,作为企业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张怀勇及其他人物形象从薛立功那里“瓜分”了不少笔墨。以往的关于20 世纪90 年代工业文学叙事,虽真实再现了改革之阵痛,但也常常让有着高贵情怀的主要人物在面对现实窘境时采取了妥协的暧昧态度,稀释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浓度。但作者对薛立功形象的塑造颠覆了这种模式。薛立功有着90 年代企业家的一些共同特征,如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改革思想,善于铁腕治理,急切期盼钛白粉项目上马;也有着冷漠和不端的心理,甚至有着和很多国企领导悲天悯人情怀迥异的内心世界。薛立功的形象刺激了读者的反思意识,引导了人们对改革与人性、改革与人文关怀关系、企业家精神品质构建等问题的思考。这部分写作还有一个特点是大量展示张怀勇的日记内容,通过这些日记,我们知道他在参与改革时的遭遇、行为、心理,这些日记极大地强化了对其形象和心理的刻画效果,为第三卷张怀勇的正式出场,凸显他的独特精神气质及彰显作品关爱工人的人性导向做好了铺垫。
第三卷名为“前程”,有着明显的理想和乐观的寓意。当然,这也与现实有着合理的吻合度。归纳起来看,当代小说对工业领域境况的书写大致呈现着“建构———解构——再建构”的阶段性特点。这三个阶段大致对应着20 世纪50—70 年代、90 年代、21 世纪。对于前两个阶段特点,当代小说书写得较为充分。但相对于“十七年”工业故事的写作和关于90 年代前后的工业故事的写作,当代作家有关21 世纪以来的工业领域的生活或题材的写作并没有得到及时、充分反映。这从21 世纪以来的那些即使是比较优秀和重要的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也能看出来——要么重点写前两个阶段,要么象征性地写到21世纪时间,然后匆匆收尾,要么是重点书写私有企业的故事。面对当代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现状和当代中国工人的实际精神面貌,当代作家的发现和捕捉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及文学叙事能力无疑将遭受多方拷问。在这一方面,《锦绣》突显了自己的价值。我们看到的是,张怀勇走马上任后,对企业立即进行新一轮股份制改造,跟国企强强联手,重新上马钛白粉项目,搞技术革新,攻克无外加熔剂法,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锦绣厂逐渐做大做强。尤其是张怀勇念念不忘重招本厂下岗职工的行为,着实体现了新一代企业家的人文精神和情怀。小说还写到工人培训、企业文化建设,以及古河两岸环境优化等内容,这在新世纪小说中极为罕见。李铁以相当大的精力和篇幅书写新世纪中锦绣厂人的拼搏和经营、生产、管理过程,真正呈现了21 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工业“构建”阶段的情形,呈现了国有企业当下镜像和工人的精神面貌。《锦绣》对新世纪工业故事的充分叙述,是对前两个阶段故事及内涵的拓展和深化,《锦绣》就此具有了更强烈的现实感和更丰厚的意蕴。在这里,人们领略了新世纪国企领导者形象的魅力,领略了父一代子一代的精神赓续状况,领略了工厂空间与工人生活空间的紧密融合情形,领略了当代工匠精神的魅力。写新世纪工业故事,对李铁来说并不偶然。这几年,他紧盯现实,逐渐聚焦现代工业领域的书写,体现了当代作家一种可贵的责任意识和书写魄力。《锦绣》就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写作。
《锦绣》以特有的形式,较为全面地再现了当代中国工业走过的坎坷道路和蹉跎岁月,深刻揭示了当代工人的心灵历程。说它是一部当代中国的工业史诗并不为过。
二、父一代子一代形象的成功描绘
《锦绣》一个突出特点是描写了父一代子一代群体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家族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等常有这种父子(母女/父女)关系的人物描写,但在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则很少。实际上,计划经济时代的“接班制度”或普遍性的行业倾斜政策,形成了中国国有企业中相当普遍的父一代子一代现象。以往的工业题材小说,都不太重视父子关系人物的描写。这应该是工业文学叙事不容易受人们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重视并选取父子关系人物描写,李铁应该是有着叙事策略方面的考虑。即通过父子关系构成的私人空间链接、融合类似国家/现代化的宏大空间,实现对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的展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大理想,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大力发展工业,势必会形成工厂内以大规模生产为出发点,制约和影响人们生活的模式。加上一定阶段内受不断绷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工人的家庭生活或私人空间遭到工厂、社会公共空间的不断挤压和消融。自20世纪50 年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当代文学创作普遍强化工厂这个公共空间中的工人们的工作行为,遮蔽或弱化工人们在家庭私人空间的生活表现。《锦绣》里有个情节,车间主任刘英花因长时间大干工作不回家,其丈夫提出了离婚的要求。这足以说明作者对私人空间作用的重视。李铁在之前的长篇小说《长门芳草》中就描写了几位工人世家成员的身影,如施玄山与儿子施大伟,乔芳草与女儿于小雨……在《锦绣》中,有父子关系的人物更是占了相当比重,如张大河和张怀智、张怀勇、张怀双,牛洪波和牛太白,闫振邦和闫海端,姜连子和姜爱国,侯德奎和侯卫国,老吴和吴中凯,潘章和潘唯一,钱玉贵和钱奋斗,赵平安和赵红,王裕国和王建设,李旺发和李振华,等等。此外,有母女关系的人物,如古小闲和姜小妮,刘英花和谢丽,袁老师和田宇莹。还有父女关系的如老邱和邱宇、杨红星和父亲等人物。如此“拖家带口”,体现了作者对私人空间在反映生活、揭示人物心理方面作用的在乎。而父与子代际人物群体的描写,将更加丰富的人性元素和内涵浸润到宏大国家/现代化空间,弥补了以往工业叙事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
谈到父一代子一代式人物描写,人们容易想到“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笔下的父子形象。他们的小说故事时间主要定格于“下岗潮”波涛汹涌的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应该说,对这个时期中国工人下岗后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以文学之笔揭示得最为深刻的很可能就是“三剑客”。然而,“三剑客”的写作往往是在未曾做过工人或有过短暂工厂经历的“工二代”的视角下进行的,他们对父辈“工人”在工厂劳作的记忆和叙述是有限的、不完整的(当然这也不是“三剑客”的写作意图)。他们笔下的父与子的故事往往不是发生在工厂(工厂往往已经不存在了),是发生在家庭或社会,不是“完型的”工业叙事情景下的父与子关系的描写。《锦绣》将父与子的行为同时放置在工厂和家庭,让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机融合,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选取父子关系人物,李铁还有在小说叙事学方面的其他考虑。首先是叙事框架。《锦绣》的故事时间跨越数十年,没有人能在工厂里一贯到底。最好的能起到连贯作用的办法是父子关系人物的前后出场,否则小说三卷之间显得游离,缺乏肌理。第一部讲的是以张大河等为代表的父一代故事,后两部是以张怀勇等为代表的子一代的故事,如此,小说的叙事框架得以有机建构。第一部叙述张大河等父辈们(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成长、成熟的经历,依循着这一积淀,张怀勇等二代人物形象的精神塑造有了原点。而第一部中父辈们之间的故事和行为的集中性和统一性,与后两部中子辈们之间思想行为的多样性或复杂性,都真实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历史和当代工人的心灵轨迹。其次是叙事语法。小说中发生的故事与事件均离不开行动者(角色)。在《锦绣》中,许多父子形象往往经历着功能性事件,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如在上马“钛白粉”项目和生产特殊锰方面,这几乎是父子两代人的共同追求,在这方面,父子的角色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充分彰显。如牛洪波书记和张大河,他们的儿子牛太白和张怀勇、张怀双等都是如此。而诸多父子的努力,都是来源于实现工业现代化、建设好自己的工厂和家园的理想。所以,工厂作为一种力量和精神归宿的家园,其盛衰一直牵动着每位职工和家属。时间跨度的关系,诸多父子形象无论是主角还是承受者,都表现得比较充分。“主角在追求对象的过程中,可能受到来自敌对势力的种种阻挠,也可能得到来自朋友的种种帮助,这样,在基本的角色模式中便必须再增添上两个角色,这便是助手与对头。”[1]在张大河的成长过程中,姜连子和古小闲帮助过他,算是他的“助手”。在张怀勇对工厂进行改革和经营中,父一代的张大河和子一代的牛太白、张怀双、杨红星、吴中凯等做过“助手”;姜小妮做过他的“助手”,也做过他的“对头”;哥哥张怀智做过张怀勇的“对头”,弟弟张怀双做过“对头”(带头上访、对峙),也是“助手”……而在处理下岗和调离工作这两件事上,张怀勇是薛立功的“助手”,是弟妹谢丽、妻子田宇莹等许多工人的“对头”。由于大多数功能性事件由父一代子一代关系的形象完成,加之彼此之间的特殊亲近关系,故事的张力和可读性也较强。如张怀勇和张怀智几次角逐是兄弟之间的角逐,父亲时时加入阵中相助老二。锦绣厂在和国企南钢洽谈合资时,遇到的麻烦对手竟是当年锦绣厂厂长闫振邦的儿子闫海端。张大河和古小闲之间有过情感故事,他们的后代张怀勇和姜小妮之间也有过微妙的情感交流;当年刘英花“破坏”了张大河的婚姻,后来她的女儿成了张大河的儿媳妇。“锦绣厂”一把手薛立功竟然和田宇莹发生关系,张怀勇蒙受了极大羞辱……
突出父子关系人物的描写,彰显了小说的思想深度和人性温度。在现代性的一些理论视域中,亲情似乎是和工厂所代表的现代工业理性要求相悖的,但作者对此明显有自己的深层思考。20 世纪90 年代工人下岗有个很值得注意的情况,不少工人家庭成员都在一个单位,一旦工厂倒闭,整个家庭将失去保障。如果说工厂表面上的明确目标是上马“钛白粉”项目,搞技术革新,提高经济效益的话,那么张怀勇念念不忘的理想则是有朝一日将大多数的本厂下岗职工重新找回。小说所突出的这一情结和理想,在新时期以来的所有工业文学叙事中极为罕见。这虽然有理想化的色彩,但又极有坚实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体现着一个当代作家神圣的精神向度和人文情怀;而这一精神、情怀又与小说设计和描写的父子关系人物有着深刻的联系。张怀勇成长、生活、工作在许多人彼此有千丝万缕的亲情笼罩的环境中,其思想情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正因如此,他在工厂政策性破产与依法破产之间选取了较有人情味的前者,在制定工人下岗方案时尽最大努力体现出对工人的关心,实现了锦绣厂前后召回1100 名下岗职工的豪迈理想。同理,市委书记(后为副省长)牛太白也十分关心锦绣厂和古河沿岸老国企,固然是领导干部职责所在,也与他是锦绣厂子弟且他从小在锦绣厂家属区长大有关。乡村、血缘、族亲曾在五四作家笔下作为批判性的描写对象,在柄谷行人看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既要“超越血缘与地缘”,也要熔铸进前现代的王朝国家历史中“亲族和族群那样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相互扶助之同情心”[2]。在现代性的视域下,似乎工厂的公共空间不应该顾及家庭和血缘、亲情,但这是中国的实际现状。在近70 年工业历史大变迁中,父子两代人都将一生投在了工厂,工厂事业对于老一辈工人来说,不仅是一生的追求,更是家族后代事业的接力棒和生存依托,他们要代代为实现工业兴国而努力。这种从小在父辈那里耳濡目染的工厂情结是一点一滴渗入这群“工二代”骨髓中的,从小长在工厂中的子辈们受父辈影响,对工厂有着最深厚的感情,也在历史进程中有着最清醒的认知。父一代子一代形象的描写,使得作品因具有了浓郁的人性暖意而有别于当今许多工业题材小说。
三、对工匠与工人价值的深层思考
卢卡奇说道:“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3]这是他谈及资本主义生产活动时的认识,对我们认识在现代社会的企业生产中工人的工作特点、状态、作用有一定启发。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机器面前,一切工作流程、动作都标准化、固定化,工人的能动意识和主体地位似乎有所弱化。但《锦绣》想强调的是,在现代化机器面前,伴随着新中国发展步伐成长的工人并不是被动的,他们往往在一些关键环节和时刻,发挥出惊人的能量,体现出人最应该有的价值。作品几处描写冶炼场景时,都强调了张大河、姜连子、张怀双、姜爱国等摊长和配电工作为“技术大拿”或“工匠”的重要作用。从开始的新中国的第一炉锰、第一炉钒铁、第一炉也钛铁……到后来的生产优质锰产品,都突显了这些工匠的身影。如叙写金属冶炼厂扩建部分投产之初,锰铁质量差的症结在于摊长的眼力和火候拿捏问题时,写到张大河的惊艳出场和意义——“烧到一定火候时,他冲助手喊,给我盛一勺水出来。他说的水是锰水,在炉里滚沸成红色。助手用长把勺子勺出,递到他眼前,他的脸立马就有一种烧灼感。他看了一下,像是心不在焉,心里已有了谱,喊另一个助手,把话递给另一位置的姜连子,姜连子调整电流。几个来回,一炉好锰铁就炼出来了”[4]。张大河和苏联专家比武,也是较量着双方的眼力。第三部中,在张怀双、姜爱国联袂炼质量要求极高的特殊锰失败时,再次写到已经退休的张大河的出场。在试炼这一炉时,张大河根据几十年的经验积累,临时增加了预热原料和在原配方的基础上加一些辅料的环节,取得了成功。
作品对工匠较有看点的描写,还有他们在机器面前和在作业时所具有的非凡、特异的感觉。之前的《工厂的大门》曾写到刘志章对机器有着超人的理解,他能从轴瓦运转的声音里察觉机器的异样。《锦绣》再次突出了这一点。第一部写到张大河对电炉的特殊感觉,认为电炉是有生命的,电流是血液,热度是温度,炉膛里沸腾的锰水就是心跳。第三部写到,张怀双看锰水火候的能力与生俱来,盛出一勺锰水,一眼看下去,准确度不次于其父张大河。作者还强调,这项技艺凭的不全是经验,还有天赋,这就给这项技艺带来了一种神秘色彩。“大拿”们的技艺并不是一种机械化的操作与锻炼,它是工匠与生俱来的观察力与手感,是人与工厂、机器间神奇的、难以言说的感觉与默契。这是对人的潜在能力的挖掘和膜拜。
当然,李铁并非有意神化工匠和故作玄虚,他几次写到产品出现的问题恰恰出在炉前工的身上,即摊长对冶炼火候的把握。这一正一反,都在强调着人在现代化生产面前的作用问题。这仍然基于人对劳动的态度和对生产经验的长期总结。由此,作品屡屡描写工厂对工人的培训问题。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工人以主人公身份参与厂里的技术革新、岗上练兵,已成为新中国工业发展历史上极有时代特征的传统与现象。但后来,尤其8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作品青睐将企业家描写为主角,普遍强调企业困境及改革问题,工匠形象则出现不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当下工人价值认识有缺失的表现。李铁是当今有强烈“工匠”情结的作家,他之前的作品就有过“工匠”或“技术大拿”的身影,《长门芳草》《乔师傅的手艺》等作品描绘了工匠的至高地位,也描写了青年女工不惜以身体为代价去交换手艺的行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可以看出,同样有工匠情结,与《长门芳草》《乔师傅的手艺》所表现的女工的女性意识迷失不同,《锦绣》则突出当代工人主体意识的积极构建,可以说是一部为当代工人形象铸魂的作品。张家父子两代四人,按身份可以划分出工匠与企业领导两类。总体看,作品描绘前者的笔墨并不少于后者。“工匠”叙事可以说是本部作品的重要任务。作品刻画了第一代工匠形象的代表张大河和姜连子,两个工匠联手能炼出一炉好锰铁。后来,他们的儿子张怀双与姜爱国配合默契,炼出的产品质量全厂第一。这寓意着当代中国工人成长的轨迹,也蕴含着作者对当代以工匠为代表的工人作用地位的思考。
张大河虽以分厂厂长的身份退休,但骨子里是一位优秀工匠。第一部除了表现他在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更多的是突出他如何有技术和如何想发挥技术的更多作用。他只知道能多出产品,出质量好的产品,一切以技术规定和标准要求工作,体现了对现代科学和管理的充分尊重,这是当代工人体现出的现代性的一面,也是作者关于国家工业化想象的具体实践。他批评刘英花将设备刷成红色;要求无关人员离开开炉点火现场;喜欢传帮带,认真向徒弟和工友传授淬火方法;他曾赢得与苏联专家炼锰铁的比试。这些工匠用过硬的技术手艺承担工人的生产任务,是工厂的“定海神针”。
张怀双给人的印象很深刻。表面上他不如两个哥哥出息,甚至其岳母不认可他作为普通工人的价值。可张大河觉得他自己最有出息,因为他是父辈工匠精神的继承者。从父亲身上能看到更多自己的影子。在张怀双身上,也寄寓了作者自己的理想。张怀双和父亲一样,技艺精湛、性格直爽,有性格、有脾气。但张大河毕竟为了个人发展牺牲了爱情,因为虚荣不敢承认自己侵犯过古小闲。而张怀双身上具有着一种更加坦荡的胸怀和坚韧的意志和气质,透示着作者关于新时代工人精神塑造的一种理想。妻子下岗,没有屈尊求哥哥;为使工人少受下岗冲击,带头上访并和厂领导交涉;不愿离开生产一线,拒绝当锰冶炼分厂的副厂长;拒绝为徒弟赵红旗回锰分厂找哥哥说情,让他凭本事公平竞争;甚至在照顾父母方面也绝不因为自己家境差而低于哥哥们的标准。作者让张怀勇不似张怀双和父亲一样当上全国劳模,并不意味着对工人和工匠的漠视,而是要表达对现代工人提升文化层次的一种愿望。“工匠”一词原本与传统有关。传统的工艺制作和手工制作催生了工匠的出现。传统的工匠除了注重精益求精和技艺上的高超,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和传播者。《锦绣》在保留着这些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几位工匠形象,更加注重突显现代工人的自立自信意识、创新精神。
工匠精神涉及传承问题。小说突出描写了父一代子一代人物形象,也描写了师徒关系的人物群体。张大河的徒弟有王裕国、李旺发、赵平安,张怀双的徒弟有周跃进、钱奋斗、赵红旗。在中国传统里,师徒关系近乎血缘关系般密切。这部作品虽没有沿袭文学史上诸多作品过于迷恋这种关系的书写方式,但仍给了这种关系予以一定的关注和表现。如张大河逼着当厂领导的儿子张怀勇给自己的徒孙赵红旗安排回厂工作,父子、师徒关系人物的描写使得作品充满人情味。写师徒关系和写父子关系一样,是为了前后叙事结构衔接的考虑,但更主要的是想探索一下现代社会、现代企业中的师徒关系的延续、发展乃至创新的问题。作品中,师徒关系相对轻松、平等,彼此可以调侃、逗笑,他们一起以班组的整体力量炼出合格的锰铁产品,一起为个人生存和工厂前景担忧。
《锦绣》还有一些优点值得关注,如日记形式的利用,有着叙事学方面的创新和突破;对工厂、生产的景观与场面的描写比不同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都充分了不少;等等。小说的主要不足恰恰与它的优点有关。尽管选取三个时代为正面描绘背景,也达到了跨越和覆盖70 年的故事时间的目的,这在当代实属了不起,同时,以日记等形式“倒叙”了一些背景,但仍弥补不了不能充分塑造人物形象和反映当代工人成长历程的缺憾,以至于作品内涵厚度显得单薄一些。尽管如此,《锦绣》仍是当代一部值得充分肯定的工业叙事作品。
-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今文《尚书》否定词“非”“匪”“ 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