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命题
宋培军
自从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命题后,基于不同国情与各自立场,各国学术界也有不同认识,我国比较集中的讨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性质大论战时期以及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前者更倾向于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等同于原始社会(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初版)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1页)。,或者加以取消(2)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前言。,进而论证苏联时期标准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体系框架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后者引介六七十年代苏联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不同认识及其对五种生产方式体系框架的冲击,更多具有思想解放意义(3)马克垚:《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简介》,《国外史学动态》1977年第1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古代社会的几点体会》,《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指出学术界正在探讨其关于马克思读摩尔根改变“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88页)。魏光奇《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提到日本学者岩泽君夫也有类似看法(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0-261页)。。进入新时代,李根蟠《“亚细亚生产方式再探讨”——重读〈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思考》有一个重要突破,那就是注意到“公有制和共同生产”作为“古代的更简单的形式(alten einfachern form)”在印度人、斯拉夫人中的存在(秘鲁、威尔士克尔特人都是其派生形式)(4)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9页。,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关于“亚细亚的形式”的段落中只出现了农业公社、统一体两种主要派生形式(5)李根蟠:《“亚细亚生产方式再探讨”——重读〈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其遗留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并未直接出现“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只是间接出现了“东方的生产方式”,因此,把“亚细亚的形式”视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要特别谨慎。易言之,对马克思“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概念持什么态度,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不得不深思细考。笔者在反思、检讨此前研究的前提下,提出自己进一步的探索性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马克思“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话语的原初语境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作为马克思使用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首次出现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段落中。人们对此耳熟能详,也影响巨大。他是这么说的: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asiatische)、古代的(antike)、封建的(feudale)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modern bü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英译modern bourgeois modes of production)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参见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MEW)(Berlin: Dietz Verlag, 1956), Band 13, S.8-9.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reface,” in Marx: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 Terrell Carv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9-16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当时是用德文写作的,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对应的就是我们熟知的汉译“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使用的也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正像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是历史的一样,它的性质和这种性质的规律也是历史的。亚细亚的,或古代的,或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是实质上不同的规律。”(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3-164页。笔者在此提请人们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另一处正式使用与发表。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再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不过,更为限定了其时间坐标,表述为“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altasiatischen Produktionsweisen)”,多了一个“古”字。侯外庐先生早就注意了这一添加,但是他认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与“古代的生产方式”同处“古代”范围里,可以互换(8)侯外庐:《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中华论坛》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1945年8月。,与马克思把它们视为“不同的规律”是冲突的。
很显然,《资本论》第1卷不仅是简单照应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的生产方式序列思想,而且内涵阐发更为明确。《资本论》第1卷德文本相关表达如下:
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按:altasiatischen, antiken usw. Produktionsweisen,“古希腊罗马的”按照原文应译为“古代的”)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共同体(按:Gemeinwesen,马克思校对的法译本作communauté,恩格斯校对的英译本作primitive communities)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这些古老的(alten)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与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参见Karl Marx, Das Kapital(Berlin : Dietz Verlag,1955), S.85. 德文第三版与此一致,见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MEGA) (Berlin : Dietz Verlag, 1975), II 8, S.10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1章《协作》指出:
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indischer Gemeinwesen)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Stammes)或公社(Gemeinwesen)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这两点使得这种协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古代世界(antiken Welt)、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Sklaverei)为基础。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不过,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
至此添加第24个小注,也指出:
小农经济(kleine Bauernwirtschaft)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共同体(klassischen Gemeinwesen)在其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8页。Karl Marx, Das Kapital, S.350.
此段旧版译为:“无论是小自耕农经济或是独立手工业生产,总有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而另一部分则在封建生产瓦解之后跟资本主义生产一起并存。但是同时,当东方式原始公社财产业已瓦解,而奴隶制度还没有来得及握有任何显著程度的生产之时,小自耕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却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11)转引自《顾准笔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247页。在此之前,还有“独立的农民或独立的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作比较”(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5-386页。Karl Marx, Das Kapital, S.348.的说法,说明“小农经济”就是“独立的农民的生产方式”。按照当时尚农的部族传统,“独立的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则是被释放的奴隶的生产方式。
奴隶制作为劳动形式是与雇佣劳动并列的概念,马克思指出:“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Gesellschaft der Sklaverrei,应译‘奴隶制社会’)和雇佣劳动(Lohnarbeit)的社会区分开来的,只是从直接劳动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51页。Karl Marx, Das Kapital, S.22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指出:“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klassischen Altertums)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民族中,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英国的自耕农,瑞典的农民等级,法国的和德国西部的农民,都属于这一类。在这里,我们没有谈到殖民地,因为那里的独立农民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11页。Karl Marx, Das Kapital, S.858.马克思还指出:“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1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694页。恩格斯把小农的生产方式视为“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16)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7页。。可见,古代的生产方式的内涵是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此前则是小农的生产方式。
在后来马克思校订的法译版中,关于生产方式一句改为“在古亚细亚的,一般说来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modes de production de la vieille Asie, de l’antiquité en général)下”,关于基础一句改为“或者以个人——可以说历史尚未隔断把他同原始部落的天然共同体(communauté naturelle d’une tribu primitive)联系在一起的脐带——尚未成熟为基础,或者以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despotisme et d’esclavage)的条件为基础”(17)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9页。Marx, Le Capital, Traduction de J. Roy(Paris: Flammaron, 1985), 74.。
在恩格斯校订的英译版中,生产方式一句译为“the ancient Asiatic and other ancient modes of production”,遵循了马克思认可的法译;“原始部落的天然共同体”译为“primitive tribal community”,少了“天然”字样;“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译为“direct relations of subjection”,似不如法译明确。可见,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基本是以马克思校订的法译本为基础的。“原始”字样,恩格斯只是根据法文后文在前边也添加了一处,也就是说并非都是恩格斯所新加,而且同一个词“共同体”后文被李根蟠视为“公社”也不合适(18)李根蟠:《“亚细亚生产方式再探讨”——重读〈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第25页。。
通过考察马克思“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概念的原初语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马克思一生中至少三次明确使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概念,一次间接使用“东方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间接谈到“东方的生产方式”,强调的仅仅是共同体内“农业与工业的结合”:“生产方式本身越是保持旧的传统(在农业中,传统的方式是保持得很久的,而在东方的那种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中,保持得更久),也就是说,占有的实际过程(Wirkliche Process)越是保持不变,那么,旧的所有制形式,从而共同体本身,也就越是固定。”(19)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4页。MEGA, II/1.2, S.398.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版中,其时代坐标更为明确,处之于古代,并且与具有特定内涵的“古代的生产方式”一先一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在逻辑上,马克思的用词是“大致说来”,是比所谓“古代的生产方式”更为古老的一种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校订的《资本论》的法译本中,表达更为简洁、确当,倾向于把“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置于“一般说来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范畴之下认识,不再单列“古代的生产方式”。就此而言,在德文外译的过程中,由“大致说来”到“一般说来”,马克思所谓“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无疑可以包括多种,至少包括“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和“古代的生产方式”两种形式。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四种马克思所谓人类社会史前时代对抗的生产方式之上,再加上一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构成一个五种生产方式演进序列。在马克思看来,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历史环境”不同,并不“注定要走这条道路”(20)《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导言》,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第9-1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8页。,由此表现为西欧道路之外的“多条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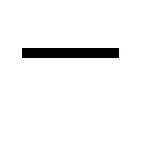
其三,马克思列举的生产方式至少有公社的、家长制的、古亚细亚的、小农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等七八种之多,尽管有的类型马克思语焉不详,但是可以大大拓展我们对《序言》生产方式类型的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指出:“家长制的(patriarchalische),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旧的生产方式”(alte,按照《资本论》当译“古老的”生产方式),“即公社的(Gemeinde)、家长制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等等,就处于解体之中,并准备了真正雇佣劳动的要素。”(31)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上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105、468页。MEGA, II/1.1, S.91, 92; II/1.2, S.377.在1853年1月马克思的英文写作中,明确认定“家长制的社会制度(the patriarchal state of society)”“比封建制度(the feudal state)低一整个阶段”(32)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夫人与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71、572页。MEGA, I 12, S.19, 20.。“家长制的生产方式”应该对应的是希腊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罗马盖尤斯时代的家长制家庭公社(3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页。。马克思法文书信说:“原始公社(communautés primitives)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34)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8页。MEGA, Band 25, S.229.印度公社作为“原始公社”,具有特定的血缘脐带内涵,因此,“公社的生产方式”前置于“家长制的生产方式”。
其四,以“印度的所有制形式”或“印度的公有制形式”为典型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或“亚细亚的公有制形式”,不仅亚洲有,欧洲也有,具有普遍性。对于“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形式”,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二版中特意转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同一个页下注,马克思申明“原始的公有制的形式(按:Form des naturwüchsigen Gemeineigenthums,原译‘原始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公社’字眼应为‘共同’)”“原始公有制(naturwüchsigen Gemeineigenthums)”“原始形式(Urform)”就是“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页。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5页。Karl Marx, Das Kapital, S.83.。马克思所谓“我在我的著作中多次指出的”地方,还包括马克思在研究了毛勒著作后于1868年3月14日致恩格斯的书信,其中表示:“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再次得到了证实”(36)《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3.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3页。。《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恩格斯加注指出:“村社(village communities,法译communes rurales)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3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注释2。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London,1888), 7.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Paris,1953),56.可见,在马克思那里, “亚细亚的公有制形式”“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标志类型的概念。
其五,“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特殊性,因此难以成为东西方文明共同的历史起点,但是并不排除其成为西方文明的逻辑起点。“亚细亚公社”就是“村社”“农村公社”。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对“亚洲村社(asiatische Gemeinwesen)”与西方“小家庭农业(与此相结合的是家庭工业)”做出区分,视之为“劳动与劳动条件之间原有的统一”的“两种主要形式”(38)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65-466页。MEW, Band 26, S.414.。无论是所谓“亚洲村社”还是所谓“村社”,都是从社会形式角度说的,与马克思从所有制形式角度做的说明是一致的,亚洲村社共同体或原始共同所有制都是对原始社会之社会形式或经济形态的说明,与作为所有制形式之前提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实际的占有过程本身不是一个概念,是马克思做出的基本区分。东方形式的特殊性在于共同劳动,手工业和农业两者的结合具有简单协作性。《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指出:“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共同所有制(东方形式)。”其中,“直接的共同所有制”德文原文是unmittelbares Gemeineigenthum。马克思提示说,印度和斯拉夫人的“共同生产和公有制(Gemeineigenthum und Gemeinschaftliche Produktion)”比秘鲁部落(Stämmen)的派生形式更古老“更简单”(39)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9页。MEGA, II/1.2, S.400.。马克思对“共同劳动”的举例是“例如像东方的灌溉渠道那样”(40)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5页。,这是东方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特点之一,由此可见,“共同劳动”并不一定就是“集体耕种”“共同耕作”,“集体耕种”“共同耕作”仅仅保持到家庭公社阶段(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42页。转引自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第16页。,既是“共同劳动”又是个体“份耕”,完全有可能。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共同生产”(42)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60、477页。就是“集体耕种”“共同耕作”,共同劳动含义更广,包括共同修筑公共灌溉工程等等。政府公共水利工程这一项指标,直到近代也根本见不到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发生什么变化,在古希腊、罗马的“古代的生产方式”之前的阶段当地也未见公共水利工程的存在,晚近欧洲名义上“政府修建的水利工程”其实还是私人资本“兴建”的(43)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下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24页。。
基于此,可以澄清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等同于“原始社会”这一主流认知所存在的认识论缺失及其思想根源。
第一,郭沫若把antiken译为“古典的”,指向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但是没有注意到古典古代内部还有阶段划分,因此对“古代的生产方式”内涵的准确理解并不能自然意味着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理解没有缺失。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的理解,“部落所有制”被视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把其时代汉译为“古典古代”很容易引发混乱,因为“古典的”其实马克思有另外的专词“klassischen”或“klassischen Altertums”(古典古代)。侯外庐对此没有注意区分,也影响到他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的基本认知(44)侯外庐:《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中华论坛》第一卷第七、八期合刊,1945年8月。作者《附记》自言“在我写完时,又发现了理论大师的遗著,佐证了我的假定”,但是该文及其后多次修改稿,都未能呈现马克思关于“东方的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点是共同体内工农业结合的相关段落,他对《资本论》“古典古代”的引用其实是“小农的生产方式”。。《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典古代世界(antiken welt,又译为古代世界(45)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6、318页。)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所决定的。”(4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页。恩格斯在此语之后的补语指出:“在古代诸民族(antiken Völkern)中,一个城市里聚居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权利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但是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限于地产。”(47)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48、320页。《德意志意识形态》接着谈到第二种所有制形式,即“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48)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82、254页。。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也有奴隶制的成分,正如其前的部落所有制有奴隶制的成分一样——在“最早的所有制”下,奉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这种“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49)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4、208页。。《德意志意识形态》针对“地产日益集中”之后的古罗马帝国,专门指出:“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50)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36、308页。马克思法文书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更明确指出“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是伴随着小农的生产方式的衰落才“发展起来的”。“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查德文译为Sklavenarbeit beruhende Produktionsweise,即“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51)参见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第9-10页。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页,“奴隶占有制的”一语译为“奴隶制的”,恐不确切。MEW, Band 19, S.112.,应该比汉译更为准确。可见,有“奴隶制(Sklaverei)”并非就一定形成了“奴隶制社会”,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应该是明确的。列宁、斯大林把“奴隶占有制社会”等同于“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52)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5-47页。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6页。,其实马克思更倾向于特指罗马破产小农的“面包和娱乐时代”(53)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2页。。
第二,马克思《序言》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并非“古代的生产方式”完全取代“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而是避难就易,在东西方临界地区的薄弱环节首先实现突破,长期并存。共同所有、共同生产、共同耕作可以抽象为东西方文明起点的共性,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所强调的共同劳动、公社内手工业农业的结合(并非局限于家庭内的农副业结合)却不见于西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区分了“成文史”与“文明史”两个起点,指出“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史的领域”,并且两次提到文明时代的历史是两千五百年(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5、97、113页。,也就是从梭伦改革(前594年)算起。对于家长制家庭,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5页。在1853年6月的英文写作中,马克思谈到印度当时存在的“村社”时,也说“在这种村社内部(Innerhalb)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56)《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6.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2页。MEW, Band28, S.268.。马克思后来进一步说:“财产的各种原始形式”作为“第一种历史状态”,“由于劳动本身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农奴制和奴隶制)之内而在本质上发生变化”,“它们全都包含着奴隶制这种可能”。对工具的所有权作为“第二种历史状态”,“不包含奴隶制和农奴制,但可以在种姓制度的形式中得到类似的否定的发展”(57)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2页。。“在斯拉夫公社、罗马尼亚公社等等地方,才第一次出现最原始意义上的领主的财产支配权。在这里奠定了向徭役制过渡的基础等等”(58)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8页。。恩格斯也说:“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没有地主这个名词”,“只有土耳其人才第一次在被他们征服的东方国家推行了一种地主封建制度”(59)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9-520页。。可见,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社会,奴隶制、农奴制、地主制都是可以存在的,在此前提下,才可能考虑主导趋势的问题。
《反杜林论》提出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的“两条道路”,除了社会职能的国家化这一东方道路,就是西方“农业家族”(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2-525页。即“家长制家庭公社”吸纳奴隶劳动的道路。不过,在梭伦改革废除债务奴隶之后,雅典、罗马这些农业民族所需要的“外面的劳动力”,很大程度上是以战争奴隶来替代的。按照世界历史学家对古希腊罗马历史的阶段划分,古希腊“古典盛期是从马拉松战役开始,而古典后期则在330年结束”(61)朱龙华:《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30-431页。。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两者之间的历时演进关系,只有放在世界历史东西方结构性演进的视角下,以希波战争相勾连才会凸显出来。
“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后,西方“农业公社”存续时间不长,即出现“小农的生产方式”,其后是社会分化为奴隶主、隶农(colonus)、奴隶(专营手工业)和被释奴,在面包和娱乐时代“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在东方则是“亚细亚的形式”“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工农业统一之上”,“这种财产形式所能改变的最小”。马克思虽然也叫它“东方的普遍奴隶制”,但是特别声明,单个的人只是土地占有者,只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所以奴隶制在这里并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62)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2、496、493页。。
无论如何,东方的“奴隶制”“封建制”,并不具有西方那样的奴隶专营手工业畜牧业、封建制与农奴制两面一体这样的连带机制。东西方分途可以希波战争为标志时点。马拉松战役作为强大的波斯帝国对雅典发动的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90年,距离春秋、战国的分界即公元前475年,也就是郭沫若划定的封建社会起点不过15年(63)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2、25页。。很明显,马克思认定的“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其对应的历史时段恰恰是郭沫若认定的奴隶社会。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希波战争应该是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与小农的生产方式之战。恩格斯在谈到罗马共和国末期奴隶排挤小农的地方,紧接着引述了波斯战争期间希腊世界的奴隶数字(每个自由人平均10个奴隶)(6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4页。,很容易让人误认为希波战争时期也发生了相似的情形,其实他后来专门表示“不必去研究已经完全开垦或大部分开垦了的土地,有多少是由奴隶(如在希腊的极盛时期)所耕种”(6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1页。,因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当时是小农耕种。由此可见,对中国历史认识的推进,不仅需要实证研究,还需要理论困境的破除。范文澜与郭沫若对西周大盂鼎中的“庶人”是农奴还是奴隶有不同认定(66)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第一册认为“庶人是农奴一类的人”(第73页);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27页)及《奴隶制时代》(第17-19页),将庶人解释为奴隶。,由此导致的西周封建说与战国封建说的分歧,似乎至今无人弥合。如果从马克思“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理论出发,也许可以避免西方道路阶段论的误区,从而解释更广泛的中国历史素材。
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前提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特别强调东方尤其是亚洲国家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职能而非统治职能,指出:“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67)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2页。马克思当时对印度社会“经济基础”基本特征的这一重要揭示,已经蕴含了后来“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别于印度,对中国来说,“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可以概括为四点:父权家长社会、东方专制政治、蒙古游牧因素、国家形态变迁。
第一,父权家长制度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马克思在谈到中国的“家长制”时,特别凸显了其“君父”“父权”特色,指出:“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68)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0-691页。
马克思在1868年11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俄国公社……这种公社直到最细微之处,都同古日耳曼公社完全一样。此外,在俄国人的公社里还可以看到(在一部分印度公社里也可以看到,不是旁遮普的,而是南部的):第一,公社的管理机构的性质不是民主制的,而是家长制的;第二,向国家交税采用连环保的办法等等。”(69)《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1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84-185页。对于旁遮普公社,马克思指出:“旁遮普……其成员属于同一个克兰(较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氏族)甚至往往出自同一个始祖的土地占有者公社,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尤其在札提人部落中常常可以看到,每一个共同占有者都有一定地段,通常由他本身来耕种……每一个公社社员距始祖远近的不同,决定着由他支配的地段的大小。”(70)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5页。与马克思这一说法有些不同,恩格斯把印度西北旁遮普和高加索的公社界定为“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长制家庭公社”(7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页。。无论如何,父权、家长制是重要制度因素。
第二,东方专制制度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政治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在苏联文本所添加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这一论题下,其实有农业公社与统一体两种表现形式。所谓“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社内部,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72)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474页。,符合马克思所说“农业公社”的内涵。与之不同,“亚细亚的基本形式”的内涵是:“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统一体能够使劳动过程本身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能够成为整套制度。”“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在东方专制制度下……这种部落的或公社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一个小公社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73)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可以说,“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以“农业公社”为基础的,其特殊性仅仅在于它只是更多保留了某种东方原始性,其实指的就是作为“亚细亚形式”之“前提”的“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以及公共的“灌溉渠道”“交通工具等等”,这就把作为“历史前提”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与作为“所有制形式”的“亚细亚形式”(74)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4、474、493页。从概念上区分开来。此前马克思类似的说法也有,只是没有直接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概念而是与“经济基础”的概念联系起来:“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些家庭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75)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2、765页。这一农副业家内结合模式,延续到现代,就成为印度圣雄甘地发动手纺车运动的社会基础。恩格斯整理并于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指出:“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7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2页。马克思1859年《对华贸易》为了证明“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引证了英国官员考察长江沿线、福建沿海的报告:一方面中国农民“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交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另一方面“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帮助,自己织布”(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3、846页。。这些报告呈现的或许可谓“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次生形态,但显然并不是“小农的生产方式”。恩格斯1886年明确谈到中国的生产方式问题,指出中国是“最后一个闭关自守、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1894年依然说“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78)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3.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致劳拉·拉法格(189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5页。。正是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对中国的说明符合马克思“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核心要义。说马克思读摩尔根《古代社会》后改变此前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马克思“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论,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看到马克思说的“印度公社”其实就是摩尔根研究的“氏族公社”。
第三,中国作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具有有别于印度原型的特殊性,那就是中国边疆独特家长制“游牧的生产方式”与中国内地“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并存、共生。马克思对蒙古的认识很可能来自黑格尔:“居住在干燥的高原上的居民——例如蒙古人——过着家长制的游牧生活,就‘历史’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来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他们常常大群地集合起来,像暴风雨一般地侵袭文明国家,在遍地造成毁灭和灾难。”(79)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55页;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485页。“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的命名应该来自公社所有制印度原型论,而非蒙古起源论。马克思在1853年7月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札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0页。马克思1870年2月中旬致路·库格曼的信指出:“公社所有制起源于蒙古的说法是一种历史的谎言。正如我在我的著作中多次指出的那样,它起源于印度,因而在欧洲各文明国家发展的初期都可以看到。俄国公社所有制的特殊斯拉夫的(不是蒙古的)形态(它也可以在非俄罗斯的南方斯拉夫人中看到)甚至最像经过相应的改变的、印度公社所有制的古代德意志的变种。”(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37页。MEW, Band32, S.650.可见,欧洲各文明国家起源于“印度公社所有制”或“亚细亚所有制”,但是,并非起源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本身。
第四,国家形态从封建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变迁,具有普遍性。《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等级君主国(1888年英文版改为半封建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是其过渡形态。恩格斯1884年指出,“通过君主专制把民族结合起来”,“等级的君主制仍然是封建君主制”(82)恩格斯:《关于“农民战争”(1884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59页。。这也可佐证,封建君主制(feudale Monarchie)、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ie)是两个不同阶段、两种不同国家形态。夏商周中国,四土均是王土,实行纵向垂直分封。与此不同,西欧封建的特点则可能存在封君封臣的闭环线路,“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皇帝专制制度建立后,中国长期存在的是封建边疆、郡县内地的二元结构。封建专制政治之下,内地体现为王田制、均田制、地主制等的接续更替,边疆则奉行封建政治(万户制等)、经济制度(农业公社、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等),具有多元统一特点(83)参宋培军:《马克思“农业公社”思想放弃论之我见》,《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清末民初土司的国体地位因革:从四川土司到云南土司》,《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三、结语:“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带有原始部落血缘共同体、专制制度政治共同体的双重属性,无论是把它像郭沫若那样归入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还是像侯外庐那样归入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84)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9页。参见日知:《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文史哲》1952年第2期。,都与马克思的原初语境背离。它是东方独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视之为西方诸生产方式演进的逻辑起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无法回避这一历史起点。我们不能依据《序言》的五种生产方式直接、简单得出马克思主张五种社会形态的结论。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命题倒是启示我们,在西方近代殖民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具有有别于印度、日本、俄罗斯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国作为东方“最后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恩格斯语),自然难说经历了古代的生产方式(不是奴隶制本身)、封建的生产方式(封建农奴制)、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雇佣劳动制)等西方类型诸生产方式序列的典型发展,而经过特殊的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革命诸环节,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联合生产方式,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确实走通了。本来的理论可能性,正在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实践。其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条件下,革命之后要补现代生产力的课,而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古代国家社会职能的较早发育,按照马克思的区分,相对于“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古希腊人这样的“正常的儿童”而称之为“早熟的儿童”(8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9页。,应该是恰当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动力与前提,这其实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通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要以自己的方式走好这关键的一步。在马克思“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理论指导下,汲取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近代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宝贵经验,是重要的理论资源、历史资源,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也要肇基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