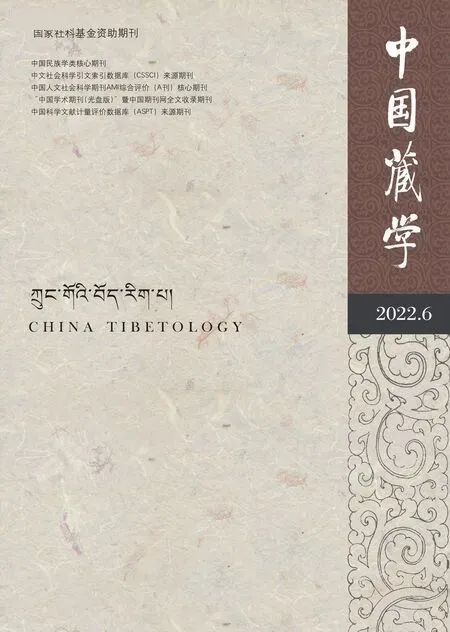成都:一个延续两千年的民族协作传统
——成都在汉藏民族交往中的地位与特点①
石 硕
我因为做藏学研究,结识一些藏族朋友。不少西藏的藏族朋友告诉我,他们到北京等地出差办事,只要回到成都,就像回到家一样,有一种亲切感。进一步询问原因,回答林林总总,不外乎有这样几个理由:1.成都人不欺生,待人热情友善,无论是到面馆吃面,还是问个路什么的,总是很热情。不会因服饰和语言显示你是藏族人而有任何歧视。2.他们在成都大多有亲戚朋友或熟人,这颇能让他们对成都这座城市产生一种亲近感。3.成都东西好吃、种类多,物价不贵 (以西藏为参照),物品丰富,应有尽有,生活舒适方便。4.成都是入藏门户,坐不到两个小时飞机就回家了,所以,回到成都就像到了家门口一样。这是我所接触的藏族朋友对成都带有普遍性的印象和认识。我有一些来自西藏的藏族学生,他们告诉我,近些年,西藏尤其是拉萨的藏族人在成都买房的很多,他们也开始过上“候鸟型”的生活,冬天尤其是春节前后,成都气候较西藏温暖,于是全家到成都生活一段时间,也享受一下大都市的繁华生活。开春后尤其是天气一天天炎热以后,他们又返回西藏。这些都是悄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只是我们平时不太留意罢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在概括成都“天府文化”特点时,提炼出成都的一个重要特点“友善包容”。从以上藏族朋友对成都的印象看,这还真不是成都人的自封和自夸,而是很客观、很贴切并受到周边地区及民族普遍认同的特点。那么,成都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与传统?这个问题很值得深入探究。对一座城市而言,一个传统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几年或几十年的事,往往需要漫长的历史积淀。由此,我想到一个事件,一个发生在成都的延续两千多年的汉藏协作的案例。本文拟对此案例作一分析讨论。虽不能说此案例就是成都“友善包容”特点与传统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但透过此案例,或许能帮助我们认识成都这座对青藏高原地区有巨大辐射力的大型城市,在汉藏民族传统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之一斑。
一、民族学家马长寿揭晓两千年“谜底”
古代遗留下来有关成都的记载,最丰富、最具史料价值的史籍,无疑要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按地方志体例撰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可谓中国地方志的“鼻祖”。①刘琳:《〈华阳国志〉简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第82页。《华阳国志·蜀志》对蜀地的记载尤为丰富、翔实,目前我们对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前古蜀国的情况,尤其对“开国何茫然”的古蜀国先王世系的了解和认识,均来自《华阳国志》。新近三星堆发掘取得的一系列令世人惊异的考古发现,对这些考古发现的认识,均有赖于《华阳国志》提供的重要背景和线索。
《华阳国志》成书于晋代,作者常璩是蜀人,是东晋时蜀郡江原人 (即今成都附近之崇州)。史载他撰著《华阳国志》时,曾“遍读先世遗书”,尤谙熟蜀地及西南之地理、历史及风土社会。②[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我们现在所知晓的“成都”这一地名三千多年不变,其依据正是《华阳国志》。所以,《华阳国志》对我们认识和了解成都的历史,是一部极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史书。
《华阳国志·蜀志》记叙成都时,提及位于蜀之西 (即成都之西)岷江上游“汶山郡”时,有一条重要记载:
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③[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第184—185页。
“汶山郡”是汉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111年)设置的一个郡,主要在岷江上游地区,郡治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县城一带。这条记载说,岷江上游“汶山郡”的“夷人”冬天“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华阳国志》这条记载,被南朝刘宋时范晔所撰《后汉书》完全采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
(冉駹)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众邑。④《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8页。
从以上两条记载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认识:第一,《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完全是源自《华阳国志》;第二,二者均记载岷江上游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夏则避暑反落”,均称“入蜀为佣”“庸赁自食”。但他们“庸赁自食”和“入蜀为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入蜀后他们具体做什么工作,记载中却只字未提。检阅其他史籍和相关研究发现,《华阳国志》和《后汉书》这两条记载,在两千多年中并未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
东汉时期岷江上游“夷人”“入蜀为佣”“庸赁自食”到底是从事什么营生?这个谜底最终揭晓,是在两千多年后的20世纪上半叶。揭晓此谜底的,是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1936—1942年,马长寿多次深入岷江上游嘉绒地区进行田野调查。①王欣:《马长寿先生的川康民族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第134—145页。此后,因抗战和参与筹建中央博物院工作而滞留于成都,并于成都居住。②王欣:《马长寿先生与中央博物院 (下)》,《西北民族论丛》2015年第1期,第194—218页。这使马长寿不仅对岷江上游嘉绒藏族情况有深入了解,也对成都较为熟悉。基于此背景,马长寿在撰著《嘉绒民族社会史》中,③马长寿:《嘉绒民族社会史》,原载于《民族学研究集刊》1944年第4期,收入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专门提及了嘉绒人“入蜀为佣”之情形:
汉佣之制,“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返其邑。”此说常璩《蜀志》亦言之。今日嘉戎尚多如此。每年秋后,嘉戎之民,褐衣左袒,毳冠佩刀,背绳负锤,出灌县西来成都平原。询之,皆为汉人作临时佣工也。其中虽有黑水羌民,然为数无多。按嘉戎佣工精二术,莫与来者:一为凿井,一为砌壁。成都、崇庆、郫、灌之井,大都为此辈凿成。盖成都平原,土质甚厚。井浅则易淤,以深为佳。汉工淘凿无此勇毅。故须嘉戎任之,砌壁更为此族绝技。……所砌壁,坚固整齐。如笔削然,汉匠不能也。④马长寿:《嘉绒民族社会史》,载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第129页。
这段记叙非常重要,其突出价值有以下四点:
1.确凿证明至1940年代,岷江上游的人季节性到成都做佣工的情形仍然延续 从文中“询之”一语可知,马长寿不仅目睹这些到成都做佣工的人,且对其进行过询问,得知他们是“为汉人作临时佣工”。
2.首次明确“入蜀为佣”者是岷江上游的嘉绒藏人 马长寿刚对岷江上游嘉绒地区进行过为期半年的详细调查,所以对于这些人是嘉绒藏人十分肯定。指出他们中“虽有黑水羌民,然为数无多”。澄清了过去多以到成都做佣工的人群是羌族的误解。⑤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记:“茂汶羌民,直至清末民初,犹有多男女结对入成都平原及川北各地卖药、打井及佣力者。”参见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第189页。冯汉骥也认为来成都打井的人群主要是羌人。冯汉骥:《禹生石纽辨》,《川大史学·冯汉骥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39页。
3.首次明确嘉绒藏人到成都所做佣工是“凿井”“砌壁” 如果说我们对《华阳国志》和《后汉书》所记岷江上游“夷人”“入蜀为佣”具体做什么并不清楚,那么,马长寿这段记叙则提供了明确答案:“一为凿井,一为砌壁。”故他们的行头也相对简单:“毳冠佩刀,背绳负锤。”
4.马长寿十分肯定,1940年代嘉绒人季节性到成都做佣工正是《华阳国志》和《后汉书》所记岷江上游“夷人”“入蜀为佣”的延续 马长寿为著名民族学家,尤以民族史研究见长,谙熟民族史料。这段记述中,他一开始即引用《华阳国志》和《后汉书》关于岷江上游“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返其邑”的记载,接着即指出“今日嘉戎尚多如此”。这意味着,马长寿十分确定,每年秋后嘉绒藏人来成都“凿井”“砌壁”这一传统,正是史籍所载岷江上游夷人“入蜀为佣”传统的延续。
综上所述,马长寿这段叙述,揭开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但却在成都居民生活中鲜活存在的事实:岷江上游嘉绒藏族延续两千多年的“入蜀为佣”传统。
二、嘉绒藏族“入蜀为佣”传统何以延续两千年
综上所述,岷江上游地区嘉绒藏族冬季“入蜀为佣”,从事“凿井、砌壁”之佣工,夏季不耐暑热而返回聚邑的传统,从汉代起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延绵了两千多年,真可谓源远流长。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使岷江上游人群“入蜀为佣”的传统能延续两千余年?产生这一传统的机制与内涵是什么?
很显然,这一传统得以产生并延续两千余年,必有其特殊的机制与内涵。从诸多线索看,这是一个民族之间相互协作的传统,这一协作传统之所以产生并源远流长,其核心机制应是成都平原地区居民在凿井取水上的需求,同岷江上游地区嘉绒藏族在“凿井”“砌壁”上特殊技能的有机结合。大体来说,该传统的形成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所造成:
第一,在传统农业时代,成都居民日常饮用水主要靠凿井取水,但成都平原是一个巨大的冲积平原,其泥沙夹卵石的特殊地质结构对凿井提出了极高的技术要求。
富饶且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是数千万年以来在来自青藏高原的岷江、沱江等河流冲击下形成的巨大冲积平原。①钱洪、唐荣昌:《成都平原的形成与演化》,《四川地震》1997年第3期,第3页。在这样的冲积平原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山泉水可以利用。唯一的取水方式,就是凿井取地下水。所以,在没有自来水以前的漫长的传统农业时代,成都平原居民日常生活所需饮用水主要依靠地下水,故凿井取水,成为成都平原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件大事。但是,由于成都平原的地层主要是泥沙夹卵石的地质结构,在这样的地质结构下凿井取水,如果井打得浅,很容易被地层中渗出的泥沙所淤积,井的寿命会很短。如马长寿所言:“盖成都平原,土质甚厚。井浅则易淤,以深为佳。”②马长寿:《嘉绒民族社会史》,载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第129页。因此,过去成都的井,主要是深井。今成都市正通顺街原巴金故居附近,尚有一口作为文物遗迹保留下来的井,名曰“双眼井”。井口的直径不大,大约不到1米,但是井的深度却令人咋舌——至少有10米。要把井打得深,就面临一个很大难题,由于泥沙夹卵石的地质结构,井如果打得很深,井壁很容易垮塌。所以,如何在打深井的情况下能够砌出坚固、结实的井壁,就成为成都平原打一口井成功与否的关键。
第二,至汉代以来岷江上游嘉绒藏族及其先民拥有建造碉楼的精湛砌石绝技。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记载东汉时岷江上游冉駹夷时云:
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
这里所说“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的“邛笼”,正是今广泛分布于嘉绒地区的碉楼。③石硕:《“邛笼”解读》,《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第92—100页。这也是汉文史籍中最早关于青藏高原碉楼的记载。此记载说明,至少东汉时期岷江上游的冉駹夷已有建碉楼的传统,当然也产生了与之相应的砌石技术。需要注意的是,《华阳国志》和《后汉书》所记“入蜀为佣”者,均是在“汶山郡”的条目下。①参见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第184页;《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7页。史籍也明确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在冉駹夷地界设“汶山郡”。②参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7页;[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第184页;《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7页等。既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明确记载,建“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之“邛笼”的正是冉駹夷,则当时岷江上游“入蜀为佣”者,正是有着建“邛笼”传统的冉駹夷人。
对“入蜀为佣”者是有着建造“邛笼”传统的冉駹夷人之事实,尚可由以下两点得到有力印证:
其一,1942年马长寿通过对嘉绒地区为期半年的调查,进一步确认史籍所载“冉駹地理环境,与今嘉绒区全合”,③马长寿:《嘉绒民族社会史》,载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第128页。从而得出“古之冉駹”即“今之嘉绒”的认识,并确定他们正是建造碉楼的人群:
今四川茂、汶、理三县,以岷江为界,自岷江以东多为屋宇,以西多碉楼。且愈西而碉楼愈多,从杂谷脑至大、小金川,凡嘉戎居住之区,无不以碉楼为其建筑之特征。大体言之,碉楼的分布与嘉戎的分布是一致的。④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其二,笔者在做青藏高原地区碉楼的整体调查与研究时,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岷江上游嘉绒藏族地区是迄今整个青藏高原范围碉楼建造最为普遍的地区。嘉绒地区不仅碉楼分布最为密集,也是数量、类型最多的地区。从造型上看,嘉绒地区碉楼从三角、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十二角到十三角均有,具备了碉楼的所有类型。从功能看,则分别有家碉、寨碉、战碉、经堂碉等,按当地民间说法还有公碉、母碉、阴阳碉 (风水碉)、姊妹碉、房中碉等。⑤石硕等:《青藏高原碉楼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从碉楼分布的密集程度看,嘉绒地区亦堪称青藏高原之最。从碉楼数量看,嘉绒地区也是目前青藏高原保留碉楼最多的地区,属于嘉绒地区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因保留有碉楼562座,被人们誉为“千碉之国”。⑥杨嘉铭:《丹巴古碉建筑文化综览》,《中国藏学》2004年第2期,第93页。
综上可以肯定,《华阳国志》《后汉书》所记岷江上游地区季节性“入蜀为佣”者,正是冉駹部落的夷人。从《后汉书》关于“邛笼”的记载看,在东汉时今嘉绒藏族的先民冉駹人已经有建碉楼(“邛笼”)的传统。要建“高者至十余丈”的碉楼,必有高超的石砌技术。至此,我们不难明白,东汉时岷江上游冉駹夷人是凭借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入蜀为佣”。从民国时马长寿记嘉绒藏族季节性“入蜀为佣”主要是“凿井”“砌壁”来看,他们正是凭借精湛的石砌绝技,从事与打井相关的工作。
岷江上游地区石砌技术有多厉害,对当地砌石绝技作过深入调查的任乃强曾有如下描述:
康番各种工业,皆无足观。唯砌乱石墙之工作独巧。“蛮寨子”高数丈,厚数尺之碉墙,什九皆用乱石砌成。此等乱石,即通常山坡之破石乱砾,大小方圆,并无定式。有专门砌墙之番,不用斧凿锤钻,但凭双手一筐,将此等乱石,集取一处,随意砌叠,大小长短,各得其宜;其缝隙用土泥调水填糊,太空处支以小石,不引绳墨,能使圆如规,方如矩,直如矢,垂直地表,不稍倾畸。……此种乱石高墙,且耐久不坏……历经地震未圯,前年丹巴大地震,仅损上端一角,诚奇技也。①任乃强著,西藏社会科学院整理:《西康图经·民俗篇》,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2—254页。
其实,在整个川西高原地区,不仅仅是碉楼,当地高达数层的民居建筑等,均用乱石块砌成。当地工匠,诚如任乃强所说:“随意砌叠,大小长短,各得其宜;其缝隙用土泥调水填糊,太空处支以小石,不引绳墨,能使圆如规,方如矩,直如矢,垂直地表,不稍倾畸。”②同上,第254页。但最能体现精湛石砌绝技的无疑是碉楼的建造。有两个例子可以印证当地砌石绝技达到的精湛程度与水平。
其一,今大渡河上游属于嘉绒地区的金川县马奈镇,屹立着一座高达49.8米的碉楼,是迄今青藏高原地区留存下来的最高的碉楼,号称“碉王”。大渡河处于横断山区鲜水河地质断裂带,是地震频发区域。马尔邦碉王,能在此地震断裂带上巍然屹立达数百年,足证其精湛砌石绝技非同寻常。
其二,2008年在震惊世界的5·12汶川大地震中,呈现了一个让人惊异的事实。近十余年,随着旅游业强劲发展,为进一步吸引游客、增加人文氛围,人们在一些存在古代碉楼的景点又新建了一些现代碉楼,这是现代人用石块砌筑的碉楼。但是,这一类新造碉楼在5·12大地震中大多垮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唯古代遗留下来的碉楼,除个别上部受损外,则大多完好。这充分印证了任乃强“历经地震未圯,前年丹巴大地震,仅损上端一角,诚奇技也”之言。也说明在科技十分发达的今天,古人建造碉楼的精湛砌石绝技仍令现代人难以望其项背。
当地精湛的砌石绝技正是东汉以来在建碉楼的传统下孕育和发展起来,并臻于登峰造极。多年前,我在川西高原调查碉楼时,一位老人告诉我,建碉楼可不是一般人所能为,一寨之中或方圆几十里内仅有一两位这样身怀绝技的工匠,他们的绝技大多是父子或师徒相传,行内有很多行规和秘诀,通常要几十年工夫才能学成。半个世纪前,康藏研究著名学者任乃强充分意识到当地石砌绝技在中国建筑史上的独特价值与地位,将之称作中国建筑之“叠石奇技”。③同上,第252页。
两千多年前,身怀砌石绝技的岷江上游冉駹夷人开始季节性下到成都平原,用其精湛砌石绝技为成都平原居民从事凿井、砌壁的工作。他们成功解决了在泥沙夹卵石地层中开凿深井之难题,用精湛的砌石绝技砌出深达十余米、下大上小的坚固井壁,解决了成都平原居民凿井取水之难题。正如马长寿所说,他们的砌石绝技为“汉匠不能也”。④马长寿:《嘉绒民族社会史》,载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第129页。岷江上游嘉绒藏人季节性来成都平原“凿井”“砌壁”,覆盖地域甚广,如马长寿所说“成都、崇庆、郫、灌之井,大都为此辈凿成”。⑤同上。这意味着他们凿井、砌壁范围覆盖整个成都平原地区。此外,井的使用是有寿命的,一口井用上数年后,其出水量会下降或渐渐干涸,需要进行疏淘,或开凿新井。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亦常以砌壁之绝技为成都平原居民做地面砌墙之类的工作。总之,从马长寿记民国时期嘉绒藏族来成都的行头是“毳冠佩刀,背绳负锤”看,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凿井”“砌壁”。从“褐衣左袒”的衣着特征看,他们无疑都是藏族。
综上所述,在成都的发展历史中,存在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汉藏民族协作传统。正是马长寿对民国时期嘉绒藏人秋后“入蜀为佣”的记叙,为我们揭示了这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两千多年来,岷江上游的嘉绒藏人不仅用他们精湛的砌石绝技建造起众多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碉楼,①青藏高原碉楼已被中国政府正式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参见石硕等:《青藏高原碉楼研究》,第3页。同时也以精湛砌石绝技造福于成都平原居民的凿井取水,书写了汉藏民族协作的佳话。从此意义说,被任乃强称作“叠石奇技”的精湛砌石绝技,其应用范围远不止于岷江上游地区,它不仅建造了当地众多碉楼,也构筑了两千多年成都平原的地下井壁,造福了成都平原居民的饮用水。两千多年来,嘉绒藏族以精湛砌石绝技实际上建造了两座“碉楼”,一是地上碉楼,二是成都平原的“地下井壁”。二者有两个共同点,均下大上小,均为嘉绒藏族及其先民精湛砌石绝技之杰作。
三、当今成都已成为汉藏等各民族和谐共享之城
毫无疑问,成都居民与岷江上游地区藏族之间这种跨越两千多年、源远流长的互助协作传统,正是我们理解成都“友善包容”特点的重要角度之一。这一互助协作传统,不但反映汉藏民族之间的彼此需要与协助,也蕴含了汉藏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积淀。
两千多年过去了。今天,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我们欣喜地看到,成都与青藏高原各民族之间互助协作的传统,仍以新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得到延续和扩大。例如,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青藏高原地区使用最多、最重要的礼仪商品——哈达,绝大部分都是在成都平原的崇州、邛崃等地生产的,再发往涉藏五省区销售。此外,再进一步深入了解,我们会发现,目前销往涉藏地区的许多物品,包括藏式图案的地毯、各类寺院所需宗教用品、藏式风格的文案用品、工艺品、旅游用品,以及藏文书籍及各类印刷品,很多都是在成都平原地区生产,再运往青藏高原各地销售的。这些企业的老板,绝大部分是来自涉藏各地区的藏族年轻人,他们不仅在涉藏地区有广泛的人脉和销售渠道,同时有很多成都本地汉族朋友作为合伙人。我曾询问过其中一些年轻民营企业家,在成都地区生产面向涉藏地区销售的商品有什么优势和好处,他们的回答虽各有侧重,但有一共同点,都提到一个关键——成都容易聘请到各类专业人才。比如,很多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环节,已经离不开电脑,但在涉藏地区找到电脑方面的专业人才就会困难一些;而在成都,电脑专业人才不仅多,而且水平一流,聘请成本也相对低。这让我想到了一点,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起,岷江上游嘉绒藏族的先民正是凭借建造“高者至十余丈”的碉楼所练成的精湛砌石绝技来成都平原“凿井”“砌壁”,解决了“汉匠不能”的深井砌壁难题,造福了成都平原的居民;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生产面向涉藏地区商品的企业大量落户成都平原,同样是要借助成都地区的技术与人才优势,来助推和繁荣青藏高原地区的商品经济与社会发展,造福涉藏地区各族人民。这一现象蕴含着一个深刻道理,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从来就是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相互需要、相互依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源远流长的互助协作传统。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及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在生计即经济上因相互协作所产生的共同性至为重要。“民以食为本”,各民族在经济生活上的相互联系、彼此依存,始终是民族之间产生凝聚力、形成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内容和主要驱动力。马长寿在谈到民族融合时指出:“融合不但是外表的生活样式的变动,更重要的是有着共同经济生活。”②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今天,在中国西部最靠近民族地区的昆明、成都、西宁和兰州四大省会城市中,成都已成为向民族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区辐射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城市,成为青藏高原地区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选择退养、居住、就医、观光购物,以及年轻人求学、创业,实现梦想及享受现代都市生活的主要目的地。成都出现了除拉萨之外销售藏式工艺品、宗教用品的最大商业街——武侯祠商业街,也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诸多藏族人居住社区,如武侯祠、双楠、茶店子、营门口等地,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族人往往按不同地望、籍贯结伴居住。藏语有卫藏、安多和康三大方言区,因成都集中了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藏族人内部遂将成都戏称为藏语“第四大方言区”。都江堰成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后院”,从阿坝州移居都江堰的人自嘲为“十三军” (因阿坝州共有13个县,故名),当地人也亲切以此称呼他们,此称谓带有四川人特有的幽默意味。成都双流 (原为县,现为“双流区”)因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移居成都的集中居住地,甘孜人遂将双流戏称为甘孜州“第十九个县”。除此之外,在成都周边的温江、崇州、邛崃、郫都等地,都居住着大量来自西藏、青海、甘肃乃至云南迪庆的藏族人,他们往往以原所在地三五成群集中购房居住,或是选择“候鸟型”居住模式。成都及其周边平原地区之所以受到青藏高原地区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青睐,成为其退养、居住、求学、创业、就医,乃至观光购物、享受现代都市生活的主要目的地,除了气候温暖、经济发达、生活舒适等特点外,也与成都人自来乐观幽默,对少数民族同胞“包容友善”的传统密切相关。这种历史传统与人文禀赋,使成都受到青藏高原地区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高度认同与青睐。记得有一段时间,成都五城区内限制外地人购房,一位拉萨藏族朋友对此深感遗憾,对我说:“能不能请老师帮我们呼吁一下,很多拉萨家庭听到这个政策深感失望,断了我们在成都居住和享受现代大都市生活的梦想。”我国在民族政策方面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即“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同奋斗,共享社会发展与繁荣成果,正是我党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
成都平原居民同青藏高原藏族先民间延续两千多年的协作互补,是民族“共享”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成都“包容友善”特点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成都受到青藏高原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认同与青睐,形成普遍“共享”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