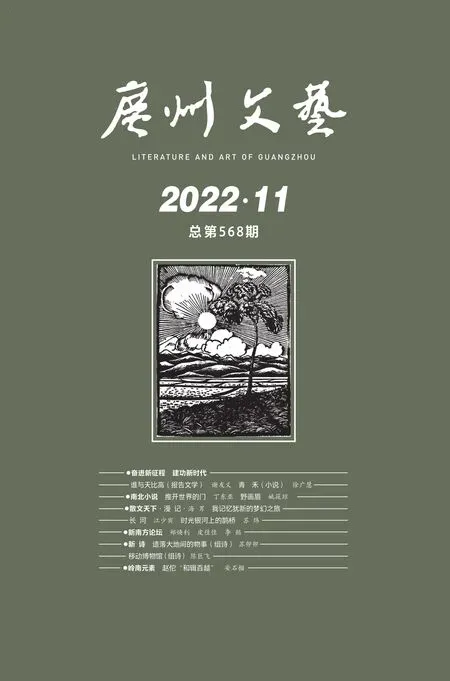书写南中国的野生气息
——五条人音乐的地方性视角
郑焕钊
在我看来,最具标志性的记录全球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艺术家,一个是用电影作为眼睛的贾樟柯,一个则是用音乐讲述故事的五条人。贾樟柯借助其镜头下的小武等人物,让山西汾阳成为一个全球化中的中国社会的独特样本;而五条人则在他的音乐中,把海丰县城和广州城中村作为铭记这一过程的中国南方的独特标志。
事实上,不是那些外表光鲜的中产阶层,而是生活于县城,乃至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的小镇青年,其如塑胶袋一般漂泊流动和粗粝轻浮的情感、欲望、希望与失落,最典型地表征着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最多数,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情感与心理结构。在小镇青年的男男女女身上,凝结着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全球与地方所交混的文化特质。他们似乎是一面面变形的哈哈镜,把这个转型过程中的方方面面进行扭曲与变形,让这一切在“非其所是”与“如其所是”中显现。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贾樟柯的电影与五条人的音乐中找到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书写城乡底层小人物、记录被遗忘的社会转型记忆、纪实性与荒诞性的夹杂等。
如此,地方性就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人物生存的某个具体的地理环境与人物风情,也不只是一种影响艺术家创作的本土资源和经验视域,更不同于那种作为写作的对象。地方性被嵌入一个更大的历史历程和空间视野,它成为一个时代整体结构的一部分,是一个时代所谓整体性与普遍性的分形: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时代精神的具体例子意义上的普遍与特殊,而是离开特殊就没有普遍的那种具体的地方性。贾樟柯的北方与五条人的南方显示出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的不同面相:一种是国企转型、全球资本与阶层分化下的中国北方县城青年的精神世界与道德图景;一种是商业、流动与喧嚣市井声中的拥挤在一起的底层走鬼、发廊男女与打工青年的情感与现实。
全球化与地方性、转型中国与城乡社会,正是以各种不同的地方性面相显露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书写地方性,就是要找到时代之于特定空间的具身性。实际上,五条人的音乐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这种地方具身性理解的自觉。在2009年发行的第一张录音专辑《县城记》的第一首歌《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中,五条人就确立了其全球地方性音乐表述的框架:县城小人物以具体的地方性感受体验着在全球化流动的历史时间的冲击。在这里,五条人既用充满地方方言特色的语言来表达一种对全球化的地方感受,比如,用着传统认知中的“旧年番薯今年芋头”来理解国家经济与楼价的疯长,又通过各种乐器、环境声乃至呐喊的声音(“乒乒乓乓啊,摆着圈”)营造一种抽象的感受“震惊”性。“今天啊全球化,明日就自己过”,音乐更直接将全球化和个体性的关系作为主题标出。这是一种以海丰方言为主体的方言民谣。“海丰”在这里,不仅作为一种南方方言、一个南方小县城,更是全球化的一个舞台,上演着被卷入全球化的中国南方小县城小人物的情感和故事:看守所中的道山靓仔、“倒港纸”的古巴的表叔公、平淡艰难的李阿伯、光棍阿炳耀……他们生活在“农村唔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踏架脚车牵条猪》)的县城,一边似乎还是充满田园乐趣、岭外扬帆清早捕鱼的农耕渔樵生活(《绿苍苍》),另一边则是摩托声震耳欲聋的街道、因为移民而分手的恋人、代表着工业化的永艺服装厂……全球化似乎离他们很远,又似乎离得很近。五条人正以其生猛的方言与粗粝的音乐风格,记录下全球化时代小县城这些终将被遗忘的声音。
诚如“区区五百元先生”对五条人音乐“立足全球,放眼海丰”的概括所显示的那样,全球地方感视角是五条人音乐记录全球化时代与转型中国时期广东南方性的一种独特视野。如果说,“立足地方,放眼世界”是我们经常所遇见的一种书写地方的表述框架的话——在这种表述框架中,“地方”的特殊性、具体性成为出发点、立足点,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根据;而“全球”则成为一种地方性参与下的世界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思考——那么,“立足全球,放眼海丰”则呈现了一种不同的地方表述的模式。在这里,“全球性”,或者说世界性/普遍性成为一个立足点、一个出发地;“地方性”在此不再以其特殊性和具体性而呈现其价值,而是成为全球性的一个具身、全球化的一种显现、世界性的一种表述,乃至于普遍性的一种可能。
从写海丰县城的《县城记》,到离开县城走向大城市、生活于城乡接合部的《一些风景》(2012年)、珠三角大城市城中村的《广东姑娘》(2015年)、《梦幻丽莎发廊》(2016年)、《故事会》(2019年),再到疫情时期的《活鱼逆流而上,死鱼随波逐流》《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2021年)中的武汉、越南等,五条人音乐中所记录和表达的地理空间不断流动与变化,而其歌词语言也随着其空间的变化与对象的不同,显露出多样化的特征。普通话、粤语、客家话、长沙话、包头话,甚至英语、泰语,构成其音乐歌词语言的鲜明特色。比如,记录广州购书中心门口摆地摊的走鬼小贩日常的《很多很多》,就用不同方言腔调的“很多很多”描摹城管与各种不同“走鬼”的生动神态。《陈先生》用三句简洁的歌词概括军阀陈炯明的一生:“1897年,伊生于海丰;1933年,佢死于香港;1934年,其葬于惠州”,三句分别用海丰话、粤语和客家话吟唱,不置评价,而是以不同地域对应的方言来呈现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在简约与空白中留下巨大的历史空间。《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则主要用普通话表达着一个大城市中来自各地的男男女女的爱情与梦想。五条人的音乐并不固执于某一方言,其器乐声音更是包罗万象,手风琴、木吉他、贝斯、二胡、鼓,甚至塑料桶都可以成为他们声音演奏的一部分。而在其《彭阿湃》等代表作品中,更直接将潮剧唱腔道白、环境声与摇滚、民谣等混杂在一起,而近期的作品更不断融合电吉他等而制造迷幻的音乐风格,未来感与复古风格完美融合。
这种混杂性非但没有削弱五条人音乐的地方性标志,它甚至增强并彰显了他们音乐的南方性,这得益于五条人音乐中的叙事方式。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通过比较故事、长篇小说与报纸信息的区别,指出“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而这种经验的交流,正是得益于其“避免诠释”的奥妙,“作品由读者以自己的方式见仁见智。由此,叙述赢得了消息所欠缺的丰满与充实”。本雅明所强调的讲故事的不诠释的特征,正是五条人音乐中鲜明的故事性表述方式的特点,他们的第四张录音专辑直接致敬《故事会》,串联起各式小人物的故事。
可以说,贯穿于五条人不同时期音乐风格的是其写小人物小故事的白描方式,以及通过各种声音的组合去再现和表达特定氛围、情绪的音乐性特征。他们在三笔两画中,写活了各式小人物:道山靓仔、阿珍、阿强、李阿伯、阿炳耀……他们用属于这些人物的方言俚语,捕捉住人物特有的情绪与状态,比如“人生倾像种荔枝耶,有雨也累,无雨也累”道出了李阿伯的艰难。他们更善于通过音乐结构的戏剧性和叙事性的构建来呈现更丰富的时代经验乃至历史经验。比如《曹操你别怕》中的戏台上的曹操与田垄上的械斗双线叙事,又比如《彭阿湃》对彭湃革命形象的正反对立方的讲述所带来的戏剧效果。正是借助于故事的白描、留白与戏剧结构的对立与复调,乃至于某种电影蒙太奇般的拼贴与渲染,五条人音乐中充满着丰富的故事层次感、生活戏剧感和独特的人生态度。五条人对这些故事的白描,以及多层次对话关系的铺陈构设,让这种故事中的经验呈现出开放性的意义向度,甚至透过不同的乐队现场与录音版本的不断演绎和实验,践行着一种故事口头传统的经验交流的属性。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视野来看,地方性表征着一种与总体性、普遍性与宏大叙事不同的差异性、具体性和个体化叙事。无论是情境艺术、人体艺术,都强调艺术表达的地方性和现场性。五条人音乐中的底层性、现场感,乃至于地方性,都凸显了这种后现代叙事的特征。
五条人音乐中各种各样的故事,无不关联着各种丰富的时代和历史经验。张晓舟曾经这样评价《广东姑娘》,认为这张专辑主打爱情,“比较甜,像当地的甜豆浆或者狗尾糕,甜甜腻腻的。你能在他们的音乐中闻到香水味、汗臭味,还有春天刚下过雨,木棉花散落在地上的那种潮湿味儿。他们这张唱片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情歌表达的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爱情’,唤醒的是一种集体记忆,一种关于旧时代南方歌厅,南方舞厅的历史记忆,‘广东姑娘’是一个大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符号”。南方独有的乡土文化、全球化时代岭南的时尚风情,乃至于糅合着务实而又怀抱着梦想的南方小人物形象,以及那些在燥热的城中村的爱情与生活,构成了五条人音乐叙事的南方气息,这是一种乐评人邱大立所说的“南中国的野生之气”。对五条人而言,包括方言在内的各种地方性文化要素,都是服从于其南方叙事的总体气息:一种全球化时代亚热代南方躁动的生命气息及其展现的生命样态与精神状态。正是这种内在的全球地方性气息,使五条人的音乐即使是面向疫情时期的全球化反思,比如《地球仪》《隔壁的诗人》,乃至于充满哲学气息的《世界的理想》《在码头》《塑料花》,也让人一听就感受到那份独有的南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