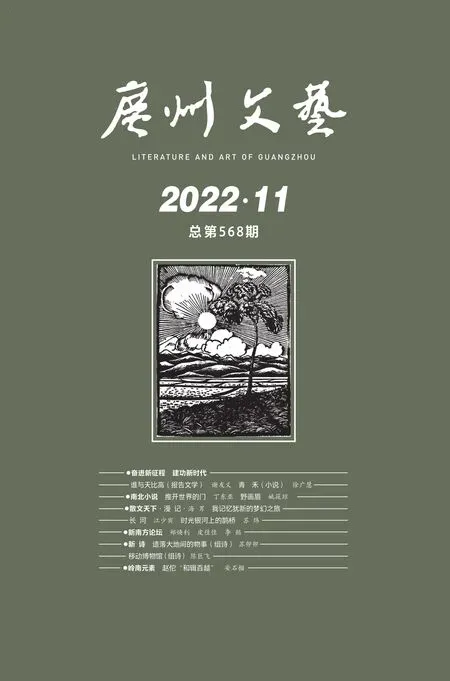长 河
江少宾
天阴着,西北风冷飕飕的,洪水一样灌进门。他从门缝里探出头来,望天。他望天,是担心雨雪。雨雪天,路上泥泞,他拄拐杖,走路,进山,都不方便。
这是一间逼仄的堂屋。中堂上挂着一幅钟馗图,钟馗图下面蹲着一张单薄的方桌,桌面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方桌上搁着一只暖水瓶,瓶胆外围包着一圈篾片。暖水瓶周围,摆着几只喝水的玻璃杯子,有的豁了口,有的很久没有动过了,里里外外都是灰。最显眼的,是一只手掌大小的紫砂壶,壶身圆滚滚,上面横着一枝修长的兰花。堂屋右侧连着一座冷锅台,锅洞旁边摆着一大三小四只箩筐。大箩筐里装着山芋,另外三只小箩筐里,分别装着鸡蛋、挂面和十几只粗粝的蓝边碗。堂屋左侧是他的卧室,进门是一张平头床,床上乱糟糟、黑漆漆的,被褥和衣服裹成一团。衣柜是最豪华的家具了,漆色幽暗,柜门上浮着两小面木雕。木雕是喜鹊登梅,一面梅枝向左,一面梅枝向右,枝上隐约可见两三片积雪。喜鹊肥肥的,拖着长长的尾羽,昂着头,似乎在说,前面就是春天。
他抄冷水洗脸,呼呼呼,响亮地擤鼻涕。一块掉色的干毛巾挂在门后的绳子上,他伸过脸,潦草地擦了一把。
穿上黑色的圆头布鞋,扣好草绿色的军大衣,系好毛茸茸的耳帽,背起旧褡裢,他将拐杖夹在腋下,在渐渐亮起来的天光里出门了。拐杖是一根圆木棍,手腕一样粗细,安着一个龙头形状的把手。龙头已经磨得圆圆滑滑,像一块温润的老玉,裹着岁月的包浆。这是什么木头呢?许多人打眼瞅过,瞅不出来,能打眼瞅出来的,是这根拐杖已经走过不少年头。他倚重这根拐杖,也珍视这根拐杖,到哪儿都不离身。孩子想拿过来玩,他死活不松手,说,一根打狗棍,有什么好看的?狗还以为你要打它呢……
他寄居的这座老街还不到一里长,百货商店、早点铺、邮电局、家电修理铺、理发店、裁缝店、录像厅、照相馆……挤挤挨挨地排成两列。腊月皇天,小街清寂,空荡荡的,黄叶漫卷。他拄着拐杖,微微倾着上半身,步幅很小,步履坚定。
出门时天方破晓,归来时薄暮冥冥,橘红色的夕阳慢慢滑向长河,河水汤汤,红绸子一样荡漾。长河,不长,也不宽,从小街身后缓缓流过,不紧不慢地汇入长江。“回来啦?”擦肩而过的邻居照例询问。他空茫地微笑着,点点头,算是回应。漫长的枯寂岁月里,他成了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嘴唇薄薄,抿着,脸紧绷绷的,像两片瓦。
几十年了,长河岸边的垂柳老态龙钟,枝干大面积皲裂,中间腐出一个个空洞。灰椋鸟在其间筑巢、孵蛋、育雏,不亦乐乎。都以为树已经死了,其实,树比人耐活。几百年的古树,在偏僻的乡下,尤其是在那些旷远的山坳里,我见过很多。当春风捎来雨水,老柳又爆出嫩芽,枝丫一夜泛青。没有黄鹂。细雨中,一群白鹭拎着瘦长的小脚,优雅地低飞,像一团团积雪扑进长河。
几十年了,拐杖成了他的第三条腿。他带着这条腿走路,也带着这条腿讨生活,风里来,雨里去。择屋基,相坟山,泥墓,立碑,这是乡下顶重要的几件事。这几件事都需要堪舆。这不是封建迷信,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
他是方圆数里最受欢迎的堪舆师。堪舆师,牌楼人称之为“相公”,就是看风水的师傅。
他怎么就成了相公呢?不止一个东家问他,师出何门?师从何人?他总是微微一笑,讳莫如深。
说来话长。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知道原委的人,走的走,老的老,几乎没人再提了。
他叫二祥,那些年,牌楼人管他叫“二少爷”。他父亲是个老石匠,五短身材,一年四季,至少有三季打赤脚。长年累月的锻打,老石匠的右胳膊明显比左胳膊粗,硬邦邦的,像一块浑圆的木头。老话说,“世间三样苦,打铁撑船磨豆腐”。这三样我都见过,确实苦,但这三样都比石匠苦吗?我不觉得。石匠是传承时间最久的职业,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旧时代,开采石头全靠手工,累,还不安全。留传千古的碑文、精美绝伦的佛像,无不出自石匠之手。鬼斧神工的背后,是繁复的工艺,其苦自不待言。石匠风餐露宿,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说。知道石匠苦的,或许,只有山间的松风和山巅的明月吧。
老石匠一生只带了六个徒弟,有的是同宗,有的是同族,有的是直系亲戚。来拜师的后生很多,绝大多数是为了混一口饭吃。手艺人做工,哪怕是学徒,肚子总是能填饱的。但口腹之欲还是抵抗不了做工之苦,有些人还没摸到边呢,便从老石匠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老石匠风风雨雨里辛苦了半生,心如明镜,对那些半路离开甚至不辞而别的,既不生气,也不计较。“水生昨天没来,今天没来,你猜猜,水生明天来不来啊?”他一只手抱着二少爷,一只手拎着大铁锤,自问自答似的说,“学手艺啊,除了慧根,也要缘分。缘分到了,自然会来;缘分没到的,来了也会走……”二祥懵懵懂懂地听着,津津有味地吃着蛇莓。巢山上蛇莓很多,但敢吃蛇莓的人不多,直接摘下来吃的人,更少。蛇吃的果子,人怎么能吃呢?有毒的。
“蛇莓真的有毒吗?”我不止一次问过父亲。父亲总是模棱两可地说:“我们都没吃过,那么些蛇莓,差不多被二少爷一个人吃光了。”
老石匠四代单传,对于二少爷这个膝下唯一的男丁,自然是百般疼爱。老石匠抱着他吃饭,搂着他睡觉,出门干活更要带在身边,须臾不离。石匠做的似乎都是粗活,但粗中有细,设计、打石、雕刻,每一道工序都来不得半点马虎。老石匠武师授徒一般,细细拆解一招一式,慢慢说给二少爷。他的心思明摆着,百年之后,二少爷得像他年少时一样,接过老太爷传下来的衣钵。木匠的斧子,石匠的锤子。老太爷用过的锤子,图腾一样挂在墙上,每一次抬头,他心里都直敲小鼓。老话说,三岁看大,六岁看老。六岁的二少爷根本坐不住,一进山就成了脱缰的野马,挖穿山甲,抓野鸡,追野兔,直到汗流浃背,才气喘吁吁地坐回老石匠身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心不在焉地听着。
老石匠变着法子哄他,说尽了好话。
又过了几年。二少爷十岁,个头已经赶上老石匠,依旧好动,三心二意,天一冷便赖在床上,磨蹭着,不愿意进山。独自进山的老石匠垂着白苍苍的脑袋,经常一路走,一路唉声叹气。阴雨天,不能进山,他便一个人窝在家里喝闷酒,喝完了,哀哀地哭。
老石匠和我父亲同龄,又是世亲,逢年过节,我们两家总要互相串门,哪家有了大事,对方都是坐首席的人。有一次,父亲请老石匠喝酒,说:“表爷啊,凡事都要想开些,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做长辈的,尽到责任就是了,你别把自己愁坏了。你看你这两年,头发都掉完了。”
老石匠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便抱着头,长吁短叹。
“二少爷脑子灵光,不管找点什么事做做,随他自己,只要肯吃苦,还愁没有饭吃嘛。”我父亲给老石匠满上一杯酒,又说。
“老太爷的锤子还在墙上挂着,要是在我手上丢掉了,我就是死,也不能闭眼啊!”老石匠忽然端起杯子,又是一饮而尽,接着说,“你要是我,你怎么搞?他不学,就让他不学吗?那还不翻天了!”
父亲有些尴尬,好半天之后才咳嗽了一声,说:“吃菜,吃菜。”
又过了几年,二少爷十四岁,还是浑浑噩噩,驴唇不对马嘴,连最基础的打石也干不下来。有一次,老石匠一面喝酒一面骂:“老子前世作了什么孽哦,养了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老子十四岁不到,就自己出来单干了……”
当时,二少爷正蹲在门口的泡桐树下喝稀饭,老石匠话音未落,便听得门外哐当一声,二少爷怒目圆睁,手里的碗砸在地上,已经摔得稀巴烂。
战争一触即发。
日落时分才归家的二少爷,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像往常一样径直走进厨房,揭开锅盖,正准备盛饭,忽见老石匠蹿出耳房,手里拿着荆条,阴着脸,眼里几乎喷出火来。他准备拔腿,已经迟了,老石匠拦在他面前,双腿利索地向身后一钩,大门吱呀一声,合上了。
二少爷无路可逃,他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索性站在老石匠面前,梗着脖子说:“你打啊,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拇指粗细的荆条,冲着二少爷,雨点一样砸下来。二祥妈心疼儿子,张开双臂,拦在儿子面前,母鸡一样护着。老石匠气不打一处来,他更加疯狂地挥舞着荆条,一面挥舞一面恶狠狠地说:“看老子打不死你!看老子打不死你!”荆条不认人。二祥妈知道自己护不住了,儿子难逃一顿打,只好跺跺脚,狠狠心,挎着篮子,进了田畴。
“你打吧,你打吧。你自己养的,你自己打死。”
门开了,孤立无援的二少爷不仅没有夺门而逃,反倒一声不吭,驴拉磨一样在室内转圈。
荆条打断了。老石匠气喘吁吁,一屁股跌坐在凳子上。
恨铁不成钢。这一次,老石匠固然下了狠手,但他还是手下留情,二少爷的脸好好的,没有一点伤。
又过了几年,东风吹来满眼春,我父亲承包了村里的轮窑厂,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是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小伙子穿上了喇叭裤,媳妇们踩上了缝纫机。那也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老百姓的口袋渐渐鼓了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比赛似的盖房子。砖瓦供不应求。开窑那几天,厂里挤满了抢购的老百姓,白天人声鼎沸,夜晚灯火通明。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厂里除了烧窑的师傅,还有十七个小工。父亲吃住都在厂里,既当厂长,又做厨师,事必躬亲。厨房就是一间很简易的铁皮棚子,中间垒着一座高高的土灶台,灶台上坐着两口大铁锅。父亲往锅洞里塞干柴,幽蓝色的火焰绸缎一样抽上来,呼呼呼。锅盖上热气蒸腾,热气里米香翻滚。那么浓郁的米香,除了父亲的窑厂,我在其他地方没有闻到过。时候到了,揭开锅盖,洁白的大米在高温下一粒粒胀开。那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大锅饭。我可以寡口吃,不要菜。
二祥妈经常到厂里给我父亲打下手,只干活,不要钱。她做的萝卜丝烧肉很好吃,色香味俱全,用锅盛上桌,十几双筷子便要在锅里打架,一时间兵荒马乱。一到饭点,二少爷就来了,蹲在锅洞旁边,头插在碗里,猪拱食一样呼啦呼啦,吃完抹抹嘴,碗一丢,掉头就走。他怯火我父亲。每次照面,我父亲总是一言不发,沉着脸。
“表爷啊,二少爷不学手艺,总要学着做一点事,难不成,你们还能喂他一辈子啊?”有一次,父亲对老石匠这样说。
老石匠红了脸,说:“我在一天,保他一天,没其他法子想。总不能看他活活饿死啊!”
“你们还是惯他。我说句你别介意的话,二少爷,硬是给你们惯坏了。”
老石匠叹了一口气,说:“我晓得,要讲坏,他已经坏尽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怎么搞呢,我不晓得怎么搞。”
“他日子还长呢,总要娶亲。这样游手好闲,东打油西打浪,哪个女的愿意跟他?”
老石匠怔怔的,好半天之后才缓过神来,慢腾腾地说:“有福是他享,有祸是他担。我现在巴不得早点死,眼不见为净。一天熬到晚,一年熬到头,你不晓得,熬得苦焦苦焦的。”
“表爷,你哪能这样想呢?就算不学手艺,这年头,也饿不死人啊。”父亲沉吟了片刻,接着说,“他可愿意到厂里来呢?只要他愿意来,随便他做么事,我总不会亏了他。”
“他一个是好吃懒做,另一个,他怯火你。”老石匠望着我父亲,说,“我估计,十有八九,他不肯来。”
我父亲不说话了。
知子莫如父。二少爷果然不肯进厂,连二祥妈也没有再来帮忙,路上碰到我父亲,她总是闪到路边,红着脸,讪讪的。父亲后悔自己说了重话,打人不打脸,二少爷就是再不堪,总归是他们拉扯大的亲生儿子啊。
父亲虽然后悔,但也没有往深处想,抬头不见低头见,又是多年的老亲,还能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
造化弄人。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老石匠突遇飞来横祸,撒手人寰。
那一天,老石匠埋下的炸药迟迟没有爆炸,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作为一个久经风霜的爆破手,他已经见怪不怪了。他像过去一样往上爬,想看看炸药为什么没有爆炸,谁料他刚走近炮眼,炸药就响了,他和乱石一起被炸上天,而后又摔下山。
父亲从窑厂急匆匆赶来,老石匠身上千疮百孔,人也已奄奄一息了。“表爷,你睁一下眼!我是江友正!表爷,你睁一下眼!”父亲跪在地上,把老石匠血糊糊的头搂在怀里,贴着他的耳朵,喊。
他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嘴里一直在漫血,噗,噗,像沸腾的气泡,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快把他的脸淹没了。
二少爷傻傻地站在他面前,久久地盯着,像盯着一个陌生人,一言不发。
卫生所的唐医生赶来了。他翻开老石匠的眼睑,对二少爷说:“别愣着了。赶紧给你大换身衣服,准备后事吧!”
“表爷,你有什么话,就对我说吧!”父亲握着老石匠的手,哽咽着说。
老石匠的呼吸越来越重,胸腔突然急剧起伏。父亲知道他有话要说,赶忙低下头。
“二祥,我只能托你了。你无论如何,要想想法子,帮他讨一门亲……”
“好,你放心。”
“小仓里,有根拐杖,老太爷的,不要扔……”
话未说完,他的脑袋便耷拉了下来。
归啊!归啊!杜宇声声,老石匠再也听不见了。山墙边,杏子已经熟了,绿叶间,黄灿灿。这是他种的杏子树啊,还有一大蓬燃烧的栀子花。远处的田畴里,小麦已经开镰了,乡亲们顶着草帽,埋着头,飞快地舞动着镰刀。田畴尽头便是父亲的窑厂,又要开窑了,稻草垛一样圆滚滚的窑顶上,白烟袅袅。这是三夏时节的牌楼,一碧如洗,梅雨就要来了。
父亲丢下窑厂,坐镇指挥老石匠的葬礼,他从头到尾地操持,不厌其烦,事无巨细。直到七七四十九天,烧了灵屋,挂了遗像,父亲才喊住二少爷,说:“小仓里有根拐杖,是老太爷的。你大留了话,不能扔。”
二少爷去了小仓,从仓门后面掏出一根拐杖,神情漠然。父亲端详了片刻,那就是一根平常的拐杖,手腕一样粗细,龙头形状的把手,光滑水亮。
“你大走了,你妈身体也不好,这个家,往后要靠你撑了。”父亲沉吟片刻,接着对二少爷说,“你要是愿意,就到厂里去做点事。随便你想做么事都行,我总不会亏了你。”
二少爷一直没来。父亲眼巴巴地候着,最终等来的,是又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
老石匠留下三间瓦房、几亩薄田。在田畴里抢收抢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的,是满头白发的二祥妈。转眼就是初秋,田畴里的二祥妈忽然一个踉跄,大家都看着呢,谁料她再也没能站起来,张着嘴,睁着眼,一脸惊恐。
不幸突如其来,大伙惊呆了。半年时间不到,前脚撵后脚,老石匠夫妇俩的命,也太苦了!扼腕叹息之余,大家一致将矛头指向二少爷。
“根子还在那个败家子,好吃懒做。他稍微争点气,娘老子也不至于这样烦神;不烦神,也不会走得这么早。夫妻两个,五十岁都不到。”
“他夫妻两个,可怜是真可怜,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全喂了那个败家子。我讲句不怕雷打的话,还不如喂条狗!”
……
葬完母亲的二少爷,沦为一个人见人骂的巨婴。他虽然已经成年,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几乎是个废人。他有三个姐姐,在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岁月里,三个姐姐先后远嫁。她们商量好了似的,跪在门外,朝父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一路走一路哭,再没有回过牌楼。
骂归骂,恨归恨,人心都是肉长的,老石匠尸骨未寒,就一根独苗,谁也不忍心看着他在家里饿死。胡家吃早饭了,想起二少爷,送去一大碗菜泡饭;曾家吃中饭了,想起二少爷,拿出一只蓝边碗,米饭压得实实的,又盛了一大碗红烧冬瓜;朱家大婶手巧,端午了,想起二少爷,做了十几个蒿子粑粑……每次去,二少爷都可怜兮兮地靠在门框上,泪汪汪,手里握着拐杖。
“你可知道姐姐家在哪儿?”
他摇了摇头。
“三个姐姐,你一个都不知道啊?”
他还是摇了摇头。
“二少爷,到底怎么搞呢?他这样漂着,浮萍一样,不算个事啊。”老人顾念老石匠,经常在我父亲面前唠叨。
“我晓得不算个事啊,没法子想。怎搞呢,逼逼他也好。”
——这句话,成了父亲晚年最大的心结。他万万没有想到,二少爷居然不辞而别。
发现端倪的,是满升大爷。“四爷,我跟你讲个事,你分析分析。”这天正午,满升大爷忽然跑到厂里,对我父亲说,“二少爷门上落了锁。我观察了两天,二少爷,肯定不在家里。”
父亲慌了神。他丢下满升大爷,直接冲出窑洞,穿过田畴,往二少爷家里跑。
前门后门都落了锁。父亲凑近窗户,卧室里,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父亲急得团团转,像热锅上的蚂蚁。唐庄、杏庄、桃园、破罡、万桥……父亲访遍了附近十几个村镇,逢人就问,但谁也没有见到二少爷。
父亲第二次丢下窑厂,外出寻人。他从镇里找到县里,又从县里找到省里,最后甚至去了邻近的江苏、江西、河南、山东。
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二少爷杳无音信。
父亲寝食难安。那段时间,他几乎不能合眼,只要合眼,老石匠便一脸愁容、一言不发地站在他面前。
又过了两年,二少爷依旧踪迹全无。多年东奔西走,父亲的窑厂经营不善,不得不宣告破产。巨额的债务和解不开的心结,沉甸甸地压迫着父亲的晚年。
父亲飞快地老了下去,母亲过世后,他不得不进城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寄居在城里,但每年清明、冬至,父亲都要带着我们回牌楼,到老石匠坟前,祭拜、烧纸。每一次,父亲都要说:“表爷啊,我对不起你,我没帮你看好二少爷。你要知道他在哪儿,你就托个梦给我,我跑不动了,我让儿子找去……”
老石匠给父亲托过梦吗?我不知道。或许也托过,只是他没有说。
父亲是带着遗憾走的,直到过世,他也没有再见到二少爷。弥留前夜,父亲拍打着床沿,呜咽着:“我怎么去见你老表爷?我怎么去见你老表爷……”
二少爷的消息,我是听春生说的。春生是从牌楼考走的第五个大学生。大学毕业的春生,不顾亲友强烈反对,又回到牌楼,流转两百亩土地,主打生态农业。他赶上了好时候,家庭农场发展迅猛,养殖、垂钓、原生态蔬菜、无公害瓜果,一时间风生水起。春生祖父过世早,他想给老坟立块碑,听说扫帚沟老街来了个相公,道行深,便眼巴巴地跑去请,一看,居然是二少爷。
“扫帚沟,也不算太远。他房子还在,怎么一次都不回来呢?”我有些不解。
“他什么都不记得了,”春生说,“我翻来覆去地盘他,盘到最后,高低不睬我。我请了两次,他高低不来,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真的假的啊?”我有些惶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这是电视里常演的事情啊。
春生说:“他给人做相公,不给钱也行,只要有酒。手艺人,出门又不带锅,本来就要管酒管饭啊。你讲,谁不喜欢请他呢?排着队去请。”
“他喜欢喝酒,出门,总要揣一个小酒壶,酒壶里总是满满的。闲下了,别人聚在一起抽烟,他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坐在旁边,拧开酒壶盖子,有滋有味地抿在嘴里,慢慢咽下去,再咬一口红彤彤的干辣椒。酒是他的还魂汤。几口酒下肚,灰扑扑的脸立即泛起酒红色。酒,真是好东西,他说,饭啊,只能吃进胃里,但酒不一样,酒啊,直接喝到心里。他酒量大,胆子也大,在棺材上面走来走去,没事人一样,脚下阴森森,能望得到白骨。老坟,有煞气的,这是顶忌讳的事。他不忌讳。哪里有什么鬼哟!鬼,都在你们心里。更何况,我做的是积德事。没有人敢和他争辩。信的,始终信着;不信的,依旧不信。”
我越听越诧异,问春生:“你认错人了吧?”
“门对门住着,好几年。他就算化成灰,我也不会认错啊!”春生说。
扫帚沟老街,离牌楼不足一百里,我迫不及待地动身,去见二少爷。我是想知道,当年他何以不辞而别,这些年他又经历了什么,以至于让他忘记了过去,或者说,不愿意回到从前。
“找相公啊?往里走,直接走到头,门上没有锁的矮房子。”一位在长河边拉二胡的老人,指引我说。
门虚掩着,果然没有锁。斑驳的土墙,粼粼地荡漾着长河的波光。我推开门,室内漆黑一团,好半天之后,一个老人从阴影里慢慢浮出来。我兀自一惊,几十年光阴,呼啸而过。
春生说得没错,他是二少爷,但他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二少爷”了。他老了很多,和老石匠一样提前脱了发,肤色幽暗,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深深的皱纹,石刻一般,眼窝深陷。我叫了一声“二少爷”,他拄着拐杖,想站起来,又坐了下去,好半天之后,才迟疑地说:“你找谁啊?我是相公,张了然。”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牌楼的,”我走到他面前,一字一句地说,“我大叫江友正,我是他小儿子。过去,你经常架着我翻墙,偷小顺家的桃子。”
他一脸茫然地望了望我,摇了摇头,在地上划拉着拐杖。
“这根拐杖,是老太爷的遗物,你也不记得了吗?”
他的脸,受惊似的抽搐了起来,好半天之后,他才自言自语似的说:“我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的,必定都是可有可无的,不必去想。”
乱云飞渡。我盯着他饱经风霜的脸,密密麻麻深深的皱纹——每一道皱纹里,都填埋着一段沧桑的岁月。究竟是什么,刻出了这一张令人悲伤的脸?
“你来找他,有什么事吗?”他并不想立即把我拒之门外,这让我有些意外。以至于我竟无法确定,他究竟是刻意逃避,还是选择性失忆。
“我来找他,是想了我大一个心愿。他不辞而别,前前后后,我大总共找了他五年。”
“生,赤条条地来;死,赤条条地走。有什么可告别的呢?”
“人,不单是为自己活,还有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总是有挂碍的吧!”
“有挂碍,便不快乐。”他提起拐杖,指了指门外,说,“知道我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吗?因为这条河。一年四季,奔流不息,日日夜夜都在唱歌。人一生,不也是一条河嘛,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挂碍呢?无非就是一碗饭、一张床,最后变成一堆土,而已!谁都一样。不管你多有钱,也不管你当多大的官。”
“照你这样说,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还是没活明白。什么叫有意义?”他再次提起拐杖,指了指门外,说,“这条河,一直流,一直流,有意义吗?你要说有意义,它就有意义;你要说没意义,它就没意义。”
“明白了,活着本身就是意义,对吧?”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对,也不对。归根结底,一切皆身外之物。”
……
那一次,我们聊得很投机,他陪我在长河岸边走了小半天。我几次喊他“二少爷”,他立即用拐杖敲打地面,和颜悦色地说:“我叫张了然,不是什么二少爷。”长河奔涌,逝水无声。我们在落日的余晖中,微笑着道别。
今天想来,他究竟是不是“二少爷”,已经不重要了。我见到的,是一个冲破欲望的枷锁,在烈焰中度过苦厄的老人;是一个看破无常的人世,和另一个自己秉烛夜谈的相公;是一个在长河边坐而论道,和天地对话的哲人。
像一滴水,二少爷在茫茫人海里蒸发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二少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