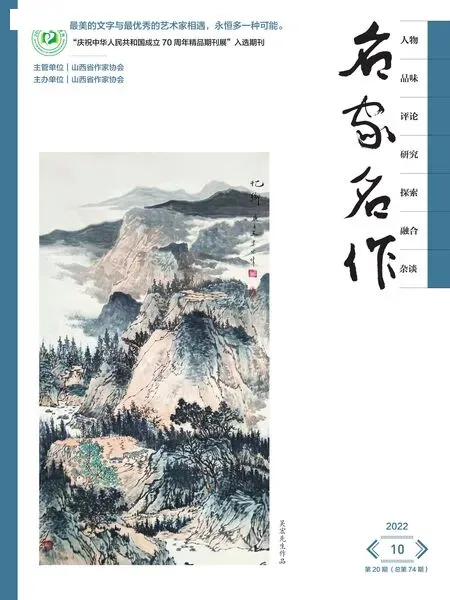浅析珂勒惠支版画作品中的雕塑感
赵晓丹
珂勒惠支作为德国知名画家,创作出来的绘画艺术作品对美术史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革命美术来说,在其发展过程中更是占据核心地位。珂勒惠支的绘画作品构图大胆,以线条、光影和造型赋予作品情感,让看似简单的黑白处理画面充斥着控诉和悲愤。1913年,珂勒惠支的绘画作品深受鲁迅青睐,进而引入内地,自此,我国美术界开始加强对珂勒惠支作品的研究。珂勒惠支早期的绘画作品大多以版画为核心,末期多以雕塑和木刻为核心,同时伴有不同材料的手稿。自1910年珂勒惠支首次尝试雕塑作品创作之后,更加关注作品创作的节约、简单和肃穆,以雕塑性语言表达战争、母爱和面对人生及死亡的态度。因此,珂勒惠支的作品从本质上来说也可称之为贯穿其一生的自画像,也是底层劳苦人民人生发展的自述史。
一、珂勒惠支艺术风格形成的背景及其特点
珂勒惠支,1867年生于德国,学习于柏林,1889年前往慕尼黑进行绘画深造,同时在慕尼黑学习了铜版技法,并将铜版技法运用于版画,展现出社会底层工人阶级的生活。20世纪初期,正是传统学院派艺术向现代艺术转型的重要发展阶段,珂勒惠支在院校学习美术的过程中,就已经涌现出很多著名的艺术家,例如马克思·利伯曼等,开始运用现代绘画语言来表述作品内涵。但是在珂勒惠支成长的德国,其绘画表达方式仍以传统的风俗画和历史画为主。在这种传统和现代转折、交接的社会背景下,珂勒惠支也在其中不断探寻自我,并寻找到真正属于她自己的艺术风格。
珂勒惠支在作品创作过程中,更加喜欢用简单且独具特色的风格线条对轮廓进行勾勒,整体的形象表达具有概括性,有着非常强大的表现力。在她的作品中,更加关注人体体态的表现,而忽视除人体之外的其他物品。因此在珂勒惠支所刻画的人物中,眼眸深邃,身体结构突出,人体形象以简单的线条进行概括,整体有力,带有压抑之感和沉郁之绪。在作品风格表现上,大多较为粗犷,以黑白色为主调。除此之外,她的社会批判类作品和人文关怀类作品值得深究,鲁迅先生将她的作品称之为“有力之美”。在她的作品里,有着非常浓厚的同情心,也曾有人这样评价她,说她的作品和爱德华·蒙克的作品可以称得上平分秋色。
珂勒惠支的作品十分关注光感的运用,习惯聚焦光线,刻画在光线聚拢之下的人物形态和人物表情,为人们带来了十分强烈的视觉冲击,可让观看者对画面主题进行深度思考。例如在她的艺术作品《死亡》中,画面刻画了桌上的残余烛光,在残存烛光的照射下,小孩子睁大眼睛,表情无辜,凝聚双眼看着死神紧抓自己母亲胳膊的那只手,这个画面占据了作品的核心。而这样的画面处理模式,真正地抓住了观看者的眼球,让其视线集中在画面重点中。除了残存灯光的光线聚焦之外,画面的其他地方都被处理为灰暗色调,整体画面悲凉,死亡气息浓厚,就连父亲的背影也看起来非常深重。
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十分关注人物的雕塑感,通过巧妙的刀法和光线的结合,刀法表现较为朴实、粗犷,在画面中形成十分强烈的黑白灰颜色对比。如在她的作品《哀悼李克内西》中,她将画面处理为黑色,将哀悼者的面部处理为灰色,和白色的尸衾对比鲜明,光线从上向下照射,将哀悼者此时的悲痛之感刻画得入木三分,撼动人心。
二、珂勒惠支版画语言的雕塑性缘起
珂勒惠支在完成《农民战争》这组画作之后,在对版画进行创作时,开始运用更加丰富多样的方法,同时创造出了一批样式更为独特且更具风格特点的作品。在她后期的作品中,其风格面貌都是源自她在雕塑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获得的感悟。在1904年,珂勒惠支与罗丹、泰奥菲勒·亚历山大·施泰因伦见面,罗丹鼓励她在雕塑作品上加强创作。1907年,她荣获别墅协会奖,同时获得去佛罗伦萨游学的机会。在意大利的这段时间,她看到了很多与众不同的雕塑作品。1910年时,她开始尝试雕塑作品的创作。珂勒惠支的一生创作了很多雕塑作品,但是真正流传于世的却很少。在目前遗存的珂勒惠支雕塑作品中,如《母亲与两个孩子》《母亲与她肩膀上的孩子》等,和她的画纸绘画作品在取材上高度相似,在人物外形上也十分接近。大概也是因为珂勒惠支认为通过雕塑可以更加清晰直观地展现出人物造型,具备更强的感染力和画面表现力。于是她开始将在雕塑中积累的经验和表达方法运用于纸面作品的创作中,将画面中的边界感和环境界限直接剔除,更加清晰直观地展现出主题,用概括有力的方式表现人物形体,让纸上的人物更为立体,就如雕塑作品一样具备厚重感和坚实感。
三、珂勒惠支版画作品中雕塑感的体现
(一)构图
在珂勒惠支的很多版画作品中,构图多为居中偏下,给人带来十分稳定的观感,画面看起来饱满且有力量。1923年珂勒惠支创作的《双亲》这幅作品,就是其中比较具备代表性的具有雕塑感的版画作品。在画面的构图设计上为居中偏下的正三角形。画面中两个人物的中心线位置和底部的腿部位置呈90度垂直,并将重心放置在双腿上,整体的腿部结构形状设置就好比现实中雕塑作品的底座,带给人一种稳定之感。1923年,珂勒惠支又创作了木刻作品《母亲们》,在这部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其中的雕塑性语言,画面构图以圆式为主,将母亲的肩部以线性状进行展示,给人带来直观的收拢之感,看起来坚不可摧,好比雕塑作品一样,给人带来十分厚重的坚实感。后期珂勒惠支雕塑作品《母亲塔》的创作和《母亲们》这部作品高度相似,在构图上基本无太大差异,都可表现出作品的沉重感和坚实感。
(二)造型
珂勒惠支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人物造型基本没有使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而是融入雕塑造型特征,通过对外形进行概括,对块面进行表现,以展现出画面造型的整体感。虽然其描绘重点放置在了对象的大轮廓上,通过简洁的表达形式凸显作品的主题,但是在人物的局部细节处理上,却具备突出的象征意味。手可代表人物除了脸部的第二表情,珂勒惠支非常善于通过对手势动态的捕捉,展现人物此时的精神和情绪状态。举例来说,在《不应碾磨播种的种子》这幅作品中,通过线条概括了人物的简单形态,并初步交代了画面中的转折关系和结构关系,将母亲的身体形态和手的比例进行了扩大,视觉冲击力十分明显。通过整体的夸张视觉造型,展现出母亲的强大之感,用母亲的双手为孩子带来安全。另外,在珂勒惠支的自画像中,也不会对表情进行细致刻画,而是通过较为粗糙的艺术表现手法,以手掌半掩面的形式表现,通过对手部的局部深入刻画,展现人物的沧桑感和憔悴感,给人带来十分直接的观感。
(三)光影
珂勒惠支在光影的表现过程中,融合了戏剧舞台的灯光表达效果,画面有着非常强烈的明暗对比。试图通过光影聚焦展现画面焦点,并通过光影来凸显人物此时的心理和情绪状态,促使画面的神秘感不断增强。如《母亲与死去的孩子》这幅作品,光影表达就非常值得考究,光线好比聚光灯一般,从孩子的头顶照到母亲的身体,孩子头部光线较强,到母亲身体时变得越来越弱,有着非常丰富的黑白画面层次。整体构图以雕塑性为主,孩子头顶的光芒就好比灵魂已被抽离,和此时画面中母亲左腿的受光上下呼应。在画面上,并未通过画面语言对脸部进行详细刻画,而是让母亲的脸部埋进了深深的黑暗里,让整个画面的沉重感陡然增强,更可展现出永久的伤感。
(四)肌理语言
不同的版画品种带来的激励效果也有所不同,画面的表达情绪及表达观感也会由于材料肌理的不一致而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如在珂勒惠支的《死神怀抱少女》这幅作品中,线条表达粗犷且随意,但是却在画面中运用了颗粒般的细腻质感,与雕塑作品中的石雕高度相似。另外,画面中没有设置太多的细节,只是将重点放在了形体转折上,并通过黑白关系的明暗对比,让画面中的光线集中在画面女人的头部和手部,通过肌理感的运用,表达出像雕塑一样的立体感和空间感。但同时又具备木刻版画本身具备的质朴感和沧桑感,实现了与雕塑作品简约大气的结合,让整个画面具备更强的一致性。
(五)线条
在对作品线条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珂勒惠支尽量将版画的刀刻线条和传统作品中的素描明暗对比线条区分清晰,实现木刻版画纹理和雕塑刀刻的有机融合,表达出木刻版画的沧桑感和朴拙感,实现与雕塑语言简约大气的高度一致,将作品中的主体和情感作为作品创作的核心目标。如,在珂勒惠支广为流传的木刻版画《战争》这幅作品中,整体的线条表达浑厚,具备较强的沧桑感,将战争之后亲人的悲痛情绪与悲伤之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在组画第三幅《父母》这部作品中,主要表现的是相拥哭泣的父母,在线条的表达上,其作为展现人物造型最核心、最基础的手段,没有运用看起来矫揉造作的柔和线条,而是通过雕塑性语言和大刀阔斧的刀刻线条对人物的轮廓造型进行勾勒,线条表达粗犷,但却十分有力量。同时通过刀刻线条的交织融合以及疏密处理,使画面不但不呆板,反而将战争之后双亲心中的悲痛之绪、绝望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情感看起来更加纯粹、直接和深刻。
四、珂勒惠支艺术作品对中国的影响
在现代美术史的发展过程中,珂勒惠支是较早通过个人作品以及独具特色的风格展现无产阶级生活的版画家之一,其作品引入我国后,对我国的革命美术运动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在珂勒惠支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德国阶级生活以及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与当时的中国极为相似,展现了社会苦难以及底层人民在社会压迫之下的强烈反抗意识,为我国当时的艺术青年带来了深刻的触动,对我国当时的革命艺术家也带来了心灵与精神上的高度鼓舞,使其革命信心变得越来越坚定。珂勒惠支作品在进入我国之后,成为我国新兴木刻的典范,并运用在了版画教科书中。珂勒惠支的自画像作品,也是学生对木刻画进行学习的重要参照物。珂勒惠支以其独特的个人视角以及作品表现风格,对我国艺术家的审美带来了颠覆性的转变,为我国现代美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期间,我国很多钟爱木刻版画的进步青年,无论是作品的表现技法还是作品的创作风格及创作思想,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珂勒惠支作品风格的影响。比较具备代表性的如上海新兴木刻文化,彼时的上海,很多进步青年在艺术上颇有造诣,但是在政治上却随时有可能遭到社会迫害。在创作作品时,也受到了当时资产阶级艺术的严重冲击,对生活艺术及作品创作上的压迫不断加重,虽然身处的社会环境十分艰难,但是珂勒惠支作品中所传递出来的艺术精神以及独具特色的作品表现风格,仍指引着当时的艺术青年不断坚定个人的理想信念,持续在作品创作上进行奋斗,并从手中的刻刀,作为表达对社会不满的武器,从未间断过作品的输出,这也开辟了当时新兴木刻运动的风潮,致使新兴木刻版画逐步演变为我国木刻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西方特色和西方风格的变革,走上了真正的发展之路。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木刻,却和历史不相干”,这代表着我国木刻版画在经历辉煌、衰败之后,又重新走上了繁荣发展之路,有了新的起点。
五、结语
综上所述,珂勒惠支作为德国当代女性艺术家的代表之一,通过其对社会的感知以及强大的共情能力,以女战士的身份对当时德国的社会形态进行了深刻揭露,真正展现出了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在她的作品中,表达了战争、母爱及生死,画面线条总体铿锵有力,可直击人的心灵深处。尤其是在其后期接触雕刻作品之后,画面构图有了雕塑作品中的沉稳感和力量感,并通过雕塑性语言塑造人物造型,塑造出更具特色的三维空间,进而表达出人物的心理情感,又可对人物进行大刀阔斧的概括,激起观者内心的深度共鸣。不管是在彼时的战争年代,还是身处的21世纪的和平年代,其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向命运抗争的思想意识、与死神搏斗的不屈精神,都对当代美术作品带来了坚定不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