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快递
胡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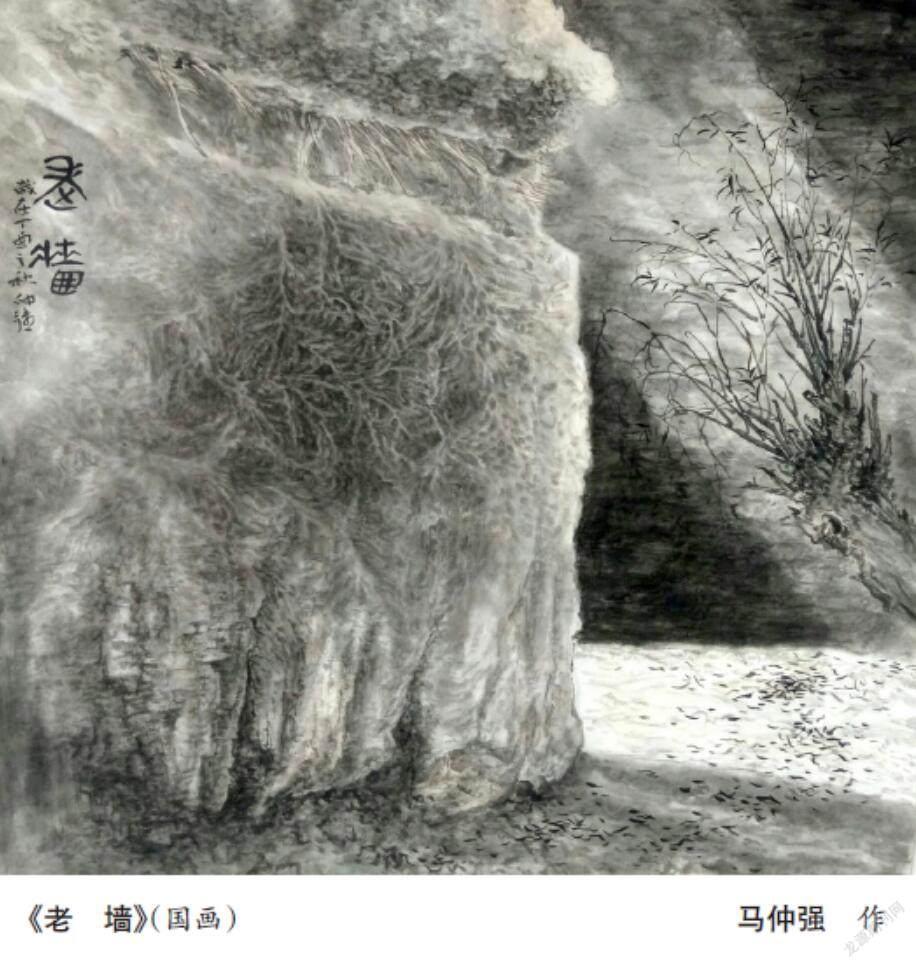
快递员飞哥发动他那辆快递三轮车,天嗖的一声就全亮开了。
飞哥送完当天所有的快递包裹,将那辆快递三轮车停下,天又嗖的一声全黑了。
飞哥就是把每天的日子干得两头黑的那种快递小哥。他的车轮轧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飞哥每天早晨从床上爬起来,睁开眼,刷牙,洗脸,健身,快快地吃过早餐去公司打卡上班时,天还是黑的。傍晚送完所有的快递,驾着空了的三轮车赶回公司做当天的业务交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飞哥的快递业务是那么地忙啊,总是见他驾着那辆快递三轮车飞驰而来,又驾着那辆快递三轮车嗖的一声便不见了他的踪影。
在这之前,飞哥是干报刊投递的,也是每天早早地起床,骑上用脚蹬的二八自行车,把两只鼓鼓的邮袋驮到自行车的后座上面,蹬起自行车沿着马路的每一个报亭、彩票投注点投递报纸杂志。偶尔也会从报刊市场的熟人那里批发过来一些畅销书刊,自己晚上到地铁口、天桥边摆上一个双人床单大小的地摊,把这些刊物摆出来,按定价的八五折出卖。卖得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一百来块钱。近些年纸质期刊发行量走向低谷,报刊投递这一行越来越不好干,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少,濒临破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网购进入了千家万户,快递业务一下子繁忙了起来。飞哥就通过在大街上送报刊时认识的同行老乡的介绍,在一家中型规模的快递公司干起了快递。飞哥的主要业务是把公司分配到他负责的那一片小区的快递(包括信件和包裹)按照到件的时间顺序摆放好,然后驾上自己的快递三轮车顺着每天设定好的路线,一件一件地给收件人送过去。待收件人取走快递之后,他又将这些签收过的快递的详细信息反馈给公司,公司收到反馈上去的信息,给了肯定的回复,飞哥当天的快递业务才算完成。
飞哥租住在郊区的平房里,这个村里的平房小院大多数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建起来的红砖房。一家院子连着旁边的一家院子。整个村子十几家,二十来家,都连在一起,连成一片,这让飞哥刚来的时候想起过《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曹操的士兵多是北方人,不惯于水战,于是就用铁锁将船只一只接一只地连在一起。进入新世纪之后,涌向这座城市的外来工越来越多,住房一时紧张起来,这座城市一下子进入了寸土寸金的时代,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房租猛涨。市中心的房价太高,那些拖家带口,操着外地夹生普通话的外来工就开始涌向郊区租房,郊区的平房村刹那间一房难求,这时就有人把那八九十年代盖的红砖平房掀了顶子,就着下面的一层老房基在上面再加盖一层,这样原来的平房就一下子变成了二层的楼房。有的人家觉得盖起了二层楼房还是不够高,不够宽,为了能收更多的房租,他们还会在新盖起的二楼顶上再盖一层高度相对要低些的三层,三层盖起来,看上去摇摇欲坠,但还是可以住人,房少人多,那些可怜的外地人,为了要一个栖身之所,即便是更差一些的住处,很快就会有人租住。那些九十年代的猪圈、鸡窝,经过轻微的改造都租出去了,外地人同样在这里住得好好的。飞哥就住在这个城中村改造后的三楼上,三楼上一共住了八户人家。外墙是单砖砌的,四面墙都是单砖,它的厚度不及一楼二楼墙体的一半。八户人家各户之间的间隔墙都是用木板隔起來的,木板上敷一层薄薄的石灰膏,初眼看上去和结实的砖沙墙体并没有什么不同,用手轻轻一敲,就发出咚咚的响声,隔音效果很差。飞哥之所以租住这样的房子是为了节省房租,他要把自己干快递挣来的工资尽可能多地寄回老家去。家里有六十多岁的父母,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弟弟。父亲三年前在果园里伐树,一棵大苹果树猛地栽倒下来,父亲躲闪不及,左腿被砸成了粉碎性骨折,现在走路只能靠单拐,干不了重活。飞哥和母亲一起支起了一个炉子,每逢赶集时,由母亲推着炉子,父亲拄着单拐跟着,到集上去摆摊卖麻辣烫。弟弟上初中三年级,学习成绩不错,每年都可以评上“三好学生”。弟弟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个头还只有飞哥的胸口高,瘦削,脑袋显得尖尖的。那一天,父亲去山上干活,把家里的一只红壳暖壶遗留在南山坡地边的草丛中忘记带回来,到晚上吃饭时才记了起来。父亲一拍自己的脑袋自责自己不长记性。弟弟放下手中的碗,对家人说他要去把暖壶拿回来。从南山上的坡地回来要经过猎人峰,猎人峰下有一道山谷,大晴天白天都很少有人经过,遇上阴天更是昏暗,烟雾缭绕。那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没有月亮,天空中仅仅只闪烁着几颗星星。小屁孩说完就冲进了黑暗,一路凭着记忆在黑夜里奔跑,一个人穿过猎人峰谷,爬上南坡,从草丛中取回了暖壶,又一个人原路跑了回来。就是那一次,就是那一件事,飞哥觉得弟弟比自己强,他决定退学,去外面打工,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他要挣钱供弟弟读到大学。
工作之余,飞哥有两个爱好,一是看书,另一个是下象棋。飞哥日常吃穿都很节俭。不抽烟,不喝酒。飞哥年年被评为优秀员工。年底公司组织聚会,飞哥被安排在优秀员工席上,这个时候他也会喝酒,敬领导,敬同事。别人敬他的酒,他都会喝,但绝对不喝醉。飞哥把自己挣来的工资的一部分拿出来买书。他租住的地方虽然只有十几平方米,但有一个占了大半面墙的书架,这书架是他从淘宝上淘来的,旧,但结实耐用,飞哥把这书架视作可以信赖的朋友。书架上摆满了书,桌上,床的一边,抽屉里都是书。书太多了,就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很多书没有时间读。那就先买下来,存放在那里,有时间了再读。人家休息日是去同女朋友约会,飞哥的休息日是在出租屋里独自看书。
飞哥曾经谈过两个女朋友,先后都同居过一段时间,觉得彼此不合适,就好聚好散了,互不相欠。在一起是彼此需要了,来一个暂时的组合,无关乎爱情。城市太大,远离家乡,青年男女需要抱团取暖。城市太大,人又太多,各自的选择爱好、三观都不一样,在这座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仿佛是从这大千世界采集下来的独立的样本,搁在一起时,又都可以合群。但真正在一起,一涉及情感、婚姻这些问题时,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便充分地暴露出来了。飞哥说,婚姻这个东西他也不反对,什么事情不都应该辩证地看它不是,既然在一起不幸福,又何必谈婚论嫁。再说他飞哥还有自己的梦想没有实现。飞哥的梦想是什么呢,这个他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他只是在一本书的扉页空白处写到过。他说他的梦想是供弟弟读完大学,让父母过上安稳的日子,在这座城市里有自己的一家快递公司。看看,飞哥还有不小的梦想,他想自己做老板,经营自己的快递公司。
飞哥住的蛋壳楼的一楼旁边原来是一个鸡窝,经过改造后变成了一间四平方米用白石棉瓦盖顶的小房间,租给了一个河南来的收废品的中年汉子。绿漆木门上经常挂一把黑色的永固大锁,锁是开着的,“2”字形挂在门鼻上。门外空水泥地上搁着一台生着红锈的旧磅,磅上摞放着四只大小不一的砝码。这磅是用来称废品的。磅的右侧立着一张一尺来高的方桌,桌面上一天到晚摆着一盘象棋残局。那个河南来的乡下汉子下得一手好象棋,自称少有对手。收废品空闲的时间多,闲下来,他要么与人对局,招来小区里的闲人观看,要么就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布局,自己跟自己下棋。下到高兴处,他猛地停下来,坏笑着,把面前的象棋局造成一个残局,像一个猎人一样精心布下一个陷阱,只待猎物奔跑过来,失足掉进陷阱,他才会开心地笑出声。河南汉子布下的棋局一般人难以破解,不少高手过来坐到棋局旁边搔首挠耳,举棋不定,磨蹭半日,难下一子。也有人说有人破过他的棋局。来者是个棋艺很高的老者,老者在汉子摆下的棋局旁转了两转,平静地坐下来,只走了三步,汉子就输了。老者的举动,令汉子目瞪口呆。从此老者就成了汉子的棋友。小区来往的人经常看到汉子棋盘前坐着一个衣衫破旧的老者,两个人默不作声面对面坐着,之间搁着一盘象棋的残局,汉子不下一子,老人也不下一子,他们常常就这样静坐着彼此注视良久,把周围的人都忘记了,把自己所在的这一座城市也忘记了。他们在棋盘中回到了他们人生中已经逝去的那些岁月,回到了他们遥远的如今早已回不去的老家,那个让他们记忆十分稠密的地方。人们看到老者同汉子共用一个茶壶喝茶。茶壶不大,里面有汉子泡的浓茶,是从乡下带来的粗劣茶叶,泡了一壶,搁在棋盘旁边,两个人渴了,一先一后地抓起茶壶,将茶壶嘴对着嘴,饮起茶来。他们喝茶从来不用茶杯,直接对着茶壶嘴喝。
老者是小区外面马路边靠捡破烂为生的老头儿。他至少有七十岁了,穿一身破旧的衣服,脸很黑。那一双粗糙的大手,手上的皱纹又深又黑,皱纹的深处布满污垢。老头儿姓什么,没有人知道,连河南汉子也没有问过他,听他说话是安徽淮北口音。他每天往返于小区和附近两条半马路捡矿泉水瓶和旧纸壳盒子。收入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挣到三十元钱。他没有钱租房子,就在小区围墙的拐角处,用破石棉瓦,旧得破了胶皮的电线借着围墙的两边搭起了一个窝棚,窝棚里只有两床破旧的脏兮兮的棉被,棉被旁边放着一个盖子拧不紧的一尺来高的塑料瓶,瓶里装的是从小区旁边的公共图书馆里接来的凉开水。
那天傍晚,楼下传来男女大声说话声。女孩说:“完了完了,这么好的风筝今天算是报废了。”男孩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不要往这边放。”女孩说:“我哪知道它飞得这么快,一下子就蹿到树上。”男孩说:“这一下可好了。”女孩说:“你会不会爬树?”男孩支支吾吾,说:“爬树嘛,爬树其实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的……”
飞哥从楼上的窗户向下看去。见楼下的枫树底下站着两个二十出头的男女,两个人同时仰着头看向满树绿叶的枫树梢,两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忧愁。叶丛中栖着一只足有半米长的大蜻蜓,牢牢地挂在了一根树枝上。在两个人束手无策的时候,只见不远处走来一个老头儿,站在枫树下,先目测了树枝的高度,又打量了一下手中竹竿的长度,然后蛮有把握地举起手中的竹竿,竹竿对着树叶丛这样鼓捣一阵子,风筝竟然自己从叶丛中掉了下来。两个青年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又一天下午,小区公共厕所门前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小伙子染着红头发,脑袋看上去像一只刺猬。他上身穿一件西装,还打着领带。只见他在厕所门外急得团团转,打量着每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对向他走过去的人保持着警惕。他很希望有人走过去帮他,又害怕有人走向厕所,尤其是男人,他对每一个向厕所走过去的男人都充满提防。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陆续走进厕所,有人从厕所里出来。小伙子在厕所门前来回走动,他在等一个人。从小区的大门处走过来一个老头儿,他的肩膀上扛着几块纸壳板,这是他在大厦前的垃圾桶边蹲守了大半个上午的收获,今天的收益不错。老头儿走在路上面露喜色。小伙子见老头儿过来了,他一下子高兴得快要跳起来。小伙子跑过去,一把抓住老头儿的胳膊,火烧眉毛似的说:“大爷,有一件事您一定要帮我。我在这里等您很长时间了。”老头儿把纸板从肩膀上卸下来,人一下子松快多了。他转身,拿右手在身后的空气中拍了一把,把三只跟了他一路的蒼蝇给赶走。老头儿冲小伙子笑了笑,他若是有一个这么帅气的孙子就好了。他今天的心情不错。他问小伙子到底有什么事。小伙子说,他刚才上厕所时一不小心把苹果手机掉进厕所里了。手机一脱手,在瓷砖地面上弹跳着打了几个翻身,掉到马桶眼深处去了。小伙子急得头上直冒汗。这台手机是他上个星期才买的,花了七千多元。
小伙子说:“爷爷,我不会让您白白帮我的。您把我的手机捞上来,我给您一百元钱。”他说着,习惯性地伸出自己右手的小拇指,做出一个拉钩状。老头儿觉察出小伙子身上有几分孩子气,觉得有一些好笑。不过为防止小伙反悔,他还是要小伙子先把钱掏出来,交到他的手中。小伙子果真掏出一百元交到老头儿的手里,老头儿二话不说向厕所的坑边俯下身去。
五分钟后,小伙子又一次看到了他那台心爱的苹果手机。手机失而复得让小伙子喜出望外。他一个劲地给老头儿点头表示感谢,似乎忘记了自己刚才已经给了老头儿一百元钱。老头儿眯着眼睛把正要离开的小伙子叫回来,说:“你的手机掉得不深,我一伸手就把它拿到了。这钱我不要,干这么简单的活儿不值一百元,我不能昧着良心挣你的钱。”小伙子接过老头儿退还过来的钱,身体晃动了一下,他突然有些不认识面前这个老头儿了。他拿了这一百元,跑到不远处的小卖店买了一块香皂,交到老头儿的手上,说:“爷爷,这个您总得收下吧。”老头儿接过香皂。小伙子又把一张五十元的钞票装进老头儿的口袋里,说:“爷爷,这五十元您一定要收下,要不然我的内心不安。”说完,小伙子握了一下老头儿的手,没等老头儿再说什么便匆匆地走了。
河南汉子跟老头儿已经成了一对老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杀将,有时到深夜还为一盘残局僵持不下。有一次,两个人竟然争吵了起来,老头儿面红耳赤,一气之下把河南汉子茶壶里泡好的茶水全都倒在了地上,水泥地上顿时黄汪汪的一片水,顺着地面向低处流去。这时飞哥送完快递正骑着三轮车从外面回来。老头儿见飞哥过来,停住了争吵,转过身来对骑在三轮车上的飞哥说:“你给评一评理,看有没有像这样下棋的?都说落子无悔,他倒好,悔一步棋还不算,还要再悔一步,哪有这种下法?”河南汉子也气呼呼的,脸都红了,像刚喝了很多酒,见老头儿搬另外的人来评理,气不打一处来。只见他一抬手,把面前的棋盘一下子打翻在地,棋子七零八落,四散而逃。从二人的争吵中可以听出,他们为了一局残局下了一下午,双方仍不分胜负。老头儿突发奇想,他换了一种走法。汉子一下来了精神,但是他一时还看不出老头儿的真实意图,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勉强招架。哪知越到后来,他越占下风,眼看节节败退,自己的马炮即将走入死胡同。河南汉子使了欲擒故纵。他的办法是走一步悔一步,想用这种手段来试探老头儿的真实意图。只向下走了几步老头儿就被激怒了,这才发作起来。飞哥见两个老棋友争得面红耳赤,说:“二位不要争了,听我说一句吧!如果有兴趣的话,我来陪二位各下一盘,算是化解二位的矛盾。下完这两盘棋你们握手言和怎么样?”这二人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飞哥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都觉得新鲜。河南汉子双手抱在胸前,他想看一看飞哥究竟有几斤几两。他不再跟老头儿计较,把矛头指向飞哥。汉子说:“我先跟你下。”说着弯下腰伸手把掉在地上的棋子一一捡起来,重新摆好一盘棋。飞哥先走一子,汉子跟走一子。飞哥又走一子,汉子又走一子。二人杀了十多个回合,只见飞哥卖一个破绽,没想到汉子果然中计,飞哥说一声“将军”。这一子下下去,汉子完全没有想到就这样被将死在地了。落子无悔,飞哥赢了。轮到老头儿下时,老头儿不住地咳嗽,咳到急了,喘不过气来,把脸憋得通红。飞哥觉得老头儿一定患有重病,要不然怎么会把自己的脸咳得像一块猪肝。但不得不说老头儿的棋下得稳健。毕竟是历经沧桑的人,每一步都走得实诚,考虑得周到。从这一点上讲,河南汉子远不及老头儿。几着棋下来,飞哥在内心里已经有了计较,他可以断定河南汉子是下不过老头儿的。老头儿新的一阵咳嗽又升起来,他的后背处像装了一个风箱,一阵咳嗽过去,眉眼和腮帮布满了痛苦。飞哥盯住对方的将军营帐,做出一味的冲杀状,在己方的营盘放松守备,只饶了一着。老头儿果然察觉到了飞哥在防范上的“疏忽”,只一个回合,将死了飞哥。两个人对视着笑了一回。飞哥起身给老头儿递一根纸烟,又给在旁边看棋的汉子也递过去一根烟。飞哥说:“姜还是老的辣,我甘拜下风,输得心服口服。”老头儿看飞哥的眼神变得意味深长。
飞哥重新骑上三轮车离开,车拐到胡同口的大槐树下,还听到老头儿发出的一连串咳嗽声……
飞哥送完附近的快递正从楼上下来,刚走出电梯,在单元门口,就听到一个老人的声音,“送快递的。”飞哥回头,见是那位捡破烂的老头儿。老头儿拎着一只蛇皮袋,手上又拿着一根木棍。木棍头上用铁丝绑着两根粗钢丝弯成的钩子,形状如象牙。“您今天的收益不错吧?”飞哥问。老头儿说:“就这么个样儿,能捡多少算多少呗。”这已经是午后了,老头儿的那只布满油污的蛇皮袋子的一半还没有装到,看来他今天的收入会很少,飞哥的鼻子里顿时生出一些酸楚。老头儿说:“送快递的你上次和我下棋时为什么要让我一着?”飞哥没有想到老头儿会问起这个,这让他有些始料不及。飞哥说:“哪里哪里,我没有让您,是您的棋艺高超,我下不过您,我甘拜下风。”老头儿沉思良久,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一着棋,你本來可以先我一步将军的,可是你没有,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老头儿说着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从那以后,飞哥时不时地就在小区的马路上,在自己住的村子的村道上碰到老头儿。有时是老头儿先看见飞哥,有时是飞哥先看见老头儿,这时候飞哥就把三轮车停下来,和老头儿说一会儿话。飞哥从老头儿的话中得知,老头儿是安徽人,今年七十一岁,无儿无女,一个人来这座城市里讨生活已经快二十年了。家里原先有三间瓦房,几年前卖给了邻居。老家还有一个长他五岁的老姐姐,日子也过得非常艰难。这有很多年没有和她通音讯了。他一个人漂在这一座城市里,靠捡破烂生存。逢年过节,生活艰难时他也想到过回老家去,可是又没有路费,家实在是难回。老家的田地已经被征收了,房子没了。他住过大半辈子的山村几年前就空无一人了。山清水秀,绿树成荫,可是人们不再愿意在那里住。多么美的乡村,多么清新的空气,可是人们就是不爱那里,都往外跑,所有的人都出来了,都往城市里跑,村落衰败下去。老鼠、蛇聚满村庄,成了名副其实的鼠村、蛇村。好端端的村落再也看不见袅袅炊烟了,再也看不到牧童吹短笛了,再也没有鸡犬声相闻了。落日余晖下,留在那里的是衰草连天,残垣断壁的荒凉。飞哥深知此情。飞哥老家的村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儿时无边玩耍的那一片青山绿水,如今早已失去了人气。枯萎,衰败了。每一年春节回家,总能听到说某某人搬走了,又是某某人搬走了。搬走的人不再回来,空房子还留在了那里。后来又经常听说某某人死在了外面,因为舍不得老家的青山绿水,烧成骨灰也要带回老家安葬。人走了,灵魂仍然希望留在自己的出生地,出行千里,叶落归根。
冬天夜里,气温骤降到零下十摄氏度。飞哥把他自己的棉被拿出来一床给老头儿送去。老头儿住在小区围墙边拐角处的窝棚里,天刚刚黑他就躺在了两床破旧被窝里,把身体缩成一小团,在黑暗中蠕动。飞哥没有叫起老头儿,他摸着黑轻轻地把被子放在窝棚门口,然后自己悄悄地走了。
傍晚,飞哥骑着三轮车行走在村道上。老头儿迎面走过来,脸上还是那一副笑眯眯,有些讨好他人的表情。飞哥跟老头儿打招呼,老头儿顿时立住了脚,像是有话要说。老头儿告诉飞哥他想寄一个快递到安徽老家,不知道具体要收多少钱。飞哥见老头儿说得小心谨慎,就问道:“到底是什么宝贝,看你这么神秘。”老头儿把双手在飞哥面前一拍,带有一些孩子气地说:“你还别说,你猜对了,真的是一件宝贝!”老头儿向左右瞧了又瞧,见周围没有其他的人路过,向飞哥走近两步,这才压低声音,悄悄地说他今天在天外天别墅区里捡回来一个宝贝玩意儿,可能是个古董。只是瓶口处破了一个小缺口,要是拿胶泥把这个缺口补好,它就是一个漂亮的古董。在飞哥的追问下,老头儿才告诉他,今天上午他和往常一样去天外天别墅区捡破烂,在小区的垃圾堆里见到一只两尺多高,身上印着很好看的山水画的瓶子。这瓶子并不是用来装东西的,是白瓷的,里面干干净净,瓶身上了釉,釉下印的是天青色的山水画,一看就是好东西。他就把这个瓶子捡了回来。老头儿说,他想把这个瓶子寄回老家去,由他的老姐姐把它保存下来,问飞哥寄一个快递要多少钱。飞哥说,这要看到实物才可以定价格,对于易碎品,还要对它进行精细包装,具体多少钱,要等验完货物之后才可以确定。飞哥让老头儿明天上午把他的宝贝带到所在的快递公司去,先检测一下物品的质量、硬度、可携带性等方面的问题。
老头儿抱着他的宝贝走进屋时,飞哥正在柜台前整理快递运单,把手中的运单整理好了,他就要外出送上午的快递。他抬头看见老头儿抱着一个大家伙从外面走进来。那是一只敞口瓶子,很像是清代烧制的青花瓷器,上面印有一幅山水图,看样子应该有一些年头,瓶口处碰了一个豁口儿。老头儿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俨然把它当成了一件旷世奇珍。飞哥从老头儿手中接过瓶子,瓶子不重,比飞哥预计的要轻一些。跟同事们说了老头儿的情况,负责称重的工作人员就过来给瓶子称了重量,又交到后面仓库里去给瓷器件做木制包装,这些要花小半天时间才可以做好。飞哥让老头儿在办公室里坐下来,老头儿接过飞哥递过去的一纸杯开水,刚碰到嘴边,就迎来了一连串的咳嗽,一阵咳嗽下来,老头儿的脸咳成了猪肝色。
下午包装做好了,计算好快递费,飞哥告诉老头儿,寄到安徽老家,需三百元快递费。老头儿的身体左右晃了一下,随即答应下来。只见老头儿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零碎的纸票子。把纸票子在柜台上面一张一张撑开,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一分,分门别类地叠好。好一会儿工夫,总算整理出了三百元钞票来。快递运单上写好了他老家的详细地址,在一个镇上。收件人是他年迈的老姐姐闻兰香。
夜里九点多了,飞哥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飞哥以为是哪个客户打来查快件派送情况的。他接起电话。原来是老头儿。老头儿在电话里说,他的快递不打算寄了,要把寄的那个瓶子要回去。飞哥问他,为什么不寄?老头儿说担心搬运的过程中会把他的宝贝摔坏,想一想还是不寄。飞哥估计了一下时间,知道这一批快递还没有发走。他向公司说明原因,让这个快递先不要发货。第二天上午,老头儿来公司,取走了他的瓶子。
飞哥去郊区送快递时接到公司里打来的电话。他从同事的电话中得知老头儿又把他的那个宝贝瓶子抱来发快递了。公司里的调度告诉飞哥,老头儿一进门嚷着要见飞哥,说他要在飞哥手上发快递。工作人员说让别人负责他的快递行不行?老头儿坚决不同意。他坐在工作间的沙发上一言不发,非要见飞哥不可。飞哥从郊区送完快递回来已经是下午了,老头儿还没有走,一直抱着他的宝贝瓶子守在办公室里。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都看着老头儿,问老头儿到底是谁啊,是飞哥的什么人啊。
飞哥进门时,老头儿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坐的时间长了,他的腿部有一些不适。他是从椅子上滑下来的,半蹲着,蹲了一会儿,慢慢地向上站直身体。老头儿瞅住飞哥一会儿,脸上这才打开一片半害羞半讨好的笑容。老头儿站直身体,伸手往自己的胸脯上一拍,说:“这次想好了,寄回去!”飞哥说:“你就不怕在运输途中把它给碰坏了?”老头儿十分肯定地说:“不怕,碰不坏,反正它已经是一个有缺口的破瓶子。”飞哥就说,他们公司以前也做过古董运输,在做好包装之后,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在运输的途中碰坏的,这个可以放心。老头儿说:“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你。”
早晨雾很大,马路前方能见度不到三米。白茫茫的雾把这个早晨打扮得有几分鬼魅气。马路还是昨日的马路,因为霧大,出行的人少,路上的车也比往常稀。这样的鬼天气其实很容易出交通事故。飞哥的三轮车刚驶出胡同口,只见一个黑影向它扑过来。飞哥赶忙停下三轮车。黑影向他靠近,原来是老头儿。老头儿见车停下了,他抢上前来,“嘿,早上好!”老头儿看上去乐呵呵的。飞哥发现雾气已经打湿了他的头发、眉毛和花白的胡须。老头儿告诉飞哥,他天不亮就来这里等候。他是专门来会飞哥的。老头儿说他要把昨天寄的那个瓶子要回去。飞哥问为什么又不寄了,老头儿说他昨天夜里想了一宿没有睡着觉,反复考虑过,这瓶子他还是不发了,他要留着这个瓶子在他的身边,同他做伴。他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亲人,只有让这个瓶子同他做伴,要是把它寄回老家了,他又孤单了!飞哥叹了一口气。看了又看眼前这个年迈、疾病缠身的老头儿,心里突然生出了一股酸楚。他赶紧给公司的发货员打电话,告诉他那个瓷瓶子不发了,让先扣下来。说完挂上电话,扔下老头儿,一踩离合器,嗖的一声便跑远了。
飞哥想,这个老头儿好像精神有一点不正常,以后还是少跟他来往了。有几次飞哥骑三轮车从小区里经过,老头儿跟他打招呼,飞哥只微微地向老头儿点了点头,就开着三轮车过去了。再一次见面时,飞哥假装没有看见老头儿,就把三轮车开过去了。
从那以后,老头儿就淡出了飞哥的视野。在小区的马路上,在村道上也不见了老头儿的踪影。飞哥想,老头儿不会再来纠缠了。这一下子,飞哥也觉得清静了。
寒冬腊月,寒风不分昼夜地在这座城市上空呼啸,路边上枯萎了的枫树叶子被刮得到处飞,被寒风裹挟着,像无家可归的鸟儿在天空中游荡,最后飘落在马路边不被人察觉到的黑暗角落里。
那只瓷瓶子第三次被送到快递公司来的时候是一个傍晚,马路上到处是忙碌着下班回家的人。飞哥的三轮车今天在送快递的途中坏了两次,为此飞哥的心情很郁闷。一回到公司,就看到那只瓶子搁在了快递公司的柜台上面。调度员告诉飞哥,这个瓶子是一个小时前被一个中年男人送来的。中年男人嘱咐调度员一定要交到飞哥手里,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对飞哥说。调度员说着伸手从瓶子里掏出一张纸条,纸条上写有一个电话号码。
飞哥按照纸上写的电话号码拨过去。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小区里收破烂的河南汉子。汉子的语调低沉,他说让飞哥到他那里去一趟,他有重要的事当面对他说。
河南汉子收破烂的摊位有了很大的变化。那台旧磅不见了,象棋摊也收起来了。屋里原来大堆小码的废品也被清理一空,男人睡觉的单人铁架子床还在,一盏海螺状的节能灯管在拼命地发着光,是一只旧灯管,灯管靠灯头处显出一团浅浅的暗红。一走进屋,一股铁锈气夹着油漆味儿扑面而来,屋内显得又干又冷。河南汉子坐在一张小圆桌边,就着花生米,喝着劣质的白酒,酒气飘了满屋。河南汉子见飞哥进来,也没有站起来的意思,只是把目光往旁边的一张空木椅上一丢,示意飞哥坐下,椅子靠背上也带着酒气。飞哥想一想,没有坐,他站在椅子边上。男人把半杯酒倒进嘴里,说:“老闻头死了。”飞哥吃了一惊,赶忙问:“什么时候的事?”“三天前的上午。在附近小区里捡破烂,倒在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警察火化了老头儿的尸体,只留下一小盒骨灰了。”飞哥心里猛地一沉,没有想到这些天不见老头儿,他就出了这样的事。河南汉子又往嘴里倒了一杯酒说:“老头儿在一个星期前就开始犯头晕。他告诉我,走路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他还说,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让我把这一封信亲手交给你。”河南汉子从床头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把它交到飞哥的手上。飞哥的心里顿时沉甸甸的。
信封里装的是两万元钱,还有一张字迹歪歪斜斜的纸。是一封写给飞哥的信。信上说,如果他死了,请飞哥帮他把骨灰寄往安徽老家,就用这个瓷瓶子将骨灰安葬在老家村子后面的祖坟山上。老头儿还在信上说,这只瓷瓶并不是他捡来的,是他花了二百元从一个城里人的手中买来的,目的就是想用它来盛放自己的骨灰。将自己的骨灰装进这个自己最喜欢的瓶子里,这是他一生剩下的唯一愿望。看完这封信,飞哥的眼泪不知不觉就滑了下来。河南汉子没等飞哥问,就从他的床底下捧出一个骨灰盒。“这是老头儿的骨灰,是我从火葬场里捧回来的,现在交给你了!”说到这里,河南汉子把脸扭到一边,飞哥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
飞哥所在的快递公司没有托运骨灰这一项业务。老头儿的骨灰只能成为一个问题邮件,只能当成一个特殊快递处理了。老头儿的老家只有一个年迈的姐姐,行动也不方便。没有人来领取老头儿的骨灰,老头儿的灵魂将在何处安息?
飞哥整顿好行装,背起装了老头儿骨灰的瓷瓶子,驾起一辆从同行那里借来的摩托车,车头划破黎明的黑暗,驶向了南去的国道,奔向那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山区……
[栏目编辑:韩爱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