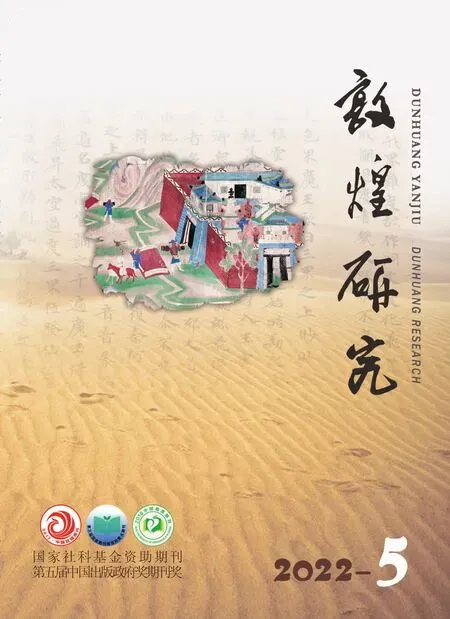丝路传法旅行图
——莫高窟第217、103 窟尊胜经变序文画面解读
沙武田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一 提出问题
莫高窟盛唐第217、103 窟主室南壁各画一铺大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后文简称“尊胜经变”)(图1)①见[日]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南壁经变の新解释》,《美术史》第157 册,2004 年10 月,第96—115 页,丁淑君中译本见敦煌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编《信息与参考》总第6 期(2005 年),第74—86 页;牛源中译本见《敦煌研究》2011 年第2 期,第21—32 页。 另见下野玲子:《唐代仏頂尊勝陀羅尼經変における図像の異同と展開》,《朝日敦煌研究院派遣制度紀念誌》,朝日新闻社,2008 年。详细而全面的研究参见下野玲子 《敦煌仏頂尊勝陀羅經變相圖の研究》,勉诚出版,2017 年,第25—63页。,具体是依据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绘制而成的。在经变画的西侧部青绿山水画面,表现的是该经“序”文的内容,即唐代定觉寺主僧志静所记佛陀波利前往五台山顶礼文殊菩萨过程中先后发生的诸多事迹, 包括佛陀波利在长安翻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相关史实[1],相同的佛教历史故事在《宋高僧传》卷第二“译经篇”之“唐五台山佛陀波利传” 中有完全一样的记载[2]。第217、103 二窟保存较为完好的尊胜经变中以青绿山水出现的一幅佛陀波利沿丝路来往的僧人传法/ 求法图,即是把佛经中“序”文内容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以独特的绘画语言,形象地表现了佛陀波利从“西国”罽宾来到五台山,再返回西国,再次返回中土,途经长安见到“大帝”(“天皇”),在长安两次先后在宫内和西明寺翻译佛经, 最后入五台山金刚窟不出的有趣历史故事(图2)。 为行文方便,结合画面故事内容,我们姑且命名这幅壁画为“佛陀波利丝路旅行图”。

图1 莫高窟第103 窟南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图2 莫高窟第217 窟主室南壁尊胜经变序文画面
这两铺尊胜经变,在经变画结构形式、画面布局、画面内容、人物组合关系等方面,变化不大,大同小异,可以认为使用的是同一幅粉本画稿。在没有发现长安、 洛阳等中原内地有同类经变画的记载之前, 此两铺经变画无疑可以认为是目前所知和所见最早的尊胜经变, 鸿篇巨制, 人物情节复杂,有重要的艺术史价值。
仔细观察两铺经变画, 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二窟两铺经变画在表现经文序言即佛陀波利故事画面时, 两铺经变中佛陀波利的丝路旅行均出现在青绿山水之间, 同时佛陀波利也均是以骑驴的主要形象反映他的长途丝路旅行经历。 但两铺经变画在人物组合关系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不同:第217 窟佛陀波利的组合是一人一驴,还有一身作为随侍的婆罗门男子(图3);而第103 窟的组合中除了之前在第217 窟已经出现的一人一驴之外,还增加一头载物的大白象,作为随侍的婆罗门男子则增加至三人。
第217 和103 窟是莫高窟盛唐洞窟, 属于同一期,《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认定第217 窟建于“盛唐早期景云年间”[3],即高宗710、711 年,另据敦煌研究院考古分期研究, 第217 窟为唐前期第三期洞窟的标型窟,属于唐中宗神龙(705—706)前后①见樊锦诗、 刘玉权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158、159 页。,是这一期洞窟中最早者。 第103 窟是同一期即唐前期第三期洞窟, 但时间应该略晚于第217窟②参见樊锦诗、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但在文中的第三期洞窟号中没有列出第103 窟,而在具体的分期论述中有该窟。,二窟时间相差不会太长,据山崎淑子女史的研究,二窟在粉本和样式上的关联性很强③见山崎淑子《敦煌莫高窟における初唐から盛唐への過渡期の一樣式——莫高窟二一七窟試論》,《成城文藝》第174 号,东京,2001 年3 月。,均为8 世纪初期作品。
既然二窟为同一时期的洞窟, 两铺经变画又使用了相同的粉本画稿, 为什么到了略晚的第103 窟中对表现佛陀波利丝路旅行的人物组合上做出较大的改动, 由之前第217 窟的佛陀波利一人一驴一婆罗门男子改为佛陀波利一人一驴一载物大象三婆罗门男子, 增加了一头大象和两位婆罗门男子。从洞窟时间关系而言,显然第103 窟整体上使用并延续了第217 窟的粉本和样式, 只是在画面局部作了改动和调整。
第103 窟壁画对佛陀波利丝路旅行情景的改动,增加一头载物的大白象和两位婆罗门男子,显然是画工对之前第217 窟粉本的改动, 这种改动应当是有所据, 应是画家基于现实生活所见而做出的一种调整, 准确而言应是对西来胡僧丝路旅行情景更加真实的绘画描述。所以,可以认为此二窟两铺尊胜经变中表现“序”文的画面,虽然在此二窟中具体记录的是从罽宾而来的佛陀波利在丝路上旅行的图像反映,事实上可以推而广之,实是两幅十分珍贵的反映历史时期西来的胡僧沿丝路旅行的真实而有趣的画面, 由于此类作品的时代可以早到8 世纪的盛唐初期, 其历史和学术价值更值得重视。 鉴于此,草成此文,就教于方家。
二 骑驴的佛陀波利
佛陀波利以骑驴形象出现在壁画中, 考虑到壁画使用粉本创作于7 世纪晚期至8 世纪初期的时间关系, 历史发展到这一时期沿丝路来华的胡僧数量已颇为可观, 正是在他们的努力和推动下大量的佛经得以翻译并传播, 汉唐时期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也得益于这些西来的胡僧,对此尚永琪先生有深入的专题探讨[4]。 同时期活跃在唐朝境内的胡僧也不少,尤其是唐长安和洛阳两京地区,是胡人云集之地,也是胡僧主要的活动空间。
就汉唐时期来华胡人的交通工具而言, 一般而言大家印象深刻的主要是马和骆驼, 这一点在大量的北朝隋唐墓葬出土胡人牵马俑、 牵骆驼俑中有丰富多彩的形象资料, 可以间接反映胡人在丝路上长途旅行的真实情景。但事实上,就丝路上的胡商而言, 根据我们对敦煌壁画和吐鲁番文书的梳理, 发现毛驴在丝路交通贸易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且往往是中小型商队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5]。 在敦煌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壁画中,我们看到的胡人商队的运输队伍中有骆驼有毛驴,商队首领往往骑马,著名的第45 窟观音经变胡商遇盗图中只有驴, 似乎表明类似的商队商人平时或步行或骑驴贩运。在吐鲁番过所文书中,驴是主要的商队运输工具, 统计其中的12 份过所文书显示,在唐代活跃于沿安西四镇、西州、河西、长安广大丝路上的胡汉商队, 其中可归入运输工具和方式类的马21 匹、驴106 头、牛7 头、骡3 头、驼5峰[6],其中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商队牲畜数量骆驼2 峰,驴26 头[7];另据《石染典过所》 记载曾在开元二十年、 二十一年(732、733)频繁出现在瓜州、沙州、伊州、西州从事商业活动的兴生胡石染典,先后两次分别从瓜州都督府和西州都督府户曹处申请的过所公验中,就记载了他分别带有驴10 头、骡11 头[7]40-42,48,这是石染典在这几个地方来往的运输规模。 可以看到毛驴在丝路运输中所占比重是最高的, 正是敦煌壁画显示, 因此可以认为毛驴在漫长的中古丝路贸易长途运输中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佛陀波利作为西来的传法/ 求法胡僧, 两铺尊胜经变中把其描绘为骑驴的丝路旅行者的形象,应该不是特指,或者说其非个案现象,而是这一时期创作经变画的画家们的丝路印象或日常知识,就是说在8 世纪初前后这一时间段,骑着驴沿丝路而来的印度、中亚、西域胡僧形象,是汉地人们比较熟悉的丝路风景。 考虑到第217 窟在艺术特征和艺术样式上浓厚的长安风格和绘画特色[8], 再结合作为全新经变画尊胜经变最早出现在敦煌的洞窟壁画, 基本上可以断定其艺术粉本来自于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内地, 敦煌本地创作此类经变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所以说骑着驴沿丝路而来的胡僧形象,对敦煌人而言并不陌生,同样也是长安等中原内地人的丝路印象。
既然在丝绸之路上有众多的胡人商队驱赶着驴子往来贩卖, 那么作为往往和丝路商队结伴来往的丝路传法、求法僧人,骑着毛驴出现在丝路上当属历史的真实。
尊胜经变中骑驴的佛陀波利形象描绘, 除了以上丝路旅人的特色之外, 还应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1.佛陀波利作为普通僧人的身份
僧人受戒律的规范,不聚财,平日身上也无盘缠,所以骑驴也能够代表僧人的身份,因为驴属于“劣乘”,骑驴属于廉价的出行方式,如果以乘车、骑马或骑骆驼出行,则显得奢华,不符合僧人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 也有可能受到社会习俗或相关制度的约束,唐文宗大和年间王涯奏文称“师僧道士,除纲维及两街大德,余并不得乘马”①(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中华书局,1960 年,第575 页。(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第647 页。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四八,中华书局,1983 年,第4581 页。,此记载虽然时间晚于第217、103 窟的时代, 但还是可以说明有唐一代对僧人骑马出行是有等级要求和限制的,西来的佛陀波利显然属一般僧人,按规定要求是不能乘马,因此画面中以骑驴形象出现。不仅僧人如此, 社会其他各阶层也有类似情形,《封氏闻见记》卷十记载:
时刺史有马,州佐以下多乘驴,严光作诗曰:郡将虽乘马,群官总是驴。[9]
《太平广记》卷一八三《贡举》记载:
又咸通中,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时场中不减千人,谁势可热手,亦皆骑驴。 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袖长秋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10]
显然骑马或骑驴在唐代是有身份区别的。
2.驴为唐人出行常见交通工具
骑驴出行,在唐代是非常普遍,各地的驿站也提供驿驴方便过往旅客, 不少客店专门养驴给客人租赁,被称为“赁驴小儿”,日本僧人圆仁就曾在唐境多地见到过雇驴出行者:
(四月)七日卯时,子巡军中张亮等二人僱夫令荷随身物,将僧等去。 天暗云气,从山里行,越两重石山,涉取盐处,泥深路远。 巳时,到县家。都使宅斋。斋后骑驴一头,莊从等并步行。少时有一军中迎来,云:“押衙缘和尚等迟来,殊差使人催来。 ”未时,到(兴国寺)。寺人等云:“押衙在此, 不得待迟来, 只今发去。”寺主煎茶。便僱驴三头,骑之发去。驴一头行廿里,功钱五十文。 三头计百五十文。 行廿里到心浄寺,是即尼寺。 押衙在此,便入寺相看,具陈事由。 押衙官位姓名:海州押衙兼(左二将)十将、四县都游奕使、(勾当蕃客)、(朝议郎)、(试左金吾卫)张实。 啜茶之后,便向县家去,更僱驴一头,从尼寺到县廿里。 晚头,到县,到(押司事)王岸 宿。 驴功与钱廿文。 一人行百里,百廿文。[11]
在唐宋小说中驴作为出行工具, 按照出行目的可分为赴试京师、远任赴官、出游采风、日常骑行几类[12],在唐代的墓葬中有三彩驴出土,颇能说明问题。
3.骑驴出行特有的文士气息
驴是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诗人颇为喜爱的坐骑, 中国文学史上以骑驴著称的诗人代表有唐代孟浩然、李白、杜甫、贾岛、李贺、郑綮等,其中一些著名的骑驴故事和骑驴语录广为流传, 如有杜甫“骑驴三十载”,贾岛在驴背上推敲写诗,李贺骑驴觅句,郑綮有“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的佳话,均属中国文化史上文人骑驴特有的文化景观[13],隐喻文人的失意、落魄、孤傲与超脱。 所以有研究者指出,“由于驴是一般人未作官时的出行工具,因此那些仕途不达的落魄英雄、 没中第或虽中第但无官的诗人骚客都骑驴, 甚至由于不作官的人才骑驴,致使它又成为隐士处士等高人的坐骑,给人以虽穷但很旷达的感觉。 ”[14]
4.骑驴与寻仙访道
在唐代笔记小说中, 驴子往往是主人遇仙的媒介,对此有研究者已有梳理[15]。魏晋时期骑驴往往和成仙有关,《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 ”[16]为什么河东人刘白堕酿的“鹤觞”酒,又名“骑驴酒”,似有骑驴喝此酒如同仙鹤,可以一日千里,也有清冷孤高的精神寄托。考虑到佛陀波利前往五台山顶礼文殊菩萨,遇见圣老人,与唐宋人遇仙颇有几分相似;再者,唐宋时期方士、道士骑驴也是常见,佛陀波利作为从西而来的一位僧人,和方士、道士在身份上颇有类同,故骑驴出行符合他此行的神秘色彩。
所以,我们推测,受以上几个方面的社会现象和日常生活景象的影响,画家在把作为丝路旅行者的佛陀波利描绘成颇有几分文士气息而乘驴出行。
三 戴斗笠的佛陀波利
对于第217、103 窟尊胜经变序文画面多处佛陀波利骑驴前行的场景, 学者们普遍认为以骑驴姿态出现的佛陀波利头戴的是帷帽 (图3)[17],但经仔细观察这两幅壁画中佛陀波利的形象, 可发现佛陀波利的首服并非帷帽, 而是一种以僧衣裹头,外戴斗笠的形象。

图3 第217 窟尊胜经变佛陀波利旅行图局部
帷帽是一种始于隋代,兴于初唐的首服。 《事物纪原》卷三载:帷帽是“用皂纱若青,全幅连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18]。关于唐代帷帽的相关实物形象, 可见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 号墓出土的骑马女俑头上的锥形帷帽,该帷帽帽檐周围有一层网纱,下垂至颈部,仅遮挡头部(图4)。 由于该墓葬出土的墓志和文书属于武周时期和天宝初年, 因此女俑服饰装扮所反映出的应是“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篱渐息”[19]。

图4 阿斯塔那187 号墓出土唐代骑马女俑(局部)
仔细观察佛陀波利的形象, 可发现第217、103 窟佛陀波利的头部服饰并未出现帷帽帽檐周围的一层网纱,其与文献记载、实物图像所见的帷帽有一定的区别。同时,我们发现在第103 窟尊胜经变序文画面, 表现佛陀波利向五台山顶礼拜谒的画面中, 脱下首服的佛陀波利在其头部下方有一帽状服饰与所着僧衣紧密相连, 应是僧衣的一部分或脱下的风帽。这一突出的服饰特征,充分地说明第217、103 窟佛陀波利头戴的并非帷帽,而是僧衣裹头或风帽与斗笠的搭配。
第217、103 窟佛陀波利头戴斗笠的形象,也可以得到其后各时期敦煌同类绘画的佐证①关于敦煌壁画中佛陀波利形象的研究参看陈凯源《图像的转变与重构:敦煌“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图像研究》,《中国美术研究》待刊稿。。 肃北五个庙西夏第4 窟文殊变中出现了头戴斗笠的佛陀波利形象(图5),另外,与佛陀波利头戴斗笠的形象稍有不同, 敦煌画稿和石窟壁画中还出现了背挂斗笠的佛陀波利形象。 P.4049“新样文殊”白描稿画面左侧上方的人物为佛陀波利,该佛陀波利老年胡僧形,双手合十,身着短袍衫衣, 背挂斗笠, 脚缠绑腿,作远行状(图6)。由于画稿中佛陀波利的人物形象、服饰特征与莫高窟五代第61窟西壁五台山图“西台之顶” 的北侧和 “北台之顶”与“东台之顶” 中间分别两次出现的佛陀波利极为相似,故P.4049 白描稿中的佛陀波利应是第61 窟五台山图中佛陀波利形象的画稿[20]。 无论是头戴斗笠还是背挂斗笠,主体人物仍然是佛陀波利,所以本质是仍然是对佛陀波利丝路旅行形象的描述。

图5 五个庙第4 窟佛陀波利像

图6 P.4049 画稿中的佛陀波利
斗笠是一种以竹篾等材料制作而成的帽子,因其宽敞的帽檐具有遮阳挡雨的功能, 还轻巧便携,因此广受欢迎。 在古代,斗笠不仅常作为农民百姓日常劳作时所戴的帽子,其在佛教中亦是僧人远行云游时常见的随身物品。 《宋高僧传》记载贞观时期,游学京邑的僧人元康“又衣大布,曳纳播,戴竹笠,笠宽丈有二尺。 装饰诡异,人皆骇观”[21]。 《大宋僧史略》云:“西域有持竹盖或持伞者。 梁高僧慧韶遇有请,则自携杖笠也。 今僧盛戴竹笠,禅师则葼笠。 ”[22]认为汉地僧人流行的斗笠,源自于西域僧侣的竹伞盖。 《禅苑清规》指出“入院之法,新住持人打包在前,参随在后。如遇迎接,或下笠敛杖问讯,或右手略把笠缘低身,或请就座茶汤,但卸笠倚杖就坐,不可卸包。”[23]尽管这里记述的是行僧进入寺院挂单时所需注意的相关礼仪,但其中多次提到关于斗笠摆放的规则,从侧面可说明, 斗笠已成为行脚僧人出门远行时常见的随身之物, 因此需制定相关礼仪对斗笠的放置进行规范。
佛教僧人为寻师求法而云游四方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初盛唐时期,由于唐王朝国力的强盛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丝绸之路上活跃着一大批东西往来弘法求法的高僧。 因此,画史文献中就保存有不少唐两京地区寺院壁画绘制行脚僧像的记录①《历代名画记》记载,吴道子、李果奴等人曾于两京地区的佛寺中绘行僧图像。 《唐朝名画录》亦载,周昉于大云佛寺殿前画行道僧。 详参(唐)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年;(唐)朱景玄撰,温肇桐注《唐朝名画录》,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 年。。 唐代寺院壁画中行脚僧像的出现,反映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中外高僧弘法求法活动的兴盛, 行脚僧像则可视为是一批批在丝绸之路上西来东往取经弘法佛教僧人的缩影。 尽管唐两京寺院壁画中的行脚僧画像早已消失不见, 但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纸绢画和五代宋西夏敦煌石窟中出现的行脚僧画像, 为我们了解这一形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据统计,敦煌行脚僧图像至少有20 余幅②王惠民《敦煌画中的行脚僧图新探》,《九州学刊》第6 卷4 期,1995 年,第43—55 页。 另载氏著《敦煌佛教图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93—115 页。,观察这些行脚僧图像, 可发现其大多都存在头戴斗笠或将斗笠置于所背经囊之上的情况(图7)。 可见, 作为胡僧西来或僧人外出远游常见随身之物的斗笠,已影响到行脚僧图像的创作,并成为这类图像不可或缺的构图要素。将五代、西夏时期的佛陀波利形象与敦煌行脚僧图像进行对比后可发现,这两种类型的图像,其人物形象、服饰装扮等特征均极为相似。这种图像的相似性,似可说明佛陀波利与行脚僧之间的相关性。唐代志静所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记载佛陀波利从西域来华,在五台山上受文殊老人点化, 随后又不远千里返回西域,再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带到中土弘传,在这里佛陀波利传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事迹,和求法弘法的行脚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图7 敦煌藏经洞出土行脚僧像
因此, 若将斗笠视为一种图像母题, 从第217、103 窟开始, 斗笠就作为佛陀波利所戴的首服出现,此后这一母题被广泛运用于佛陀波利和行脚僧图像之中。 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莫高窟第61 窟五台山图中,有多处行脚僧人朝圣、礼拜五台山的画面,而这些画面中,行脚僧人亦头戴斗笠。 可以说,斗笠这一图像母题,除出现在世俗人物日常劳作的画面外,其已成为行脚僧身份象征的重要标志。 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第217、103 窟尊胜经变序文画面中骑着毛驴、头戴斗笠的佛陀波利,应是敦煌石窟中行脚僧图像的雏形,是最早的行脚僧图像。
四 载物大象与丝路僧人
第103 窟尊胜经变中增加一载物大象, 显然是对之前以第217 窟尊胜经变为代表图像的修订, 在原本一人一驴一婆罗门男性随侍基础上增加一头载物大白象(图8),之所以要作如此修订,显然是第103 窟壁画的绘制者认为, 第217 窟壁画相同画面内容对佛陀波利故事的表现不是十分理想。 因此可以认为在第103 窟中如此表现佛陀波利的丝路旅行, 或许更加符合当时人们对以佛陀波利为代表的丝路僧人旅行情景的认识。

图8 第103 窟尊胜经变佛陀波利旅行图局部
当然,在丝路长途旅行中出现载物大象,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玄奘法师在游历印度十六年之后返回大唐, 随行带回了他在印度和西域各地搜求所得佛经、佛像,数量丰富:
即以安置法师于西域所得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 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留影金佛像一躯……又安置法师于西域所得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凡五百二十夹, 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疋马负而至。[24]
如此数量的经像,从印度经西域带回大唐,需经过险峻的葱岭和迷幻的西域流沙,谈何容易,非玄奘一人或几人所能够实现。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计划回国之前是“以经像等附北印度王乌地多军,鞍乘渐近”,就是说开始时法师借助的是北印度王的部队力量, 后来又得戒日王相助,“更附乌地王大象一头, 金钱三千, 银钱一万,供养法师行费”,国王赠送玄奘一头大象,显然是作为法师的驮运牲畜,在过雪山时“时惟七僧并雇人等有二十余,象一头,骡十头,马四匹”,是一支非常庞大的运输队伍, 后至朅盘陀国时“逢群贼,商侣惊怖登山,象被逐溺水而死”,因此法师在到达于阗后给唐王李世民修表时特意提及“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迦毕试境,越葱岭,流波谜罗川归还,达于于阗。为所将大象溺死,经本众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24]113-123。 从法师在写给唐太宗的信中对大象的特意强调可以看出, 大象在玄奘法师东归的运输队伍中的重要性, 究其原因应是大象的驮载量之大,符合大象的实际驮运能力,所以我们在第103 窟尊胜经变中看到负重的大象随佛陀波利队伍一行穿行在漫长的丝路崇山峻岭之间。
玄奘法师东归途中使用大象驮经, 结合第103 窟的图像,似乎可以认为丝路上求法/传法僧使用大象驮载物品(包括经像)是较为常见的丝路景象。 第103 窟壁画绘制的时间距离玄奘法师东归已有半个多世纪, 期间或之前之后从印度来华的僧人未曾中断, 想必这些僧人在来华之路上要穿越常年积满白雪和道路崎岖险峻的帕米尔高原,又要穿行西域的沙漠戈壁,必然要依附于熟悉道路的商队,或自身有一支保障性队伍,方可成功到达中土。 所以对汉地人们而言,丝路上求法/传法僧的形象并不陌生。
丝路上传法/ 求法僧使用大象载物, 或者说汉地绘画者在表现这些丝路画面时, 给传法/ 求法僧搭配载物大象, 还应有以下几点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1.传法/求法僧的印度属性
佛陀波利来自罽宾国, 罽宾位处葱岭兴都库什山南麓, 东至今叶尔羌河上游和喀喇昆仑山之间,西达印度河平原即今天伊斯兰堡一带,东北到达今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斯利那加(Srinaga),南到今天印度西北部边界, 相当于今天巴基斯坦北部和东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 属于古印度西北部。 罽宾国都原在迦毕试(今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 后来迁到循鲜城, 即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Taxila)古城一带①参见(英)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法显传》作“竺刹尸罗”[25],《大唐西域记》作“迦毕试国”、“呾叉始罗”[26]。这里总体上属于西北印度, 总体也可以归为历史时期的北天竺地理范围, 大象在古印度地区使用于运输和作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早在张骞时期就已有相关记载:
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27]
至于罽宾乘象则更是为唐人所了解,《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传》:
罽宾,隋漕国也,居葱岭南,距京师万二千里而赢,南距舍衞三千里。王居脩鲜城,常役属大月氏。 地暑湿,人乘象,俗治浮屠法。[28]
所以, 画家给来自罽宾的佛陀波利搭配载物的大象,确也符合其来源地的身份属性。 据此,可以推而广之, 唐代绘画中给西来的胡僧搭配载物的大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更加有趣的是, 我们注意到第103 窟尊胜经变画中,在其中的一个画面中,居然把这头大象画作六牙白象,显然视其为佛教圣象。六牙白象是佛教神圣性的象征, 莫高窟初唐第329 窟乘象入胎壁画中可以看到。从这个角度来看,第103 窟尊胜经变出现在白象载物, 也和僧人的佛教身份与属性有关。
2. 唐代大象作为交通运输工具使用的历史事实
据文献记载, 有唐一代大象确实有作为交通运输使用的情况,《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下“典厩署”条:
典厩令掌系饲马牛,给养杂畜之事;丞为之贰。 凡象一给二丁,细马一、中马二、驽马三,驼、牛、骡各四,驴及纯犊各六,羊二十各给一丁,(纯谓色不杂者。若饲黄禾及青草,各准运处远近,临时加给也。)乳驹、乳犊十给一丁。 凡象日给藁六围,马、驼、牛各一围,羊十一共一围(每围以三尺为限也)。 蜀马与骡各八分其围,驴四分其围,乳驹、乳犊五共一围;青刍倍之。 凡象日给稻、菽各三斗,盐一升;马,粟一斗、盐六勺,乳者倍之;驼及牛之乳者、运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施盐三合,牛盐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盐六勺。 (象、马、骡、牛、驼饲青草日,粟、豆各减半,盐则恒给;饲禾及青豆者,粟、豆全断。 若无青可饲,粟、豆依旧给。 其象至冬给羊皮及故毡作衣也。 )[29]
既然太仆寺下典厩署饲养大象, 应属交通运输使用。这是在北方长安,其实在南方使用大象运输就更不足为奇了。
同在《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下“乘黄署”条:
后阅视武库,得魏旧物,有乾象辇,驾二十四马;又有大楼辇车,驾二十牛;又有象辇,初驾二象,后以六驼代之,皆魏天兴中之所制也。
说明在北朝时期已经使用大象驾车了。 事实上更早的汉代,大象就频繁出现在汉画中,负重载人均有。 敦煌唐代报恩经变中出现大象身上架设豪华座具,其上坐人,也是大象作为交通运输的图像反映。 至于发展到普贤菩萨骑象和佛传故事中乘象入胎,则完全是大象神圣化的体现,但也多少有大象负重载物的遗痕。
五 文人骑驴图式借用
第217、103 窟两铺尊胜经变,可以看到佛陀波利丝路旅行的画面,总体上是一幅唐代前期的青绿山水画,除了画面中为了强调佛陀波利顶礼五台山见文殊化现老人并受其指点返回西国而出现中亚式城,另有表现佛陀波利入长安见“大帝”并在西明寺译经的情节出现长安城和西明寺之外[30],整体上是一幅难得的唐代青绿山水画,佛陀波利一行的丝路旅行是穿插在山水之间。 若从画面的比例结构而言, 与其说是在表现佛陀波利的丝路旅行,倒不如说在描绘一处人间美景,这类绘画样式在经变画中极为少见。
据保存数量最为丰富的敦煌石窟和藏经洞各类绘画中的经变画可知,唐宋时期的经变画画面结构主要以建筑为框架, 如各式西方净土变、药师经变等,在主尊说法会周围是天人众,分处不同的建筑空间;另有像法华经变,是以虚空会、灵鹫会即两处释迦佛说法为中心式的结构,周围上下左右穿插各品故事画,整个画面布满各式各样的人物;在个别的弥勒经变中出现大型的山水背景,但并不影响处于中心三会说法和天人众眷属形象的丰富表现,弥勒世界诸事则穿插在上下左右位置,代表者如莫高窟盛唐第446 窟、榆林窟吐蕃期第25 窟等;还有像华严经变,则完全是以九幅小型说法图来架构整体的经变画,画面中全是说法图中的主尊佛和其胁侍眷属形象,既无建筑更无山水;到了五代宋时期大型经变画就更加突出建筑主体,到了西夏时期则出现经变画画面中只有主尊佛和海会菩萨的形式,属于经变画的简化版,当然西夏时期也有以榆林窟第3 窟和东千佛洞第7 窟净土变、文殊山后山万佛洞弥勒上生经变为代表的界画式的经变画,建筑画成为画面的主体。
所以,总体来看,山水风景画在佛教经变画中并不流行, 或者说山水风景画并不是唐宋经变画的常见构成元素, 即使是从中唐吐蕃时期开始突出表现五台山文殊化现的文殊变和普贤变[31],作为背景的五台山也并不突出,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夏时期有所改变, 榆林窟第3 窟大型文殊变和普贤变,突出水墨山水风景。即使是莫高窟五代第61 窟大型巨幅的五台山图,虽然画面整体是一幅地理图,山水风景充满整个画面,但从整体的观察还是感受不到强烈的山水风景属性, 更多的仍然是画面中的建筑、人物、生活场景、世俗风情、神异现象,等等,惟有藏经洞绢画EO.3588 五台山文殊菩萨化现图有所例外。
整体来看, 第217、103 二窟出现突出山水风景的经变画画面内容,实属例外。 其实,即使是这两幅尊胜经变本身, 除了画面一侧表现序文佛陀波利故事的部分之外, 经变画主体仍然是传统的唐宋经变画重建筑和人物情节故事的画面构成特色,是符合以上所述唐宋经变画的整体特征的。如果再考虑到同时期第23、31 窟尊胜经变, 序文佛陀波利丝路旅行情节完全不再出现, 一直到五代宋时期的第55、454 窟的两铺尊胜经变,这部分内容也再没有出现,充分说明对于经变画而言,这种大面积描述山水风景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并不流行, 因为经变画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对经文内容的图画表现并宣传佛教教义, 均是以主尊为中心而展开的, 而本文所论此类画面更多强调的是一位西来译经僧的入华经历和传奇, 虽然是今天非常看重的佛教历史史料, 但在历史时期此类故事的图画创作并不流行, 当然这一点也受到佛陀波利本人在佛教求传/求法史上地位的限制。
所以说, 作为经变画创作和构成非主流绘画因素的山水风景画出现在第217、103 二窟的尊胜经变中,虽然有佛经序文内容的支撑,但毕竟不是同时期经变画流行的题材和样式, 因此画家在设计这一经变画时会依据什么内容进行创作, 值得深入思考。
探讨这个问题, 还得从佛陀波利骑驴形象入手,因为这个形象在整幅画面中反复出现,同时也是整幅画面中核心人物和相应故事情节的顺序变化发展线索图景。
在这里佛陀波利骑着一头小毛驴穿行在丝路崇山峻岭之间,颇具丝路长途旅行的孤独意境,很容易让我们联系到具有类似情境的唐宋时期流行的文人骑驴图。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骑驴现象和其所包含的深刻文化含义,学者们讨论颇为热烈,让我们看到骑驴所体现出来的古代文人独特的人文情怀和文化心态之历史趣味, 进而看到文人骑驴成为宋元明清以来一类独特文人绘画的象征和符号[32]。对于典籍文献中人物骑驴的记载,据孔艺冰的统计,“有865 条之多,其中唐代之前有7 条,主要在汉魏时期;唐宋时期263 条,包含唐42 条,五代6 条,宋213 条;宋以后597 条,包含民国27条。 ”[33]
虽然目前可以看到最早的文人骑驴绘画是五代的作品,一是台北故宫藏南唐赵幹的《江行初雪图》(图9), 一是北京故宫藏关仝 《关山行旅图》(图10),文人骑驴图到了宋代则颇为流行,是这一时期一类常见的绘画题材, 以至有研究者认为文人骑驴有绘画的象征性和符号性意义[32][33]。

图9 台北故宫藏南唐赵幹的《江行初雪图》局部

图10 北京故宫藏关仝《关山行旅图》局部
唐代有没有骑驴图像,据孔艺冰的研究,最早的文人骑驴图像,即出现在唐代,她认为“文人骑驴图像源自唐代,《孟浩然骑驴图》《杜甫骑驴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33]13。 具体是据一些文献的推断,如她认为既然《新唐书·孟浩然传》中有王维给孟浩然画像的记载,“初,王维过郢州,画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 咸通中,刺史郑谓贤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28]5780,及至南宋牟巇有《王维画孟浩然骑驴图》 诗流传下来, 再联系到苏轼“又不见雪中骑驴孟浩然”的诗句,可以认为宋代有王维画《孟浩然骑驴图》,图文呼应,可以佐证唐代已有绘制的文人骑驴图。 另据杜甫《画像题诗》“迎旦东风骑蹇驴,旋呵冻手暖髯须。 洛阳无限丹青手,还有功夫画我无”诗句,从侧面反映出在唐代应有画家绘制文人骑驴的作品, 其中可能就有《杜甫骑驴图》之类的绘画。到了宋代释绍昙有《杜甫骑驴游春图》一诗流传,说明宋人有“杜甫骑驴图”,有可能其最早出现即是唐代[33]12,13。
尤其是台北故宫藏据传李思训所作《江帆楼阁图》(图11), 虽然学术界对其真实的成作时代有疑问①见傅熹年《论几幅传为李思训画派金碧山水的绘制时代》,《文物》1983 年第11 期,第76-86 页。 何乐君《〈江帆楼阁图〉 年代再探讨》,《四川文物》2016 年第2 期,第86-94 页。盛玫《界画和服饰——古代书画断代的两大关键点——〈江帆楼阁图〉断代试析》,《收藏家》2017 第3 期,第57—60 页。, 但学术界对其所体现出来的李氏风格多持赞同意见②见金维诺 《李思训父子》,《文物》1961 年第6 期,第13—16 页。 Kwong Lum.The Recovery of the Tang Dynesty Painting:Master Wang Wei’s Ink-wash Creation“on the wangchuan rive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yics,Culture and Society. Vol.11,No.3,1998. pp.441. De-nin D.lee,Fragments for Constructing a History of Southern Tang Painting,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No.34,2004,pp.31.Mary H.Fong,Tang Tomb Murals Reviewed in the Light of Tang Texts on Painting. Artibus Asiae A/0I.45/N0.1,1984,pp.35—72.宁晓萌《李思训绘画研究》,《文艺研究》2017 年第6期,第121—135 页。, 而孔艺冰能够阅读出其中的人物并非骑马而是骑驴, 则打开了我们观察此类图像的一扇新窗户, 也启示我们山水风景画背景中出现的文人骑驴图有可能可以早到唐前期, 至少到了盛唐时期伴随着《孟浩然骑驴图》《杜甫骑驴图》的出现,此类图画已成较为固定的图像样式开始传播。

图11 台北故宫藏据传李思训所作《江帆楼阁图》局部
所以,我们推测,第217、103 窟尊胜经变表现佛陀波利丝路旅行图的创作, 或者准确地说此类经变画在长安创作的粉本画稿, 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已经在唐代出现的文人骑驴图如《江帆楼阁图》《孟浩然骑驴图》《杜甫骑驴图》等的影响。反过来,或许我们也可以认为, 第217、103 窟佛陀波利丝路旅行图的样式, 即骑驴的人物穿行在山水风景画中, 应是其后五代宋及其以后大量文人骑驴山水风景画的早期遗痕,雪泥鸿爪,至为珍贵。
至此, 就可以理解二窟两铺尊胜经变画中时时出现在佛陀波利前后,跣足徒步,或牵驴或引象的婆罗门形男子人物,其瘦弱的形象,显然是对古代文人骑驴图后面徒步跟随的瘦小书童的写照,位置和场景替换, 在这里以佛陀波利随侍的形式出现,又以婆罗门人物形象出现,是符合佛陀波利来自罽宾国真实身份的。一位婆罗门随侍左右,可能也受到印度当时对待高僧习俗的影响, 玄奘法师在那烂陀寺时就曾受此礼遇,《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记:
引入那烂陀寺……给净人婆罗门一人,出行乘象。[34]
所以说, 佛陀波利丝路旅行图中始终有婆罗门僧随侍前后,其实既受中土文人骑驴图的影响,也是印度本土习俗的写照。
六 结语:中古传法僧与取经僧图像遗痕
第217、103 二窟两铺尊胜经变中的佛陀波利丝路旅行图, 是为数不多的表现丝绸之路上西来的传法/ 求法僧的画面。 汉魏以来从印度、中亚、西域各地沿丝路而来的入华的僧人络绎不绝,历代僧传等佛教典籍文献有详实的文字记载, 但在汉地颇为发达的佛教艺术品中并没有留下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实属佛教艺术史上的历史疑问。
检索史料,也有线索可寻。据唐人张彦远的记载, 在长安城西明寺“东廊东面第一间传法者圆赞,褚遂良书”,另在千福寺有“卢稜伽、韩干画,里面吴生画。时菩萨现,吴生貌”的“绕塔板上传法二十四弟子”图[35],西明寺和千福寺两铺传法图,均属唐前期作品,时代和莫高窟壁画相当。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画面核心内容是对西来传法高僧的图绘,应以人物画像为主,是否为山水画背景下的人物旅行场景,看不出来,不过“传法二十弟子”倒是有可能和石窟所见依据《付法藏因缘传》而表现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所记“西天二十九祖”有关,但数字上不合。 另在《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益州名画录》记载唐长安、洛阳和益州等地寺院多绘画一类 “行道僧”“行僧”壁画, 据于向东梳理考证, 此类人物画像出现在初唐,到了盛唐、中唐时期明显增多,主要身份是指自第一祖大迦叶至第二十八祖达摩之间的传法祖师,均为天竺高僧,但在敬爱寺东禅院出现了“刘行臣描”的“唐三藏”即玄奘法师像,说明唐代内地出现的行道僧身份应该是对佛教做出重要贡献的祖师大德, 具体的图像遗存以龙门石窟擂鼓台中洞和看经寺祖师像为代表[36]。 但这两类画史所记唐代的“传法图”和“行道僧”似与本文所论丝路传法旅行图有明显的区别。
不过保存于武威明代重刻唐《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则留下重要的线索,该碑的时间是高宗景云二年(711),碑文记载司马逸客任河西节度使、凉州都督期间[37],司马公和同僚们于凉州大云寺画壁画,“后司马公复兴军州共为营构, 总剔四面, 更敞重檐。 于南禅院回廊画付法藏罗汉圣僧变、摩腾法东莱(来)变、七女变”[38],其中的“摩腾法东莱变”应是东汉明帝十年(67)摄摩腾、竺法兰二胡僧携带经像至洛阳白马寺, 后二人译出最早的汉地佛经《四十二章经》,此变相应该是这二位传法僧东来故事经变, 应属于本文所论西来的胡僧丝路旅行图, 可惜画面构图形式和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使用“变”,说明此二人故事绘画的情节还是颇为复杂的。
我们注意到,凉州大云寺“摄摩腾、竺法兰东来变”壁画绘制的时间即唐景云二年,也正是莫高窟第217 窟洞窟营建的时间,也就是说诸如“摄摩腾、竺法兰东来变”、佛陀波利丝路旅行图等此类胡僧入华的传法或求法图,在这一时期较为流行,河西的凉州和敦煌二地均有出现, 说明在中原内地的长安、洛阳等地应该更加常见。 所以,虽然出现在凉州大云寺的“摄摩腾、竺法兰东来变”没有图像留存,但第217、103 窟佛陀波利丝路旅行图,倒是提醒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其绘画或多或少的图像结构和内容,两者应有共同之处。
对于大家熟知的达摩图像, 只表现其神通渡海,画面情节过于简单,不具长途旅行要素。 现在可以认为属于最早的且情节较为丰富的有关求法僧的图像即是学界讨论热烈的玄奘取经图, 此类图像最早者保存于陕北的宋金石窟中, 据造像题记可知有政和二年(1112) 的子长钟山第12 窟、1100 年前后的钟山第10 窟、 绍圣元年至崇宁元年(1094—1102)的安塞招安第3 窟、崇宁二、三年(1103、1104)的宜川贺家沟佛爷洞石窟、北宋绍圣二年至政和五年(1095—1115)的黄陵万安禅院第1 窟、北宋宣和元年至五年(1119—1123)的安塞石寺河第1 窟、 金皇统元年至贞元七年(1141—1159)的富县石泓寺第7 窟、北宋元祐八年至政和三年(1093—1113)的樊庄第2 窟等丰富的取经图像[39],另有同时期的敦煌石窟群中瓜州榆林窟西夏第2、3 窟、东千佛洞西夏第2、5 窟壁画,这一时期的玄奘取经图人物组合以一人(玄奘)、一猴行者、一马为基本的图像构成元素。
早期玄奘取经图一人一猴行者一马的组合,很容易让我们联系到第217 窟传法僧佛陀波利的丝路旅行图景,同样一是一人、一婆罗门形人物、一驴,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画面中除了核心的传法僧或求法僧之外, 另有一身猴行者或婆罗门形人物,属于僧人的随侍,玄奘取经图中的马早期均为驮经的形象,宋金、西夏之后出现玄奘骑乘的图像,虽然二者出现的时间相差较大,但二者似乎在图式上存在一定的延续性或关联性。 若再考虑到五代宋以来常见文人骑驴山水图景中出现的一人一驴一书童的样式, 再次印证了以第217、103 窟尊胜经变佛陀波利丝路旅行图图式创作的深厚历史渊源关系。
再结合佛陀波利头戴斗笠图像从第217、103窟出现之后,一直出现在五代第61 窟五台山图和西夏时期的文殊变中, 包括藏经洞白描画稿P.4049,可见其固定而悠久的图像传统。
所以,总体而言,第217、103 二窟尊胜经变佛陀波利丝路旅行图的创作粉本, 显然是长安的画家们受到了已有的类似于传李思训 《江帆楼阁图》,以及更晚的《孟浩然骑驴图》《杜甫骑驴图》一类绘画的影响,根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文内容描写,进行了巧妙的图像借用,进而创作出今天仍然保留在第217、103 窟中的二幅大型青绿山水风景画。而其中佛陀波利骑驴和头戴斗笠的形象,以及第103 窟载物大象的添加, 均有相应的图式依据和历史背景可参考。 因此,可以认为,此二铺佛陀波利的丝路旅行图, 实是8 世纪左右长安画家对西来传法/ 求法胡僧在漫长丝路上行进情景的充分了解后的图像写照, 同时也受到已有文人骑驴图式的影响。
综上, 历史时期对活跃在漫长丝绸之路上的传法/ 求法僧的图像表达, 总体上是借用了文人骑驴的山水风景图式, 其中的较大面积和空间感的山水风景是其构图的背景, 至于头戴斗笠的形象和作为随侍的婆罗门形人物, 除了有图式的因素之外,也是现实生活的写照。 所以,观察第217、103 窟尊胜经变佛陀波利丝路旅行图, 更大的收获, 或者说主要的启示是对历史时期丝路传法/求法僧图像的探寻与想象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