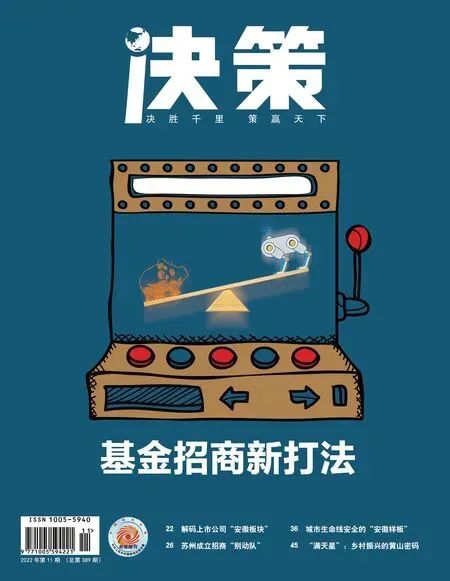无语凝噎(上)
文/余清平
一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了,马书雪驱车来祭奠白帆。他摆好祭品,然后,坐在白帆坟前的石头上,思绪像孤独的云,在空中游走。
那是前年冬月初二。对,就是那天上午,地点是北清市的建筑工地,马书雪正在做预算。他的思维在一堆堆阿拉伯数字里游走。马书雪让它们在自己的纸上排队,寒风,也阻止不了汗水从他的额头滴下。忽然,马书雪的手机“滴滴”地响起来。马书雪皱一下眉,还是伸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屏幕,是他老乡白帆的电话号码。马书雪接听时,电话里传过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对方声音疾风暴雨一样,“哔哩吧啦”的,说他是白帆的同事,又说白帆走了,让马书雪赶去白帆的单位。
“白帆走了?他能走哪去?”马书雪笑着说。“对不起!是白帆死了。”对方急忙解释。“死了?他死了?”对方的话就像个秤砣,砸在马书雪的百会穴上,眼睛顿时发黑,思维停滞。白帆,比马书雪还小一岁,才二十九岁,如爬上三竿高的太阳。马书雪连忙跑步到公司,向人事部经理请假,工作服来不及换就传呼滴滴车赶过去。
马书雪与白帆同是旮旯村的,也是远房亲戚。旮旯村坐落在大山里,每个村小组散落在大山的皱褶处。旮旯村方圆十几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足两千,稍微有一点事,就将旮旯村的沟沟壑壑填满。
白帆的原名不叫白帆,叫白宝玉,是家中独子,他父母的掌中宝。但是,白帆长大懂事后,觉得这名字俗气、市侩,遂改成白帆。白帆说:“白色的风帆,遨游在湛蓝的大海之中,波涛熠熠,点点白帆在跳跃,多么富于诗意的名字。”
白帆读书比谁都勤奋,考上名牌大学,毕业后,又获得硕士学位。马书雪虽然也优秀,也算得上是电子专业的高才生,但与白帆比,还是差一截。在旮旯村,白帆是金凤凰,马书雪只能算是孔雀。两个农家孩子,都是旮旯村的亮点。但找工作时,距离就凸显出来。
白帆的工作单位是他院校保送的,而马书雪就得自己去找。马书雪大学选读专业时,市场上电子人才供不应求。作为一个农村孩子,马书雪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找个好工作,改变自己的人生,更是有经济实力来孝顺父母,让苦了几十年的父母可以过得舒适一些。然而,等马书雪四年大学毕业,电子专业人才却变成一职难求。四年间,变化太大了,全国各所高校毕业了许许多多的学子,致使供方砝码加重,需方砝码减轻,供需双方失衡倒置。马书雪的几个要好同学都如他一样,出了学堂门,进入社会,在学校里踌躇满志的精气神就被狂风吹得一点儿不剩,找不到对口专业的工作。
不过,马书雪那一辈子与泥土厮混的父亲就从不指望他光耀门庭。他大学毕业时回家住了一段时间,与父亲摩擦“生了几次电”。父子两个差点铁锤撞铁锥。
至今,马书雪想起父亲那句话,耳朵还在“嗡嗡”作痛。一次,马书雪的父亲在狠狠地咽下一口唾液后,再狠狠地从那大口吃饭大口喝酒的嘴巴里砸出一句话:“马书雪,你这忤逆子,你得给老子找个儿媳妇,给老子生一个孙子,你这不孝的东西!”马书雪的父亲骂他不孝,是有原因的。当年,他的父亲抱孙子心切,好不容易在村里给他说了一门亲事,他一口拒绝,没有商量余地。马书雪还抗争说:“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不差我给添一个儿子。”那次,气得他父亲差点抄家伙拍他。
马书雪知道,他可以不理父亲的切盼,可以不成家,可以不生儿子,但是,必须努力工作挣钱让父母亲过上好日子,这是一个农村孩子必须考虑的,也是必须有的志向。但是,马书雪的处境无法让他父母过上好日子。没奈何,马书雪不得不降低目标,退而求其次,有工作就行,有银子收就可以,反正银子在哪儿都是等重的,不会因为工作不对口而失去比重。这样,他屈尊于南江市建筑公司,在工地做预算员,每天戴着黄色安全帽,像一把活着的工具,在建筑工地的空隙里钻来钻去……理想,暂时得为生活让步。
工作几年,马书雪给许多建筑做过预算,但他自己没有预算到一套房子,至今租住出租屋。马书雪知道白帆的工作比他优越不少,但也没有买房,与他一样租屋住。两个人的父母都住在乡下旮旯村,马书雪算是白帆在这城市里唯一的住得近的亲人。
“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追求,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别偏离了正当追求的轨道。”
二
马书雪赶到了白帆的住处,整理白帆的遗物。一件件,睹物思人,泪水溢出马书雪的眼眶。忽然,马书雪看到白帆写给他的一封信,上面贴了3.2 元的邮票,压在电脑键盘下。这是白帆一封未发出的信。马书雪拆开信看。白帆在信里嘱咐马书雪帮他照顾他的父母。也写着,说他这几年常常感到危机临近……说他一个农家孩子,好不容易走出大山,走出贫瘠的土地,走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走进大城市的繁华,却不能好好孝敬父母……马书雪思来想去,理不清头绪。
马书雪反过来仔细一想,也有些许明白,即使寄了又有什么用呢?马书雪忽然想到一句话:诚实的代价。马书雪忆起,有一次,他与白帆一起小酌,白帆说:“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追求,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别偏离了正当追求的轨道。”
“莫名其妙。”马书雪听了,笑道,还伸手摸了摸白帆的额头说,“你没发烧?咋说胡话?”马书雪一天到晚,跟着工程跑,应约与白帆小酌,也是想放松一下他自己绷紧的神经,免得神经过度以至于崩断。过了一会,白帆问马书雪;“人活着,很憋屈,像被大山压着,你说你该怎么办?”
马书雪盯着白帆看,一会儿后,笑了,说:“看你‘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洛阳花’的,却说出这些晦气的话来,我一介寒儒,却也活得毫不妥气。”
马书雪的志向还没生出翅膀,别谈什么羽毛丰满,飞不起来,更不想提那些高大上的说辞。有时候,人现实一些比空乏的理想来得实际。以前在学校时,马书雪生出的远大理想被现在的生活这台打磨机打磨得面目全非,想让父母人前人后衣着光鲜、饭桌上有小酒小肉就是他的小追求小幸福了。
马书雪又指着马路边一棵从水泥墙缝里长出来的弱小榕树,端正了面容说:“有憋屈怕啥?你看那棵小榕树,哪怕没有土壤,也得顽强地展示自己的风姿。人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那次小酌,是马书雪与白帆的最后一次见面。
马书雪想起书里看到的句子:在长长的沉默之后所说的话,原本就是不愿意说的。他读了白帆的信,深深理解了这句话的哲理。原来,白帆的憋屈,与他的局领导有关。白帆是局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局座的吃喝拉撒都要管。
白帆也告诉过马书雪,说他的局座们都很器重他,一致认为他实诚,能办事,会办事,也懂得怎样办事。白帆也是个明白人。他清楚,该请示的得请示,该装糊涂的就必须糊涂。可是,人在很多时候,难得糊涂。白帆此刻就是想糊涂一些,再糊涂一些。然而,现实中,容不得他糊涂,真正的糊涂是装不来的,那得道行深厚、修炼成仙才行。白帆如坐针毡。
马书雪记得白帆对他讲过这样的一件事。白帆的父亲也不愿意白帆离开旮旯村,还告诫白帆,不要瞧不起农村人。白帆的父亲是乡村医生,在县城卫生学校培训学习过几个月,但到底是一辈子生活在这边远的农村,去省城的次数绝对没超过一只手的几根手指。白帆认为他父亲的眼界高不过门前那座海拔五百米的山。白帆指着四周的山笑着说:“爸,你看,这里多封闭,外面的信息进不来,这里的信息出不去。我读书这件事您别再反对,我要努力学习,我要跳出了这山、这水、这土地的包围圈。”
白帆父亲拿白帆没办法,终究依了白帆,不再逼他,更不再干涉他的学习。白帆还知道父亲是为了他好。白帆更知道父亲是想让他继承衣钵,在乡村行医,一心一意扎根于农村,平平静静地生活。白帆说他父亲的愿望和企盼也很平实。他父亲对他说农村人淳朴,不欺诈,比城里人活得轻松自在。
白帆对于他父亲这观点,是不认可的。白帆认为贫穷是无知的根源,父亲的信念说得好听一点是想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说得不好听是做一个不求上进的人。人生,如果这样碌碌无为地活着,于白帆而言,那是对生命的亵渎。有些东西,求同存异,各自理解才能各自安好。
三
工地预算员是需要考证的。马书雪拿到这个证是源于白帆的一个建议。那是在大三那年的一个周末,白帆来看马书雪。马书雪拉白帆去大学城的小餐馆里慰问两人那馋得不行的肠胃。两个学子谈起以后的理想。白帆建议去多考几个证。白帆说:“书雪,你看看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考证,不如,我们趁现在多拿几个傍身。将来出了学堂门,参加工作,再去考证,不仅麻烦,也来不及。”马书雪一听,瘪嘴道:“白帆,我们得有自信,考那么多证干嘛?现在正是放松自己的时候,哪有逼自己吃苦的道理,累死。”但后来,马书雪觉得白帆的建议有道理,多一个证多一条活下去的路,就报考了报关证、工地预算员执业证等。反倒是白帆,一个也没考。
白帆与马书雪的性格几乎是南北两极,但这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情。马书雪的性格有些像汽油,遇火就燃,怎么也捂不灭。这几年在职场摸爬滚打,马书雪就像一把好久没有磨过刃的刀。但刀永远是刀,刃虽钝,但若经过磨刀石打磨,绝对会锋芒毕露。不过,马书雪自己知道,生活不会给予他磨刀石了。而白帆恰恰相反。白帆性格好,遗传了他父亲的基因,口风紧,一直是流言蜚语的终结者,无论什么是非到他这里就再也不会外流,这也让他在别人眼里心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马书雪记得高二那年去白帆家玩,就听到他与他那与世无争的父亲一段对话。白帆父亲说:“孩子,装事的篓是要有两处位置,一处是心,一处是肚子,心里面装的是必须做的事,而那些是非就要放到肚子里,必须将它们清除掉。”“知道啦,爸,‘荆棘丛中休入步,是非门内早抽身;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您老的话,我谨记在心。”白帆笑了起来。马书雪知道白帆能养成了这个优良的习惯,信奉“荆棘丛中休入步,是非门内早抽身”与他父亲的告诫有关。
后来,白帆将许多往事告诉过马书雪,可惜,马书雪不是一个好听众,总是心不在焉地听,也不做任何评论。在马书雪心里,初心的愿望和追求,在工作和生活双重马车的碾压下让他喘不过气,直不起腰,偶尔的休闲也是想隔绝这喧嚣。
这许多年来,白帆比马书雪幸运多了。马书雪大学毕业后,是窜了东家窜西家,也没找到心仪的单位。马书雪去市建筑公司应聘,倒是很顺利。建筑公司本来就没有几个名校毕业生,马书雪去应聘,几乎没有遇到难题,建筑公司也正缺预算员。双方一拍即合,签了聘用合同,尽管,马书雪没有实践经验。白帆则不同,他是他学校的宠儿,得到学院领导们的一致青睐,被推荐到南江市发展局应聘。白帆找工作的过程是康庄大道,没遇上一个坑洼儿,就像一张展平的纸。然而,白帆的应聘比马书雪的应聘更有传奇色彩。白帆对马书雪细细描述过。描述的过程,白帆微笑得像个女孩,淳朴,洁净,有点羞涩。
白帆说他去发展局应聘那天,太阳大得很,很耀眼,光芒一幢幢地叠得很密实,射到他的心窝里,很温暖。他也说他虽然很高兴,窃喜着,认为这是个好兆头,预示他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但心脏还是“砰砰砰”地跳得剧烈。
招聘白帆的主考官是南江市发展局的人事科科长,姓邢,长得细眉凤目,面如桃花。邢科长目光像激光一样有穿透力,虽然一句话不说,但白帆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给他看个透,也许连每一根神经末梢的蠕动也没放过。邢科长盯着他白帆看了足足有十多分钟。
白帆讲的时候,马书雪听得出白帆的心情是愉悦的。白帆说他当时的脸红了,脸上的温度也陡然高了。反正,白帆感觉到他自己的脸发烫皮肤发烫心也发烫,因为他不习惯这样被人盯着。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
白帆极力保持镇定。邢科长的两只眼睛就像两面镜子,平滑、明亮。邢科长盯着他看,确切地说是认真地盯着他看,那不动声色的样子令白帆心情忐忑。不过,结果是好的,邢科长说一句:“很好,就你了。”边说边抬手拿起签字笔在面前摆着的招工简历表上签上大名。
邢科长只说了五个字,这五个字决定了白帆的前途,决定了白帆未来生活的高度和质量。白帆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归位了。邢科长嘱咐:“小白,明天来报到。”接着,邢科长又向白帆交代了一些必须带的生活用品。白帆看得出,邢科长那样子,是很关心的。
白帆去单位,邢科长吩咐后勤给白帆安排了一间单人宿舍。就这样,白帆做了邢科长的下属。白帆的工作与马书雪的工作有天壤之别。马书雪是在地下“跑”的,白帆则是在天上“飞”的,一个地上一个天上;马书雪是劳累的白帆是轻松地;马书雪吹着的是自然风而白帆享受着空调冷气;马书雪在建筑工地奔波而白帆则是闲庭信步;马书雪每天戴着安全帽在工地穿梭,白帆则是每天给邢科长送报纸、递文件,再就是抹抹办公台,搞搞卫生,还有,有时候也给邢科长斟斟茶倒倒水。邢科长办公室的一切白帆给承包了,打扫卫生的阿姨不用进来。阿姨也乐得清闲一些。
白帆与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打小就能吃苦,绝不自己娇惯自己。所以,办公室里的卫生,白帆是很乐意为之。不过,白帆也有思想跑偏的时候。白帆对马书雪说:“我有时候想,早知道工作是如此的舒适娴静,自己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浪费了那么多年的时间,特别是浪费了父母亲的辛苦钱。要知道,在农村,一个孩子读书是多么大的负担?会压断父母们的腰杆。”马书雪连忙打断他的话,反驳道:“看把你高兴得糊涂了,你反过来想想,如果不好好读书,会被招进这么优越的单位吗?”
白帆又说:“想起家乡里那些在黄土地里刨食的乡亲们,我的心是安逸了。”马书雪想起自己的处境,笑着揶揄了他一句:“不是安逸,是安逸得不起一圈涟漪。这日不晒雨不淋的工作,不就是你当初所追求的生活么?”白帆说:“是的,这么一想,心就会很释然。”
(原文刊发《辽河》杂志2020年第5 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