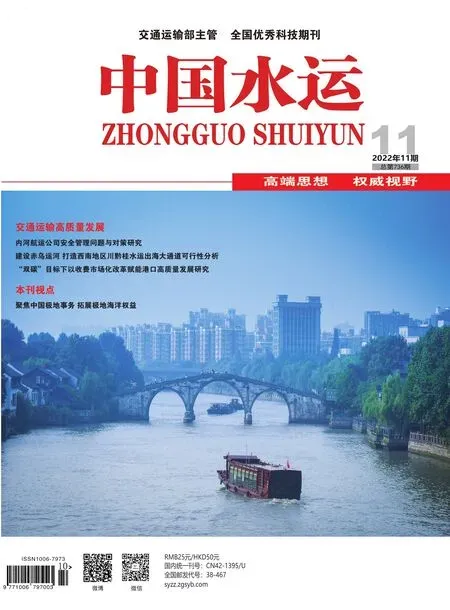强化对我国航运联营体的事中监管
刘美丽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6)
由于航运联营体具有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扩大规模效益和提高海上运输服务质量等特点,而逐渐取代班轮公会,成为当前各航运公司联合经营的一种重要模式。然而,其舱位互租、码头共享、设备共用等形式的合作面临着垄断的风险,此外,航运业是比较特殊的行业,航运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日常沟通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其对外贸发展所带来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实际业务中,航运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可能会逾越反垄断法下的红线,不能满足豁免的要求和条件,因此存在违法的可能性。这侧面说明了航运联营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如何进行监管,保证其在法律界限范围内运营成为一个难题。
无论是从立法层面还是从学术界层面来看,当前我国对于航运联营体的规制,仅仅体现在事前规制和事后监管。《国际海运条例》的相关规定中缺乏事中监管制度,而学界对航运联营体监管的探讨也多集中在是否应该单独赋予其豁免权,这是对航运联营体的事后监管措施,对于如何对其进行事中监管的研究却鲜见。
1 各国对航运联营体监管模式对比
对于航运联营体的监管,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模式,其中典型的当属欧盟模式与美国模式。
1.1 欧盟事后监管模式
欧盟对航运联营体的监管是直接适用模式,采用的是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事后监管模式,并没有相关事中监管的措施。航运公司之间的各种合作协议均无需事先报备或者事先审批,只有违规事项发生时可以对其进行审查,进而援引适用反垄断豁免条例,这是一种纯粹的事后监管模式。但纯粹事后监管模式存在着一定弊端,因为如果事先不要求船公司将其合作协议进行报备或审批,一方面,反垄断监管机构无法及时掌握国际航运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与具体信息,另一方面,也会放任船公司之间从事有违竞争规则的行为[1]。
1.2 美国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模式
美国在对航运联营体的监管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美国对于航运联营体的准入,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制度,是典型的“报备+审批”模式,不但要求航运公司将协议报备,更是要求协议在审查之后生效。此外,美国联邦海事局(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FMC)实施规章第535 节第G 分节“报告与记录保存的要求”中,FMC 根据不同协议的类型(分“红-黄-绿”三种不同类型)有权责令相关当事方负担各种不同“报告义务”,甚至要求通报相关会议记录,实践证明这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事中监管措施。对于目前的三大航运联盟,FMC将其认定为“红色协议”并为其制定严格细致的监管方案,目的是通过监管措施避免航运联盟运用市场势力将运价提高至竞争水平以上,而协议生效后若发生限制竞争的行为,同样会受到规制。美国实施的是全过程的监管方式,然而事前审批制度过于严格,造成资源的浪费,加大航运联营体进入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阻碍其发展。
1.3 我国事前、事后监管模式
我国对于航运联营体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国际海运条例》中,在事前监管方面,《国际海运条例》及《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了事前向交通运输部备案的制度;而在事后监管方面,《国际海运条例》中也规定了事后出现违法行为的调查和处罚措施,此外,《反垄断法》中规定的豁免条件也属于事后监管措施,但是对于事中监管这一方面的措施是缺位的。因此,补充我国对航运联营体的事中监管措施是必要的。
2 对航运联营体事中监管的必要性
对航运联营体事中监管的必要性,一方面源自于航运联营体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从监管体系来看,对于航运联营体的事中监管,可以降低整个监管环节的成本,此外,对于航运联营体的事中监管不仅可以减少其违法行为的出现,更是可以方便事后监管,保证航运市场秩序的健康良好发展。
2.1 航运联营体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无论是从国际还是从国内层面,航运联营体的发展正面临着现实困境。
美国白宫发文称担忧三大航运联盟垄断局面导致市场缺乏竞争,必要时FMC 有权对其发动挑战,而FMC 也于今年六月对三大联盟启动调查,要求三大联盟及其成员船公司提供更多定价和运力数据,该数据用于评估运营商行为和市场趋势,以此来防止反竞争的费率和服务。而欧盟将航运联营体豁免期限延期至2024 年,此次延期却遭到了欧洲托运人理事会(European Shippers' Council,ESC) 以及全球托运人论坛(Global Shippers' Forum,GSF)在内的托运人团体的反对[2]。此外,按照惯例,每次延期均以5 年为一次界限,此次延期减少一年,这是否意味着欧盟对航运联营体豁免政策的态度有所转变,这有待于在2024 年集体豁免条例(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EBR)检讨中去寻找答案。亚洲地区的韩国对航运联营体也进行着严格的监管,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2021 年对“黄海协议”进行反垄断调查,委员会认为联营体“由于在韩国-东南亚航线上操纵运价,进行串谋”,将对12 家韩国国内班轮公司和11 家外国班轮公司处以罚款,总计962 亿韩元,约合8070 万美元[3]。这其中涉及到我国多家航运公司,而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并未作罢,其后又对日韩航线进行调查,后续仍值得关注。不难看出,各国政府对航运联营体的监管问题亦是十分关注,一方面,各国希望航运联营体发挥其优势作用,但另一方面又担心由于对其监管不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我国航运公司众多,航运公司之间在很多航线舱位互换的情形亦是不少,并且多个航运公司同属于一个航运联盟,加强对航运联营体的监管是必要的,而我国当前已有事前、事后的相关监管措施,对其进行事中监管是现实需求。
2.2 监管成本理论
探讨事中监管的必要性,首先需要确定各类监管方式所支出的成本。而根据监管成本理论,监管成本分可以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所谓显性成本就是在监管过程中所支出的成本,一方面是监管者在监管过程中所支出的成本,另一方面是被监管者为了配合监管所支出的成本。而隐性成本则是指监管者在监管过程中对被监管者所造成的损失[4]。对于航运联营体来说,其事前监管的显性成本主要体现为交通运输部备案过程中所支出的成本以及航运企业准备相关材料的成本,而若监管不力,则可能会产生后续诸多问题,进而带来较大的隐性成本。因此,事前监管的显性成本较低,而多体现为隐性成本。事后监管则多体现为显性成本,对于航运企业的违规行为,事后监管从立案调查到处罚,往往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历时长,难度大,复杂性强,因此其显性成本较高。反观对航运联营体的事中监管,从监管阶段来看,较事前监管周期短,其产生的隐性成本不如事前监管高,从监管方式来说其所采取的措施力度不如事后监管大,产生的显性成本也不如事后监管高,因此就从节省监管成本这方面来看,加强对航运联营体的事中监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监管手段。
2.3 促进航运市场健康发展
加强事中监管可以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是减小违规行为的危害程度,二是控制违规行为的社会影响,三是保证市场的公开公正环境[5]。对于航运联营体的事中监管贯穿于整个航运联营体的经营活动,对其进行事中监管可以弥补事前监管的漏洞,防止部分航运公司利用航运联营体从事违规行为,降低违规行为的危害性,同时,强化对航运联营体的事中监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断已出现的违法行为,降低事后监管的难度,优化了整个监管环节,促进航运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3 我国航运联营体事中监管不足的原因
我国对于航运联营体的事中监管措施不足的原因,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3.1 对事中监管重要性认识不足
我国对于航运联营体的监管主要集中在事前准入监管和事后反垄断监管,而学术界对于航运联营体监管的研究也多集中于事后监管,而很少聚焦于事中监管。这源于对于事中监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无论是从监管成本上,还是从对整个航运联营体监管体系的完整性上来看,事中监管措施都是其营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然而当前由于认识偏差导致对航运联营体事中监管无法得到重视、监管方式单一,而监管方式的单一性也无法满足事中监管的动态性特点,这就使得事中监管始终缺位。
3.2 监管机构不明晰
我国目前对航运联营体进行监管的机构并不十分明晰,交通运输部既要负责对航运联营体事前监管的工作,即航运协议的报备管理工作,又要负责事后监管工作,即事后的调查和处罚工作,而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具有竞争监管的职能,在事后监管方面,二者存在着交叉,分工并不明晰。然而,在当前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成立独立的航运监管机构存在困难,诸多行业都成立相应的市场监管机构也不现实[6]。那么当前究竟如何对航运联营体进行监管,监管机构不明晰,事中监管必然存在一定的难度。
3.3 事中监管资源匮乏
我国对于航运联营体的监管主要以政府监管为主,缺乏行业自律监督和企业自身监督,加之航运新业态的出现,以航运区块链为例,必然需要相应的监管措施。此外,在政府“放管服”背景下,监管更多地倾向于事中、事后监管,事中、事后监管需要更多监管资源,而事前监管的资源并不能在短期内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资源,这将导致航运联营体事中监管资源匮乏问题进一步凸显。
4 强化对我国航运联营体事中监管的建议
4.1 多渠道强化对我国航运联营体的事中监管
加强对航运联营体的事中监管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作用,利用多种监管渠道,强化事中监管。
对于航运联营体的政府监管,首先要明确监管机构,可以在交通运输部下专门设立航运联营体的监管机构,负责对其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此外,政府监管机构要构建良好监管秩序,利于航运联营体的健康发展。
同时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对航运联营体的监管作用,对航运联营体的监管,要从发挥航运公司、港口以及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最终形成新的监管模式。
4.2 建立对我国航运联营体常规系列检查抽查制度
在对航运联营体具体的事中监管制度方面,可以参考美国的分类报告制度,让各个航运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主动报告其经营情况,以减少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同时,明确对航运联营体经营过程中的抽查相关办法,明确抽查的航运联营体营运的类别和比例、抽查内容以及抽查方式和程序。同时,组织定期抽查和不定期抽查,抽查后要及时公布抽查结果,在事中监管过程中若出现违规行为,及时督导航运联营体进行整改和重新报告。
4.3 对我国航运联营体新业态进行有效及时监管
航运新业态的出现需要新的监管方式的融入,在对航运联营体进行事中监管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大数据的先进理念,探索利用区块链等相关技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有利于监管机关及时获取和运用信息,强化对航运联营体新业态的及时有效的事中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