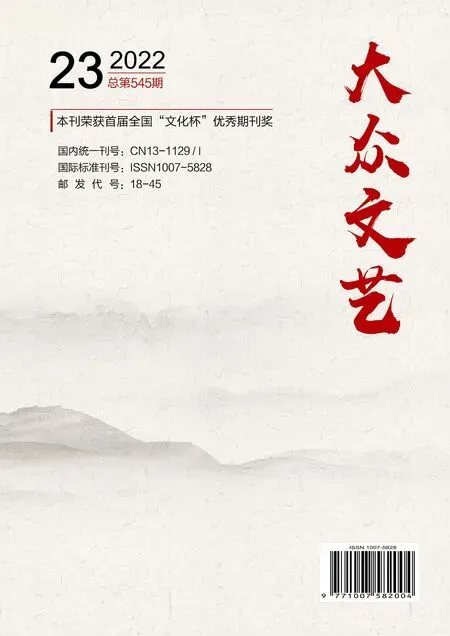心理创伤“自愈”的叙事复原力
——《海边》的生命叙事学
周江义
(广州华立学院,广东广州 511300)
一、引言
1.心理创伤
“创伤”(trauma)是一个医学专业名词,同时也是一个文学专业名词,它主要指不幸事件带来的身体上的伤害或心理上的障碍。现代心理创伤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80年,因为精神病学和医学的专著中首次出现了“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即“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美国精神病协会首次确认了精神障碍完全是被环境决定的,并且成年时期发生的创伤事件能够导致持续性的心理影响[1]。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它是一种“奇怪的情绪”[2]。我国东汉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怪神》中讲述了这么一则故事:
予之祖郴为汲令,以夏至日请主簿杜宣,赐酒。时北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中,其形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损饮食,大用羸露,攻治万端不为愈。后郴因事之至宣家窥视,问其变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还听事,思惟良久,顾见悬弩,必是也。则使门下支将铃下侍徐扶辇载宣,于故处设酒,杯中故复有蛇,因谓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怿,由是瘳平。[3]
此段引文是中国成语故事“杯弓蛇影”的最早典故出处,给后人的启示是:如果人心里疑神疑鬼,“奇怪情绪”会导致人生病,所以我们要心胸坦荡,不要疑神疑鬼,才会健康,身体的疾病往往是从心理疾病开始。笔者认为患者心理状态积极的变化,表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复原力”。孙思邈所言“善医者必先医其心,后医其身,在医其病”。正所谓“药所不及者,宜以心治心”[4]。
2.叙事复原力
本文提出的叙事复原力主要与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医学观和哲学观相关,康吉莱姆关于生命的定义,“生命,无论采用任何形式,都需要通过自我调节来实现自我保护。”[5]如何让患者产生类如杜宣那样的“复原力”?应彬的做法,非借助于针药,应彬把自己变为了一个“积极的倾听者”[6]。“为医当以大仁大德之心详辨万物,方能穷极医理,人归正流。而人之疾病始于利欲、背行天理,用药治之非能根除。[4]”应彬以大仁大德之心详辨万物,开导杜宣,解除其“背行天理”的疑怪。正如哈弗医学院教授阿图尔·葛文德(Atul Gawande)在其著作《最好的告别》中体现的理念“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7]”阿图尔的理念体现了当今社会亟需的医学人文主义之风。文学与医学的交叉领域,恰恰是对人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的关怀。泰纳在《艺术哲学》第五编当中提出,“绝对正确的模仿并非艺术的目的,要适当的加以改变,要注入理想。自然不够完美的地方,要艺术加以来补充。”[8]人文、艺术、哲学等归属于社会科学的内容,医学在现代学术分类的视野下,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医学在本性上是关于生命的内容,生命与社会息息相关,所以医学更蕴含着社会科学的内容。例如,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作出了最好的范例,其内容不仅限于医学,而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地理密切相关。
文学家关注社会的方式与医学家不同,文学家通过创作,激发新的思考,尤其关照日常司空见惯的事情,赋予其另类的经验,正如黑格尔在其1817年出版的《小逻辑》中所体现的思想之一,“熟知并非真知”[9]。在探讨“真知”的道路上,文学家总能平静地讲述,独具匠心地呈现出读者可以反复回味和阐释的“新意义”,医学如果注入人文理想和人文关怀,那将是万千“含血之命”的福音。
3.本文创新性
文学研究的方法众多,比如档案研究法、图识研究法、自传体研究法、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法等。本文创新地采用了跨学科研究的视野,通过心理创伤到自我愈合的轨迹阐释,融合文学作品中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
二、生命叙事学
1.叙事、故事、书写
生命叙事学离不开对叙事(narrative)的探讨。首先,杰拉德·普林斯把叙事定义为“代表至少两件真实或虚构的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并且彼此都不是充分必要的关系。[10]”布莱恩·理查德森则把它定义为“叙事是一系列有因果关系事件的反映。[11]”生命叙事学反映人生故事,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是我们可能会由于交际情景而产生另外的生命叙事(文本),所以生命叙事不同于自传、小说和历史故事。生命叙事文本为个体的人生故事提供了实证性的参考资料。斯科尔斯和费伦等人在《叙事的本质》开篇就提到:“叙事有两个必不可少的特征,出现了故事和讲故事的人。书写(writing)要成为叙事,需要的就是一位讲故事的人和一个故事。”[12]
2.叙事治疗
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是一种心理学治疗方法,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星期六》的主人公,神经外科医生亨利·佩罗恩感叹“当我们去注意那些大的事情,政治局势,全球变暖,世界贫困,这一切显得那么糟糕,一切毫无转机、一切毫无盼头。但是,当我们关注小事(think small),关注自己刚刚认识的女孩,关注喜爱的流行歌手Chas的歌曲,或者下个月的滑雪,那么一切又是那么的美好。所以,这将会是我的座右铭,关注小事(think small)。”[13]在当今处处充满宏大叙事的社会,我们需要关注小事(think small),内视自身而使自己的内心充盈,从而达到身体与心理的健康。梭罗在其《瓦尔登湖》写道:“我去森林是因为我希望从容地生活,只去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不能学会生活不得不教我的东西,我不希望到临死才发现我没有生活过……”[14]“我去森林”,正是在阅读内心,反照自己,让内心去除和自己无关的事务,只去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即生活的本质,我觉得自己“生活”过了这一生。
三、《海边》(By the Sea)
生于1948年,出生于坦桑尼亚的英国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荣获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海边》是古尔纳的第六部小说,他讲述了一个后殖民时代的离散故事。年过六旬的落魄商人萨利赫.奥马尔为避免自己继续遭到世仇迫害,于是从东非的桑给巴尔流落到英国,因缘巧合,在他乡遇到仇家的儿子拉蒂夫,然后小说从两个人的历史视角,回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最终两人冰释前嫌,相互和解,也跟自己和解。小说的特色是采用了“碎片”化的回忆叙事,在历史叙述中,进行人物的塑造;同时,古尔纳与传统经典互文,比如阿拉伯经典故事《一千零一夜》,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书记员巴托比》,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因而形成了众多隐喻,所以小说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流亡者的代表奥马尔的“自愈”,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通过历史叙述对话实现的叙事复原力,笔者主要从文学与文化批评的理论、生命叙事学的视野以及心理创伤理论来进行阐释,以期丰富《海边》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
1.“后殖民主义”和“后现实主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出现在当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下,随着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及随之“伯明翰学派”的诞生,文化研究也正式出现。后殖民主义以“现代性”为基础,质疑和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批判一系列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和其所带来的后果和伤害。“后现实主义”重点关注和探讨的主题主要是“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命、情感、家庭、爱、勇气、承诺、疫情、生态、暴力、乌托邦、未来想象等。”[15]
后殖民主义揭示了全球视野文化下的话语和权力的较量。《海边》主人公奥马尔见到他在东德的笔友伊莱克,作为东道主的伊莱克认为“我们是欧洲人。我们能去世界上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你是问为什么你们要去拿走属于其他人的东西,然后称作是自己的,通过欺骗和武力,获得繁荣吗?……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似乎我们有权利那样去做,有权利到那些满是黑皮肤、鬈曲头发人种占据的地方。这正是殖民主义的含义。”[16]
2.心理创伤—历史与现实的反照
“文学创伤理论之母”凯西·卡鲁斯认为:“心理创伤是‘历史经历的危机’,如果‘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症状的话,与其说是一种无意识的症状,倒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症状。我们可以认为,受到心理创伤的人,他们体内携带着一段不可能的历史,或者他们成为了自己无法完全‘入主的’历史的症状。”[17]《海边》的叙事围绕着奥马尔的家族历史命运,不仅记录了东非桑巴尔这个海边故土的政局交替、经济发展、宗教和社会的变迁,更刻画了后殖民帝国统治之下,主人公命运的遭遇。按照时间顺序,故事的开端是1960年,这一年开启了非洲众多国家相继取得独立,社会动荡及流血屠杀事件接连不断的历史,而非洲的宗主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在二战结束后,处于经济和社会恢复的时期,随着美苏对峙的加剧,世界格局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一边是经济的恢复繁荣,一边是人们对未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古尔纳从文学家的视角,关切流亡身份的人生状态,也含沙射影地关注分布在欧洲的犹太人的命运,让读者通过奥马尔和拉蒂夫的对话,回到漫长的历史事件中,利用文本的情动功能,使读者由此及彼,也许能在历史的创伤中,受苦受难之人能实现内心的自我疗愈,正如小说的结尾,“哪怕厄运急转直下,但我有阿方索的毛巾。”[16]这里,古尔纳隐喻阿方索,笔者猜测指的是西班牙历史上的国王阿方索十三(1886-1931),因其竭尽全力地保护犹太人而闻名于世。
3.身份复原力-寻找新的人生意义
身份和认同是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在海边》的开篇讲述了沦为难民移民的奥马尔和在伦敦大学做教授的拉蒂夫时隔35年后,因为前者装作不会英语,所以英国移民局指定移民律师为他寻找翻译,于是找到了拉蒂夫。拉蒂夫惊奇地发现对方竟然和他父亲的名字一模一样。这里的身份话题,首先从名字这一符号上发生了重叠,好奇的读者会疑问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发生?随着情节的深入,读者发现奥马尔的人生在欧洲帝国主义统治的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共和国,充满了荆棘,商业破产、房产被占、亲人的离世、遭到报复,被遣送监狱,护照被没收,出狱后在故土等待他的仍然是未知的危险……最后,奥马尔才发现他的救命稻草是拉蒂夫父亲的这一个名字。对于生活在欧洲世界的移民官来说,一个名字似乎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但是对于六十多岁的奥马尔来说,流亡来到曾经的殖民宗主国,英国,那是他的余生。正如1939年萨特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本质“能动性”评论的那样,“我们不是在某些隐秘的地方才发现我们自己,而是在路上、在城镇上、在茫茫人海中、在万物之物中、在万人之人中。”[18]《在海边》故事的结尾,古尔纳从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口吻,诙谐地讽刺“尽管在英格兰的岁月,我从来没有尝过外卖的味道,所以我希望这会是他的选择。通过这种逼迫的方式,我能够偷摸地尝试这著名的炸鱼的味道。”[16]
结语
古尔纳的第六部小说《在海边》是一部以伊斯兰国家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后现实主义”小说,作者通过“碎片化”的回忆叙事,通过奥马尔同拉蒂夫的对话,表达了对流亡者身份命运的关注,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和犹太人心理创伤的慰问,展现出了文本的叙事复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