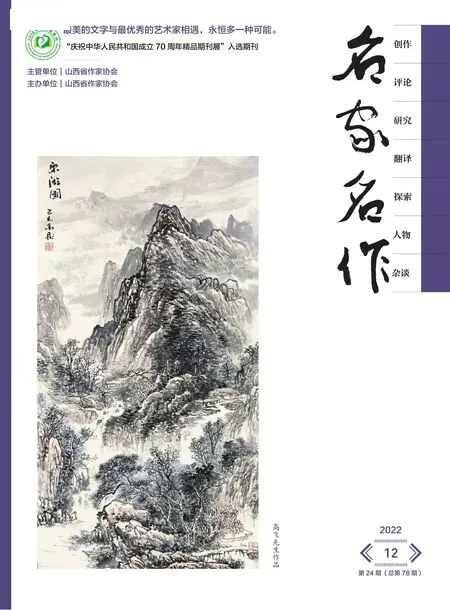《等待野蛮人》中的道家思想和生态女性主义
徐子烨
曲捷认为库切的作品《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具有“无意识的道家循环论思想”[1],然而库切的道家思想并不是无迹可寻。首先,库切的作品中有诸多中国元素,譬如《耻》中“It reminds me too much of Mao’s China”,《等待野蛮人》中 climb the bronze gateway to the Summer Palace,而且他本人也曾有到中国生活的想法。其次,库切受道家思想推崇者和借鉴者马丁·海德格尔生态哲学思想的影响,得出此结论的渊源在于库切曾在《纽约时报》书评副刊(2001年7月5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保罗·策兰诗歌及其翻译的文章《在丧失之中》(In the Midst of Losses),文中多次提到海德格尔,“在法国,策兰被解读为一个海德格尔式的诗人”“他已从与里尔克和海德格尔的亲缘关系中成熟长大”,从这些语句中我们不难推测出,库切在研究策兰诗歌翻译的同时,也深受海德格尔思想影响。海德格尔作为道家思想的推崇者,其诸多思想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如“天地人神合一”与道家“天人合一”,并且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老子的名言,学者曾繁仁曾指出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与存在关系的探讨,显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在的生态整体观,为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2]老子的“道生万物”同样也是一种整体生态观,而库切作品也蕴含着整体生态观,可见,海德格尔思想中蕴含的道家思想也同样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库切的创作。因此,从道家思想来探索库切的生态思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库切的特殊成长历程让他深刻体会到人类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父权制造成的文化冲突以及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和摧残,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批判父权制社会,倡导男女平等,关爱弱势群体,鼓励女性精神觉醒,反抗殖民主义和父权制思想的压迫。
二元论展现了等级排斥、疏远与敌对的特征——人有高低之分,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将各类群体的特点强行分割,这些都受到生态女性主义的极力反对。无独有偶,中国道家思想同样否定二元对立。道家的阴阳学说强调阴阳不是二元对立,它们不是否定的逻辑,而是互补的逻辑。在东方,阴代表女性,阳代表男性,也可以理解为两性的和谐共处,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不谋而合。此外,道家第一原则:“道法自然”也强调顺应自然,不要过于刻意,反映了人与自然复杂而紧密的联系。从二者结合的角度探究作品中的女性与自然在二元对立社会中的处境,解读作者希望解放女性与自然,发展女性自我意识,追求建立一个万物和谐相处的乌托邦。
生态女性主义反对破坏自然平衡、污染环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各类有机体和无机体的和谐发展。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强调尊重维护自然和谐,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 “道生万物”,蕴含着一种整体的宇宙生态观。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是一种融合关系,女性形象长期与自然融为和谐整体。而且女性在长期的社会分工中,从事的工作多接触自然,并与自然互动,积累了许多经验。美国生态学者罗尔斯顿指出:“人性深深地扎根于自然。”[3]说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一种共赢的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害。
殖民主义想要征服的不仅有被殖民者,还有自然。在《等待野蛮人》中,行政长官送土著女孩回到部落,出发前,早春的水禽、振翅盘旋的鸟儿、万物复苏的土地、冰冻融化的湖面、早春的暖风、可以大饱口福的猎物。出发后,光秃秃的田野、沙尘扬起的红色云雾、凛冽的寒风、发臭的绿色污泥、变咸的湖水、寸草不生的盐碱土质湖底。土著人恶劣的生活环境,与城邦内居民的舒适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土著人受到殖民者的压迫,被迫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区域,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土著女孩喝咸水后没有任何不适,而行政长官和另外三个随行人员却上吐下泻,长期生活在被殖民者破坏的环境下的女性,被迫融入且适应恶劣的自然条件,而被人类破坏的环境也在惩罚人类,使人类自食其果。军队进入野蛮人区域后,在打击土著部落的同时,也毁坏了自然环境,土著部落没有与其正面冲突,而是将其带到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带,导致军队自己溃败,表明人类受到自然的惩罚,表达作者对人类破坏自然的批判,对恢复生态环境的渴望。此外,行政长官从设陷阱抓狐狸的猎人那里买了一只银色的小狐狸崽儿,黑人女性认为动物都应该在屋子外面,男性反问是否是让他把狐狸放归野外,她又说狐狸太小,会被小狗叼走,由此可见,她心中既有对动物回归大自然的生态和谐观念,又有珍惜爱护动物的女性保护主义观,尊重物种差异,希望万物能够和谐相处的整体生态观。
“中国古代道家思想为生态女性主义对二元论的批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生态女性主义与中国道家思想在寻求非二元论与和谐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4]道家思想主张“阴阳和谐”,《太平经》记载:“阴阳者要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可见,阴阳和谐,人类社会才能和谐发展。“社会发展现象、自然形成、发展和死亡现象、人体自身的运动变化都受到阴阳平衡的限制和制约”[5],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看,“阴阳和谐”就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呼吁的两性平等、两性和谐,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美国非裔女性作家艾丽斯·沃克在一次采访中说,“为了让地球得以继续存在,我们得承认人与自然是一家人,是同一个大家庭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地球的组成部分之一,男性主导的社会是不平等的,女性受到的阶级压迫也是不平等的,应当尽全力反对父权制,追求男女平等,消除二元对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待野蛮人》是一部寓言式小说,小说没有明确的国家背景,整体是一幅殖民者压迫剥削被殖民者的画卷,适用于任何一个遭受殖民苦难的国家。行政长官在与新来的年轻军官的对话中说道,那些他们称为野蛮人的人们不过是一些游牧部落,为了生存,每年不断地在高地和低地之间迁徙,然而年轻的长官却认为野蛮人是想阻止帝国在他们土地上的殖民扩张,最终目的是想要回自己的土地。这充分显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扩张,在殖民者的世界里,并不把野蛮人平等对待,充斥着单一主义思想,不认为他们同自己享有同样的权利。土著女孩其实一开始就明白这位白人男性就是一名糟糕的引诱者,然而她没有拒绝和反抗,而是任由行政长官摆布,屈服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从而沦为被“超级剥削”群体中的一位。行政长官试图回忆起土著女孩被捕的样子,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表现出在社会中,女性长期处于弱势和被压迫、被忽视的失语状态。土著女孩因为月经期间在野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她遮挡,行政长官因喝咸茶上吐下泻,在解决生理问题时也同样没有任何掩饰自己的东西,男女平等,阴阳相合,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东西是平等的,在同样的环境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得不承受因自然遭到破坏而陷入窘迫境地的后果。此外,行政长官因为与月经期的土著女孩住在一起,而被认为受了污染,而被要求和女孩进行洁净礼仪。“我要歌颂大地、万物之母、坚实的根基、最年长的生物。她养育一切在神圣的土地上行走、在海里漂游、在天上飞翔的创造物。”[6]女性和大地一样遵循生物圈的规律孕育生命,而男性却把女性周期性的生理现象视为不祥之事,男性不尊重女性孕育生命、抚养生命的无私奉献。当然,黑人女性并不是帝国主义和父权制文化的唯一受害者,帝国内的白人女性同样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压迫、剥削和迫害,在士兵们抡起警棍殴打被他们带回来的野蛮人时,周围围满了人群,其中“一个女孩被她的朋友推上前来,咯咯地笑着,捂着自己的脸……她站在那儿直发愣”,可见她自身是没有意识去做这件事情的,然而朋友的一推、围观人群的鼓动(叫嚷声、玩笑声、暧昧的教唆声等)、士兵给的警棍,这一切的外界因素使她茫然,她无法思考,失去自我,选择服从、顺从,从而举起警棍,猛地砸向囚犯。人群中还有“一个小姑娘,紧紧牵着母亲的衣角。她的眼睛圆睁着,大拇指含在嘴里一声不吭,看着那些全是赤裸的人挨打又害怕又好奇”。这些描写足以看出小女孩的单纯稚嫩,她甚至不知道这些人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些囚犯被殴打的时候周围的人在微笑,帝国无情、残暴、剥削的种子在她心中还没有生根发芽,但是眼前发生的一切却像梅雨季节的雨水一样不断地浇灌着这颗纯净的心灵,让其发霉、污染、腐烂,受其所害,这个单纯的女孩最终将成为帝国的附庸者、帝国主义的沦丧者。还有她周围人的表情“没有仇恨,也没有杀戮欲望,只有好奇之极的神情,像是全身只有眼睛还活动着在那里享受着新奇难得的视觉大餐”。他们是没有思想的躯壳,看着那些受到剥削和压迫的野蛮人,他们没有思辨,最终在帝国的统治下,帝国内的女性受到男性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的双重压迫和残害,成长为新的殖民者。
人与人的精神和谐属于整体生态观包含的一种生态和谐关系,道家也有关于精神平衡的观点。如老子《道德经》中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意思是天下万物都背着阴而抱着阳,阴阳相交可以相合,也就是强调万物保持阴阳平衡才能存在。人受天地之气而来,在世间生存需要保持和谐状态,最重要的是自我身心的和谐。庄子认为人心本然是和谐的,他在《人间世》写道“形莫若就,心莫若和”,意指以虚无之心、平和之境应接事务。然而自然界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女性受到男权的压迫,内心的和谐思想受到压迫,需要摆脱男权思想牢笼的束缚,平衡女性自我精神主体的健康。长期受困于父权制文化的女性,在精神世界里迷失自我,男性缺乏对女性精神世界的关爱,生态女性主义则希望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整体精神生态系统,女性需要反抗男性霸权,寻找精神自我。“全面发展的女性需要由全面发展中的男性来塑造,全面发展的男性也需由全面发展中的女性来塑造”。[7]由此可以发现,男性与女性和谐相处和全面健康发展是彼此依靠、相互依存的关系,而精神生态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女性的精神觉醒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从根源上彻底改变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父权制。
男性缺少对女性精神世界的关心和爱护,精神世界的不平衡必然产生矛盾,库切反对这一父权制社会的诟病,他笔下的女性具有争取自我的反抗精神。《等待野蛮人》中行政长官在不了解土著女孩的情况下,对其身体进行触摸,“她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你想在她的身体上得到什么……她会哭了又哭”,行政长官只是在利用自己的男权伤害处于边缘地位女性的身体,不关心其内在心灵感受。“你难道不想再做些别的什么事吗?”这是女主人公第一次主动提出与性相关的话题,处于二元对立弱势一方的女性只是男性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不能反抗,只能被动接受。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土著女孩只是被动地接受男性的抚摸,而且她甚至觉得白人男性与其他女性发生关系是对她的侮辱。如果说前面的问题是她身体的觉醒,那么后者是她在意识上、精神上的第一次觉醒,尽管白人男性有时候觉得她还像从前一样是一名囚犯,然而在土著女孩心里,两性关系应该是平等的,挑战了男权中心主义。“我非常明确地想要求你跟我一起回到镇上去——这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想要的。”行政长官与土著女孩告别仍然在行使自己的男权,看似给了女性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是却仅仅握住女性的胳臂,他不考虑女性自己的想法,只是想用身体的暗示让女性屈服于自己。“不,我不想回到那个地方”,女孩离开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她选择反抗男权和殖民压迫,尊重自己的内心,她不愿意再过不受男性尊重和被殖民者压迫的生活,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受父权制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文化上、道德上和经济上得到回报,相反,女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的”。[8]由于文化的不断传承,大多数女性不仅在身体上,甚至在思想上都接受了这一观念,并受到男性的支配。库切从这一角度出发,令其作品中的女性具备一种对自身性别角色的反思意识,并渐渐觉醒。生态女性主义和道家思想都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更深的层面上,关注万物精神世界的和谐。从两者相通的角度分析库切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其作品中包含了对自然生态平衡、男女平等、阶级对抗以及女性精神觉醒的思考,自然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由破坏自然而自食其果的帝国军队可知,人与自然是一个生态整体,需要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库切追求两性和谐相处,以其独特的男性作家视角,解构行政长官和土著女孩的关系,强调阴阳相合。女性在长期受父权制文化的压迫下,造成了更深层次的精神生态危机,土著女孩的自我精神觉醒是对殖民主义的成功反抗,表达了库切反对殖民主义,期望建立一个生命相互依存、多元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