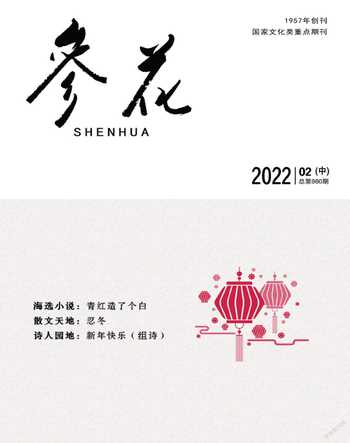试从影视艺术角度探析《福贵》的改编艺术
2005年,根据《活着》改编的电视剧《福贵》上映,引发巨大反响,本文试从影视艺术的角度探析《福贵》的改编艺术。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优质的小说文本作为文化IP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已十分常见,如近些年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庆余年》等。而在传统、严肃文学领域,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小说《活着》与据原著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福贵》在各自领域及受众群体中,都引起强烈的反响,并获得成功。简单而言,长篇小说《活着》为电视连续剧《福贵》提供了优秀的文本和素材,电视连续剧《福贵》也为长篇小说《活着》提供了多种宣传渠道,使《活着》这一文化IP更加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小說和影视剧分属不同的艺术类别,传播媒介及原作者和影视编剧、导演在自身的审美价值观、人生阅历等方面的差异性,使影视改编作品的最终呈现效果与原著小说文本之间会存在部分差异,这通常是由于改编造成的。综合来看,小说与影视剧有各自的局限性,也有各自的倾向性,但最终都在创造优质的文艺作品。
一、原著小说《活着》的艺术手法
长篇小说《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品,其笔触逐渐转入温情化。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92年的《收获》杂志,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外引发巨大反响。小说《活着》延续余华传统的表现手法,保留惯用的手段来展现故事。开篇采用倒叙手法,从第三人称视角出发,以与老人的相遇为起点,讲述主人公福贵40年来的风风雨雨,而身边的亲人朋友在这40年里一一离他远去。
小说里本是大少爷的福贵,被人设计,嗜赌成性,在赌场败光了自己的家产,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父母的离世。幸好还有温婉善良的妻子对他一直不离不弃,而后子女双全。本以为可以过上平淡美好的日子,可在十多年后,儿子、女儿、女婿、妻子、外孙却都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故,不幸离世。到了最后,只剩福贵和老牛一人一牛共度余生。
“……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1]
不得不说,福贵的一生是一部悲剧,在余华的笔下,这种人生的命运是与时代相结合产生的,也是个人性格所导致的一种必然。而这种认知,不可避免地为《活着》这部作品注入了悲观色彩,这种悲观是余华作品共有的特征,成为余华作品中极为明显的表现手法和基调。
二、影视剧《福贵》的改编特色
影视剧《富贵》虽然源于小说,但是与原作相比又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新作品。
2005年,由《活着》改编的33集电视连续剧《福贵》登上荧屏,该剧由朱正导演,谢丽虹编剧,在社会上引发了热烈反响。相较于小说而言,电视剧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而相对于另一种改编形式——电影来讲,电视剧时间更长,受众更广,可展现的内容也更为丰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更加深远。因此,电视连续剧《福贵》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小说进行了二次加工和改编。
下面,本文通过对比来探析《福贵》中的特点与表现手法。
(一)感情戏刻画更加细腻
在影视剧的改编过程中,为了增加看点,编剧往往会采用增加感情戏的做法吸引观众,《福贵》也不例外。
在原著中,由于作者余华的惯用手法是采用接近冷漠的口吻叙事,因此,对感情、故事人物的描写,在情感刻画中趋于理性,显得冷静而内敛。在《活着》中,福贵与妻子的婚姻描写,放在电视剧中却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因此,在《福贵》中,增加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交集,人物情感刻画更加细腻,使剧中人物形象更加鲜活,也更具看点。剧中开头,福贵前往陈记米行唱跳花鼓戏,陈记米行大小姐家珍放学归来,家珍被花鼓戏吸引,福贵也对家珍的美貌十分着迷,心生爱慕,为两人的婚姻打下了基础,后来福贵要求上学,在学堂求婚,与情敌斗智斗勇,到婚礼现场抢婚,这部剧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戏十分精彩。他们的爱情贯穿全剧,虽历经悲欢离合、沧海桑田,但始终不离不弃。
与描写主人公之间的爱情一样,原著对哑女凤霞情感生活的刻画也趋于平淡。因此,电视剧《福贵》在改编的过程中增加了胡老师、二喜、凤霞三人的感情纠葛。该剧编剧谢丽虹在刻画这一情节时,为了避免这一情节落入俗套,巧妙地安排了三人之间的情起情灭,从独特的视角去审视这一感情变化,带给观众更丰富、更独特的情感体验,描绘出普通人真挚美好的情感与现实之间的博弈与斗争,刻画了小人物在社会现实中卑微且无力抗拒的一面,也使这一影视剧沾上了一丝文学的意味。谢丽虹编剧将三人的情感纠葛植入在一个动荡且复杂的社会背景里,这样更容易打动人心,而文学的色彩也让整部电视剧的悲剧性更加凸显出来。
当然,如果只有爱情色彩,这部剧是无法成为经典的。剧中,人物之间的其他感情相较于原著而言,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刻画。福贵、家珍之间的不离不弃、情比金坚,他们与二喜、胡老师之间守望相助的真情,凤霞和有庆真挚朴实的手足情,有庆和胡老师之间传道授业的师生情,乡亲之间携手共济的友情,这些普罗大众之间的情感,虽朴实但真挚,最能触动人心,这些情感最终汇聚为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苦难的人们在生活中继续前行。
(二)人物形象塑造更加鲜活
人物形象是否深入人心,是影视剧改编中的一大要点,好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打造经典,例如王刚饰演的和珅,张国立饰演的纪晓岚。这一点在电视剧《福贵》的改编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现,对原著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了增补,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胡老师与懒汉二愣。
胡老师是一名体育老师,在《活着》中其实没有过多的笔墨描写他,在《福贵》中却增加了很多戏份,在剧中也很是抢眼。胡老师是有庆的贵人,他发现了有庆的运动天赋,成了有庆的老师,并将有庆带入体校。后来,他又与凤霞互生情愫,差一点成为福贵的女婿。如果用当下的视角审阅胡老师,那他一定是一个“老实人”,生性善良、懦弱、待人温和。在后续的剧情发展中,尽管胡老师安分守己,却依旧次次被推入浪潮。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生活非但没有打败他,反而塑造了其坚韧不拔的品格,也有了后来胡老师为民请命的情节。编剧对胡老师的这种安排,是符合剧中与原著的精神内核的,这种内核也是后期支撑福贵活下去的精神动力,这也许是编剧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一种精神。
相较于对胡老师的补充,懒汉二愣的形象则是《福贵》一剧中进行的最彻底的人物形象改编。
二愣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却染上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气,是典型的地痞流氓形象。然而,他却摇身一变,从一个令人不齿的地痞无赖成为令人畏惧的反派,倒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只不过两个人物的结局不同。二愣形象的变化也大大增加了福贵一家的悲剧色彩,无比牵动观众的心弦,也推动了整部电视剧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将剧中的矛盾冲突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辜的胡老师被抓走,间接造成了二喜的死亡。
其实,二愣的这种变化恰恰是悲剧的一种,他好逸恶劳的性格和品行,必然给他后续的发展带来困扰,带来灾难,同时,这也给故事带来了戏剧性,刻画出一个经典的地痞流氓形象。因此,笔者认为,二愣是《福贵》改编过程中,塑造得最成功、最深刻的一个人物形象,其也成为电视剧《福贵》中的一大亮点。透过二愣,了解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本质的弱点。
(三)融入民间传统艺术形式
从《福贵》一剧的影视手法中,不难看出,剧作者相较于原著而言,加入了一些民间传统艺术,或者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安徽省的花鼓戏。
剧中福贵与家珍缘起花鼓戏,同时,花鼓戏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部剧的可看性和娱乐性,给福贵的内心带来一丝慰藉,冲散了这部戏的悲剧色彩。为此,电视剧《福贵》的编剧将故事的发生地定位为安徽省。如此一来,花鼓戏这种源于安徽民间的传统艺术便不再那么突兀。
與此同时,编剧还巧妙地将花鼓戏与时代相结合,让其成为时代变迁的见证者,例如,剧中福贵前往农场看望岳父,告诉他凤霞正在学跳花鼓戏,岳父心里一阵紧张,因为在过去,跳花鼓戏是灾荒之年外出讨饭的手段,老人在为自己的外孙女担心。福贵赶紧向岳父解释,现在都能吃饱饭,跳花鼓戏已经成为庆祝丰收的一种演绎形式,这也使花鼓戏这一安徽民间传统艺术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除此之外,花鼓戏还成为贯穿整部剧中男女主人公一生的线索,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正是因为福贵前去顶替顶班跳花鼓戏,才和家珍相遇,二人逐渐互生情愫。土地改革后,福贵分得了五亩好地,兴高采烈地和家珍一起在田间跳起了花鼓舞。在家珍最后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光里,福贵也是在强忍悲伤地跳花鼓戏将家珍送走的。在哑女凤霞爱情失意的时候,她也将注意力转移到花鼓戏上,儿子有庆不幸逝世之后,福贵来到有庆的坟前,在田间跳起了花鼓戏。其实可以理解为,跳花鼓戏是福贵与凤霞的一种情感寄托,是他们宣泄内心情感的一种途径,借此来排解心情,这一行为充斥着内心的沧桑与无奈。
三、《福贵》对影视剧改编的启示
(一)做好观众贴心人
与诗歌、散文、小说等相比,以电影、电视剧为代表的大众艺术,是讲究效益的。
基于以上观点,影视剧的改编应该慎重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切忌过于追求阳春白雪,从而影响观众,这一点,《福贵》一剧就做得很好。
相比小说,观众往往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观看和了解福贵冗长的一生,不然难免会产生枯燥乏味的感觉,这就很考验编剧的素养,能否做到合理转化。
同时,在改编中也要慎重考虑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原著中,福贵的结局是带着浓郁悲情色彩的,只剩他一人去面对这悠长的一生。而在电视剧中,结局却带上了一抹温情色彩,有一头老牛陪伴着福贵,不至于自己孤零零地走向生命的终点,这一叙事考虑到了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满足了观众对于苦尽甘来的团圆结局的一种期盼,尽可能地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核,这种对观众心理的揣摩,值得其他影视剧学习。
(二)不断打磨作品质量
文字化与图像化是传媒的两个趋势,影视剧改编则是将文字化的优质内容图像化,因此,需要不断打磨作品质量。
众所周知,文字是小说文本的呈现方式,但文字往往又是抽象的,无法给人直观的感受。因此,影视剧往往需要考虑观众充分的想象力与自身阅历的影响,从而复刻出小说文本所叙述的世界。原著《活着》所叙述的世界处于几十年前,许多读者是没有这个阅历的,许多文本中呈现的场景可以调动想象力去理解,正因如此,小说文本可以通过文字表达更深场景或层次的深意。
而影视剧就大不一样,它能够经过镜头语言和声音的处理带给观众一种宏大的视听盛宴。观众可以从这种营造出的图像中直接获得想要表达的内容,它是更加具体可见的,无须进行复杂的理解,因此,受众更加广泛。
通过影视剧中呈现的语言、神态、动作以及画外音、背景音乐等元素,观众往往可以轻易了解影视剧想要表达的含义,但这种营造出来的场景往往是浮于表面的,较多观众也抱着消遣的心态去观看,因此,容易忽略作品文本所表达出来的深层次含义。
四、结语
在将文本化转变为图像化的过程中,编剧需要进行不断的取舍,由于容量、时长、技术等问题,部分原著文本所呈现的精彩之处,并没有办法在影视剧中进行复刻,只好进行省略。因此,剧作者在改编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地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差距,合理化地做好取舍,做好对原著内核的保留,这样才能做好文本的图像化,才能打造出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陈越擎,女,硕士研究生,吉林动画学院,研究方向:影视艺术)
(责任编辑 于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