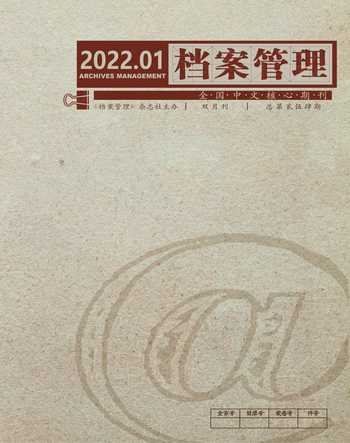境外部分国家档案利用救济法条对比分析及其启示
李宗富 张倩
摘 要:新修订《档案法》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档案利用权利救济途径,但有關档案利用权利救济制度如何尽快完善并有效实施等仍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笔者对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日本、法国、美国等国家档案法律中有关档案利用救济的条款进行梳理总结并对比分析,提出了需尽快制定档案利用救济相关制度,完善档案利用权利保障体系、设计具体可行的档案救济程序,规范档案救济行为准则、加强与其他法律的衔接,协调救济权利适用性及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监督机制,规范自由裁量权等建议和措施,以期为我国档案利用救济制度的建设及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档案法;档案利用;档案利用权利;权利救济
Abstract: In the newly revised 'Archives Law', the remedy way of Archives utilization right is put forward clearly for the first time, but how to perfect the remedy system of Archives utilization righ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mplement it effectively still needs furthe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e author summarizes and compares the provisions of Archives utilization relief in the Archives laws of Australia, New Zealand, Denmark, Japan,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formulation of Archives utilization relief related systems, improve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Archives utilization right, and design specific and feasible Archives utilization relief procedures. Som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such as standardizing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archival use relief,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with other laws, coordina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right of relief, establishing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involving multiple subjects, and standardizing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archival use relief system in China.
Keywords: Archives law; Archives utilization; Rights of archives utilization; Right relief
新《档案法》第二十八条首次提出“投诉”这一档案利用救济途径,尽管投诉渠道单一,却为我国档案利用救济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法律支撑,具体的制度措施也需要通过实施条例和一系列配套的法规规章加以细化。[1]有关我国档案利用权利救济制度的研究,早在2006年,宋明等[2]就在分析我国香港档案开放救济制度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内地可通过设立信息委员会、确立行政复议前置规则等来完善档案开放救济制度;2012年黄夏基等[3]从公民档案利用权利视角出发,提出了《档案法》修订需重视公民权利具体化的要求;2021年连志英等[4]在梳理我国档案利用救济制度的历程上说明了档案利用救济制度设计依据及制度构成。
然而目前我国档案利用救济制度研究依旧过少,且时间跨度大、视角较为单一,加之新《档案法》内容变化很大,很多条款需要重新尽快科学阐释完善。因此,本文根据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出版的《境外国家和地区档案法律法规选编》一书,对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日本、法国和美国六个国家档案法律中规定的档案利用救济法条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档案利用救济制度的完善及有效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境外六国档案利用救济法条梳理
1.1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1983年档案馆法》共9章71条法规,其中有18条规定了档案利用救济各方面内容。第40条决定的告知共计12款条文,主要规定了公众向国家档案馆申请利用或申请延伸利用公开档案的内容,包括申请人的申请需求、国家档案馆的职责、法庭的职责等。[5]
第42条对决定的复核规定当申请人依据第40条提出申请且对申请决定不满意时,他须在收到决定通知的28日内或在国家档案馆许可的时间范围内,以书面形式向国家档案馆提出对决定进行复议的申请。国家档案馆必须复议该决定,并安排必要的复核,将复议的决定通知申请人。[6]
第43条向行政上诉法庭的申请中,申请人可就国家档案馆对利用档案所作的决定或是复核后的决定再次向行政上诉法院提出申请。(如,拒绝申请人的扩展利用、档案扣留而暂停利用及档案处于待查而暂停利用等情况。)法庭的解决方案在申请期限、重新审议、法庭判决等环节均有详细的处置规定。[7]
第44条还赋予法庭一定的权利,在44条第(2)、第(3)、第(7)小款情况下法庭有权依规定复核或裁定国家档案馆就申请利用档案所作的决定,其作出的决定与国家档案馆作出的决定有同等效力。
第46条和第48条规定了豁免档案的诉讼组成法庭范围和《1975年行政上诉法庭法》第42条在适用本法程序时应当依据本法作出的专门修改办法。
1.2 新西兰。新西兰《2005年公共档案法》共计4章67条,其中第30条免除、第4章申诉程序部分条款均涉及档案利用救济,内容包括申请主体及起因、申诉程序、部长(现任负责本法行政管理的内阁大臣)权利及档案咨询委员会的作用等。同澳大利亚法条不同,该法中的申请主体为公共机构和地方政府,而部长的决定权至关重要。
第30条规定了档案馆馆长与申请主体的相关权利。对于公共机构或地方政府提出的免除遵守档案馆馆长所发布的标准或指示的请求,档案馆馆长可在其认为适当的条款和前提(如果有)下,对该类请求进行豁免;对于依据前款所作出的裁决,公共机构或地方政府行政主管可以依照第51条对该裁决进行上诉。[8]
第51条规定了公共机构或地方政府向部长申诉的相关内容,包括拒绝第22条公共档案延期移交的部分要求、反对档案馆馆长依据第30条免除作出的豁免决定的决定等,并依据第52条、第53条、第54~第56条提出申诉。[9]
第52条提起申诉中要求公共机构行政主管需依据第51条,在档案馆馆长作出決策向主管公共机构通报之日起的20个工作日内,向部长提出书面申诉。[10]申诉书必须包含:申诉的对象,即(档案馆馆长)决策的所有细节,以及申诉理由。
第53条规定了相关申诉效力。档案馆馆长作出具有申诉权的决策之时起至申诉期满或已提出申诉且至部长给出裁决并依据第56条发出通报期间内,档案馆馆长不得就申诉相关事宜发出指令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等,主管公共机构必须继续维护或遵从原状。[11]
第54条申诉程序中规定部长在收到申诉通知后,一旦确认合理可行,必须通知档案委员会和档案馆馆长已提出的申诉,且将主管公共机构收到的所有相关文件的副本提供给档案委员会和档案馆馆长。[12]
第55条阐明了档案委员会(非法人团体,由部长任命,为部长提供有关档案管理和档案事务及申诉工作等建议,合理行使自己的职能)在申述期间的作用。在收到依据第54条提出的申诉通知后,一旦确认合理可行,档案委员会必须对申诉及申诉的理由予以考虑,且向部长建议批准或驳回全部或部分申诉并说明建议的理由。[13]
第56条规定了部长决策的权利。在其作出批准或驳回全部或部分申请的裁决前,必须与提出申诉的主管公共机构的责任部长协商并考虑档案委员会的建议。此外,部长须向主管公共机构的行政主管、档案馆馆长、档案委员会给出书面裁决通知,并说明原因,在政府《公报》上向公众发布裁决公告。部长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并以此约束档案馆馆长和主管公共机构。[14]
1.3 丹麦。丹麦《档案馆法》共计12章56条内容,其中第7章限制利用档案、第8章公共档案的利用、第9章对《个人数据处理法》涉及资料的利用申请、第10章上诉以及第12章刑事规定与法律生效均有条款涉及档案利用救济方面内容,条款内容包括申请人的权利、档案馆及相关机构的职责、文化大臣的权利、档案委员会的功能作用、申请过程和相关处罚等。
第7章第30条规定了申请人的权利及要求,即任何人均可请求允许其使用公共档案中有利用限制的档案,但需申明其利用有关信息的目的。第31条规定了国家档案馆馆长职责。馆长或其授权人可以许可申请人在档案封闭期终止前或是在档案开放时限终止前利用已移交到国家档案馆的各类档案,规定的例外。第37条、第38条规定了其他相关机构的权责。[15]第39条共计4小款,分别阐述了档案委员会组成部分、工作任务及文化大臣对其领导职责。
对于申请利用限制档案,该法第8章第40条、第41条也规定了其利用条件。申请人如果被许可利用限制档案,其不得泄露他(们)从中获知的机密信息,此外,如果利用的档案属于法条规定的部分特殊行政机构档案或是档案信息本身具有特殊性质,档案利用者还须签署确认遵守特别条款的声明文件。[16]
第9章规定了对《个人数据处理法》涉及资料的利用申请,包括利用主体、利用程序及依据法规等。第10章上诉仅有一条两小款条文。第1小款规定对国家档案馆馆长依据上述第31条作出的档案利用决定,当事人可向相关的行政机构提出上诉。第2小款则规定了文化大臣的责任,其应当制定有关规则,以达到使其免于被起诉的效果。[17]第12章第51条第1小款规定任何人违反第40条或第41条设定的条件均处以罚款或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18]丹麦《档案馆法》虽然仅有两条条款涉及申诉,然而全法更加重视申请人在申请利用过程中的权利保障,还设立了处罚条款。
1.4 日本。日本《关于公文书等管理的法律》共计6章34条,其中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涉及档案利用救济部分内容。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针对其利用请求的处理有异议或对于针对其利用请求的不作为行为有异议者,可以根据《行政异议审查法》(1962年法律第160号)向国立公文书馆等的首长提出异议,接受异议提出的国立公文书馆等的首长应当向公文书管理委员会进行咨询。除外的情形:(1)异议的提出不合法,予以驳回的;(2)以决定的形式将针对异议涉及的利用请求的处理予以取消或变更,允许全部利用该异议所涉的特定历史公文书等的,但关于该异议所涉特定历史公文书等的利用存在反对意见书的除外。[19]
同时,第二十二条也提出《独立行政法人等信息公开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信息公开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设置法》(2003年法律第16号)第九条至第十六条的规定也适用于上条款中异议,但需要替换法律中部分信息,如《独立行政法人等信息公开法》第十九条中的“前条第二款”替换为《公文书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等。[20]
第五章第二十九条则规定了公文书管理委员会依本法规定处理其权限范围内事项。如在本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政令的制定或修改、废除之时,委员会需要为内阁总理大臣提供相关咨询。[21]
1.5 法国。法国《档案馆法》共计两编,第二编司法音像档案全部条款涉及档案利用救济。第222-3条规定对于第二编司法音像档案全部条文决定不服后的救济渠道,由经咨询最高行政法院后的法律作出规定,[22]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救济程序,但其给予了法国行政法庭完全的自由裁定权利。
1.6 美国。《美国法典》第44卷“公共印刷与文件” 《总统档案法》第22章第2204条总统档案的利用限制中第(b)(3)款规定:在依照第(b)(1)款的特别限制利用期间,总统档案或其中可分开部分是否能够利用的决定,应当由国家档案局局长在咨询卸任总统后慎重作出。在此期间,除非在本条第(e)款(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规定卸任总统认为国家档案局局长对作出决定违反总统权利和特权而提起的任何诉讼具有管辖权)的规定外,该决定不属于司法管辖评审。国家档案局局长应当建立程序规定,任何人由于依据本段而作出的决定被拒绝利用总统档案,可以对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该程序应当由国家档案局局长或其指定者,在收到起诉后30个工作日内提供书面规定,说明该规定的根据。[23]虽然总统法仅有一条档案救济的规定,但相关主体权利、利用条件、申请程序和期限要求都阐述得清晰明了。
2 六国档案救济法条内容比较分析
通过对上述国家档案救济法条内容的梳理并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其具有明显特征。
2.1 建立具体的申请或申诉程序。上述各国法条的申诉程序不大相同且形式多样、结构复杂,但它们都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有严格完备的法律规范约束。澳大利亚法案中规定了申请、申诉、复议处理及法院审批等具体程序;新西兰法案规定了公共机构和地方政府的申诉权利和流程;丹麦法案虽仅有两条条款涉及申诉,但其更重视申请人的申请权利,同时对申请人利用档案违规行为的处罚也作了法律规定;日本法案则规定申请人可依据《行政异议审查法》向国立公文书馆首长提出相应请求;法国法案主要强调法院在救济渠道的主导作用;美国法案则规定由国家档案局局长建立程序。
2.2 明确档案利用救济途径。上述各国法案中均强调并且阐述了档案救济的初次申请程序,而澳大利亚的救济途径最为丰富,既包括行政复议也包括行政诉讼;新西兰和丹麦均强调了行政申诉途径,然而两国法案中行为主体和最终决策主体完全不同;法国声像档案简单规定了其司法救济渠道,并未作出具体阐述。
2.3 界定档案救济主体身份。在档案救济行为中涉及的主体颇多,其中,最重要的主体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一般是作出处理决定的档案行政部门),此外,也包括其他权利主体如法院、档案咨询委员会等。
澳大利亚法案规定在第一次申请程序及第二次行政复议行为中公众为权利主体即申请人,档案馆为义务主体即被申请人,此后的第三次行政诉讼行为中,申请人为原告,档案馆为被告,由法院对此行为作出最终裁定。
在新西兰法案中,其申请主体为公共机构和地方政府,被申请主体为档案馆馆长,如若申请主体再次提出书面申诉,其纠纷行为最终由部长(现任负责本法行政管理的内阁大臣)裁决,此外,档案委员会在其中代表第三方主体提供自己的建议。
丹麦法案强调任何人均可作为档案申请主体,被申请主体除了档案馆之外,还包括档案形成来源的相关机构,其决策主体为相关行政机构。
日本法案仅规定异议者可向国立公文书馆首长提出申请,同新西兰相似,公文书管理委员会也作为第三方主体提供咨询建议。
2.4 自由裁量權。《牛津法学大词典》对自由裁量权的内涵界定为:“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的权力或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这种权力。”[24]
各国决策主体的权力相对统一、集中,而且部分国家和地区还设有决策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澳大利亚法案赋予法庭一定的权利,其有权依规定复核或裁定国家档案馆的部分决定,且作出的决定与国家档案馆有同等效力;丹麦法案规定了文化大臣应当制定上诉过程有关规则;法国法案提出对于司法音像档案适用方式决定不服后的救济渠道,需咨询最高行政法院后的法律作出;美国总统法则要求国家档案局局长要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诉讼建立相应的程序规定。
此外,新西兰法案和日本法案都强调了其他相关机构在裁决时的权利。新西兰法案给予部长最终裁决权以约束档案馆馆长和主管公共机构,但在作出决定前必须与提出申诉的主管公共机构和档案委员会进行协商;日本法案第二十一条规定针对文书利用问题提出的异议,国立公文书馆首长应同公文书管理委员会商讨。
2.5 突出档案委员会的咨询职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丹麦四国法条均设立相关章节来规定档案委员会,虽然各国档案委员会的名称、任命资质不大相同,但它们内容均包括其组成部分、相关职能、行政事务等。此外,新西兰法案、日本法案还另设章节给予了档案委员会对于申诉的决策权力,并对其具体操作办法也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2.6 同其他法律相衔接。澳大利亚法案规定在澳大利亚档案法实施过程中如果有与《1975年行政上诉法庭法》的法律条款相适应的,《1975年行政上诉法庭法》要依据澳法作出适用修改;丹麦法案专门设立对于个人数据资料的利用申请的章节,如若利用公共档案馆内的个人数据资料,需要根据《个人数据处理法》的规定裁定且由相关行政机构作出决定;日本法案则规定档案申请者的异议可根据《行政异议审查法》来提出,而《独立行政法人等信息公开法》《信息公开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设置法》中有部分条款也适用于异议提出的,需要同《公文书管理法》替换部分文本信息。
3 对我国档案利用救济制度建设的启示及建议
3.1 尽快制定档案利用救济相关制度,完善档案利用权利保障体系。同其他国家相比,目前我国档案救济权利制度仅在新《档案法》中强调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这一途径,暂未强调其他途径,救济制度建设的不足是目前我国档案权利体系构建的一块短板,公民档案救济权利的落实需要靠制度来保障。
因此,一方面,档案行政主管部门需制定档案救济相关法规政策,确立公民救济权利的法律地位,包括明确档案救济权利主体的身份、档案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救济权利及义务、法院的最终处决权并赋予相应第三方主体建议、处罚与监督的权力;另一方面,还需增加档案救济途径渠道,我国可参考借鉴澳大利亚做法,制定我国档案利用救济渠道三部曲,包括申请、投诉或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途径。
3.2 设计具体可行的档案救济程序,规范档案救济行为准则。探讨档案救济程序的内容和申请步骤,是档案救济制度建设中不能缺少的一项内容。
首先,实行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相结合的救济流程。救济流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申请人针对档案利用需求提出申请,相关档案馆受理并给出答复;(2)申请人再次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或是投诉,相关部门需受理并给出申诉复议决定;(3)申请人若不满复议决定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决,需说明,上述法案中,各国最终裁定主体均可对行政救济行为作出直接判决并以此限制相关档案机构,而目前我国法院审理档案行政诉讼案件只能依据《行政诉讼法》作出维持判决、撤销或撤销部分判决和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
其次,规定档案起诉与回复时间。上述各国法案均或多或少阐述了在档案申请、上诉期间档案相关部门或法院处理的回复处理的时间问题,因此,在设计我国档案救济程序时,也可规范适宜的时间范围,对于不同类别的案件,其规定的时间也可以不同。
最后,拓宽诉讼主体范围。我国新《档案法》第28条规定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档案主管部门投诉档案利用问题。然而,在实际利用情况中相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也可提出申请或诉讼行为,因此,档案救济制度在制定时应明确规定除单位和个人外,相关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也可以作为申请或申诉主体。
3.3 加强与其他法律衔接,协调救济权利适用性。国家档案局陆国强局长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档案法作为我国档案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与其他法律法规互相补充,协调一致,促进档案事业的全面发展”。[25]
对于档案救济制度的制定,应加强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如加强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等的合理衔接。[26]
3.4 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监督机制,规范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如若运用得当,可以实现个案正义和实质正义,并且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如若使用不得当,可能会出现法官滥用权利的行为或同罪而异罚的现象。在我国以往的档案行政诉讼案件中,就曾出现不同地方法院对于同类型的诉讼案件的判定、裁决各不相同的情况。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法案在给予各决策主体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给第三方主体咨询建议的权利,要求在决策主体作出最后裁定前,需要同档案咨询委员会商讨。
通过多方主体讨论、监督的方式可以避免档案利用司法途径出现不同,从而维护相关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与公平性。此外,还需说明,虽然之前我国并未规定档案救济渠道方面的内容,以至于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中依据标准不一,所给出的判决也不相同,现如今新《档案法》规定了档案利用救济途径,为今后我国法院决策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相关参考标准,从而减少档案行政纠纷案件,提升救济诉讼裁判质量。
本文系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档案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1YJC870007)和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依法治档背景下档案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1-R-15)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本论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25]陆国强.为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06-24(010).
[2]宋明,冯含睿.香港档案开放救济制度评介——兼论我国内地档案开放救济制度的完善[J].中國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03):93-97.
[3]黄夏基,黎琳琳.从利用者的视角谈《档案法》修改[J].档案学通讯,2012(03):61-64.
[4][26]连志英,古楠珂,周眙.我国公民利用档案权利救济制度之完善[J].档案学通讯,2021(03):71-77.
[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研究司.境外国家和地区档案法律法规选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199-203,234,241,242,389-392,449,450,293,294,15,16.
[24]中国法院网.民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规制[EB/OL].[2021-10-18].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11/id/1117499.shtml.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21-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