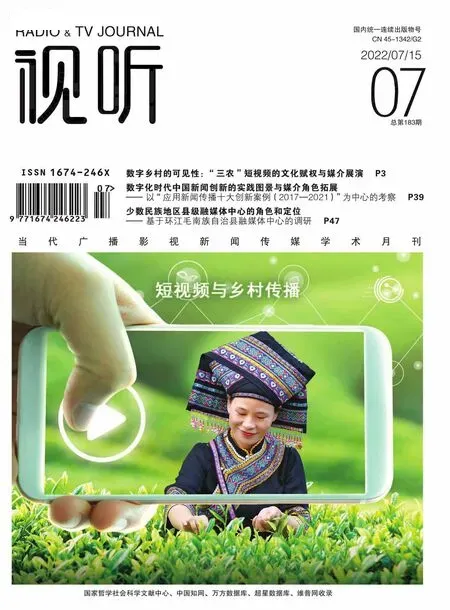文化工业理论视角下怀旧型消费空间的生产与传播
——以超级文和友为例
张 文
“文化工业”一般指的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①。被称为“餐饮界迪士尼”的超级文和友仅用8年的时间,就从路边摊蜕变为“市井文化综合体”,并将“长沙模式”推广至全国。“文和友现象”引起业界的极大关注。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超级文和友却按照文化工业标准化、程式化、商业化去生产文化产品,利用社交媒体的特性压榨分享型消费者的剩余价值,这些举措致使其产品在部分地区“遇冷”。本文以超级文和友为案例,试图通过文化工业视角对其生产和传播作深入探讨,从而揭示怀旧型消费空间当下面临的运作困境。
一、怀旧型消费空间的火爆出圈
不断加剧的现代化、全球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当代的怀旧现象,怀旧已经摆脱了最初的医学起源,内涵延伸到与感怀往日、消失的地方感、对地方的渴望和依恋等相关内容,成为当下的一种文化实践②。怀旧型消费空间的兴起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情感型补偿助推怀旧消费勃兴
对于当下一批具有雄厚购买力的消费者来说,怀旧文化不再是通过书本和影视被动式输入的文本,它能沉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心智共识。怀旧消费源于受众群体对既往的追忆与思念,其触发条件一般分为两类情感补偿机制。一是内生型情感补偿,是基于受众内在生理和心理机制之上的一种心理倾向和性格特征;二是外源性情感补充,通过有形或无形的品牌资产作为诱因,在企业的空间搭建与感官营销等外部刺激物中将个体的记忆带入产品或服务。
(二)新媒体赋权怀旧消费结构化扩张
在新媒体的加持和大众对文化需求升级的环境下,城市成为怀旧型消费滋生的土壤,为其提供精神文化价值确立和互动的场域。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工业体现在文化产品的流水线生产上,而新媒体语境下这一模式呈现出“IP—泛娱乐的整合营销”更加高级的扩张形态。相较于需要持续性内容生产与“输血”的文化项目,怀旧型消费空间在生产和传播上均有革新。一方面,新媒体语境下怀旧型消费空间在创造之初便将自身置于接受市场审视与检验的地位,将品牌资源转化为规模性的经济效益,使得“文化品牌”这一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有了充分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怀旧型消费空间以过去“单点式”经营为突破口,在此基础上实现“结构式”规模化扩张。在遵循现代市场原则的前提下,有效调度政府资金与媒体资源,有序开发文化产品及其衍生品,有意搭建新媒体自有渠道,扩大品牌的互联网声量。
作为集餐饮、娱乐和观览功能于一体的商业空间,超级文和友是怀旧型消费空间的典型代表。2019年,这一商业综合体脱胎于老长沙油炸路边摊,在长沙海信广场盛大开幕。超级文和友以还原市井烟火气和维系人文底色为宗旨,仅用1年时间便将其触角伸向广州、深圳,创始人表示有望于2021年末启动包括重庆、上海、天津、北京在内的超级文和友。迅速扩张的背后,却被打上“性价比不高”“装修没诚意”“不能代表广州本土文化”的标签。随着客流量锐减、“流量冠军”茶颜悦色的撤离以及接二连三的餐饮商户搬迁,曾经号称要“定义全国人民烟火气息”的超级文和友如今面临着尴尬的境遇,无论是深圳文和友还是广州文和友,都没能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二、怀旧型消费空间的生产之虞
从文化工业理论视角来看,怀旧型消费空间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操控性。欺骗性是指通过不断地对消费者进行说服和许诺,为其营造怀旧空间的假象以麻痹消费者;操控性则是将原本内涵浅薄的产品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当作合理的模式灌输给消费者。
(一)符号嫁接:情感异托邦的打造
在本雅明看来,城市是消费文化审美幻象的滋生地。在这里,“各种各样的陈列商品的巨大幻觉效应经常被转化为资本家和现代主义者的一部分寻求新奇的动机,成为梦幻影像的源泉。”③随着城市成为文化消费的主阵地,怀旧型消费空间成为具有符号意义的隐性消费品。为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怀旧型消费空间通常会忽视与其文化属性配套的空间环境,多选址在客流量可观的繁华商圈。自我标榜为“市井文化博物馆”的超级文和友,将“户外”装进“室内”,以长沙海信广场代替市井文化的“原生家园”长沙街头巷弄,使之沦为城市文化的附庸。超级文和友的店面装修会有意营造破旧粗糙的氛围,例如,采用早已被淘汰的马赛克瓷砖、老式灯箱店招牌、处处可见的吊灯和八仙桌,以期将参观的游客拉入生产者打造的“市井街头”。而市井文化,这一属于个体性灵感的审美乌托邦和文明的避难所,却在高楼大厦间通过怀旧物什的堆砌唤起人群的怀旧之心,“在眼花缭乱的符号的嫁接或掩盖下,竭力描绘一个割裂现实社会的现代性‘异托邦’。”④
(二)伪个性化:浅薄内涵产品的复制
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曾指出,音乐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使用音乐器材和滑动音技巧——甚至没有任何意义和美感。某些产品一旦取得成功,就会在文化工业下被大肆渲染。怀旧型消费空间正是如此,由于生产方多为本土新生企业,在没有足够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的前提之下,产品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受到现实因素和客观情况的限制。以超级文和友为例,在长沙店推出与长沙话相关的展览与市集,在广州店推出“讲什么——广州语言观察展览”“‘广州城相’许培武影像展览”,表面上做到了本土文化的渗透,似乎是以差异化的文化重构吸引不同地区的消费者,但实际上都是地方方言的露出和模式化复制。怀旧型消费空间本身及其产业链下游的展览、戏剧、市集多是一次性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衍生周边产品在没有周期性沉淀的情况下被大规模生产。在商业价值成为产业追逐的唯一目标下,文化产品的艺术风格日渐消失,大众的审美意识逐渐弱化,解读能力不断退化,最终只剩下机械的物质娱乐感官⑤。超级文和友吸纳纷繁多样的市井生活,在文化工业的揉碎、拼凑下变为仅具有抽象属性的商品,使之成为无法“反魅”的货物。
(三)消费异化:人与社会文化的危机
在现代,消费不再是纯粹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是人们借助商品符号试图展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超级文和友构建的商业逻辑里,20世纪80年代的市井生活被消费者审美化,成为被消费的一部分。从根本上看,人们不再消费物质产品,而是消费符号。一方面,不断加剧的现代化让人们直面生活的乏味和枯燥,过去的愉悦和幻想无法被追随与感知。因此,创始人文宾将个体的怀旧情结与社会的怀旧现象加以联结,使消费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怀旧符号也成为自我身份的彰显,进而符号消费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自我消费的过程。另一方面,超级文和友的怀旧符号可以为消费者消除不安,使之“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奇迹般安全”。当过去的美好不再存在时,人们将自身对意境的追求转换为对怀旧符号的消费,从不断的“购买”行为中产生安全感。
三、怀旧型消费空间的传播之困
在传播层面,怀旧消费的空间性传播可以更多地吸引到热衷于打卡的年轻群体,也决定了一般怀旧消费的核心受众是外地游客,其消费多是一次性的。而就时间性传播来说,长期的网红属性与非持续性的生产能力导致怀旧型消费空间无法深耕本地用户。因此,怀旧型消费空间的空间性传播与时间性传播实际上是不对等的。
(一)产消合一:虚拟空间传播者剩余价值被资本压榨
同多数形态的文化产业一样,超级文和友的传播可概括为“实体空间+虚拟空间”双管齐下:实体空间表现为文和友臭豆腐博物馆、文和友美术馆得以实现跨越时间的传播,虚拟空间则表现为“两微一抖”的渠道建设和小红书、知乎等平台账号的运营。超级文和友享受了许多新媒体为它带来的红利,通过一则则“市井文化博物馆”“带你回到80年代”“老长沙人的共同回忆”的高赞回答与帖子,打出感情牌,一跃成为网红打卡的新宠。但是在爆红的背后值得思考的是,大众媒介通过“种草文案”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合二为一,人们在消费后自发、无偿地进行创作,实际上附加的行为被平台资本当作商品。通过社交媒体,依靠大众的消费行为,向大众传输文化与意识形态,这种方式已成为注意力经济下的“利器”。
商品的符号价值必须借助大众传媒传播才能形成,因此,大众传媒成了推行消费主义话语的得力助手。大众传媒的鼓吹和渲染加大了符号消费的诱惑力,广告制造了商品符号的幻境,“激起每个人对物化世界的神话产生欲望”。与产品广告不同,超级文和友的广告聚焦的不是商品实体本身,而是重在渲染20世纪80年代的市井氛围,将信息当作商品去赋值。例如,“老长沙的柴米油盐”“五讲四美三热爱”,通过拼贴高意向的城市符号,形成构图场景化和仪式化,成就了一场喧哗的、炫耀的、释放消费欲望和快感的表演仪式。消费社会下商品源源不断地生产,与此同时,广告也许诺可以“通过观览与消费重回上世纪80年代”。尽管消费者已经“看穿”了广告的套路与伎俩,但出于对自我彰显和安全感的考量,依然会选择参与整个消费过程。
(二)个体游荡:怀旧型消费空间全球化风潮和地方性抵抗
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本身在操纵大众的尝试中,已变得与它想要控制的社会一样内在地含有了对抗性⑥。文化工业中也蕴含着大众抵抗与批判的积极潜能,“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含有自己谎言的解毒剂。”
在“十四五”政策背书和数字技术赋能的“两轮齐驱”下,中国文旅发展进入4.0时代,怀旧型消费空间在全球掀起热潮,是引领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热点方向。然而,在怀旧型消费空间全国扩张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单一模式”却被认为不再适用,甚至出现地方性抵抗行为。首先是地方消费者的抵抗。自超级文和友发轫以来,其发展轨迹便与长沙这座城市深度捆绑,造成后续城市很难与超级文和友这一“外来品牌”产生强关联,消费者难以产生强黏性。例如,广州文和友力图打破桎梏,“一城一策”地推出广州茶点,却被广州本土消费者称“形似而神不似”,背离了讲究务实精致和“平靓正”的广州饮食文化,实际上还是“长沙模式”的翻版再利用。其次是地方商家的抵抗。扩张的文和友一直打出“招商三定律”旗号,即入驻的商家必须有十年资质,是生意好的非连锁店。而在广州、深圳具备以上条件的商家已具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为何要再加盟超级文和友,去面对一系列未知的风险挑战与竞争威胁?
四、基于怀旧型消费热潮的理性思考
在现代化信息社会越来越仰仗创意与风格的前提下,怀旧消费面临着潜在危机:由于被利益与资本裹挟着,怀旧消费逐渐与“重现经典”的初衷和艺术价值背道而驰。随着流水线生产和工业化传播愈演愈烈,怀旧文化将沦为千篇一律的文化工业产品。
(一)流水线生产损害“光韵”
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之前的艺术充满了“光韵”(aura)。超级文和友将原本不堪盈握的虚空和转瞬即逝的体验以工业复制的形式留存,受众原有的“留白”被各式社交媒体的“种草”、打卡填充,文化参观活动变成异化的劳动延伸。通过空间搭建重现市井文化不是“光韵”的复原,只是“拾荒者”进行“自我救赎”的努力尝试。在工具理性凌驾于艺术价值的情况下,怀旧消费空间放弃挖掘原本的文化内涵,而是选择效仿好莱坞的生产流水线。超级文和友在广州的发展策略与长沙如出一辙:选取当地特色建筑作为载体,搜集当地具有怀旧因素的老物件堆砌在商业综合体中,依据“招商三定律”选拔当地小吃。这时的怀旧文化已经蜕变为“物化”的文化。纵观怀旧型消费空间,多数都只是“马赛克式”拼贴的景观符号。
(二)“大规模定制”泯灭个性
“大规模定制”是数字信息时代文化工业产品的新型生产方式,为了应对逐渐细分的受众市场,凸显定制的“个性”与风格,更具迷惑性⑦。整个怀旧型消费空间产业链按照“后福特制”式商品市场的逻辑运转,源源不断地遵循模式化公式去生产个性化内容与消费品。超级文和友的底层逻辑附着文化变现,而文化变现又是依托城市战略的。当开拓新的城市店面时,超级文和友针对地方消费者采取“类长沙模式”:将外形打造为当地风格的建筑以期唤起共鸣,利用“招商三定律”吸引地方特色小吃,开展当地方言主题大观与展览会。在此情况下,文化活动俨然成为一种有序的归类活动。
“大规模定制”实际上仍是对个性和创造性的扼杀,是虚假的“个人主义”,将被意识形态标准化了的情感承载在文化传播产品之中,并将其作为大众的消费对象。包括超级文和友在内,怀旧型消费空间的广告几乎都会模糊产品本身,很少会提到他们所供应的餐饮或是文创商品,取而代之的是对老一代记忆的描摹,这也使得广告在任何地区都可以适用。
五、结语
文化工业下的怀旧文化正在通过地方缺乏真实性的拟仿、“大规模定制”和千篇一律的“种草”传播来实现对消费者的蒙蔽与操控,消费者的私人闲暇空间也由此被技术世界的现实侵犯和压缩。然而,真正的怀旧文化不应将全部动机都放在对利益的追逐上,而应是有温度、有价值且能满足受众需求的艺术。文化工业环境之下的怀旧型消费空间虽然代表全新的文化表达形式,但其本质上仍是人类文明发展与前进的一环,需要我们理性看待,挖掘文化中真正可视、可感的价值。
注释:
①刘金风,吴宁.论当代中国青年的流行文化——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04):29-34.
②Bonnett A.Left in the past:radic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M].London,UK:Bloomsbury Academic,2020.
③[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3.
④福柯,王喆法.另类空间[J].世界哲学,2006(06):52-57.
⑤李小华,祝琳婷.文化工业视域下的IP电影热潮思考[J].中国出版,2016(18):28-31.
⑥[美]马丁·杰.阿多诺[M].瞿铁鹏,张赛美,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59.
⑦郝雨,郭峥.传播新科技的隐性异化与魔力控制——“文化工业理论”新媒体生产再批判[J].社会科学,2019(05):172-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