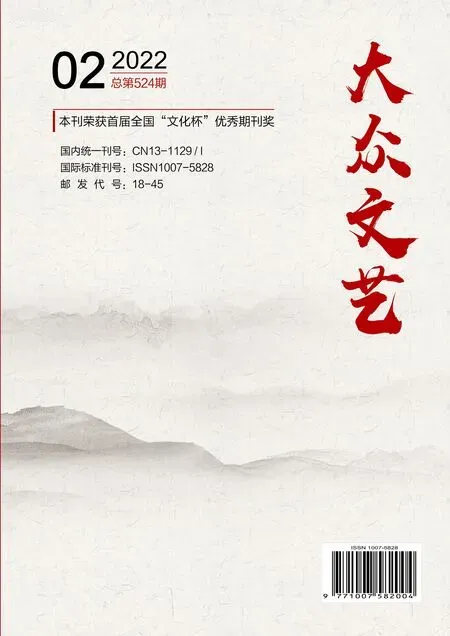学衡派世界人文主义的伦理逻辑*
方旭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今天的中国面对世界发展的困境和纷争,提出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回顾历史,我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是中国提出了这样伟大的构想,也能更好地为这一伟大构想发掘丰富的历史资源。近代中国虽屡被侵略和践踏,一度面临亡国灭种之生死存亡的危机,但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探索国家出路的努力中总有一种“天下”主义的情怀。学衡派就是在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最为特殊的时期出现的一个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思想流派,他们学贯中西,在吸收美国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试图通过中西融合建构一个世界性的人文主义体系,并希望通过世界性的人文主义来建构一个天下太平的和谐世界,其伦理逻辑对今天中国和世界依然很有启发意义。
一、人类共同体的迫切伦理需要
学衡派人文主义的提出首先针对的白壁德所谓的人道主义。白壁德认为人道主义包含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情感的人道主义,二者以知识和情感的直接扩张为目的,本质上都流于自然主义。白壁德和学衡派认为这两种思想导致的是无选择的同情和泛爱的人道主义,而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内心的“规矩”和“自制”,强调“以理制欲”“归本于中道”,是理性对欲望的节制,追求人的价值理性和自我完善。正如孙尚扬指出的,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基于对人类思想史的观察和对现代资本主义弊端的弊病的深刻洞见。在白壁德和学衡派看来,科学理性、追求个人权利意志的所谓理性、情感意志相结合并过度扩张,容易把人引向任情纵欲的不文明、不道德境地。在学衡派看来,19世纪、20世纪的殖民掠夺,帝国主义之间的不义战争,是对科学的人道主义和情感的人道主义极端追求的结果,是国家层面的人道主义导致的任情纵欲。因此,学衡派主张提倡世界人文主义,是其人文主义对人道主义针对性反思和批判的重要内容。
学衡派认为世界人文主义是对一战后混乱的国际关系秩序的一种伦理回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残酷的现实证实了白壁德对科学的自然主义及情感的自然主义的担忧和批判,即人道尽失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和极端浪漫的人道主义带来的危害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梅光迪认为:“帝国主义,即极端的民族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又为极端的帝国主义。”吴宓翻译的《白壁德之人文主义》一文提道:“白壁德曰:‘今相邻各国各族,以及一国中各阶级之间,各存好大喜功,互相嫉妒之心,更挟杀人之利器,则无论或迟或速,战争终不可免’。”白壁德认为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一国之内,如果秉持科学的自然主义与情感的自然主义,没有价值理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规约和节制,最终必然走向互相残杀的战争,即“近今欧洲大战,又非无故也,徇物而不知有人,其结局必当如是。”“徇物而不知有人”就是指自然主义导致人道被自然欲望淹没。柳诒徵则直接把一战的原因归结于进化论,他认为:“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学说,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中心,谓物类必竞争而后生存,人类亦必以竞争为生存之本。欧战之祸,即基于此,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恰恰是“徇物而不知有人”的典型表现。而白壁德和学衡派认为,国家的和谐和人类的和平应该是人们共同的需要,但它不是靠科学理性、追求个人权利的理性、情感意志相结合并过度扩张而带来的,恰恰需要能够节制科学理性及其理性思维在人文领域运用,能够节制所谓出于自由意志的情感主义的价值理性,学衡派认为这价值理性就是“以理制欲”,“归本于中道”的人文主义,而这种人文主义应该是全人类共同体追求的崇高道德价值。
二、传统“天下”主义伦理观念的自觉
学衡派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是一种超国家的伦理共同体。当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以及面对从未有过的世界大战之现实困境时,中国人应对它的智慧首先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天下”主义和世界大同的观念。传统的“天下”注重的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之“人道”价值的广泛传播,“天下”的核心特征并不是侧重于邦国之间通过利益交往而形成的政治或利益的共同体,而是侧重强调一个具有超国家主义的伦理文化的共同体。张其昀指出:“中国之名,初非土地之总称,亦无境界之限制”,即在伦理的角度不把自身限制在邦国之内,而是放眼天下,“《大学》条目,终于‘平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种世界主义或超国家主义之政治论,深入人心。……要之,中国乃文明国之义,使天下人皆勉于正义人道,虽举天下而中国之可也。孟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举彼专持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武功主义者,不几霄壤乎?”张其昀所要阐发的是传统“天下”观念的世界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特征,所要指出的是这其中的伦理文化精神,传统“中国”和“天下”及其关系虽然与今天之“中国”和“世界”并不完全等同,但其中所表达的“平天下”之笼统观念,则是一个具有伦理文化色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传统“天下”主义首先不是以政治和军事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以伦理道德即“正义人道”处理之,国与国所组成的就是一个伦理性的“天下”共同体,是“世界主义的”或者“超国家主义的”共同体。当学衡派在现代主权国家组成的人类世界中再次体悟传统“天下”观念时,他们要强调和发掘的不是中国及其文化的优越性,而是“道”的无所不包和平等性。学衡派将“天下”观念引申出来,并用“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来突出民族国家之间道德地位的平等,以此明确反对“专持”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武功主义(军国主义)的狭隘国家观念,极具理性主义人文精神,是其提倡世界人文主义的中国精神自觉之根基。
学衡派认为传统“天下”主义伦理的核心价值原则是仁爱。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中,辨别夷夏的根据是“礼”,处理夷夏关系的原则规范也是“礼”,而“礼”是超越国界的,是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伦理价值体系,是人之为人的正道,也是邦交立国之正道。学衡派认为,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依然需要伦理道德,即需要“克己复礼为仁”的“礼”“仁”合一的规范。学衡派遵奉白壁德实证的人文主义,在“天下”伦理观念及其历史实践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中,他们可以获得丰富的实证资源。如张其昀指出:“黄帝御宇,武功震铄,文治明备,书称‘克明俊德,协和万邦,淳德允元,蛮夷率服’。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此之谓也。墨子亦称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四戎,禹东教乎九夷,废力尚德,所从来久矣。”学衡派认为中国传统被赞美的上古时期的皇帝、尧舜禹等圣王,之所以能做到“协和万邦”,“蛮夷率服”,从而被后世称颂,不是通过利益笼络的,也不是通过力量征服的,而主要是靠人文道德的感召力和教化实现的,其理想抱负就是“克明俊德,协和万邦”,就是要“明明德于天下”。而这种文化天下主义的核心就是礼乐,本质是强调国家之交的交往要通过伦理道德建构一个伦理的共同体。这种世界主义的情怀及其道德理想,虽然受到了白壁德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但首先还是来源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观念的近现代自觉,也正如乐黛云指出,首先不是白壁德塑造了《学衡》诸人的思想,而是某些已经初步形成的想法使他们主动选择了白壁德。学衡派这种把中国传统“天下”主义引向“世界主义”或“超国家主义”的阐发,既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伦理自觉,也是一种伦理自信。这种伦理的自觉和自信很重要,但它必须要在吸收新思想的基础上有创造和转化,增强理论合理性和解释力,才能在主权国家组成的现代国家共同体中发挥文化影响力。
三、白壁德世界人文主义伦理观念的借鉴
学衡派借鉴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对传统“天下”主义伦理观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学衡派人文主义认为传统的“天下”主义伦理观念由于历史局限性显然已无法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中其他优秀的智慧,融合并发展之,才能为这破碎的世界建构一个“公理”。学衡派要想继承和发扬“天下”观念中的人文主义伦理精神,首先需要对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弊病进行理性的批判。传统“天下”主义观念中的夷夏之辨确实存在汉民族文化优越感,与其本身追求的文化“天下”主义有内在矛盾的地方,需要批判性反思。白壁德指出,中国传统“天下”主义中夷夏观念持有的文化优越感是要批判的,“彼以为中国为文明世界,为普天之下,其外皆边徼之蛮夷”,这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正是其新人文主义要批判的对象。世界人文主义作为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首先肯定的是不同道德主体的平等性,这是建构世界性的人类共同体的前提。学衡派坚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术宗旨,就是对白壁德世界人文精神的直接呼应,也是对传统“天下”观念中文化民族主义的扬弃。
白壁德肯定中国“天下”主义观念中的道德精神,并认为可以和自己的人文主义精神相结合,形成一种世界性的人文主义。这为学衡派对“天下”主义的拓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情感支持。白壁德指出:“中国立国之根基,乃在道德也。……中国人屡屡被外族征服,然一国之文化与兵战之胜败何关!”这就是前面张其昀指出的,这里的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而是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的共同体,是“平天下”中的一个阶段或者环节,不以国家为最高团体。能不断融合其他民族,开放包容的“天下”观念和协和万邦的道德是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而白壁德认为,“此道德观念,又适合于人文主义者也。”中国儒家的思想之所强烈吸引白壁德,就是因为它符合白壁德所追求的“以理制欲”归于“中道”的价值普遍性。而白壁德的人文主义,始终想着要解救人类近代以来的文化上和现实中的困境,并对中国文化抱有很高的期待。白壁德融合中西的世界人文主义,深深影响了学衡派。梅光迪强调:“白壁德先生兼及吾国文艺哲学,凡英法德文之关于吾国文艺哲学著作无不知,而尤喜孔子。两人固皆得世界文化之精髓,不限于一时一地,而视今世文化问题为世界问题者也。……白壁德先生尤期东西相同之人文派信徒,起而结合,以跻世界于大同。”明确提出建构一种融合中西的新人文主义,希望既可以救国,还能够救世,以世界性人文主义联世界于一体。
四、“中庸”道德理想的必然追求
白壁德和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核心精神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价值追求会把人们引向对更高的共同体的向往和皈依。人有理性之能力,就有向善之需要,有终极之关怀,就必然会期盼一个理想的人类世界,这是追求崇高的人类必然会有的道德理想。而“中庸”之道的价值体系是由“一”“多”融合的世界观,“善恶二元”的人性论,“以理制欲”归于“中道”的价值观建构的道德理想。白壁德非常赞同柏拉图说的:“世之所谓一,又有所谓多,有能合此二者,吾将追踪而膜拜之。”“一”是理念,是普遍性和实体性,“多”是的指具体事物,是多样性、个体性,“一”“多”融合的世界观就是统一个体和实体。在这一世界观基础上,学衡派主张善恶二元的人性论。吴宓指出:“人之心性(Soul)常分为二部,其上者曰理(又曰天理),其下者曰欲)。”人性中高上之部分(天理)是普遍性和实体性,也就是“一”,而人性中低下之部分(欲)是多样性和特殊性,也就是“多”。以此建构的价值原则是“以理制欲”,“归本于中道”。因为事物和人的欲望本身就是多样化存在的、特殊性的存在,而“一”是需要人们去建构和追求的,然后做到两者平衡的“中庸”境界。学衡派探求的是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人文价值。
学衡派世界性人文主义试图建构的人类共同体,是“一”“多”融合,“理”“欲”统一的“中庸”道德价值在人类社会层面的现实形态。世界性人文主义建构的共同体应该是以爱为核心,以理为爱的形式和逻辑,情理统一而建构的伦理共同体。张其昀指出,“希腊之精神曰入世,曰谐和,曰中节,曰理智”,“而吾国立国东亚,夙尚中节。尧舜禹汤,以是垂训,而国号曰中。……此则吾国与希腊精神最相同之一点”,正是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学衡派“中庸”之道主张的是有选择的同情和爱,“但有博爱不足也,但有选择和规矩,亦不足也,必须二者兼之,具有博爱之心而能选择并循规矩,斯可以”,而这个规矩就是“全体人类自有其公性与同具之真理存”。没有博爱之心和普遍原则的统一,无法建构一个和谐的人类伦理共同体。反对简单地以为“纳众生于怀中,接吻全球以一吻”。所以白壁德感叹:“十九世纪之大可悲者,即其未能造成一完美之国际主义。科学固可为国际的,然误用于国势之扩张,近之人道主义、博爱主义,亦终为梦幻。然则何苦告成一人文的,君子的国际主义乎!初不必假宗教之尊严,但求以中和礼让之道,联世界为一体。”“君子的国际主义”也是学衡诸人共同的道德理想。
学衡派试图通过以道德为核心的世界人文主义建构人类伦理共同体的思想,对今天的人类世界依然有借鉴意义。人类社会既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政治的共同体,更应该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只有要把人类看作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才有建构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的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建构,必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天下”主义情怀。从“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谐思想,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交往之道,再到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价值取向,应该以兼具中国特征和世界性的话语体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建构,应该坚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理念,探求共同共通的价值体系。既要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也要肯定和支持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融合,求同存异,站在人类伦理共同体的高度,以纯粹理性式的精神建构最基本的人类伦理原则和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