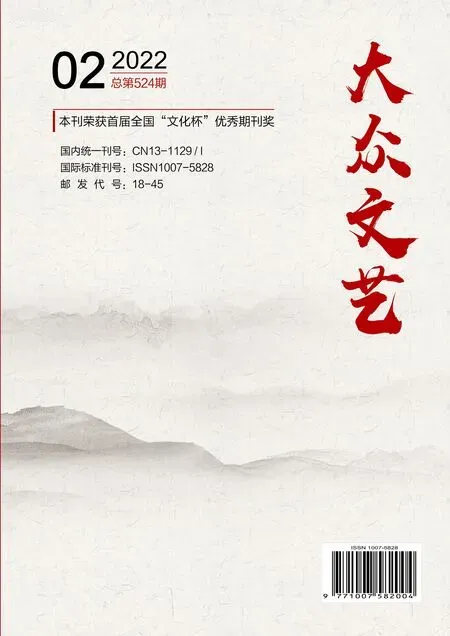走出黑夜
——《玫瑰门》中的女性与权力
李双伶
(信息工程大学,河南郑州 450000)
一、前言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初版于1988年,作为当代文学中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篇小说从问世起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80年代末,女性写作呈现一种爆发的状态。在残雪、翟永明等女性作家关注女性自身和封闭的自我世界之时,铁凝在《玫瑰门》中选择了透视自我世界之外的女性,书写女性个体与社会、权力的错综关系。在关注女性的同时,铁凝“也直面着远非完满的社会与人生,不规避,不逃遁”。这让《玫瑰门》超脱于一般仅针对女性和女性世界进行描写的文学作品,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独特的研究价值。
在《玫瑰门》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女性的命运与历史、时代的相互勾连。铁凝不做社会生活的洞见者,在她笔下,《玫瑰门》中的女性,从司猗纹到宋竹西再到苏眉,无一不是努力进入社会生活,从社会权力的边缘努力向权力的中心靠拢。这样的努力与本就复杂的社会权力生活交织在一起,呈现在文本中则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正是《玫瑰门》的魅力所在,也正是其最具研究价值的地方。本篇就着力于《玫瑰门》中女性与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探寻文本中那些走出“黑夜”的女性如何构建自己的权力和社会生活。
二、本论
《玫瑰门》与其他女性文学最大的不同大概就在于作者铁凝的写作态度。不管是王安忆的《长恨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还是翟永明的《黑夜的意识》,她们都意识到了权力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地位,但她们在作品中并不拒绝女性身处的社会边缘地位,也并不希望参与进男性中心的权力社会。翟永明把“女性气质”比作黑夜,认为“黑夜的意识使我把对自身、社会、人类的各种经验剥离到一种纯粹认知的高度”。这样的选择一方面出于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社会的避让,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她们身处权力社会的边缘,比处于权力欲望中心的男性更能清醒地认识到,对现代性有着激烈追求的社会其实正面临着“世纪末的情绪”,以王安忆为代表,她的小说中呈现的是“整个世界都已经走到了尽头”的历史终结感。她们因为边缘的社会地位而更能采取一种超脱、俯视的角度来观察权力社会。
然而这样的角度不仅超脱了男性权力的束缚,也把深受权力社会束缚而无法摆脱的女性也排除在外。翟永明就把女性文学分为女子气-女权-女性“三个不同趋向的层次”。她更认可的是作为文学理想形象的“女性”。那么,从这一角度看来,以翟永明为代表的部分女作家,她们所理解的理想的女性社会群体其实更像是女性作家的沙龙:她们以其对文学的敏锐洞见看透了权力、现代性以及物质文明的结局,主动跳出权力的漩涡,从女性“真淳与博大的母爱、柔韧的生命力”中发现“无邪的赤裸正是平常人生,是单纯、‘自然’的生存方式的回归呼唤”,为几近癫狂的、充满世纪末情绪的现代社会找寻出路。但《玫瑰门》则不做超脱的姿态,把目光对准那些在男性中心的权力社会中挣扎浮沉的女性,怀着善意与理解观察讲述她们的故事。正如谢有顺所说,《玫瑰门》“有着非常实在的生活面貌”,同时“具有经验与伦理的双重品格”,形成了“更具生存意味的现实处境学”。
因为放弃了“女性主义”的洞见,铁凝似乎也抛弃了写作中的性别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关怀有所下降,反而因为跳出了性别的限制,获得了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客观的态度。这一视角被铁凝称为“第三性视角”。“第三性”也正代表着作家创作的立场:不把女性世界作为独立存在的王国,而是作为文明社会的一部分,加以反思关照。这样的视角为解读女性与权力、社会以及男性的关系打开了新的关窍。作为文学作品的解读者,我们也不能再拘泥于作品中的女性经验和身体写作,应跳脱出女性来看女性,才能在解读的过程中更好地发现女性与权力的纠葛关系。
因此,本篇并不试图分辨《玫瑰门》中独特的女性世界,而是将以更加客观的态度,从作品中的司猗纹和苏眉两位主要女性形象入手,分析铁凝笔下的女性与权力有着怎样复杂的关系。
(一)司猗纹:倾尽一生的幻象追寻
无疑,文本中塑造的司猗纹年轻时是美丽、聪明且勇敢的。然而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在《玫瑰门》中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她的初恋带走了她的贞洁,并且一去不返;她的丈夫拒绝承认她的妻子身份并在外面另有情人;她的婆家靠她支撑,然而却对她处处提防;她的儿子、女儿、孙女、外孙女无一不对她的行为表示厌倦反感……她不仅没有得到过故事中任何人的承认,而且在文学评论中,她得到的也只是一句“是父权家长制的受害者,但又是其同谋”的评价,或者是“一株妩媚而狰狞的罂粟花”。在评论者的眼中,她是可怜而又有毒的,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然而这样一个不管从身家背景还是从外貌才华来讲都几近完美的女性又是如何走到这样一步的?
司猗纹成长于一个旧式家庭中,她的家庭教给她的是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十六岁的司猗纹进入教会学校圣心女中,赶上社会变革的大潮,她又接受了现代文明:阶级、家国和平等,并且遇到了她新式恋爱的对象:华致远。这时的司猗纹想要获得的是男权社会所赋予女性的权力。她对于得到权力的方式是“等”,等男人来赋予她权力。“他告诉她,终有一天他会回来接她,因为他爱她……雨早就停了,天快亮了,坐在窗前的司猗纹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擦干净家具,等‘他们’。”“他们”所指的正是华致远所代表的革命的力量,能赋予司猗纹自由和权力的力量。没有等到“他们”,司猗纹便出嫁了,她被她所企盼的现代文明抛弃,于是她退而求其次,等旧社会的男性赋予她权力。于是司猗纹又努力操持家庭,为丈夫生儿育女,承担起整个庄家的家庭重担。丈夫庄绍俭不回家,她就带着子女追到扬州,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被庄绍俭看到,并吸引丈夫回归家庭。司猗纹以为自己经营好家庭就能等回丈夫,然而司猗纹没有注意到,庄绍俭是规则的制定者,她不管如何努力,以期使丈夫满意,但庄绍俭随时可以更改规则,把她的努力和等待变成笑话。这次司猗纹等到的是“花柳”“杨梅”。这病是对司猗纹的侮辱,更是把司猗纹“等”男性来赋予自己自由和幸福权力的想法完全击碎。“司猗纹四十岁,她以一场恸哭结束了她的前四十年。”
司猗纹明白自己永远无法从男性手中等到权力后,她选择了主动“找”权力,不仅是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力,还有进入社会的权力。“为了找,为了找的行动,七十多岁的她从未停止过。”她主动出击,“强奸”庄家老太爷以作复仇。她利用新婚姻法与庄绍俭离婚,和朱吉开同居,追寻“一块明亮而又朦胧的未来”。在进入新社会后,她要“生存得合情合理她要与新社会同步”,他要与“‘抓住一扔’的军转干校长较量一番”,要从罗大妈手里争夺对大院的权力,要从达先生手里争夺对“列宁剧”改编的权利,拒绝知识男性叶龙北的引诱……她把仅有的异质——性欲寄托在姑爸和她的掏耳勺身上,于是她的全部就只剩对权力的追寻。她不仅要成为权力社会中被认可的一员,更要凭她的才智闯进权力社会的中心,从权力社会中分一杯羹。
“男人和女人,历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她没能逃离庄家,也没能成为校长,更没能争到大院的权力,甚至在试图阻止叶龙北对宋竹西和苏眉的引诱上都是失败的。她对性欲的唯一的寄托,姑爸也被逼死。然而权力社会越是拒绝她,她越要走入这个社会中,越是求而不得,她就越是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地去得到,甚至不惜出卖家庭、恋人、家人甚至自己。和《玫瑰门》中的其他女性比起来,她似乎对权力有着极度地几近本能的渴望,永不停息的追求。
表面看来,司猗纹对权力的追寻似乎是出于她对权力的需要和几近变态的控制欲,但容我们在这里追问几句,司猗纹追寻的权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她永远在被权力社会拒绝?又是怎样一种力量让她在一次次地被拒绝后仅作短暂的停留,然后更加凶猛地投入下一轮对权力的追寻之中?
我们回观十六岁前司猗纹的成长,不难发现,不管是她在私塾,还是在圣心女中,她的“教科书”都是男性书写的,她学到的任何知识也都是男性赋予的。换句话说,司猗纹一直接受的是男性对女性的塑造,她争取的权力,也只是男性所追求的权力。现代文明的大潮中所述的女性权力和解放,不过是服务于权力社会的,而非女性自觉的权力。司猗纹要“找”,但她已知的,能“找”的就只有男性的权力。如此一来,第二个问题也就很好解释了,因为面对男性的权力,女性和男性也永远不是平等的。在性和爱上,华致远、庄绍俭都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在大院里,罗家代表的男性社会和男性知识分子叶龙北也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在社会生活中,绝对的男权社会根本不允许她与男性一样,参与权力的分割。在这样几乎一边倒的劣势下,司猗纹不可能,也永远不会被权力社会接纳。同时,司猗纹根本没有退出的可能,更没有退出的权力。现代文明的大潮给她播下了革命斗争的种子,也剥夺了她身为旧社会女性象征的贞洁,于是她被以庄家为代表的旧社会拒之门外。在现代文明中,她接受的现代性教育让她去斗争,去和那些男性争夺权力。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身为女性存在的意义,一旦停止对权力的寻找,她所能选择的只有睡,用无意义的行为消耗自己不被认可的生命。
司猗纹不得不斗争,但她的斗争又注定是失败的,她踏入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死循环,看似通向玫瑰世界的大门后面还是一片虚无的幻象。司猗纹在对这片幻象的追逐中倾尽了一生。
(二)苏眉:诱惑与拒绝
“母亲”这一称呼,大概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最高的评价了。这一名词蕴含着奉献、爱、恩泽、生命的延续等多种意义,被社会赋予了诸多神圣的光环。但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名词上附带的浓重的感情因素剥离,去掉这些人为所造的光环,从一种更加客观的角度来看,一个女人靠牺牲自己完成繁衍这一社会重任。孩子生下后,和男性相比,母亲在抚养教育孩子方面的责任更加重大。男性的社会分工是努力在权力社会中拼搏出自己的地位,女性则要“相夫教子”,却难以通过“相夫教子”获得社会和家庭中的认同。在面对是否成为一位牺牲奉献的母亲这个问题上,女性似乎别无选择。这个问题重大而敏感,铁凝的《玫瑰门》自然也不能忽视,于是作者选择了苏眉来作这个问题的承担者。
苏眉是拒绝成为一个母亲的。她的母亲庄晨再次怀孕时,苏眉“越看妈越不顺眼”,狠狠推了母亲一把。父母都被苏眉的行为惊呆了,不能理解一个少女对怀孕的拒斥。问及苏眉为什么推妈妈,苏眉解释不清,但叙述者替她说了出来:“可谁能说妈的大肚子好看。”苏眉对大肚子这种说不清理由的讨厌在她日后生子时得到了解释:
从前她把这地方想得很神圣:到处一片洁白到处都是林巧稚。原来这里除了大肚子还是大肚子。河里没鱼市上见,就像全世界的女人只干着一件事就是生孩子。医生护士对这些大肚子早已司空见惯,她们就像看见了一块大石头,一个棉花包,一条鱼——大腹便便的鱼。
很明白,苏眉意识到怀孕并不神圣,“母亲”一词也不过是像宣传中的林巧稚一样,被宣传得很神圣。她看到权力社会运用宣传的手段把一个个女性送进产院,成为他们生育的工具,“就像全世界的女人只干着一件事就是生孩子”。
就算苏眉已经看得这么明白,她仍然无法拒绝成为一名母亲。她生活在权力社会之中,她无法拒绝社会用花样百出的手段对她抗拒母性的行为进行谴责和矫正。她推了怀孕的庄晨,然后她看到了血腥的“伊万雷帝杀子图”。庄晨肚子小下去后,社会又给了她一个充满“哥儿们义气”的妹妹苏玮来感动她,让她发觉自己行为的“粗野”。一个美好而慷慨的姨婆奶奶,司猗频的出现也证明牺牲奉献的母性的美好。庄晨一生悲剧性的追逐和探寻,更是一个完美的反面典型。于是在庄晨流着泪给她讲完司猗纹的故事后,她突如其来又顺理成章地质询:“你为什么还不要孩子?”苏眉别无选择,也根本不需要任何铺垫和犹疑,怀孕生子了。
作为一个女人,除了无法抗拒的母性,苏眉还接受着来自男性的教育和改造。搬进庄家院子中的罗大旗和叶龙北就是男权的代表。在一个玫瑰色的春天里,十二岁苏眉开始从一个女孩成长为一个女人。她开始感觉到青春的躁动和无所适从。这时首先出现在她生命中的男人就是大旗。在一个面对成长惶惑无知的少女面前,大旗像一个领导者,借助现代媒介手段报纸,将自己扮成权力的赋予者。大旗让苏眉成为“早请示”的读报者,给她馈赠,供给他上好的印刷用纸。这些让苏眉听从他的领导,热情地回答大旗可有可无的问话。在这一过程中,大旗成了苏眉的“精神领袖”,只要他出现,就能代表某种权威和力量,抚慰苏眉的不安。
大旗抚慰了苏眉的不安,院子里的另一个男人,叶龙北则为苏眉启蒙。他教给苏眉鸡下蛋时会脸红,教给她麻雀飞翔时的美,教给她世上没有一条直线,还站在苏眉和苏玮一边与司猗纹争论。在苏眉因目睹竹西和大旗偷情深受震动而离家出走时,叶龙北再次适时出现,给苏眉苏玮买了去虽城的车票,并以他的温柔和宽厚包容了苏眉。在叶龙北的温柔和宽厚中,苏眉遭遇了女性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时刻,她的第一次月经到来。叙述者以一种极为诗意的语言书写了这一刻:“在这抽噎之中她忽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春日薄冰消融的小溪,小溪正在奔流。她的心紧缩起来,脸更加潮红。于是身体下面一种不期而至的感觉浸润了她。”叶龙北给苏眉提供了依靠和保护,苏眉也在叶龙北的见证下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女性。一个男性的出现让女性本来正常的生理变化变得神秘而诱人,这也成了苏眉确证作为女性的自我的重要一部分。对一名女性,叶龙北和他代表的男性以及权力,对苏眉充满了诱惑和吸引。
男性和其拥有的知识教化了苏眉。在这一点上,她和司猗纹的人生经历达成了一致,或者说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社会中,所有的女性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不过,幸运而又不幸的是,苏眉从小跟在司猗纹身边长大,她眼看着司猗纹对男性的抗拒,这让她在面对与司猗纹争夺权力的男性时不由保持距离。她同情司猗纹的同时,也潜移默化般接受了司猗纹的启蒙。她在八百米比赛后拼尽全力的一跪,让她获得了观众的掌声和搀扶,也证明了她不仅要确证自己的能力,还要获得社会评价的认可。面对绘画,她更有着坚定的野心,她坚信自己对绘画有着独一无二的感觉,也相信自己能够通过绘画获得权力社会的认可。和司猗纹一样,她别无选择地进入社会,加入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中。相比于司猗纹的永远被拒绝,苏眉所处的时代给了她机会,她得以用她的画敲开了走向社会的大门。
苏眉看过司猗纹为了权力如何癫狂,也深受司猗纹追逐权力的伤害,所以在她认识到她和司猗纹走上了同样的路时,她是恐慌的。小说通过向后绷着的小腿建立起苏眉和司猗纹在寻找社会认同上的联系。她在和妹妹苏玮吵架时,苏玮像是报复似的,通过两人向后绷着的小腿,把苏眉和司猗纹放在一起比较。司猗纹的疯狂让苏眉饱受其害,所以这样的认识让苏眉痛苦万分。苏眉内心虽然想要获得社会认同,但司猗纹的癫狂让苏眉抗拒对权力的执着。于是苏眉抗拒卖画办展,抗拒对事业正经八百、兢兢业业的丈夫。在抗拒这些男性乐此不疲的权力争斗的同时,她试图找到女性真正存在于社会的方式。然而苏眉和司猗纹一样,只有在睡觉和在卫生间中才找到自己的存在。但不同的是,苏眉可以落落大方地欣赏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体。她看着卫生间镜子里的自己,终于和自己和解,而落落大方起来了。如果说睡觉是被权力社会遗弃后的选择,那么卫生间则是苏眉开辟出的小小的女性空间,在这里,她接受作为女性的自己,接受自己审视的目光。
“当她们摒弃了男权文化中关于女性的话语后,不可能不感到深深地迷惑、茫然与内在匮乏。”苏眉在确证女性存在于社会的路上也终于和她厌恶的司猗纹殊途同归。不同的是,苏眉有了除了睡觉外的另一个空间,一间小小的卫生间,在这里,苏眉就有了自我认同的空间。这或许是她和司猗纹之间最大的不同。
(三)女性与权力的待解之谜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说,女性看到的权力之门里的美妙幻景是一种诱惑,不计其数的女性为着这样的诱惑奋不顾身。然而门的那边还是门,还是美丽的幻景。正如苏眉对自己说的那样:“面对一扇紧闭的门你可以任意说,世上所有的门都是一种冰冷的拒绝亦是一种妖冶的诱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将放弃对权力的追寻。女性作为社会组成的另一半,天然地有资格也有权利在社会中发声。司猗纹一辈子的抗争都被拒绝和厌恶,但是她影响了苏眉。苏眉像一个接力者,秉承着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确证再次出发,并用自己的画在权力社会中占住了一席之地。就算苏眉不能拒绝母性,她的女儿狗狗额角的新月形疤痕也象征着这条探索之路的生生不息。她们把自己扎根于这个世界,用肉体的存在确证探索的永恒。就算门的后面是幻景,她们也有勇气,有毅力,有生生不息的后继者来鼓动她们再次出发。她们用自己的努力告诉世界,女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是无解,而是待解。虽然看起来遥遥无期,令人绝望,但她们用实际行动表明,她们坚持对权力的探寻,坚持寻找自己身在这个社会的确证。
三、结论
另外,作品中还有一个并非主角的角色:苏玮。她性格开朗,从小就用自己的“七折腾八折腾”,“给自己争出一块足能伸开腿睡一觉的地盘”,长大后更是如此,“她伸开腿睡一觉,脑袋在中国,腿伸在美国”。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丽都酒店获得尊重,并且拥有属于自己的感情。如果说司猗纹的挣扎是无谓的,苏眉的挣扎是迷茫的,那么苏玮其实是作者试图提供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确证自己的一种新的方式。苏玮这个形象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和刻画,因为小说和现实都不能确定这种探索是否有效,会不会又是一场徒劳,但她爽朗泼辣的性格和敢于“折腾”的勇气,给《玫瑰门》添上一抹希望的底色,让读者在死循环般的挣扎中发现希望的缝隙。这是作者对于女性权力地位确证的美好愿景,也为女性走入权力世界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在整部作品中,所有的男性形象都塑造得像个过客。不可否认,就算是过客,他们仍然是《玫瑰门》中女性世界的巨大阴影。但正是因为这些男性阴影般的存在,才证明了女性权力世界独立于男性权力世界的可能性。阴影终归只是阴影,女性总有一天会走出这片巨大的阴影,确证自己的主体地位。从这个角度看,《玫瑰门》中所有不随波逐流,不屈从于时代、历史的女性都是为女性独立地位奋斗的英雄。她们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她们和司猗纹一样,至死都带着微笑。因为不管结果如何,她们为走出阴影努力过,为身为女性的自己奋斗过。这种自觉的女性意识也是《玫瑰门》最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