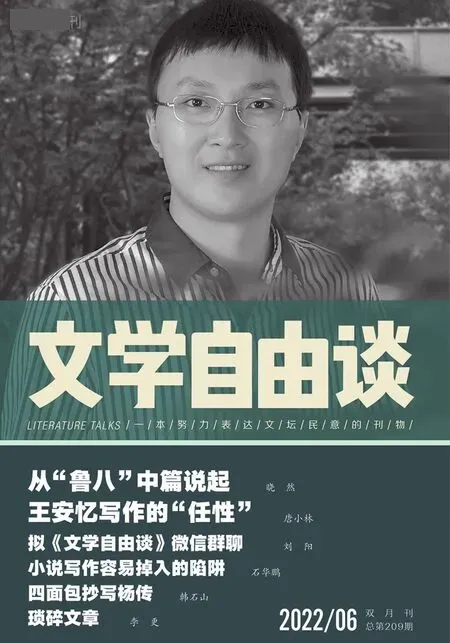琐碎文章
□李 更
1
2022年8月17日,吉林省文联主办的《小说月刊》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则通告,引发文学界热议。通告这样说:各位作家朋友,自今日起,向《小说月刊》投稿者,请在作品涉及到对话处,自行使用冒号、双引号,例如:他说:“你好,什么时候到的?”否则作品一律不予采用!敬请知情!
口水诗人基本上都不会使用标点符号,我认识几个中奖诗人,千字文中必须有五个及以上的错别字。黄小初说,个人感觉受此陋规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苏童。苏童乃是老汉认识的对双引号最为深恶痛绝的作家(几乎没有之一)。《小说月刊》如此旗帜鲜明,如同把苏老师等拉入黑名单,方是杀猴儆鸡、釜底抽薪之举。
2
多少年没逛书店了。在珠海富华里一家书店,看到《红岩》,发行上千万册了,作者却不是作协作家。那些当地牛哄哄的作家,却无一本走市场。
虽然是很多年不进书店,却像昨天才来过。这里可以读的书我都有,有的还不止一个版本;我没有的书都是没法读的。
3
刘锡诚说,198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文艺报》编辑部在北京西山一个招待所举办评论家读书班,潘旭澜是被邀者之一。应邀参加读书班的评论家,还有王愚、宋遂良、刘思谦、吴宗蕙、徐缉熙、黄则新,以及《文艺报》的阎纲、彭华生等。
以上名字今天还有几人知道?当年都是场面上的评论家。可见,评论家留下名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终归是依附于作家的作品存在,大部分都是靠作家吃饭,所以呆在大学校园里才是最合适的。何况,很多作家也留不下名字,被历史淘汰。毛将焉附?
有些文学评论家像峨眉山上的轿夫,靠抬举别人赚点辛苦钱。
4
现在很多盲人按摩院并无盲人,螺蛳粉并无螺蛳,肠粉并无肠子。
所以鲁迅奖没鲁迅也正常。
5
最近生病住了一阵医院,先后就告别了几位人物,戈尔巴乔夫、英女王,还有我的一个老师周翼南,八十二岁。
我们父子与周翼南相交多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家父李建纲和他同在花城出版社出个人专辑,李士非主编。又一同入围全国小说评奖,李建纲小说《三个李》《打倒贾威》由于某种敏感原因最终落选。
我们父子和周老师二老还一起应山东收藏家邀请去爬泰山,参加书画笔会。湖北是散文大省,周翼南的散文影响很大,关键是因为他写出了文化人的特质。我一直觉得,徐迟、曾卓、碧野、周翼南、熊召政、野夫、叶梅、李建纲、范春歌、余秀华、任蒙、李修文、徐鲁、董宏量是湖北散文的基本方阵。
6
古远清教授最近有篇文章说:在科研成果量化的年代,有人说高校老师写的是“学报体”,研究生写的是“学位体”,而教授写的是“项目体”。这“三体”固然为学术发展带来贡献,但其致命伤是“规范性”远大于“创造性”,或曰充满了“工匠气”。这就难怪《文学自由谈》发表的文章,在任何一所大学都不算成果,可上面登的某些文章,有不少吉光片羽和真知灼见,却是“学报体”论文所最缺乏的。
我觉得这个发现不亚于他的十几本书的意义。
几十年来,古老师每有新作,我几乎都会获其赐赠。我还曾帮他与书商洽谈过出版他与余秋雨官司的那本书。
古远清长于系统论,常年研究港台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他的书好读,因为没有大学里特有的学腐气,资料翔实却并不掉书袋子。你可以当学术,也可以当消遣。除了对马华文学我觉得似有拔高外,其他的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我曾几次去马来西亚考研当地华文写作。大马遍地华人,华文报章也多。可能是当年下南洋的华工固执于祖根文脉,很多地方的市街直接使用汉语为名。以槟城为例,中国大陆人初到当地,全无语言障碍,到处都是繁体字标牌,街贩以及网约车司机几乎都会闽南语、粤语、普通话。
但说老实话,当地华文教育水平不高。以钟灵中学为例,教育水准不及中国一个县城的中学。我侄子在那里学了六年,回国居然考不上一个三本大学,只是学了一下英语而已。我的湖北大学同学刘川鄂曾应邀去该校讲学,讶异于学校的墨守成规,学生见老师都要行九十度弯腰致礼等等。后来有朋友笑我,到马来西亚学汉语?那等于英国人到菲律宾学英语。脑壳灌水了吧?
实际上,大马华文写作水平也真不敢恭维,尚不及武钢的车间黑板报。所以,研究当地文学并进行评价,难免有水分。有时,一顿饭也可以左右一个做东的写手的评值。
自从“重写文学史”,各路神仙下凡,大多数都是学校老师当枪手,良莠不齐。尤其是个人写史,颇有个人排行榜的意思。他们没有时间对以往文学界进行必要、严肃的梳理,多半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甚至近水楼台,谁跟他接近,他就写谁。老作家不会巴结,大部分被边缘化,有个存目就非常不错了。结果一些文坛泡沫成为主要章节,特别是一些有资源的,比如作协现任领导、报刊主编,都有专门论述。或者,你是个做生意的老板,也可以给你重点来一段——你懂的啦。
7
这几十年读书,叫我“服琢”的不多。
波伏瓦与法拉奇,章章令我称绝。我读《第二性》,下意识旁注,然后又摘抄;后来发现她几乎句句精彩,抄不胜抄。那还是上世纪的事。
萨特虽然创造了哲学的概念,但我不喜欢。他的文字乏味,理性有余,知性不足,更无趣味性。
8
读《谈艺录》,可以看到钱先生犀利吐槽:“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师。”
诚如是。混得好的弟子往往过河拆桥、忘恩负义,混得不好的弟子又如啃老族。所以,找不到合适传人,不如不带徒弟,省得累身又累心。
9
打工文学是深圳、东莞流水线上出来的写作者的胎记,怎么也洗不掉的。
10
山西运城是中国口水诗的发源地。
这就是唐代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1
韩石山最近说到给美女的两封信,其中一函言:有人问我,见好几个人在网上骂我,为何不回应?我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三流作家,可看他们骂我的口气,像是骂二流作家,叫我如何回应?
其实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有人气,就看他在网上有没有被骂。被骂得越厉害,说明关注度越高。
我最近抑郁的是,网上好久没有骂我的了,说明我已经不值得他们骂了。
12
文学还要有陌生感,陌生感就是新鲜感。
13
衡量纯文学作品的好坏首先还是看市场,上不了市场的不可能是优秀作品。有些作家忌讳这个,因为他们的书几乎都是公家扶持的,买书号出版,属公款消费。
当然,不一定是畅销书,但一定是常销书、长销书。一定要有读者的口碑,读者绝对不会被迫去读一本自己不喜欢又难读的书。
传统的营销方式是找一帮评论家,一阵表扬,但今天的读者已经不那么容易被骗了。真正的营销应该有正反,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还有唱黑脸的。争议就是最有效的营销。当年韩少功的《马桥辞典》首印仅三千册,张颐武说他抄袭,他说是移植,看客就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本书赚得盆满钵满。韩兄应该感谢张兄,大作家应该有大胸怀。
那天到深圳和唐小林一起吃饭,我告诉他,贾浅浅应该感谢你,否则天下谁人知。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那还要有人帮助出名才行。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名气也不一定有正反,只要出了名就对了,总比无人问津好。
纯文学作家可能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以为一味表扬才是正能量。其实,在明眼群众那里,公款表扬、私款表扬,后果是一样的。
14
惠特曼刚出道时,在跳蚤市场卖他自印的诗集,门可罗雀。他想出一招,给当时最牛气的诗人寄他的书,结果人家回信全都是批评和嘲讽,说他不适合写诗。他干脆将来信印在下一部诗集中,一炮打响,大路上走来朝气蓬勃的美国诗。
15
姜天民生前经常往我住的湖北省文联大院跑,我们经常在社科院门口的14路车站碰到,会聊几句。他获奖后也没架子,可惜死得太早,才三十八岁,没有享受到后来的文学福利。现在,曾写文章怀念他的周翼南也过身了。
世事如昨。我已经活到怀念别人的年龄,生活中,怀念已经成为一种经常的状况。一个人活得越久,怀念越多。
天凉好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