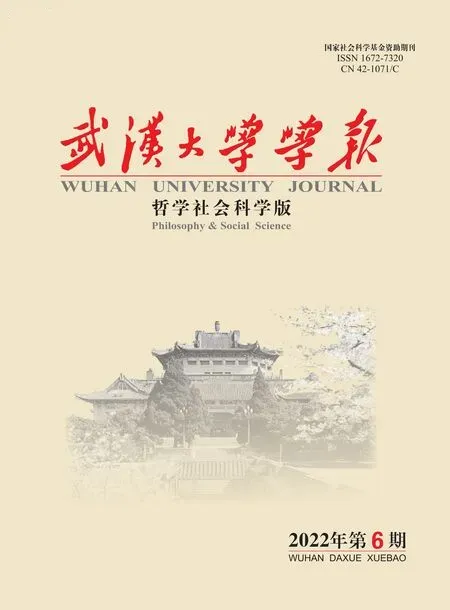元代草庐文人与他们的文学时代
邱江宁
元代草庐文人,是以吴澄为领袖,涵盖草庐讲友、草庐同调、草庐学侣、草庐家学、草庐门人等人群,大体以南方文人为主的文人群体。按《宋元学案》,元代思想体系被归为四家: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师山郑玉,就实际的影响而言,吴澄与许衡被推为南北学者之宗。吴澄继许衡之后,虽然登仕较晚,但其为学为教“主于著作以立教”[1](P556)。而且,吴澄出生于1249年,卒于1333年,一生横跨宋元两朝,学问大且寿高,有元一代文人受吴澄的影响既广泛且深远。对于元代文学以及文坛格局而言,吴澄本人文集“裒然盈百卷”,在创作上“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文章“尤彬彬”乎盛[2](P2210),而草庐文人中,无论程钜夫、虞集,再有范梈、元明善、贡奎、陈旅、王守诚、苏天爵、杜本、危素等,有元一代蜚声文坛之大家,又每在草庐彀中。
在以上看似周知的信息里,让人引为探究的问题是:程朱理学在元代被推为官学,所谓“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书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3](P658),而吴澄曾因“吴幼清,陆氏之学也,非朱子之学也。不合于许氏之学,不得为国子师,是将率天下而为陆子静矣”[3](P540)的攻讦愤而辞教国子学,《元史》又云“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4](P4313),这其中,草庐文人诚可谓其大宗,则元代文人所从所通之“经”到底是朱学还是陆学?其次,让人疑惑的是,蒙古人崛起西北,在平定西域、金朝等区域之后,人口总数尚不足300万,而南宋区域的人口约近5000万,人数最多,文明程度最高的人群,政治资源和社会地位却最边缘,南方文人最终是如何融入大一统的元代文坛并发挥其主体作用?再者,南人作为文明程度最高却政治地位最底的群体,其怨怼情绪本可想见,而元代文学在大一统时期却以雅正、清平为主体审美倾向,在这有些吊诡的现象里,蜚声文坛的草庐文人在其间的作为如何?他们到底从时代中汲取了怎样的精神进而成为元代文坛的中心,并推动着元代文坛风气的建设?本篇认为,草庐文人基于对大一统时代,疆域辽阔、文化多元、思想驳杂现实的理解,在哲学思想上和会朱陆,学宗朱子兼宗陆学;在人生态度上,隐忍精进,积极仕进与交游;在文风选择上,草庐文人倡导清和雅正之风,并借助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影响而令其审美倾向蔚为一代文坛风气。
一、“和会朱陆”思想与草庐文人的破局之功
所谓“和会朱陆”,是指吴澄把朱熹“格物致知”的笃实工夫与陆九渊“发明本心”的路径方法结合起来的倾向。《宋元学案》认为,“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5](P17)。吴澄乃朱熹的四传弟子,其研学基础得之于朱学,黄百家认为:“幼清从学于程若庸,为朱子之四传。考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朱熹),非北溪(陈淳)诸人可及也”[5](P3037)。吴澄及其引领的草庐文人在元代社会文化思想领域以及文学创作领域所获得的成功,不仅意味着南北文化争端中南方文化的胜出,也意味着南方文人在大一统时代破局努力的成功。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细述。
其一,为何吴澄会选择和成为元代和会朱陆的代表人物?这个问题无需进行太多辨析,吴澄的学源、地缘以及他自身的学养都意味着他很可能会成为朝着和会朱陆的学术路径建构他的思想体系。从学源上看,吴澄16岁到临汝书院正式师事程若庸,程若庸师从饶鲁,吴澄曾评价饶鲁的学术体系认为“朱子中庸章句、或问,择之精,语之详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邻于巧;惟详也,详之又详,流于多。其浑然者,巧则裂;其粲然者,多则惑。澄少读中庸,不无一二与朱子异。后观饶伯舆父所见亦然,恨生晚,不获就正之”,饶鲁与朱熹“不尽同”[5](P2812)的地方在于他的思想体系中已夹杂有陆学的东西[6](P731),而吴澄对饶鲁学问体系不尽同于朱熹的倾向却心甚戚戚,恨不与之同时,此亦可略见出吴澄和会朱陆的倾向。吴澄在师从程若庸之后,又师从程绍开。程绍开是陆九渊的弟子,又深受“安仁三汤(汤千、汤巾、汤中)”思想影响,他们在思想体系上学宗朱陆,尤其是汤巾,他“补两家之未备,是会同朱、陆之最先者”①《宋元学案·存斋晦静息庵学案》中王梓材案语引袁桷话云:“陆子与朱子,生同时,仕同朝,其辩争者,朋友丽泽之益,书牍具在。不百余年,异党之说兴,深文巧辟。淳佑中,鄱阳汤中氏合朱、陆之说,至其犹子端明文清公汉益阐同之,足以补两家之未备,是会同朱、陆之最先者。”[5](P2843)袁桷原文,出自《龚氏四书朱陆会同序》,云:“陆文安公生同时,仕同朝,其辨争者,朋友丽泽之益。朱陆书牍具在,不百余年,异党之说兴,深文巧辟,而为陆学者不胜其谤,屹然墨守,是犹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何益也?淳佑中,番昜汤中氏合朱陆之说,至其犹子端明文清公汉,益阐同之。足以补两家之未备。”[7](P1089)王梓材在案语中辨析认为,袁桷所述汤中乃汤巾之误。,所以,从学源上看,吴澄在思想倾向上和会朱陆是颇为顺理成章的事。从地缘上看,吴澄也完成可能成为和会朱陆的学者。吴澄“其先,自豫章之丰城迁居崇仁”[3](P859),是江西抚州崇仁人。在崇仁东边80公里外,是陆九渊的家乡金溪,陆学的发祥地,而再往西南80公里外是陆九渊讲学的象山书院所在地贵溪。南宋以后,陆学中衰,抚州亦成为朱子学的中兴之地,而抚州本土深厚的陆学基础,使它较诸其他地域更显现出朱陆融合的倾向,双峰学派、三汤之学即为典型。吴澄生于其间,得其风气熏炙,形成和会朱陆的思想倾向并不意外。
更重要的是,吴澄的学养为其成为元代和会朱陆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吴澄既以接续朱熹为己任,又对陆九渊这位乡邦前贤极为崇敬。就吴澄接续朱熹之学的一面来看,虞集在吴澄的行状有一段吴澄19岁时的豪气发愿,曾被人们反复引用:
近古之统,周子其元也,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盖有不可得而辞者矣……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于是以豪杰自期,以进于圣贤之学,而又欲推之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实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见,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为是,而自料所见,愈于人矣。[3](P859-860)
正因为“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吴澄一生着力于《五经纂言》,尤其是三礼,用力更勤。不仅因为三礼“多是记者旁搜博采、剿取残篇断简荟萃成书,无复铨次,读者每病其杂乱而无章”,极号难治;更因为朱熹非常重视三礼,却终老不及为,朱熹的学生黄幹、杨复虽曾用力于三礼,却也未能完成。所以,吴澄“研精覃思”,“凡数易稿”,在《礼记纂言》完成过程中“证之以经,载之以礼。于经无据,于礼不合者,则阙之”[8](P476),直至去世前,尤与门人手校以付刻。吴澄的《五经纂言》,完成了五经由汉唐的典制训诂转入宋元的义理疏注过程,这确是“朱子门人所不及”,也的确不愧朱子之继统[6](P736)。尽管如此,但吴澄对于陆九渊的崇慕之情溢于言表,认为“陆子有得于道,壁立万仞”[5](P1920),他在给《陆九渊集》的序言中写道:“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语如震雷惊霆,虽百数十年之后,有如亲见亲闻也……先生之教人盖以是,岂不至简易、切实哉!不求诸我之身,而求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悯也。今口谈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学者乎?果有一人能为先生之学者乎?于乎!”[9](P545)在吴澄所专注探研的《五经纂言》中,处处都体现出和会朱陆的倾向。
其二,草庐文人“和会朱陆”的倾向为何在程朱理学被推奉为官学的元代社会背景中,被其时学者所接受?且回到本节一开始就描述的发生在元代国子学中的争端。1311年,吴澄接受朝廷征聘,任职国子学。执教期间,将“朱陆和会”的理念灌注于教学中,招致以许衡弟子为主的北方学者的攻讦,他们“吴幼清,陆氏之学也,非朱子之学也。不合于许氏之学,不得为国子师。是将率天下而为陆子静矣”,争端实际涉及南北文化资源和文化权力的竞争,最终吴澄于1312年二月“一夕谢去”,执教时间不及一年。虞集在《送李扩序》中认为,许衡任职国子学期间,彼时“风气浑厚,人材朴茂”,蒙古、色目贵族弟子尚不知朱子学,故而“表章朱子小学一书以先之,勤之以洒扫、应对,以折其外,严之以出入、游息,而养其中。掇忠孝之大纲,以立其本,发礼法之微权,以通其用”,教授的是一些皮表纲要的内容;尚未及于“发理义、道德之蕴,而大启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极致”。所以吴澄“之为教也,辩传注之得失,而达群经之会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极先圣之阃奥。推鬼神之用,以穷物理之变,察天人之际,以知经纶之本。礼乐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据援引,博极古今,各得其当,而非夸多以穿凿。灵明通变,不滞于物,而未尝析事理以为二”[3](P539-540)。
事实上,吴澄在学术体系中选择和会朱陆,既在于他对固守门墙的朱门、陆门子弟的痛心,更是理学自身发展和研习所必须,吴澄认为:“夫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读书讲学;陆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实践。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而入。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呜呼!甚矣,道之无传,而人之易惑难晓也,在吴澄看来,朱、陆二人都是读书讲学者,亦都是真知实践者,学者必须会通二氏,才能得探知真正的理学内核[11]。
其三,草庐文人和会朱陆的思想倾向在其时宗教信仰多元的文化平台中具有怎样的意义?蒙古人对于其统治和管辖下的区域,往往“因其俗而柔其人”[4](P4520),“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12](P2217),让人们按照自己本民族的宗教以及思想文化信仰生活。所有宗教都具有精神慰藉和灵魂皈依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Point-d'honneur],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3](P1-2)在元代,所有的宗教都得到了尊重,可以在开放的平台上竞争,某种程度而言,这样一种现实背景对于元代儒生们的朱陆和会选择具有很强烈的刺激意义。尊德性和道问学乃是朱、陆两家在思想方法论上的重要争端,但在吴澄看来,陆九渊、朱熹、二程并无实质的不同,“论之平而当,足以定千载是非之真者,其唯二程、朱、陆四子之言乎!”[10](P351)吴澄认为:“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如果哲学不能解决精神皈依的问题,仅有道德与学问的戒律和约束,是很容易让人倦怠和怀疑的,正如吴澄在自己的教学与研习中所坚持的那样:“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果如陆子静所言矣,今学者当以尊德性为本,庶几得之。”[3](P862)
吴澄“朱陆和会”的这一理学探研路径被他的学生虞集围绕国子学的那场纷争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归正表述。在虞集看来,许衡解决的是入门功夫,但在元代那样一个草莽定国,信仰多端的社会里,许衡“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其功劳无人能过,故而“数十年彬彬然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矣”,此虞集所谓“文正之功甚大也”。在虞集看来,许衡与吴澄的区别没有争端者所谓的那么尖锐,不过是不同形势下,“立教有先后”的区别而已。作为后来者的吴澄,他对于朱子学的意义在于,真正“使学者得有所据依”,学者经过吴澄的教授点化,则学问可以落实于“日用常行之地”,而“日用常行”在精神和心灵上也“有所标指”,只有这样,学者与学问之间才能日研月磨,臻至于“归宿造诣之极”[3](P540)。
虞集认为,吴澄“朱陆和会”的理学探究路径不仅当世,哪怕“近世以来,未能或之先也”[3](P540),这并非仅仅出于弟子对老师的回护,而是虞集或者说是草庐文人基于对元代社会现实清晰认知后的判断。在元代社会多民族、多文化的碰撞环境中,在统治者信奉宗教的力量,并允许多元宗教并存的现实里,如果让儒生们长久地依靠道德的力量坚持问学,而问学又不解决精神上的信仰旨归,那么不仅是汉地哲学思想无法更广泛地推衍,而且儒生们最终也有可能十百数千地“窜名道籍”[14](P31)、被其他宗教所吸引。反之,如果能朱陆和会,“以朱子所训释之《四书》,朝暮昼夜,不懈不辍,玩绎其文,探索其义。文义既通,反求诸我。书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实用其力。明之于心,诚之于身,非但读诵讲说其文辞义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陆子之所以教也”[10](P141-142),使学问的探研入于精神与心灵的平和、渊静,才能真正吸引住学者,并使程朱理学立足于宗教多元、文化思想猬集的时代而不被淹没。这不仅是对程朱理学的救赎,也是草庐文人的时代破局之选。而吴澄及其引领的草庐文人对于元代文人的影响不仅在于他们以著述立身,影响深刻,更在于许多草庐文人“多居通都大邑,又数登用于朝,天下学者四面而归之,故其学远而彰、尊而明”[3](P556),就这一表述而言,元代的程朱理学固然宗朱,其内里实际是朱陆和会,而这也是草庐文人为核心的南方文人突破南方,大举北进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南人北上潮流与草庐文人的成局之力
草庐文人程钜夫在北廷的斡旋和努力,推动了至元二十三年(1286)的江南访贤行动,此后,南方文人开始大举北进。这对元代的文化以及文学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方文人大举北进的过程中,草庐文人的表现尤为突出,之所以能如此突出,又因为草庐文人在“人和”方面都有着其他南方区域不可比拟的优势。这种“人和”优势自然不能脱去程钜夫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草庐文人的内在精神动力。而随着南人北进力量的加强,金源文人群体一家独大的京师文坛格局被打破,具有元代文化特色的南北融合局面逐渐打开。
(一)吴澄的北进态度与南人北进风潮的前奏
毫无疑问,人们很容易将元代南人北进风潮的掀起归功于程钜夫所代表的官方力量,而事实上,没有内在精神指导和动力驱使,官方的鼓励只能令极少数人改弦更张,真正掀起风潮的背后都是思想的驱使,吴澄在南人北进风潮中的北进态度极值得关注。据《元史》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己巳,程钜夫以集贤直学士再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十一月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江南名士到达大都,而《吴澄年谱》载,程钜夫至元二十三年八月至抚州,欲征请自己的同学吴澄出仕,吴澄以母老谢辞,程钜夫遂邀吴澄作中原览胜之游,吴澄许行。至元二十四年春,吴澄由京师返回南方,与得旨南还的程钜夫同行。由吴澄当时的文章来看,此次中原之行应该动摇了他居乡一隅著书立说的想法,和程钜夫一样,他也期望在一统的时代中努力作为。可以看到吴澄在南归之际回复赵孟頫的送别诗写道:
……宋迁而南,气日以耗,而科举又重坏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际之文往往沽名钓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无怪。其间有能自拔者矣,则不丝麻、不谷粟,而罽毯是衣、蚬蛤是食,倡优百戏、山海万怪毕陈迭见,其归欲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为文也,为一世之人所不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遗乎今,自韩以下皆如是。噫!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为文;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为人。海内为一,北观中州文献之遗。是行也,识吴兴赵君子昂于广陵。子昂昔以诸王孙负异材,丰度类李太白,资质类张敬夫。心不挫于物,所养者完,其所学又知通经为本。与余论及书乐,识见夐出流俗之表。所养、所学如此,必不变化于气。不变化于气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10](P93)
尽管这篇序言表达的是文章写作理念的问题,但在吴澄看来“文者,士之一技耳,然其高下与世运相为盛衰”[10](P131),读书之意义在于成为儒士,而“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10](P523)。而且文章是写给作为宋宗室而出仕元廷的赵孟頫,并盛赞其“识见夐出流俗”,可见吴澄对赵孟頫出仕的肯定,而这种肯定中包含着对这个一统时代的认同且期望作为的心思。这可以从同一时期吴澄写给程钜夫的一篇题记看得更明显:
集贤学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而亲舍乃数千里。今以行台侍御史,得旨南还,庶几便养;而回望阙廷,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乐;日以远者,人臣之忧,此远斋所为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于君亲也,一以朝夕左右为乐,然亦难乎两全矣。子之爱亲,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无所逃于天地间。惟其所在而致其道,岂以远近间哉?余既从公观光于上国,又将从公而南。与公同其乐而不同其忧者,思有以纾公之忧焉,为是言也。或曰:“近多惧,远多誉。人所乐而公忧之,何也?”之言也,读《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何足以知公之心,吴澄书。[10](P456)
据程钜夫自己所作的《远斋记》的题尾所书知道该文作于“至元二十四年夏五甲寅”,而吴澄题曰《题程侍御远斋记后》,基本与他回复赵孟頫送别诗的时间相近,而吴澄在给程钜夫的题记中更直接地表明,“臣之事君,无所逃于天地间”,他期望为程钜夫纾解、分担其人臣之忧。吴澄的这种态度影响深远,直接触动了草庐派文人,令他们不惮于大举北进。如果说在程钜夫江南访贤之前,京师文化圈几乎是金源文人的天下,他鹤立期间努力周旋的话,那么,在他南下访贤之后,南方文人大举北进,这种情况也因此大为改观。尽管这其中本来就有南方士人需要出仕的内在动机,但吴澄作为南方尤其江西士人的精神领袖,他的行动以及精神理念对于南方尤其是抚州籍士子们的引导作用却很不容忽略。元代抚州士子的科举成绩实际也沿承之前南宋的成绩名列前茅,甚至更加出众。据萧启庆先生统计,元代抚州进士数居江南诸路的第2名,比南宋时期的第13名足足提升11个位次。尽管数量上,宋代抚州进士高达445名,元代名姓可考者却只有17名[15](P189,193)。
从程钜夫开始,在京师文坛获得巨大声誉的江西文人,吴澄、虞集、揭傒斯、范梈、傅若金以及之后的周伯琦、危素等,都是草庐文人。应该说,1287年以后,“人和”的优势给予包括草庐文人在内的南方文人京师谋得仕进机会极大的便利,多方面地证明草庐派文人在程钜夫以及吴澄的引领下大举北进的事实。
(二)草庐文人的北进态度与南人北进风潮的掀起
在南人北进风潮中,由于草庐文人的积极态度以及他们师友门人之间相互提携、带挈,极大地推动了南人北进风潮的掀起。
就率先引领和力推南方文人北进的草庐文人程钜夫的贡献而言,江南访贤之外,他还借助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不断提携和荐用南方有才华、有影响力的士大夫,“所荐士皆知名”,甚至“多至大官”[7](P1531)。据袁桷的一段描述可以侧见程钜夫对南方文人的荐引之力:
桷在翰苑时,尝以君荐于承旨程公,程公曰:“吾固知之。得无以南士累乎?”相笑而止。[7](P1379)
程钜夫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的访贤江南行程中,曾到四明征袁桷之父袁洪出仕,袁洪拒绝了,但程钜夫与袁家的密切关联并未中断。大德元年(1297),袁桷在程钜夫联同阎复、王构荐举之下,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在这段话中,袁桷表述,他曾想通过程钜夫的关系荐引金华士子潘弼,但程钜夫表示,因为他荐举的南人较多,引起了朝中北人的注意,所以潘弼的南人身份,影响到了程钜夫的荐举。尽管如此,还是能看出程钜夫在南人北进风潮中的努力。
不仅有程钜夫在朝中鼎力推动南人北进,草庐文人中,还有一批崇信草庐学派的北人,他们也是接引南人北进的重要力量,例如董士选、元明善等。董士选,乃汉地世侯董文炳次子,位至陕西行台平章政事。“在江西,以属掾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学教授。迁南行台,又招汲子集与俱,后又得范梈等数人,皆以文学大显于时”[4](P3678-3679),如所述,草庐文人中文学成绩最突出的两位弟子虞集、范梈都是通过吴澄,由董家西宾而进入翰苑,影响京师文坛的。之后,范梈又向虞集举荐自己的同乡兼爱徒傅若金。范梈的举荐信写道:
山居乏江海之使,无由上记,即日伏想神相,台候起居万福,某株守碌碌耳。近来武昌,与乡友傅汝砺会。其人妙年力学,所为诗赋,警拔可爱;其为人,静慎又可尚。谓将北行,介之以见,无他。出门而瞻望泰山、黄河以洗穷乡之卑陋,此其志也。与语,当知仆之非妄,末由参侍,更冀以斯文自爱。不宣。[3](P1220)
虞集、揭傒斯等人都非常欣赏范梈。而范梈推介的同里兼学生傅若金颇有乃师之风,也因此迅速获得京师文人尤其是草庐文人的重推。据苏天爵给傅若金所作墓志铭载,“至顺三年(1332),新喻傅君与砺挟其所作歌诗来游京师。不数月,公卿大人知其名,交口称誉之。蜀郡虞公、广阳宋公方以斯文为任,以异材荐之”[16](P213),而虞集也在给傅若金的序言中说:“德机之里人傅君与砺,始以布衣至京师,数日之间,词章传诵,名胜之士无不倒屣而迎之,以为上客。台省馆阁以文名者,称之无异辞”[17](P4),苏天爵和虞集的载记可以拼贴出傅若金在京师文坛获得接纳的完整信息。傅若金拿着范梈的信找到虞集,之后,通过虞集,并在虞集、宋本等人的推介下,逐渐在京师文坛声名鹊起。藉由声名,傅若金获得仕进机会,1333年傅若金即作为群玉内司丞、吏部尚书铁柱,礼部郎中智熙善的辅使出使安南。
此外,再如草庐讲友熊朋来,草庐门人元明善曾大力向朝廷举荐他: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礼,亲御衮冕祠太庙,奋然制礼作乐之事,朝之大儒缙绅先生,凛然恐不足以当上意。而翰林学士元公明善飏言于朝,以先生为荐。[3](P939)
除了显明的由荐举而获仕进的成功案例外,还有许多虽在京师获选,却在北进风潮中获得机会的例子,此中最可引为典型的是草庐门人夏友兰。吴澄曾记其事云:
予在国子监,幼安白慈亲,愿观国光。亲许,遂趋京师,又趋上都,觐日表于潜邸,得旨从集贤大学士李公游,出入禁闼必从。明年,龙飞御极,李公秉政,奏授将仕佐郎、同知会昌州事。[18](P507)
夏友兰,字幼安,初名九鼎,抚州乐安曾田人,曾在邑东门外创建书院,施田赡给,敦请名儒詹崇朴掌教。至大期间,吴澄被征请至国子监任教,而夏友兰即藉吴澄的关系观光上国。不仅如此,夏友兰还跟随官员们一同前往上都,并得以觐见时在潜邸的元仁宗,并得到仁宗的准许,跟随李孟游学,“出入禁闼必从”,由此,仁宗登基,李孟执政,夏友兰奏授将仕佐郎、同知会昌州事。案例远不止上述这些典型例子,充斥于草庐学派成员作品中的送行序、赠序往往都是他们的举荐信[19](P53-57),可以说,草庐门人北进的积极态度,不仅推动了南人北进的风潮,更是南人北进潮流中的中坚力量。
(三)草庐文人推动南人北进的文化愿景
对于程钜夫、吴澄等人来说,力推南方士人北进,不仅仅只是期望个人出仕,更期望的是有以施加影响,从而使包括南方文人群体的利益,更包括他们所承载的文化能被蒙古统治者所关注并在政治体制中有所体现。
典型如草庐学侣中的熊朋来,虞集载其事迹云:在其连任福建、庐陵两地提学教授之际,“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调律吕协歌诗以兴雅乐,制器定辞,必则古式,学者化焉。故其为教有不止于词章记问云者”,又载“初,先生以《周礼》首荐乡郡,而今制《周官》不与设科,治《戴记》者,又绝不见。先生屡以为言,后得周尚之以《礼经》擢第,习此经者渐广,由先生启之也”[3](P939),则南方文人身体力行,期以绵薄之力而撼顽主的心思隐约若现。而刘岳申《送吴草庐赴国子监丞序》则相对明白清晰地表达了南方士人的心意:
至大元年秋,临川吴幼清先生以国子监丞征,当之京师,郡县趣就道者接乎先生之门。明年三月,先生至洪,门生儿子从先生行与送先生而返者,咸相与言曰:“先生有道之士,不求闻而达者也。监丞七品,其进退不为先生轻重加损也审矣。”或曰:“官虽卑,以教则尊,教胄子又尊。”或曰:“官无卑,君命也。以君命教胄子,先生之任不既重矣乎。方今出宰大藩,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以故中州之人虽有杰然者不在是任,然则南士愈不敢望矣。使先生以道教胄子,他日出宰大藩与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门。是犹先生之志得而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先生不宜卑小官以弃斯道斯民之福也。”或曰先生出处进退有道,众人固不识也。先生尝以翰苑征至京而不就列,又当劝学江右至官而不终淹,今其久速未可知也,由此大任亦未可知也。临川自王氏以文学行谊显,过江陆氏以道显,至于今不可尚。先生出乎二氏之后,约其同而归于一,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者,盖兼之矣。使先生之学行,岂复有遗憾哉。将天下有无穷之休,而复临川有无穷之闻。以临川复显于天下,必将自今始。[20](P416-417)
刘岳申的这篇序言既代表他本人,其实也深刻地传达着整个南方士人阶层的意愿。他们对吴澄即将在国子监任职以及由此所可能带来的文化便利寄予了殷切的期望[21](P40-48),人们无所谓这个席位是否有称于吴澄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身份,只殷殷地期待吴澄能够通过教授胄子的关系改变那些掌管着元朝士民命运的出宰大藩和天子左右大臣,令其学行彰显于南北天下。吴澄也的确不愿孚于众望,在其任职国子监期间,“旦燃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4](P4012),比之当日许衡教授蒙古、色目子弟的认真执著有过而无不及之处。南方士人殷切如此,那将令已然凭借时间优势而把持朝中文化资源的金源文人怎么办?早在程钜夫奉旨下江南访贤之际,金源文人中的有识之士魏初有诗《送程侍御钜夫》写道:
一封丹诏九天来,御史青骢翰苑才。廊庙久劳思稷契,丘园初不望邹枚。定知天下无双士,正在君侯此一回。自昔楚材为晋用,中原麟凤莫深猜。[22](P378)
魏初的诗在理解朝廷态度倾向的同时对程钜夫的南方访贤之行表示肯定和支持,同时也期望中州士人不以此为猜,可以和衷共济。魏初的诗未尝没有表示出中原文人对程钜夫江南访贤之行的隐然防猜意思。事实也的确是。由前所述,以许衡派为中心的苏门山文人群与吴澄、虞集等所代表的南方文人群发生了较为激烈的辩争,并最终以吴澄的辞职而宣告南方文人群的落败[23],这也表明率先在蒙古朝廷获得文化资源的金源文人确实对北进的南方文人深感不安和排斥。
表面上,吴澄在国子监的教学改革由于南北文人群对文化资源的争夺而失败,由南北文人所共同推动的蒙古朝廷的开科取士也以许衡所教授的朱子《四书》学为据,而没有纳入吴澄及草庐学派所推崇的和会朱陆,同时注重五经学习的理路。事实上,吴澄从至大三年(1310)到皇庆二年(1313),在国子监的时间有三年多。期间,草庐文人的作为值得注意。可以看到,范梈于至大元年开始在董家做家庭教师,至大二年(1309),吴澄为国子监丞,虞集为国子助教;至大四年,吴澄任国子司业虽然在北方文人的排挤中愤而回南方,但此后,延祐年间,拜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行至中途,以疾辞。至治三年(1323),超拜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进阶太中大夫(《神道碑》)。泰定元年(1324),任经筵讲官。二年,主持修撰《英宗实录》之后,南方文人中虞集曾任国子博士、祭酒;贡师泰曾任国子监司业;危素任国子助教、国子监丞;吴皋任国子助教、博士、监丞、司业;王彰任国子博士;陈旅任国子助教、监丞……草庐学派成员通过教授胄子的关系改变那些掌管和改变着元朝士民命运的出宰大藩和天子左右大臣的进程并没有因为吴澄的辞职而中断过[24](P16)。随着南北融合的深入,以草庐派门人弟子为代表的大批南方士子的北进以及他们在创作上的巨大成绩,对北方文坛而言,“独东平之士什居六七……他郡仅二三焉,若南士,则犹夫稊米矣”的局面不再,而伴随着南方文人在北方“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7](P1210),相互提携援引,由程钜夫所开启的元代文坛的南北融合其实已打开局面。李治安先生认为:在元代的政治体制以及多项制度中,儒学与科举是保留南制因素最多,同时也最能体现南制优长的方面。南方儒士藉北游京师、充任家庭教师等方式,亲近蒙古贵族,在谋求利禄的同时又对蒙古贵族施加先进文化的影响。仁宗恢复科举,应是南制因素滋长并冲破蒙古旧俗束缚,得以上升为全国文官选举通行制度的突出成绩[25](P59-77)。这个观点非常有见地,但是在南方儒士大量北进并对蒙古统治者施加影响的过程中,关于南方文人特别是以草庐文人为中心的江西文人与北方尤其是以金源文人为主体的北方文人之间的冲突实际更生动细致地影响着元代文化包括文学创作特质以及文学格局的形成。
三、清和雅正风气与草庐文人的时代影响
从元代的族群人数比例来看,元朝总人数大约六千万。江南一统之际,南宋治下的人口数量约近五千万,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色目人只有几百万,而且元朝南人地位最低,文明程度最高的文人儒士在元朝所获得的发展空间极为有限,诚如戴表元所云“大江之南,民齿多者,以约计之,郡不下三十万男子,幸而为儒者,居千之一。而幸能以名字自通于上、以取荣禄显仕者,居万之一。其选可谓至艰,而得之可谓劳矣”[26](P184)。按照一般道理,南人的怨怼情绪可以想见,但元代大一统时期的文学道却以清和雅正为主体审美倾向,在这有些吊诡的现象里,蜚声文坛的草庐文人在其间的作为如何?事实上,应该是以草庐文人为代表的江西文人群体大力推动了元代正统文坛清和雅正的审美风气,进而也成就了他们的文学时代。如果说吴澄主张“朱陆和会”代表的是综观社会和时代现实情形之后,力求破除门户之见以获得汉地哲学发展上的内在升华,程钜夫等草庐文人大力推进南人北进,是力求破除民族偏见以获得南方发展的适时之选,那么清和雅正的审美风气则是草庐文人为代表的江西文人群对现实社会清晰观照之后的平衡理念体现。
与鲁斋、静修等学派相比,草庐文人在文学上的成绩可谓斐然,元代诗文创作:从至元之际的“庞以蔚”,到元贞、大德之间的“畅而腴”,至大、延祐时期的“丽而贞”,泰定、天历阶段的“赡以雄”[27](P78),尤其是后面两个阶段,草庐文人的贡献又诚可谓大,而“丽而贞”“赡以雄”,又可以“清和雅正”四个字来综合论定。
(一)消除情绪之偏的清和
程钜夫曾尖锐批评的宋季作文风气说:“数十年来,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滔滔晋清谈之风,颓靡坏烂,至于宋之季,极矣”[28](P157),这一点,吴澄的态度与之非常一致:
古之诗皆有为而作,训戒存焉,非徒修饰其辞、铿锵其声而已。是以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汉、魏犹颇近古,齐、梁以后靡矣。流连光景,摹写物象,敝精竭神,而情性之所发、意义之所托蔑如也。唐宋诗人如山如海,其追蹑风骚者固已卓然名家,然有之靡益、无之靡损者,亦总总而是。[10](P378-379)
吴澄对于文学创作非常关注,在文集中留下近200篇的诗文评论①按:这个数据以《全元文》为统计基础。,在许多的诗文评论中,吴澄承认社会的重大变化,都强调创作须“有为而作”,要求创作能关注现实,清和平易。在吴澄的这段评论中,他的核心观点是强调创作的有为而作,这种有为是基于对现实的观照而体现出的内容表达上的可观、可群、可怨。在吴澄看来,“当今天下一统,日月所照,悉为臣民,开辟以来之所未见。殊陬绝域,异服怪形,人所骇栗者时获目睹”[10](P546-547)。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吴澄曾有一段很长的议论:
今日之事,有书契以来之所未尝有者。自古殷周之长、秦隋之强、汉唐之盛,治之所逮,仅仅方三千里。今虽舟车所不至,人迹所不通,凡日月所照,霜露所队,靡不臣属,如齐州之九州者九而九,视前代所治,八十一之一尔。自古一统之世,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今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睢盱万状,有目者之所未尝睹;吚嗢九译,有耳者之所未尝闻。财力之饶,兵威之鸷,又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10](P115-116)
吴澄认为“宋不唐,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复少”[10](P93),时代总在变化之中,元王朝所出现的人与事,可谓“有书契以来之所未尝有者”,在阎立本所处的隋唐时代,看见番外进贡的狮子时即骇异无比,故图画而形容之以示后来不见者,而在元代,“远方职贡,靡所不有,虽未观画,已稔见之矣”[10](P554)。古代强调“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对于多元文化和信仰并存的元代而言,这种理念则未必可行,也不一定必须行。如果史家、作者再拘于方册之所记载,而无视罔听于耳目之见闻,就是一种缺憾了。也正是承认现实之变,强调现实变化对于创作的深刻影响,更承认元王朝赋予作家们的现实是前所未有的多变且令人骇栗,对于包括绝大多数生长南宋治下的作家而言:“观山河之高深,土宇之绵亘,都邑之雄大,宫殿之壮丽,与夫中朝巨公之恢廓严重。目识若为之增明,心量若为之加宽”,则众不免生出“此身似不生于江南遐僻之陬”的感慨[10](P104)。所以吴澄特别强调创作对现实的关注,认为这样“不但诗进,而学亦进矣”,所谓“诗境诗物变,眼识心识变,诗与之俱变也宜”[10](P474)。因为强调对现实的兴观群怨,吴澄对于流连光景,镂心于物象、辞藻、声腔的创作有些蔑如,以为这些创作实乃“有之靡益、无之靡损者”。他认为,“唐宋以来之为诗,出没变化以为新,雕镂绘画以为工,牛鬼蛇神以为奇,而《周南·樛木》等篇何新之有?何工之有?何奇之有?……辞达而已,不惟新、惟工、惟奇之尚。大篇舂容,短章参错。”[10](P382)以其温柔敦厚的经学家身份而论,吴澄的这个创作态度已经相当壁垒鲜明了,一如程钜夫在指陈宋季文风之弊的激烈程度:“《六典》之经邦国,《大学》之平天下,于理财一事甚谆悉也”,“士大夫顾不屑为,直度其不能而不敢耳,诡曰清流,以掩其不才之羞”[28](P157)。
虞集继承程钜夫以及其老师吴澄等人的思想,在理论批评中也每每反复强调以务实的态度,深省顺处,去除逼仄忿厉的情绪,用涵容博取的态度来完善自己的创作修养,做到“与造物者同为变化不测于无穷焉”[3](P499),以“涵煦和顺之积,而发于咏歌”[3](P490),形成至清至和的雅正创作风格[29](P62-74)。正如虞集的一段评论所云:
“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风来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则不足于东,既亏则不足于西,非在天心,则何以见其全体?譬诸人心,有丝毫物欲之蔽,则无以为清;堕乎空寂则绝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汩汩,一日千里,趋下而不争,渟而为渊,注而为海,何意于冲突?一旦有风鼓之,则横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则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动之风,其感也微,其应也溥,涣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诸人心,拂婴于物则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过,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于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3](P755)
虞集认为月至天心,方能朗照四境;水若至平,才可涣然生纹。站在时代多民族共存、南北融合的高度,虞集的“清和”论表达了那个时代应有的审美追求。虞集认为,只有摒除物欲之褊狭与遮蔽,才能以清明澄澈之心发见世界之全貌;如果能趋下而不争,无意于冲突,则能如水一般,溥畅明达,涣然成章。
(二)清和基础上的雅正
基于对现实清和平易的观照立场,其创作上的雅正则“非学非识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气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备,文其能以纯备乎?或失则易,或失则艰;或失则浅,或失则晦;或失则狂,或失则萎;或失则俚,或失则靡”[10](P325),基于此,吴澄对元明善的创作评价非常高:
学士清河元复初,自少负才气。盖其得于天者异于人,而又浸淫乎群经,搜猎乎百家,以资益其学,增广其识,类不与世人同。既而仕于内外,应天下之务,接天下之人,其所资益增广者,又岂但纸上之陈言而已!故其文脱去时流畦径,而能追古作者之遗。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艰;明而非浅,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韩子之堂者,不于斯人,而有望欤?[10](P325)
元明善作为终身服膺于吴澄的北方弟子,他的创作所以得到吴澄由衷认可的原因在于:他的创作从学养上看,有浸淫于群经,搜猎于百家的基础;从见识上看,因为仕宦南北,阅尽“天下之务”和“天下之人”,所以他才能真正脱去金、宋以来的时流之弊,创作风格表现为坦正而不率易,奇特而不艰涩,明畅而非浅淡,深邃却不晦暗。它不狂放也不萎缩,不俚俗也不淫靡。这是怎样的风格呢?吴澄在给吴全节的诗序中指出:这种创作首先是有着尝从硕师,博综群籍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有着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胸襟,所以才能切实平和地描述世界,令天下寒士“一览观焉,如身在辇毂之下,而睹熙朝之弥文”[30](P177-178)。它是人们身处“四海一统之时,际重熙累洽之治”的现实,不禁“太和之气贯彻于身,表里冲融”,故表现于创作“如风雷振荡,如云霞绚烂,如精金良玉,如长江大河”,虽涵泳变化,却“字字鸣国家之盛”,迥异于那种寒涩固陋、困顿穷愁情形下的凄凉、愤懑甚至激烈。这样的创作“事核而辞达,不藉难识之字、难读之句为艰深”[10](P475),具有可以群、可以观、可以兴的特点,能够真正呼应元王朝疆域辽阔,多民族、多政体、多地域、多风俗,有着不同文化、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交流、联系、共鸣的需要。
在吴澄的诸多文章中,《南安路帝师殿碑》即算得上是清和雅正风格的典型体现:
皇元国音与中土异,则尤非旧字之所可该。帝师具大智慧,而多技能,为皇朝制新字。字仅千余,凡人之言语,苟有其音者,无不有其字。盖旧字或象其形,或指其事,或会其意,或谐其声,大率以形为主,人以手传而目视者也。新字合平、上、去、入四声之韵,分唇、齿、舌、牙、喉七音之母,一皆以声为主,人以口授而耳听者也。声音之学出自佛界,耳闻妙悟多由于音,而中土之人未之知也。宇文周之时,有龟兹人来至,传其西域七音之学于中土,有曰娑陀力,有曰鸡识,有曰沙识,有曰沙侯加滥,有曰沙腊,有曰般赡,有曰俟利箑。其别有七,于乐为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七调,于字为喉、牙、舌、齿、唇、半齿、半舌之七音。此佛氏遗教声学大原,而帝师悟此,以开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18](P362-363)
引文所展现出来的吴澄视野与胸襟的开阔很引人注目。他立足于现实,在承认大元统治的基础上,深刻体认中原文化有所不及的地方。吴澄认为中土文字主于形而忽于声,获取知识的渠道主要源于见,中土之人不能认知到声音之学的玄奥,对音的辨识和理解非常有限。当大元王朝的疆域极为广泛,人员氏族以及文化背景极其不同时,倘若用汉字来上传下达各方旨意时,汉字书写繁难杂多,声读发音不够完备的弊端就非常明显,吴澄对于八思巴文字意义的认知,的确是站在国家高度、社会广度和学术深度上考察和认知后的表述。文章更值得注意的依旧是吴澄写作中所呈现的与程钜夫非常相似的对现实的平视与拥抱态度。王磐在给八思巴的神道碑中曾用简洁的语言一句带过八思巴文字创制的意义:“师独运摹画,作成称旨,即颁行朝省,郡县遵用,迄为一代典章”[31](P260),但这种文字的独特性、时代意义到底如何,王磐其实并未详述。而由上所引吴澄的表述,则能清晰地感受到吴澄对于八思巴文字迥异于汉字的独特性认知的理论高度。与汉字最根本的不同点在于,汉字主形,八思巴字主声;汉字书写千变万化,但发声读音却不与之相应,而八思巴字则字形不繁,字数不多,发声完备。相比于汉字,八思巴字字不盈千,却唇、齿、舌、牙、喉所发出之读音无不包括,“于是乎无无字之音,无不可书之言”,契合了忽必烈“译写一切文字”的期望[4](P4518),从而作为国家意志传达的工具从中原中州一直到“极东极西极南之境”,“人人可得而通焉”。吴澄深深感慨,八思巴字的创制诚可谓文字创造发展史的一大助推。吴澄的这层感慨意义不仅在于承认八思巴文字的伟大,更在于他作为文字文明高度成熟、发达的华夏子弟,承认异质文明的独特性和对华夏文明的补充与推助意义。这种胸襟或许也是吴澄及其所引领的草庐学派子弟推动江西文人群在大元文化语境中大领风骚的重要基础。
历数江西人在元代社会的活动能量,可以看到,除了“元诗四大家”占去三席,有虞集、揭傒斯、范梈外,而且元代文坛的盟主,虞集之后,有揭傒斯,揭傒斯之后还有危素、周伯琦等承接有序,代为领袖。以草庐文人为核心的江西文人群体不仅获巨大声名于元代文坛,在政治领域有程钜夫,哲学领域有吴澄,宗教领域有吴全节,艺术领域有青花瓷,地理领域有朱思本的《舆地图》,汪大渊的地理纪行著作《岛夷志略》,语言领域有周德清及其《中原音韵》,这些人及作品在当时甚至当下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容置疑的是,在江西文人驰骋文坛之际,其他地域,北方如金源文人以及西域文人等;南方如浙江文人、姑苏文人同样成绩斐然,但与江西文人在京师文坛的影响力相比,则逊色一筹。尽管江西作为南宋治下区域学术、文化的中心,诗文创作一直繁盛,但南宋治下文化的中心更在浙江①徐永明、黄鹏程《〈全元文〉作者地理分布及其原因分析》指出,元季东南作家人数尤其以浙江为最多。即便以现今所留存诗文作品的绝对数量而言,东南作家作品依旧最多。,而且若论政治优势,起初占有绝对优势的金源文人群或者更有政治优势的西域文人应该更有话语权。如果说程钜夫作为借助政治斡旋和政策的力量为草庐文人为代表的江西文人群通向大都、进入元代文坛中心导夫先路的话,那么吴澄则从思想境界及创作理念上引领和指导一大批草庐文人及江西子弟放开心扉,不立崖岸,负笈北上,不负所学。在元代社会多元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吴澄作为江西文化的代表,引领士众,创作上观风务实,以和会包举、雍容大气之态黼黻时代,确立了他们自己在元代文化领域的中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