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而来的“大神”:日结体制与悬浮社会
黄斌欢 深圳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节选自《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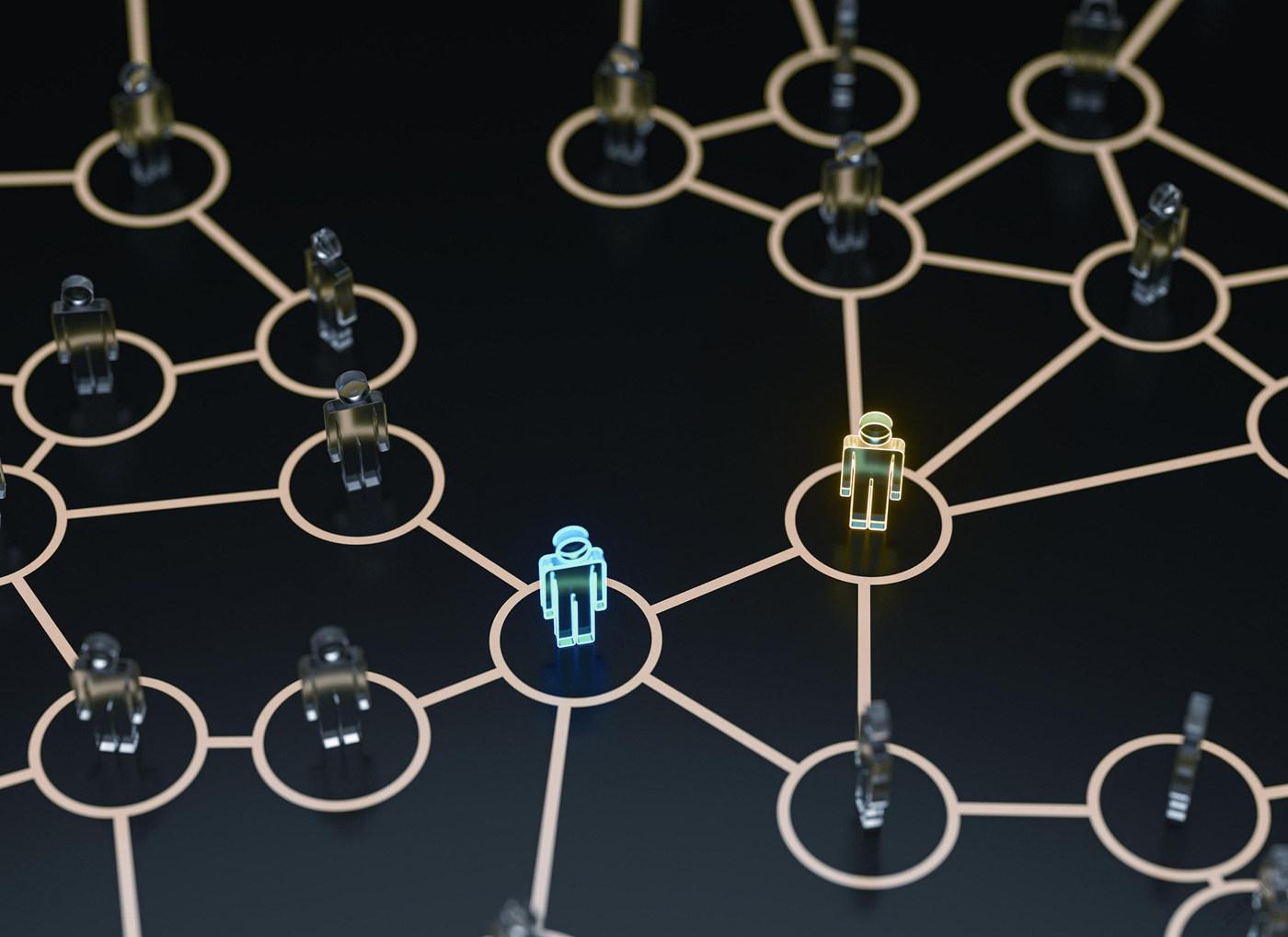
如果说“悬浮社会”是以“大神”为代表的新一代劳动者突出的特点,那么为何不同代际的劳动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面貌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40年来,中国第一代劳动者在“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下,虽然家庭分散、无法团聚,但是都努力通过给家庭汇款、再嵌入消费的方式努力“做家”。在第一代农民工看来,老家的社会生活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主角”,而城市工厂的劳动只是工具性的“配角”。老一代农民工要完成家族绵续的重任,在农村的面子竞争中努力向上流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离开农村老家进入东部沿海工厂工作,为的是完成人生的关键任务。可以看到,将这些农民塑造成为工人背后的社会过程,并非来自城市生活,而恰巧是基于农村社会生活的锻造。他们的根紧紧地联系着农村,这就是第一代劳动者劳动付出背后的社会观念,也是支撑着第一代劳动者温顺、顽强、高忍受性的劳动特点背后的社会基础。
然而,这种社会观在不同代际间进行传承时遭遇到了挑战。访谈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责任感与老工人明显不同。年轻工人家庭责任感普遍缺失,相当一部分青年对组建家庭没有向往,即便组建了家庭,也无法保证家庭的稳定性。不少工人将组建家庭视同儿戏,轻率地同居、结婚,又同样轻率地分居、离婚。跨地域婚姻、不断流动的状态,以及城市社会的诱惑力进一步瓦解了家庭存在的根基。这种轻易组建和瓦解家庭的行动,可谓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年轻工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失去了家庭的庇护和为家庭付出和隐忍的动力。
在留守生活时期,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社区人口流失、红白喜事压缩,社区公共生活大幅缩减,乡村生活内在意义感降低,基于农村传统内在要求的社会化过程在第二代劳动者身上并没有完全实现,这就导致第二代农民工不愿意以农村中世代相传的目标作为生命准则,不再如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遵循农村传统的意义体系,毕生奋斗去完成抚养优秀的后代、修建体面的住宅等关键任务。留守时期的社区生活单调乏味,大部分留守儿童被游戏工业捕获,留守生活的社会生活是围绕“游戏的世界”展开的。某种意义上,“大神们”在工作岗位上沉迷于“游戏的世界”并非城市生活期间新的习得,而恰好是乡村留守期间游戏沉迷的延续。
同样,进入城市以后,其劳动经历和城市化经历同样让他们在现实中发展穩定社会关系面临困难。劳动环境的枯燥、严苛、乏味令他们难以在某个工作场所长久坚持;而居无定所、不断漂泊的经历,使他们少有机会参与到社区生活中并形成稳定的社会交往关系。他们也无法如一代农民工一样,在城市里重建一个类似浙江村、河南村的基于老乡关系的“飞地”型社区,或者借由乡村的社会关系巩固城市的社会基础,更遑论通过结识城市市民搭建新的关系,实现社会资本的正向增长。陷入网贷、网赌陷阱以后,由于身负重债,大部分的大神更是主动斩断了与亲戚朋友的一切联系,社会资本急剧下降,产生了社会资本的负向转化。
由此可见,正是第一代农民工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工作所塑造出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构成了培育第二代农民工社会形态的基础,这就是新工人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两代劳动者不同的社会再生产的情境,以及不同的社会经历塑造了不同的社会主体。而且从某种程度而言,“大神”的产生是根植于第一代劳动者的劳动体制内部的,维持第一代劳动者社会再生产的拆分型体制,内在地孕育了充斥日结体制的“大神”,此即劳动力再生产的代际效应。
邱泽奇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本文节选自《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
就像工厂时代劳动者寻求劳动尊严一样,数字时代劳动者也寻求劳动尊严。

如果说传统的劳动尊严是劳动者的“三自”,工厂时代的劳动尊严是“岗位劳动的人性化和劳动报酬的公平性”,那么,在给定劳动机会普惠的前提下,数字时代劳动便暗含了“两类社会行动者的三个行动逻辑”。两类社会行动者即个体劳动者和数字平台企业;三个行动逻辑即劳动者劳动选择的逻辑,岗位劳动人性化的逻辑,劳动报酬公平性的逻辑。
个体劳动者的数字劳动内嵌着两类劳动:一是满足“三自”原则的零工劳动,二是依然具有工厂劳动属性的岗位劳动。零工劳动者的劳动选择逻辑可以表述为以自我能力和时空为约束的劳动选择,给定劳动机会的普惠性,劳动者只要愿意,便有机会参与劳动,劳动者再次实现了自主支配劳动的灵活性;劳动也不再是岗位对劳动者技能的选择,劳动者依靠自我的自然能力,经由数字平台企业精准匹配获得自在支配劳动的多样性;零工劳动以数字形态回归,便证明劳动可以不受固定时空的约束,劳动者重新拥有自由支配劳动的随意性。概言之,在零工劳动中,劳动者重新获得支配劳动的自主、自在、自由。
与此同时,数字劳动也面向个体劳动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劳动参与。如果说工业时代因为劳动技能的选择性带来了劳动机会的有限性,那么,数字时代不再有劳动技能的约束,也就没有了劳动机会的限制,让每个合法劳动者参与劳动不再受市场竞争的约束,社会便有责任推动劳动者参与劳动。也因此,倡导劳动光荣成为数字时代重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现代形态的时代命题,而躺平显然不是获得尊严的姿态。
陈熙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本文节选自《南方人口》2012年第6期
尽管延续香火、传宗接代是人们的普遍理想,人们为此也做出种种努力,但是现实当中,人们所向往的那种儿孙满堂的理想情景并不多见,恰恰相反,绝嗣才是更为普遍的现实。
在影响传嗣的诸多因子中,生子数的影响最为直接,在同等死亡率下,生子数越多,传嗣的机会也就越大。生子数的多少最终受制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家谱数据中表现为占据更多资源和声望的族长容易有后代,拥有功名的人也容易使得本支脉得到延续。在人口繁衍的过程中,这些占据更多资源的人群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优势被逐步累计和放大,使得他们的后代逐渐占据了人口的主体部分。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人群则逐步被排挤和淘汰,最终绝嗣。人数最多的10%支脉,占据了总人口的62.72%;而人数最少的10%的支脉,只拥有总人口的1.25%,繁衍的机会在不同支脉之间是极不均等的。
当代欧美发达国家人口不愿意多生育、而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维持相对较高的生育率,进而出现了落后地区人口比重上升,而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口比重下降的局面。这种人口的逆向淘汰的出现,前提条件是生育和死亡大体已经在人类的掌控范围之内,尤其是在人们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流行病和饥荒。然而在传统时期的中国,人们显然还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控制死亡,相反,死亡水平决定并塑造了人口的再生产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繁衍可能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那些占据较好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家族,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营养、相对清洁的居住条件,尤其是在爆发大规模流行病和饥荒时,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使得死亡率低于那些社会经济水平落后的人群。这使得优势家族在繁衍过程中逐渐壮大,而劣势家族的生存空间则逐渐被挤压,最终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