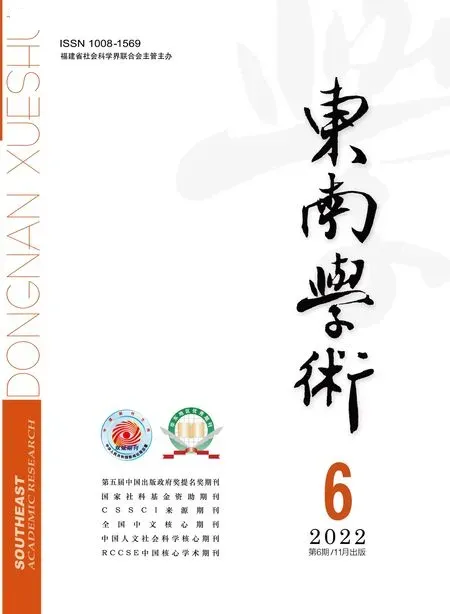网络空间虚拟共同体的出场逻辑、负向效应及规制方略
严 松
进入21世纪,网络时代已然到来。网络空间为现实个体的情绪发泄、意见表达和权益维护提供了崭新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公民诉权、维权以及监督的通道,有利于社会和谐秩序的维护。网络空间虚拟性、开放性等特征实现了多元价值主体网络空间的共在,而多元化价值主体又必然存在利益、情感和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很容易导致不同个体在网络空间的造谣、诽谤、抹黑等话语攻讦。因此,网络空间的治理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网络空间治理的范式、模型与路径。
但是网络空间并不只是个体的存在,现实的个体为了满足情感需求以及利益诉求的交往目的,会在网络空间组建不同性质的虚拟共同体,以虚拟共同体为主体的犯罪与失德行为在网络空间频繁发生,因此虚拟共同体的治理也应当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学界关于网络空间的治理大多关涉网络空间本身或者网络空间的个体行为,关于网络空间虚拟共同体的研究与治理模式的探索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在系统阐述虚拟共同体出场的历史必然性与在场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引领和规制虚拟共同体发展的路径。
一、虚拟共同体的出场逻辑
共同体体现了人类在一个不确定世界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内在需求,共同体生活方式是传统社会中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现代市民社会的建立,瓦解了传统社会共同体生活模式,使人失去了在传统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虚拟共同体是信息时代以网络为媒介所组建的一种共同体形式,满足了个体基于情感共鸣和意义分享上的价值需求,体现了人类共同体生活愿望通过网络空间达成的可行性。由此得知,虚拟共同体出场遵循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演进逻辑。
(一)共同体:人类交往自然形成的本质形式
共同体是人类在交往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既承载了人类对于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情感需求,也体现了人类对于共同善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基于历史视角考察,“人类生活的历史就是一部各种共同体发生、发展并相互制约的历史”,①高石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意蕴研究》,《求实》2015年第6期。虚拟共同体是人类在网络空间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属于共同体一种类型。探究虚拟共同体必须首先理清“共同体”的概念及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共同体是人类交往实践的产物,是“通过交谈、交往、交易、交流等等而形成的有共同的话语与理解背景的社会群体”。②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51页。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以共同体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家庭共同体是人类交往实践最初的关系形态,随着人类交往实践的进一步开展,衍生出了众多更为复杂共同体形式。发端于古希腊-罗马的“家-城邦”共同体先是在罗马帝国陨落,随后在罗马废墟上构筑起日耳曼民族的“家族父权制-庄园领主制-市镇行会制”的体系,延续了古代共同体文化。与此同时,不断形成的基督教统一信仰以及在其支配下的世俗帝国建构了关于“神的共同体”。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开展,神学逐渐被人学所取代。在此基础上,以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论证了一种“人为共同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力图建构一种体现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的共同体形式。承继启蒙思想家的“衣钵”,康德以追求永久和平的“千年福祉王国”的建构与实现为目的,证成了具有道德自律性的“伦理共同体”③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1-98页。以及强制合法性的“政治共同体”④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分工与共在的必然性与可能性。黑格尔则在其“伦理实体”的建构过程中,形塑了具有普遍理性、体现普遍利益的“国家共同体”形式。但是这些理论层面的建构却在逐渐形成与完善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现实冲击下,成为无法实现的理论幻想。
基于以上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考察,滕尼斯将共同体从社会概念中分离出来,首次确立了“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分逻辑,并将“共同体”定义为“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和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的群体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和习惯,或思想的共同记忆,是人们对某种共同关系的心理反应,表现为直接自愿的、和睦共处的、更具有意义的一种平等互助关系”。①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 52-54页。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又将共同体划分为基于生存基础上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以及基于情感维系基础上的精神共同体。个体以和谐的生活方式和共同的善为目标维系着共同体的稳固与发展,共同体以其成立的“初心”和自身固有的能量保障着每一个个体的安全以及维系着他们的情感寄托,因此,共生于此种共同体之下的个体都有着对于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以及促进共同体发展的责任感,还有对共同体强大的荣誉感。共同体型构了“人的依赖关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与市民社会相比较,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于,构成它的基本单位是共同体,而不是独立的个人,因而共同体的结合方式构成了前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基本联系方式,构成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也制约着社会的基本结构。”②王新生:《市民社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而资本主义社会则以其独有的方式开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共同体模式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
(二)虚幻共同体:人类交往本质形式的异化
资本主义制度型构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分模式,也消解了传统共同体的现实功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各司其职,其中政治国家兼具规制市民社会竞争秩序的功能,具有共同体的性质,但是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因此,它只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虚幻共同体”形式。
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私人社会领域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市民社会产生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人与共同体的脱离,变成一个又一个原子式的个体,个体受市民社会存在法则——独立个人之间相互承认和自主交往——的制约,当自由竞争和活动成为个体之间的存在形式,个体也就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成立的基石和治理的主体,即个体必须处于国家统一的权力机制之下受到管理、监控和规训,成为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一员。但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环境又使人长期处于失业、破产等焦虑之中,人情冷漠、利益优先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逐渐失去了在共同体中所拥有的安全感。虽然政治国家从宏观层面为人们提供了某种归属感,并通过国家福利政策消除人们对生育、失业、破产等方面的焦虑,但是政治国家共同体是建立在市民社会之上,根本目的是保障市民社会的经济交往秩序,即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阶级现状。因此,不可能也不会改变市民社会中人与共同体相分离的状况。
正如马克思所说,公共利益逐渐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页。国家是统治阶级利益实现的工具,应当是特殊利益的代表,但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把社会矛盾控制在一定的合理的秩序范围之内,赋予了国家政权以普遍利益的形式,国家因此拥有了被赋予的规范社会秩序、消解社会矛盾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的作用。这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国家好像成为他们生活其中利益的保障者,而实际上它只是个完全虚幻的共同体,其相关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实际上只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顺利运行,消解工人阶级的反抗情绪。因此,国家的形成不仅没有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现状,而且使得此种压迫和剥削更加隐秘化,日渐消磨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成为工人阶级新的桎梏。国家的此种虚幻的超脱性对于个人而言,成为在一定程度上同个体相脱离,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现实统治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作为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92页。基于此,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共同体称为“虚幻共同体”,而超越“虚幻共同体”社会形式将是“真正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社会。
当代一些学者一方面秉持着“公”“私”二元对立立场,强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泾渭分明,另一方面又认识到此种制度形式存在的缺陷,企图在政治国家的公之领域与市民社会的私之领域之间建构一种能够满足人们公共交往与情感寄托的共同体形式。例如,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吉登斯提出的“脱域共同体”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理论等。但是这些理论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理论范式之下创设的,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肯定和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对人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善设计的一种可能的方法,没有也无力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的逻辑,工人阶级仍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境地,这充分证明了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和最终的无效性。
总之,“共同体是持久的、真实的共同生活,社会却只是一种短暂的、表面的共同生活”,③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第71页。由于人们在现实社会无法获得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安全感,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在互联网空间中结成了虚拟共同体,企图以此满足其情感寄托、情绪宣泄,承载其在现实社会得不到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故这种虚拟共同体不可避免地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三)虚拟共同体:人类交往本质形式的网络空间重塑
基于网络通信技术全球联系的不断加强,跨越地理空间的社会联系和聚合使那些由单一的地缘、血缘和文化聚合起来的传统共同体受到威胁,更多要素被整合进“虚拟共同体”中,这是一种“围绕着一系列其意义和目标均打上了独特的自我认同符码的记号的独特价值而组织起来”④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的网络空间所独有的共同体形式。它与“虚幻共同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主体多元化,而后者的主体单指政治国家;前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主体交往需求,而后者的主要目的却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
虚拟共同体从其本质上来说,是现实个人基于互联网技术在个体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系的导引下形成的新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格局。如腾讯QQ网友结成的QQ群、微信好友结成的微信群、豆瓣网内组成的各种讨论群组,以及“百度贴吧”基于地名、机构、职业和兴趣爱好的关键词聚集相关利益人群等。这些虚拟群组通过网络而聚集,基于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情感寄托、集体记忆以及互动的必要性,表达和形塑着对虚拟群体的认同。同时,网络空间智能算法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突破实现了网络空间的内容生产、信息传播的智能化变革,能够根据网络行为主体的兴趣爱好、价值偏好以及利益诉求进行匹配式的精准推送,推动了网络空间虚拟个体的聚集,从而形成以类似价值和兴趣为纽带的虚拟群体,并且在智能算法技术的不断加持之下,群体的黏性得以不断增强,从而实现了虚拟群体向稳固的虚拟共同体的转化。虚拟共同体出场意味着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变得极为丰富、外延得以不断扩展,共同体不再仅仅局限于现实性的实体存在,也可以表示一种抽象的、没有具体形态的虚拟存在。对共同体概念的阐释不再有明确的时空要素,而是要突破时空界限,基于稳定性与流动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辩证统一的阐释视角进行现代解读。
具体来说,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明不仅给人类带来了通信技术上的革命,而且也使得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断被重组,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时空压缩和时空扩展相统一的时代,时空压缩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交往更为便捷,时空扩展意味着人口流动更为频繁、人的视野更为广阔。正如褔柯所说:“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地使人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①M.褔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因此,这个时代的共同体形式必然呈现出超越时空限制的样态。在这样一个时代共同体概念中,“血缘”“地缘”等实体性元素变得模糊不清,“趣缘”“情感”等价值性因素成为重要拼图,即共同体稳固的形态逐渐弱化,基于兴趣爱好和情感诉求建立的虚拟共同体逐渐成为主流,共同体所蕴含的同质性和同一性要素逐渐被异质性和独特性要素所取代;“熟人交往”“身份认同”等因素功能性消减,符号交往、流动交往变成重要结构性要素,即共同体变成一种形式和符号性东西,它的内在成员是动态性、流动性的。基于此,我们可以对虚拟共同体概念进行定义,即现实的个体以在网络空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以维护共同体成员共同利益、体现成员共同目的、提供成员情感寄托、满足成员发展需求以及兴趣需求的关系网络体,这种关系网络体以虚拟符号的形式存在,承载着人类相互协作谋求生活性以及精神性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共同愿望。
概而论之,互联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交往的时空界限,方便人们透过相互连接的高速网络进行串联,组成多个不同目标的虚拟共同体(同一个共同体的目标是相同的),虚拟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没有也不需要严格约束。这种交往方式与面对面的交往相比,相对隐蔽和安全,人们可以投入更多的情感,对网络社群产生新的认同,②John A.Bargh and Katelyn Y.A.Mckenna,THEIN-TERNET AND SOCIAL LIFE,Annual.Review of Psy-chology,2004,(55),PP.573-590.而且这种新的认同是以共同兴趣爱好与共同利益为主旨,加之互联网所提供的双向沟通、互动的便利和效率,使得将虚拟共同体凝结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二、虚拟共同体的负向效应
虚拟共同体是虚拟个体自发形成的一种常见网络现象,是虚拟个体适应网络文化、参与网络活动的必然选择。它具有两种形式:一是个体为满足其交往目的、情感需求而组建的,能够实现其在现实世界所无法达成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二是个体为实现某种利益而找寻合作伙伴所组建的,协同合作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效率,而且实现了价值共享。但是这两种形式的虚拟共同体在网络空间中的建构与行为会出现以下几种形式的价值错位,成为阻碍网络空间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
(一)政治操控的思想渗透与群体极化虚拟共同体
一方面,虚拟共同体“虚实共生”特征很容易导致其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对象。虚拟共同体虽然是网络空间活动的组织形式,但是其本质上却是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在网络的重塑。由于虚拟共同体的成员来源于现实的个人,以群体的力量参与社会活动能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多数虚拟共同体形成之后也必然想要重新介入现实社会。虚拟共同体此种“虚实共生”的特性导致其很容易受到西方政治势力的青睐,他们不仅组建各类具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拟共同体,而且扶植各类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虚拟共同体,不断抢占网络空间的思想阵地,并企图以此种具有西方意识形态性质的虚拟共同体向现实社会辐射,通过“网络溢出”的功能达至渗透与颠覆我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另一方面虚拟共同体“阶层化”特征很容易导致群体极化现象。虚拟共同体是一种建构性的群体,建构的过程必然存在发起者与参与者、引导者与跟随者的差异,而发起者与引导者往往成为虚拟共同体中的意见领袖,参与者与跟随者则是普通成员和临时成员,造成了虚拟共同体内部的阶层化。虚拟共同体内部阶层的不平等也导致了大量被政治操控的虚拟共同体出现,严重损害了政治民主化,对公共理性和协商民主的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从而造成盲目跟随的政治极端化现象。例如,2016年和2020年,蔡英文两次“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都采取了收买“网军”并与其组成“政治共同体”的手段,通过“网军”在网络空间制造各种舆论导向误导台湾民众盲目跟随,从而助其获得了“竞选”的最终胜利。因此,虚拟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形式上的平等交往实际上却是一种“想象的平等”,如果无法解决此种“想象的平等”的悖论,虚拟共同体在促进政治民主化中的功能性效用将大打折扣。
(二)缺乏敬畏的网络暴力与网络犯罪虚拟共同体
一方面,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匿名性、虚拟化重要特征,现实个体只需要有一部便携设备就能够随意进出网络空间,参与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在网络空间从事各种评价性活动,并不担心由于身份暴露而在现实世界受到处罚,同时加入某个虚拟群体共同进行网络活动的个体会不断滋生“集体无罪”意识,因此这些虚拟共同体及其成员必然对现实的法律、法规与道德缺乏其在现实生活中所应有的敬畏之心,从而使得他们在“法不责众”的错误认知下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诽谤性、诬蔑性、煽动性以及侵害名誉性等网络暴力活动。此种具有网络暴力性质的虚拟共同体组织形式在网络空间愈演愈烈,不仅严重影响网络空间的正常秩序,而且不断破坏现实社会既存的正义法则。另一方面,互联网空间的超地域性、开放性以及共享性的特征,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障碍,使得共享空间和时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人的交往空间扩展至全球,但也使得全球各地有相同为恶企图的不法分子可以在互联网空间中进行勾连与结合,形成了许多“网络犯罪组织或集团”。这种恶的虚拟共同体相较于传统的犯罪集团具有以下的显著不同:第一,组织架构更为松散,其组织成员主要基于一定的利益和需要,甚至是一定的兴趣爱好相互沟通、联结,并没有严格的组织约束,而是松散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的虚拟组织;第二,组合起来更为便利,移动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媒介是他们协商犯罪细节、沟通组织的工具,使他们的犯罪行为也更加隐蔽;第三,犯罪地域几乎不受限制,超地域的互联网更是前所未有地消除了距离感,为罪犯提供了舒适与方便,使得他们跨地域、远距离的作案成为可能,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就凭借一台电脑实现网络犯罪行为。因此,这些网络犯罪集团相较于传统的犯罪集团更加隐蔽,且法律更难对其进行监管与惩处,因此他们对于法律必然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会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网络犯罪活动。
(三)理想异化的娱乐至上与情感偏执虚拟共同体
互联网技术所开创的网络空间及其虚拟交往方式改变了传统的“我喜欢谁”的追星模式,型构了“谁喜欢我的偶像”的个体的群体意识。此种群体意识的建立使得以某个“明星”为标签,以崇拜、追随以及宣传某个“明星”为目的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一起,互诉情愫、互通有无,组建了偶像崇拜式的虚拟共同体。基于光环效应和证实偏见理论,一旦虚拟共同体遭遇不同于自己价值观和行为的其他共同体时,将会选择无视或者奋力反抗这两种行为。以偶像崇拜为其情感需求和寄托的虚拟共同体,当其崇拜的偶像明星在网络空间有任何负面信息,他们都会感到自己的情感受到了玷污,从而团结起来与传播此负面消息的媒体、网民或者其他虚拟共同体进行斗争,为其偶像澄清或者消除负面信息,因此可能导致在网络空间爆发激烈的价值矛盾与冲突。对娱乐明星的偶像崇拜从侧面也反映出当前青少年对科学家、人民英雄、先锋模范的崇拜、敬仰与效仿日渐式微。再者,智能算法技术将网民的兴趣爱好当成唯一的信息推荐准则,投其所好地为网民推送大量的娱乐化、欢愉化、戏谑化的信息资源,多元化的信息中难免带有庸俗不堪、胡编滥造、是非不分的成分,娱乐化的信息难免与主流的价值观产生冲突与矛盾,从而瓦解主流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四)脱离现实的网络成瘾与虚实不分虚拟共同体
随着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电脑和智能手机逐渐成为人类生存、生活、工作所不可或缺的技术依赖。这种被电脑和网络所统治的虚拟社会,造成了存在与虚无、真实与虚假的共同在场,很容易让人在这样的空间之中迷失自我,产生一系列无法预料的后果。如果将网络空间的虚拟环境当成真实的环境来对待和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会混淆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从而产生对现实世界淡漠感与不信任感。尤其是过度沉迷于网络世界,由此丢失现实生活以及现实体验,则必然会失去许多真实的以及值得珍惜的情感,甚至患上“网络综合征”。一些“模拟真实”的网络游戏的出现进一步助推了脱离现实的网络成瘾与虚实不分的“网络综合征”,例如,由美国林登实验室推出的网络虚拟游戏“第二人生”(Secend Life),玩家只需要在网上创立一个身份,就可以在网络空间模拟开展任何现实生活中能够进行的活动,如恋爱、结婚组建网络虚拟家庭。此种虚拟家庭共同体的形式能够为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情感与爱情满足的个体提供需求,但也很容易诱使人们偏离真实,从而产生消解现有道德规范与道德秩序的危险。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对互联网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消耗和上瘾问题可能会分散我们对这个时代最重要问题的注意力。”①Trebor Scholz,Digital Labor,The Internet as Play- ground and Factory,New York:Routledge,2013,p.10.互联网技术所造就的虚拟交往方式不仅使得网络成瘾正在社会上不断蔓延,而且不断消解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基于情感和共同目标的互动交流,使得现实的公共生活在现代技术的冲击下不断衰落。
三、虚拟共同体的规制方略
虚拟共同体不仅在网络空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其影响也辐射到了现实社会,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或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这就需要对虚拟共同体组织与行为方式进行有效的引导与规制。
(一)科技规制:确证虚拟共同体性质的必要条件
一是利用科技手段确证与规制虚拟共同体中的“意见领袖”。每一个虚拟共同体之中的个体都是自由加入与退出,能够在共同体内进行平等互动以及共享信息,从这个层面看,虚拟共同体的性质是去中心化的存在。但“去中心化”的虚拟共同体并没有真正实现人人平等,因为虚拟共同体中存在着普通成员和意见领袖的阶层分化。即虚拟共同体无论是在其形成之前,还是在其共同发声过程中都有一个所谓的“意见领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或是通过提出某个有价值的互动话题成为虚拟共同体的初创者,或是通过其掌握的知识和文化水平成为虚拟共同体发展的引领者。与虚拟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相比,他们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和“信息资源”,能够在虚拟共同体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引导群众情绪、提升认识、制定行动策略上面发挥重要作用。对“意见领袖”确证能够有效地理清虚拟共同体性质,对“意见领袖”引领能够有效地规制虚拟共同体行为。这种确证需要有效利用智能算法技术以及“API”(应用程序接口)①应用程序接口又称为应用编程接口,是一组定义、程序及协议的集合,通过 API接口实现计算机软件之间的相互通信。API 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提供通用功能集。API同时也是一种中间件,为各种不同平台提供数据共享。技术,通过API技术精准“抓获”已经被智能算法技术标注的特定虚拟共同体中引导其走向的“意见领袖”,对他们的网络行为进行强有力的技术规制与引导。
二是优化智能算法技术在虚拟共同体确证与规制中的效能。有效辨别和规制虚拟共同体需要发挥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的作用:一方面优化智能算法技术解构虚拟共同体性质的功能。不断开发智能算法技术在“网络群体聚集”现象方面的“画像”与大数据分析的功能,即根据网络空间中导致集群现象的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和分类,厘清虚拟共同体组建的目的和性质,有效辨别具有颠覆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网络犯罪性质的虚拟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对每一个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虚拟共同体进行大数据画像,对具有犯罪倾向与意识形态颠覆性质的虚拟共同体进行标签化处理,以技术的方式屏蔽与禁锢这些虚拟共同体的网络行为。另一方面要优化算法技术推送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功能。将具有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性质的信息予以“置顶”,并和趣缘信息一起进行推荐。让虚拟共同体在满足趣缘交往所获信息的同时,又能了解和关注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直接或间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再有就是要将智能算法技术与立体化全媒体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变文字为主的传播方式为图像、符号、文字组合式的智能推送方式,实现主流价值信息的简约化、场景化,从而使得每一个虚拟共同体在实现其价值目标的同时,有效摄入主流价值信息。
(二)法治保障:规范虚拟共同体行为的关键环节
一要强化“硬法”在虚拟共同体治理中的效能。“硬法”是指由国家立法机构专门制定的法律法规。网络空间虽然是自由交往的媒介,虚拟共同体也是遵循着自由进出、平等交往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空间可以是一个不法之地。针对网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我国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部专门的法律法规,为网络空间有效治理提供了保障。同时《刑法》及其“修正案”也界定了一系列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为惩治和预防网络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一方面这些法律法规不仅立法周期较长,而且其出台遵循问题倒逼的“应激”立法方式,至今未涉及虚拟共同体组织建设、性质界定、治理主体等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总体上现有的法律制度也并不能有效满足规制具有虚拟性、开放性、流动性的虚拟共同体的需要。鉴于此,国家立法机关应时刻关注虚拟共同体的发展态势,及时完善网络空间立法工作:一方面确保虚拟共同体的组建程序与网络行为能够有法可依;另一方面确保执法机关的网络执法行为能够有法可依,从而及时有效地依法惩治或取缔一些具有负向效应的虚拟共同体,不断推动网络空间的有效、健康运行。
二是重视“软法”在虚拟共同体治理中的效能。这里的“软法”是指多元主体非经正式的国家立法程序而制定或形成并由指定主体自身所隐含的约束力予以保障实施的一般性行为规范,如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协议、倡议、公约等。一方面虚拟共同体成员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国家属性的虚拟共同体,并在同一个网络空间活动,这就决定了虚拟共同体的同一个网络行为可能出现合法与违法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同时,网络空间的数字化、虚拟性、超地域性与全球性,也模糊了司法管辖区域的界限。因此,“硬法”的治理对于虚拟共同体的规制可能存在失效的一面。而每个国家既有法律法规也很难因为与其他国家存在冲突而废除或更改,这就要求国家之间在虚拟共同体治理上必须进行充分沟通,有效、及时地制定公约或协议,在尊重每个国家法律和主权基础上,划定虚拟共同体行为的边界,协同共治。另一方面虚拟共同体在网络空间聚集和活动是基于各类社交平台。目前这些社交平台为了实现规范运营已经出台了一系列行为规制,例如《新浪微博社区管理规定(试行)》《抖音网络社区自律公约》《豆瓣社区指导原则》等。在规制虚拟共同体行为方面,“软法”可以有效弥补了“硬法”不充分与滞后性的缺陷。这就要求各大网络平台应当根据虚拟共同体发展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在虚拟共同体的组建程序以及网络行为方面制定并适时更新各类规制的“软法”,确保各类虚拟共同体在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下得到健康运行和发展。
(三)主体协同:打造虚拟共同体的共治体系
一是打造网络执法主体之间协同治理体系。目前互联网空间已经形成了政府、网络服务商、网络和社会机构多元化治理格局,但是此种治理格局并没有形成协同共治、职能交叉、互补的合力,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政府、服务商、社会机构、网民共同参与互联网治理,并不必然会产生‘协同效应’,也可能产生治理‘碎片化’问题。”①赵玉林:《协同整合:互联网治理碎片化问题的解决路径分析——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国际经验和本土实践》,《电子政务》2017年第5期。一方面治理主体存在“九龙治水”的悖论,即对同一网络事件执法主体过多,造成各自为政、权责不清的执法乱象;另一方面治理主体存在推诿扯皮的问题,即网络事件分管部门不明确,造成转嫁问题、懒政惰政的执法乱象。基于此,对恶的虚拟共同体的治理,应当确立网络执法主体“谁最先发现谁最先介入”的原则,不能因为虚拟共同体行为管制主体的不确定性以及执法的复杂性就对其放任不管,而是要以“决断式行动”及时介入,防止其影响蔓延,从而将不确定性的负面后果压缩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总之,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高效率、强连接、即时性的功能,打通不同执法主体对于网络行为的分管界限,打造和完善执法主体协同合作平台,有效治理虚拟共同体的网络违规违法行为。
二是打造网络参与主体之间协同共治的治理体系。一些人认为网络空间管理的主体是政府相关部门及其授权的相关组织,客体是广大网民及其组建的各类网络共同体,内容是主体对客体破坏网络秩序的行为进行管制和惩罚。这种关于网络空间管理“主-客”二分的思维,一方面对虚拟共同体行为方式进行严格管控、价值理念进行强制灌输,不仅与网络空间自由属性相违背,而且很容易使共同体成员对主流价值观产生逆反情绪;另一方面使得广大网民被孤立在网络治理之外,不仅会滋长网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心态,由此扩展了各种恶的虚拟共同体生存空间,而且还消解了网民对于政府相关部门网络执法行为的监督意识,助长了政府相关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网络公共空间面临的问题不是管制和放任的两难选择,而是如何实现协同共治。”①殷辂:《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路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相关管理部门不要把自身置于大众网民之上或者对立面,并对其网络行为进行居高临下的管控,而是要以网民的身份主动参与到网络活动之中了解社情民意,与大众形成情感共鸣、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以此种“虚拟共同体”的形式组成网络空间的主体,而将网络“公共事件”或者“公共问题”当成客体,“网络事件”的有效处理作为共同目标,这样将垂直性的行政管控和命令关系变为水平式的交往和共治关系、基于交往和共治所形成的应对网络舆论公共事件的虚拟共同体,必将有利于良性有序与健康和谐网络生态空间的建构。
(四)价值引领:净化虚拟共同体风气的内在要求
一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一方面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空间在场性的价值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话语互动者必须同属一个价值规范体系,方可预期对方关于自身的期待。正是凭借此种预期来调整、规范自己的行动,社会互动才得以有意义地进行。”②T.Parsons & E.Shil(eds.),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p.105.在网络空间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为虚拟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和谐、有序交往提供基本遵循。要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空间的强大在场性,既能够不断地塑造具有爱国主义情操与友善价值观的虚拟共同体,又能够有效地消解具有意识形态颠覆性质的虚拟共同体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要创新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样化传播方式,将传统文字“独白”“说教”式的传播方式与情境互动、榜样示范、虚拟场景体验式的传播方式相结合,充分挖掘网络空间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立体化与多功能的传播模式;再者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空间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完善相结合。在网络空间引领和规制虚拟共同体价值认同的内容,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和引领网络空间其他多元价值观,更要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和指导地位。
二要强化教育引领个体理性意识的功能。虚拟共同体是由一个个参与网络活动的现实个体所组成,虽然这样的个体具有匿名性、符号化等虚拟特征,但是每个虚拟化个体背后必然对应着一个在现实世界中生活的真正的人。虚拟共同体负面效应的出现与现实个体理性思维缺失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对虚拟共同体有效规制还需要加大对现实个体的文化教育,特别是系统的信息伦理与法制教育,强化正面引导的作用,使其自觉养成正确的网络伦理观、法制观和理性判断力,从而以良好的人格参与虚拟共同体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