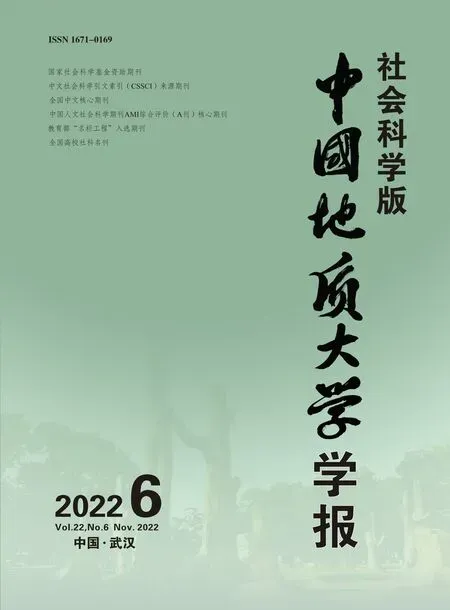从传统社会到网络社会:“陌生人”理论在西方社会的历史流变以及政治传播价值
柯 泽
一、从齐美尔到鲍曼:“陌生人”理论的社会学含义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是现代诗的开创者,他的诗歌表达了现代人的孤独感以及愤世嫉俗的反叛精神,当然也深深烙下了他自己出生成长的精神创伤。波德莱尔最早在其散文诗 «异邦人»中对 “陌生人”进行了描述,诗人以设问开篇:“请问,你最爱谁,谜一样的男人?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妹妹或者说你的兄弟?”诗人自答,自己其实是一个 “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姊妹,没有弟弟”的异邦人,这个异邦人甚至没有爱情,没有女神,没有上帝,憎恨黄金,他只是喜欢浮云[1](P371)。波德莱尔以现代诗的形式将现代人的精神孤独和创伤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引起了世人的巨大情感共鸣。但是,他的异邦人概念更多的只是具备文学色彩。
如果说波德莱尔首次以诗歌的形式描述了作为 “陌生人”的异邦人及其精神世界的话,德国学者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 Simmel)则是最早在社会学意义上揭示 “陌生人”概念的社会学家,在其1808年发表的短文 «陌生人»中,他提出了 “陌生人”概念。他认为 “陌生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地人或者流浪汉,所谓 “陌生人”是 “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是潜在的流浪人”[2](P341)。齐美尔特别指出,与那种置身于边界以及地域空间确定的当地人相比,“陌生人”总是带有异质化的品质,这种异质化的品质不可能产生于当地人内部,它是造成冲突并带来变化的重要因素。
作为德国第一代社会学家,齐美尔非常关注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冲突等诸多问题,关注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和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他还特别关注货币的出现如何改变了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并最终改变了社会结构。在1896年发表的 «现代文化中的货币»一文中,齐美尔提出,正是因为货币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从而松动和瓦解了中世纪以来形成并固化了的各种市场社区、封建团体:“在中世纪,人受到约束,隶属于一个社区,或者一处地产,隶属于一个封建的团体,或者一个社团;他的个人人格被融化进各种客观物质,或者社会的利益圈子,而后者具有直接支撑着它们的人员的性质”[2](P67)。但是货币的出现使得现代人 “依附着多得无可比拟的供应者和货源,他的生存每时每刻都是建立在千百种由货币利益促成的结合上”[2](P71)。齐美尔的逻辑是,货币的出现催生了大量流动性的商人和贸易,促进了跨地区交易,瓦解了封建经济秩序,催生了市场经济、现代组织机构以及社区的发育;一个处处充满 “陌生人”的社会不仅仅改变了社会结构,而且由于货币将人从具体的财产形式以及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于货币所具有的客观性和非人格化特征,货币同时也提升了人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不难看出,齐美尔的货币理论与随后提出的 “陌生人”理论一脉相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已经普遍完成了工业化转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跨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发展迅速,世界各地都市化进程发展迅猛,民主制度建设也在草创之中,这一切的背后都与货币流通和“陌生人”流动戚戚相关,而在这一宏大的社会变动之中,“陌生人”作为一个滚雪球般急剧扩大的社会群体,它会产生何种异质化的东西,如何将新的东西注入传统社会?新旧社会阶层将会发生何种冲突,二者将如何顺利融合?“陌生人”对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将会造成何种影响?“陌生人”又如何形塑自己的人格,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所有这些问题都隐藏在齐美尔提出的“陌生人”概念之中。
“陌生人”是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理论框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齐美尔更加愿意以社会唯名论的视角切入去理解社会构成和社会本质,他认为社会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社会互动是社会的本质,“陌生人”就是欧洲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异质化的新人类,齐美尔敏锐捕捉到了这一新人类的足迹,迅速将他们纳入到形式社会学的诠释框架之中。与之对立的是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为代表的社会唯实论,后者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事实,社会的本质是道德、习俗、制度这类观念形态的东西,正是这类抽象的观念和原则支配着社会运行,同时也支配着人的社会行为,涂尔干将具体的个人以及人们之间的鲜活互动排除在社会之外,从而否定了个体的存在。
相对于传统人群而言,“陌生人”是一种全新的人类。在欧洲历史发展中,这种新人类伴随着自由市场、工业化以及现代化进程而出现。16世纪以来,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国际贸易兴起、工业革命发轫、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大批固守在农村的原住民开始涌入都市,他们成为产业主、资本家、银行家、工程师、商人以及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他们完成了居住地的空间转换,完成了职业身份的再确立,完成了生产方式以及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当然也引发了社会关系的转变:“陌生人”开始登上社会舞台,他们彼此之间将如何互动?他们将重塑何种社会关系?他们将在形式社会学框架中获得怎样的诠释?在齐美尔看来这些问题必须得到理论解决。
如果说在齐美尔那里,“陌生人”还仅仅是停留在一个社会学概念上的话,在第二代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主将罗伯特·帕克 (Robert E.Park)那里,“陌生人”已经开始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演变为一种带有应用性质的全新社会学理论。1899年帕克留学德国洪堡大学,他曾经选修齐美尔主讲的社会学等课程,并深受齐美尔形式社会学思想影响。1913年帕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启了所谓的都市生态研究 (Urban Ecology),研究对象就是当时高度移民化和种族化的芝加哥大都市,尤其是从美国农村和欧洲各地涌入到芝加哥的新移民。帕克确定地说:“美国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划分为两个阶级,即那些已经到达城市的人,还有那些暂时没有到达城市的人。”[3](P121)据统计,从1910年到1930年的二十年间,芝加哥人口从218.5万扩展到337.6万,人口增长120万,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为移民的后代[4](P114)。在帕克眼中,这些新移民就是齐美尔所说的 “陌生人”。毫无疑问,帕克对这些 “陌生人”的关注是典型的社会学方式:他一方面关注所谓的 “都市结构”问题,也就是产业聚集、资金流动、人口流动、劳动力的分布、职业取舍等等,这是 “陌生人”对稀缺社会资源的竞争,也就是为生存而进行的战争,体现的是城市发展的 “自然史”。帕克更加关注的是所谓的 “都市行为”问题,他注意到在芝加哥移民社区,尤其是贫民窟的所谓 “边缘人”中广泛存在着道德失序、心理失序、行为失序以及社会失序问题[5](P270-271)。面对芝加哥 “边缘人”中存在的问题,帕克显然是以社会学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始终强调互动、交流、传播在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中的作用,始终强调爱、理解、尊重、道德等主观性因素在缔结共同体中的重要性。帕克希望通过反射、调节、沟通和协商在 “边缘人”和主流人群之间形成共识,从而化解文化冲突和种族冲突。他的理论既是对齐美尔、库利、米德等人社会互动理论的继承,也是基于芝加哥这个 “都市生态试验场”所进行的个案研究,正是帕克将齐美尔的 “陌生人”概念以及米德所代表的符号互动理论带入到社会学的应用层面。无论如何,在帕克所处的时代,人们对 “陌生人”对社会可能的影响已经产生足够的警觉和重视。
20世纪后期以来,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语境下极大发展了传统的“陌生人”理论。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是一种与理性、秩序和完美相关联的社会状态,要实现上述美好目标,人类发明了道德、伦理、法律等教条对人类行为予以约束,特别是以福特式的生产方式去强制规范生产岗位、生产工序以及生产流程,以满足资本对利润和秩序的要求。福特主义是那种“掘壕固守”式的生产方式,它 “用铁丝网和壕沟来标明它们的边界,同时将堡垒建得足够大”。“沉重的资本主义迷恋于庞大身躯和大的规模,且由于这一原因而迷恋于边界,迷恋于使它变得滴水不漏和不可逾越的东西。”[6](P110)在现代性社会中,资本严重依赖土地和劳动力,这体现了现代性对空间的依赖,它一方面限制了社会成员的流动,但是另外一方面,资本也为劳动者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职业,因此鲍曼认为现代性社会是一种相对固化、相对稳定、可以预期的社会。
然而,不可避免的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鲍曼认为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是一直流动的社会性,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资本越来越脱离土地和生产线,越来越摆脱空间的束缚,成为一种 “轻灵和流动”的、偏重时间的东西。流动的现代性造就了消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它使得个体更有可能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但是流动的现代性也造成了人的疏离感、破碎感,尤其是由于资本对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空间因素的依赖大大降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变得更加脆弱。
流动的社会性不仅造就了少数倚重资本和技术、周游世界的 “观光者”,也造就了更多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 “流浪者”。在鲍曼看来,流动的社会造成的社会分化绝不仅限于所谓的 “观光者”和 “流浪者”。在 «门口的陌生人»等著作中,他将区域战争、人道灾难中的难民定义为这个时代的 “陌生人”,认为他们同样是流动现代性的产物;他把冲突地区设置的难民营以及现代都市中广泛设置的门禁、摄像头、监控、侮辱性的回音室 (Echo-chamber)等都视为对 “陌生人”的排斥和歧视,视为对 “陌生人”的一种态度,并警告说:“避免现在的不适以及将来可怕后果的唯一出路,就是放弃上述危险的隔离政策,而正视当今时代 ‘一个地球,人类一体’的现实挑战”[7](P19)。
显然,鲍曼是在现代性和流动现代性的语境中去探讨新的 “陌生人”形态及其出现的根源,他们引起了什么样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冲突,以及如何处理所谓的常态社会与 “陌生人”的关系,他的问题提出的方式和解决方式与帕克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 “都市生态研究”并没有太大区别。不同的是,在鲍曼眼中 “当代陌生人”是一个更加需要呵护、包容和施舍的脆弱群体,而不是一种像齐美尔眼中那样带有异质化品格,在与传统人群和社会冲突中能够向历史和现实注入新的内容、推动社会前进的活跃因素,这也体现了鲍曼对现代社会的悲观。
二、“陌生人”理论的政治学含义及其政治价值
在 “陌生人”理论的社会学视域中,“陌生人”被看作置于社会互动视野中的特殊个体,“陌生人”理论强化了以社会互动为基本框架的社会唯名论思想。“陌生人”理论关注的是 “陌生人”之间以及 “陌生人”与熟人社会之间的紧张社会关系,理论关切点在于如何通过沟通交流和接纳融合减缓这种矛盾,帮助 “陌生人”融入主流人群,这也类似于社会学冲突理论的个案研究。但是从经验层面上看,“陌生人”概念中先天隐含着丰富的政治学涵义。“陌生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政治角色,其理论意义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社会学领域。“陌生人”理论的政治学含义以及“陌生人”的政治价值有待继续发掘。
在西方文明语境中,“陌生人”是那种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剧变的新的人群。人们对所谓异质化的 “陌生人”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1517年路德 (Martin Luther)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造就了欧洲的新教徒,新教徒奉行 “因信称义”,与罗马天主教发生尖锐冲突,并引发了整个欧洲对新教徒的持久迫害。但是,韦伯 (Max Weber)认为,正是因为新教徒对 “因信称教”“上帝预选”等教义的笃信,他们节制欲望,勤勉工作,才造就了特有的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当1620年 “五月花号”帆船搭载着新教徒踏上美洲新大陆后,这些新教徒成为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先驱。1789年法国大革命奉行启蒙运动 “博爱、平等、自由”的革命口号,废除了封建专制,将平民推上历史舞台,尽管他们招致了欧洲贵族阶级和精英阶级的仇恨,但是正是这些走向历史舞台的平民最终推翻了贵族君主制度,迎来了一个民主降生的新纪元。有感于几千年来西方基督教理性精神对人的压抑,19世纪后期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著作中公开提倡超人哲学,他所谓的超人就是抛弃上帝,抛弃传统,具有超强权力意志,具有最高“道德”能力的新人类,欧洲人对这种特立独行的新人类怀抱着深深的恐惧,这种学说无疑带有日耳曼血统优越论的腔调,它强烈激发了各种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成为日后纳粹种族主义产生的重要诱因。众所周知,希特勒 (Adolf Hitler)就是依靠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这类思潮,迷惑众人,将德国和世界拖入战争泥沼,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所谓超人就是当时德国和欧洲的 “陌生人”。
社会学者眼中的 “陌生人”是那种离群索居,独来独往,保持着独立人格的特殊个体,但是另外一方面,“陌生人”又随时准备将异质化的内容带入到主流人群中,这些异质化的东西往往成为“陌生人”影响和改变社会的助推力量,也是令 “熟人社会”感到惧怕的东西。正是因为 “陌生人”具有如此强大的政治能量,传统社会对 “陌生人”基本上持有排斥的态度。然而,“陌生人”境遇的改变始终伴随着文明进程层次的提升,或者说在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 “陌生人”的崛起而加速了文明的进程。
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诸如霍布斯 (Thomas Hobbes)、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洛克(John Locke)都设想过人类经历过某个原始时期,那是一个完全以血缘、氏族、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宗族部落时期,在每个宗族部落内部,所有成员都是熟人关系,部落之间也很少相互往来,人与人之间相安无事,卢梭认为这是人世间最美好的青春[8](P120)。由于地理的阻隔,交通不便,也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生产规模局限于有限区域,人们之间的交流、交往非常有限,“陌生人”不仅极其少见,还被视作异类。但是私有观念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对多余财产和资源的争夺,人与人之间终于发生争端,甚至战争,随后便出现了阶级社会;因为客观上需要一个第三者对这些争端进行公正仲裁,个人就必须让渡出一部分权利交给第三者,并代理每一个个体行使权力,由此个人与仲裁者之间就必须签订契约,明确个人让渡一部分权利,仲裁者保证恰当行使个人让渡的权利,这一理论被称之为社会契约论,这一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其实也为 “陌生人”的出场预设了伏笔。
显然,仅仅依靠血缘、宗族、部落连接的社会是原始落后的社会,文明社会的诞生不仅仅需要另外一类异质化的人,同时也需要异质化的法条去催生和孵化,后者就是契约精神、自由贸易和法律秩序等等,城邦和国家就是这种契约的产物,它们出现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解体原始的血缘关系,让大量异质化的人走出血缘、宗族、部落,将大量异质化的人从原始人群中分离出来,并置于契约和自由之中。无论每个个体来自何方,说着什么样的语言,沿袭哪种习俗,信奉何种宗教,具有何种身份,他们都必须遵守契约精神,通过自由贸易获取财富,同时服从法律秩序,在很多历史时期,这些人就是所谓的 “陌生人”。伯尔曼 (Harold J.Berman)认为:“11、12世纪的新城市和城镇都是宗教的联合,它们中有许多是誓约公社 (共谋集团),那些皇帝、国王、公爵、大主教或其他宗教人士主动建立起来的城镇,正是通过一种法律行为,通常是授权特许状而建立的,特许状由宗教誓约来确认。”[9](P39)金观涛也认为:“西方早期封建采邑和封臣制度虽然说是一种等级秩序,但其基础是私人契约,故人们不得不从罗马法中寻找其正当性根据。”[9](P46)
国家如何得以建立?社会如何得以构成?人群如何能够聚集?秩序如何得以建构?这些不仅是霍布斯、卢梭、洛克这些早期启蒙思想家思考的问题,也是亚当·斯密 (Adam Smith)、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等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一直穷究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最好方式就是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因为自由市场是一只 “无形之手”,它能够自发调节资源,自发推动生产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合理流向和分配,自发形成合理价格。更为重要的是,自由市场能够自发生成道德秩序,因为自由市场中的每个人要顺利完成生产交易,就必须考虑到他人的需求,道德由此而产生,人与人也由此而连接在一起。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不仅造就了经济秩序,还造就了道德秩序。人类要进入文明社会就必须解体建立在血缘、宗族、部落基础上的原始组织,而且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必然是建立在契约精神、自由贸易、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等基础之上,它们是连接文明社会中无数陌生人的真正纽带。
作为一个生动的案例研究,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弗农 (James Vernon)的 «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很好的注解。弗农关注的是现代性的由来问题,他并不像一些史学家们那样认为,英国的现代性仅仅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推动的结果,他将现代性的起源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历史,归因于更加具体可感的现实因素。弗农著作的基本观点是,英国之所以能够早在19世纪就完成现代化,是因为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以及帝国领土扩张,从而 “创造了一个新的陌生人社会”[10](P36)。早在1871年,英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个所谓的 “城市主导型社会”(Predominantly Urban Society),其最基本特征是大都市的出现以及大量陌生人口的聚集。1880年伦敦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都市,当时英国人口的半数以上都迁徙到城市[10](P23-24)。因为需要有效管理陌生人社会,英国率先创造了包括匿名官僚体制、现代人口普查、地理测量、税收、国民保险、邮政系统、选举制度、民意调查等现代化的机构和机制。因为需要进行 “超地方”的远程国际贸易,大量生产工厂、商贸公司、社团机构等社区组织应运而生,并且创造出货币体系、金融市场、股票交易、股份公司、企业巨头以及印刷文化、金融新闻业等贸易手段和方式,这一切成为英国完成现代转型的重要原因。
“陌生人”的政治价值不仅体现在促进了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也体现在更为直接的政治过程中。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陌生人”全面渗透到传统社会中,或者说传统社会也经历着全面的 “陌生人化”,“陌生人”与熟人社区在数量和影响力等方面日益 “乾坤颠倒”,“陌生人”的政治意志、政治行为越来越成为社会政治过程中无法忽视的环节,“陌生人”的政治价值也由此而愈加凸显。
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帕克式的 “都市生态学”研究的社会学问题以政治学面貌重新显现,以非裔美国人、少数族裔、新移民、甚至非法移民为代表的 “陌生人”将大量选票投给美国民主党,直接帮助拜登 (Joe Biden)最终问鼎美国总统。毫无疑问,在以白人基督教文明为主流的美国社会,人们会更多地以血缘、种族、族群、多元文化这类原始标签去界定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越来越多主流社会之外的 “陌生人”成为合法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尽管主流社会不愿意看到社会政治意识朝着以血缘、族群为标志的原始化方向聚集,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也经常成为一个事实。早在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就以非常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隐忧。他认为世界的存在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多文明并存是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这实际上是对美国国内族裔力量日益倾斜的一种恐惧,因为美国战后最令人不安的社会变化是,它吸纳了太多非裔、亚裔等来自世界各地的 “陌生人”,白人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急剧下降,以白人为基础的基督教文明正在被削弱和瓦解,“陌生人”的政治意志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压倒白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大选期间发生的 “黑命贵”等带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标记的所谓民权运动又一次印证了亨廷顿的担忧。
三、互联网时代 “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出现以及政治身份重塑
现代社会高度的流动性无疑造就了越来越多的 “陌生人”,网络社会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陌生化,催生出无数活跃在虚拟空间中的 “网络政治陌生人”。这类 “网络政治陌生人”在现代社会中开始扮演全新的政治传播角色,也正在拓展和丰富传统 “陌生人”理论的政治学内涵。
其一,“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出现。传统政治行为主要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政治行为一般发生在可见的物理空间:人们在各种建筑大厅举行会议,在大街小巷展开集会,在规定的场所进行表决或者投票,在学校、餐馆或者家庭内部进行日常性的政治讨论和意见沟通,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彼此是谁、谁在干什么、谁在怎么干的真实世界。但是网络社会出现之后,政治行为被大量移植到网络虚拟平台,人们经常以匿名方式在各种社交媒体或者虚拟社区发表意见,举办政治集会,举行政治投票,进行各种政治动员;人们不知道,通常也不需要知道对方是谁,属于何种性别,属于哪个党派或社会阶层。虚拟社交平台中的政治行为经常是隐匿了身份信息的隐性行为,网络上的每一个人相对其他人来说都是陌生人,过去以空间距离来区分陌生人的传统标准界线完全消失,因为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消除了空间和时间的虚拟空间。这种活跃在网络社会,积极扮演政治角色,开展政治活动的人可以称之为 “网络政治陌生人”。
由于网络社会提供了非常便利的通讯手段,“网络政治陌生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机会,能够借助于文字、音频、视频、表情包、动画、虚拟仿真等极为丰富的现代网络技术手段,针对各种政治话题或政治事件进行超视距聊天、讨论、争辩、跟帖、评论,发起包括游行示威在内的各种政治集会,完成各种民间和官方的选举投票,以此在网络社会中集聚,形成巨大的舆论、民意和政治能量。在中东和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网络政治陌生人”不断将虚拟政治能量带入到现实,在一些地方促成了重大社会变化,例如2003年以来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相继发生 “天鹅绒革命”,2010年的突尼斯的 “茉莉花革命”引燃了 “阿拉伯之春”运动,“网络政治陌生人”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政治作用。
其二,“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再原子化和再自我化趋势。现代大都市兴起之前的社会是一个人群散居的社会,人们彼此之间联系松散,个人以一种彼此孤立的原子化方式存在,这种状况被认为特别不适合政治意识的发育,也不适合民主社会的发展。塔尔德 (Jean Gabriel Tarde)等西方学者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考察了现代报刊的出现对公共舆论以及个体政治意识所产生的影响,他把那些散居各地,彼此之间甚少往来的原子化存在的人定义为群众,而把那些通过报刊联结起来的人视为 “精神关系的组合”,也就是公众。塔尔德认为,公众是 “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他们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的组合”[11](P214)。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组合体现了社会的精神发育和成长,是民主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未曾言明的意思是,现代报刊就像是社会的神经中枢系统,将散居各地的原子化存在的个体贯穿连接起来,从而培植政治意识,促进社会民主。
库利 (Charles Horton Cooley)、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和杜威 (John Dewey)等美国本土学者显然继承和发展了塔尔德的思想,他们都认为民主制度的运行有赖于民主人格和民主意识的孵化,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强调报刊等现代传媒的精神联结作用之外,还特别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互动以及真实的社区在造就民主人格和民主意识中的作用,他们所期待的是,政治意志、精神共同体沿着现实社会中大规模人群聚集、社区建构、大型都市化发展这样的物理性方向发育繁盛,而不是沿着社区失落、生存原子化的个体化方向发展。为此,库利提出了首属群体、镜中我等理论,米德提出了符号互动理论,杜威提出了精神共同体等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基于真实的人群聚集以及真实的社会互动。然而,二战之后欧洲经历了深刻的 “社区拔根”运动,都市人口开始向郊区和乡村迁移,城市社区逐渐衰落,尤其是网络社会出现后,虚拟社区迅速挤占和取代真实社区,社会真实互动开始大量被虚拟互动所取代,个体的社会存在朝着网络原子化方向急剧倾斜,愈加背离了库利、米德、杜威等民主理论家们有关个体存在社区化、都市化这种物理性发展假设的期待,网络政治陌生人甚至完全脱离了真实的社区空间和时间,个体成为网络世界真正的原子化存在。
然而,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再原子化不同于 “社区拔根”运动中由于人们物理上的疏离和区隔而发生的个体原子化,也不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民主人格和民主意识等精神共同体的衰落;恰恰相反,由于网络社会高度的开放性、自主性和选择性,“网络政治陌生人”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自由,具备了更加突出的个体化特征。
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的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中就尖锐批评了个体化过程中工业化所强加给人的制度化和标准化。他认为,在当时德国所兴起的个体化浪潮意味着 “个体的人生脱离了既有设定,这样的人生保持开放,依赖决策,就像是每个人的行动使命”“生活处境和生命历程的个体化意味着人生具有了 ‘自反性’,社会先赋人生转化成了持续自我生产的人生”[12](P166)。他甚至认为这种个体化体现了 “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它与建立在启蒙运动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所具备的 “第一现代性”,也就是制度化的个人主义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形成对照,制度化的个人主义因循很多启蒙运动的规范教条,相反,基于网络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的个体性则更加开放自主[13](P178-179)。乌尔里希·贝克言及的个体化过程非常契合今天人们面对的网络社会,从这一点来看,“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再原子化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个体自我选择以及自我强化的政治意志,而且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网络社会的个体化和原子化趋势成为网络政治陌生人成长的沃土。
其三,“网络政治陌生人”的政治意志重塑。在网络社会崛起之前的传统社会中,个体政治意志的形塑极大受制于真实的社区和社团因素,受制于传统媒体传播的各种政治信息,发生在家庭、学校、社区、社团中的互动、交谈、教学、会议、仪式等等也都成为个人政治意识的重要来源。尤其是,政治议题和政治讨论基本上被官方和主流媒体垄断,人们直接参与政治讨论的机会被严重限制和剥夺,个人政治意志事实上处于被抑制之中,或者被主流媒体所掌控的议程设置所左右。传统媒体传播的新闻报道、政治讨论、政治事件等等也在潜移默化培育着个人的政治意志。
然而,在网络社会中,个体政治意志的形塑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全球性带来的流动性以及网络社会的崛起意味着社区、社团以及社会互动等物理边界的拆除,大规模人群的流动性增强和网络虚拟空间的出现,这两种趋势相互叠加,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陌生化趋势加剧。以推特、脸书、优兔为代表的数字社交媒体在短短十几年间催生了海量的 “政治陌生人”,“政治陌生人”的政治意志在网络空间中快速重塑,伴随着 “社区拔根”而出现的政治参与冷漠迅速加温,个体参与政治的热情重新被激发出来。
此外,网络虚拟空间中 “政治陌生人”的聚集方式变得快速灵活,线上线下政治行为切换机制日益成熟,政治行为成本急剧下降。传统政治行为基本上发生于可见的物理空间以及不可逆的线性时间轴线之中,同时也受制于社区社团之中的熟人关系,政治行为的效能往往受到很大限制。网络社会中的虚拟空间不但成为政治意志孵化的良好场所,也成为海量 “政治陌生人”聚集的场所。在这种全新的 “超视距”“超现实”虚拟时空中,人们政治参与的机会变得更多,政治参与的方式更加迅速快捷,手段更加丰富灵活,政治行为的成本开始变得低廉。更为重要的是,虚拟空间中的政治聚集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迅速转化为线下政治聚集。伴随着政治行为的线上线下切换机制日趋成熟,现实社会中的 “陌生人”与网络社会中的 “政治陌生人”高度混杂融合,甚至连体合一,传统社会中的 “陌生人”政治效应在网络社会中被极限放大。
四、余论:“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历史再回溯以及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
在传统政治学视域中,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最早将人视为一种政治动物,他认为政治的最终目标是善和美德,确保每个人能够过上道德的生活,而城邦是实现美德政治的最好形式,“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种政治动物”[14](P7)。人的政治属性被确立以后,剩下的问题自然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建立城邦制度,也就是说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基础是群居聚集,建立组织机构,孤独的个体断然形成不了组织和社会,不存在一个人的政治。历史上人们解体血缘关系,走出种族部落,建立城邦城市,缔结现代国家诚然是追逐经济利益的结果,同时也是追逐政治,实现政治目标的过程。人群聚集规模的逐渐扩大,社会组织机构的日趋复杂,商业活动的去地方化和国际化都意味着陌生人如滚雪球般汇入更大的陌生人的滚滚洪流之中,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出自人类的政治天性,也必然出现结社组党、集会游行、投票选举等等特殊的人群聚集形式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从中不难看出政治过程中从人到 “陌生人”,再到 “政治陌生人”这样一条天然的政治演化逻辑。
传统政治活动显然严重受制于自然空间和时间。由于自然地理空间和自然时间造成的人类迁徙的阻碍,人类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地方性特征。人类交往,包括政治交往也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地方熟人圈子中。种族、民族、文化以及地理往往是现代国家得以缔造的重要因素。英国政治心理学奠基人沃拉斯 (Graham Wallas)也认为,大部分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按照江河走向、高山方位以及其他地理条件划定的[15](P176)。如果说历史上大量 “陌生人”和 “政治陌生人”的出现确曾影响了无数政治进程的话,由于科学技术的制约和自然时空的阻隔,人类并没有能力催生出数量更多的 “陌生人”,包括 “政治陌生人”,从而更加有力地去影响和改变政治进程,正是互联网和网络社会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互联网的兴起意味着 “时间之死”和 “空间之死”,意味着 “地域的消失”,也意味着人的感觉、知觉和能力的空前延展。网络社会的崛起则意味着真实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被完整或者部分移植到虚拟时空之中,人类政治活动的门槛被悉数拆除,与政治相关的交往、筹款、言论、组织、集会、游行、示威、投票等等几乎能够以零成本在虚拟世界中进行,虚拟世界中的政治活动完全能够在相互陌生的人们之间发生,或者说,网络社会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陌生人,这是一个 “网络政治陌生人”登场的时刻,它是历史上传统 “陌生人”和 “政治陌生人”的延续。“网络政治陌生人”就是那些完全失去了现实生活中血缘关系、族群关系、利益关系,彼此之间也完全陌生,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基于某种政治共识而进行政治活动的人群,网络媒介彻底消除了自然时空障碍,使得 “网络政治陌生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网络政治陌生人”的政治行为影响力自奥巴马 (Barack Hussein Obama)时代以来在美国总统选举等重大政治事件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和验证。在最近几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候选人和选民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开始高度互动,催生了无数 “政治陌生人”,对选举结果产生了直接影响。有研究显示,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就打造了自己的竞选网站 (My.BarackObama.com),创立了3.5万个群组,注册用户超过150万人,在youtube上奥巴马竞选视频的观看总时长达到1 450小时[16]。竞选期间,Youtube用户上传支持奥巴马的视频高达44万个,在其竞选官网上留下了40万篇博客[17]。竞选双方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Twitter、Facebook、You Tube、Instagram以及Pinterest等。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高达40%的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站进行政治参与[18]。在2012年奥巴马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总统接受提名演讲,其支持者每分钟发布超过5万条相关推文,会议期间共发布了近1 000万条直接相关推文[19]。2012年3月奥巴马的推特粉丝超过1 200万,名列全球推特粉丝第八位,2013年7月其粉丝数量达到3 450万人,2020年6月奥巴马的推特粉丝达到破纪录的11 946万人,位居全球第一名。这些天文数字的背后都是活生生的 “网络政治陌生人”的政治意志在涌动,他们通过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积极参与政治。
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被普遍认为是依靠推特意外胜选美国总统竞选的政治家,早在2009年3月特朗普就开通了其个人推特账号 “@realdonaldtrump”。研究表明,至2017年4月8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共发布推文3.471 4万条,从2016年2月1日在至2017年11月8日当选美国总统,共计发布6 214条推文[20]。截止2019年11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的互动高达1.81亿次,远远超过所有民主党候选人的总和[17]。相关研究显示,“2020年9月至10月美国总统竞选最为激烈的阶段,特朗普在Facebook上共发了720个帖子,获得1.3亿次关注,在Instagram上发了89个帖子,而拜登在Facebook上发了317个帖子,获得1 800万次关注,在Instagram上发了149个帖子”[18]。特朗普推特上的粉丝最高峰的时候超过八千万人,2020年1月8日,也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占领国会后两天,脸书和推特公司先后发表声明,宣布永久封禁特朗普总统的账号,理由是担心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进一步的政治暴力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社交媒体巨头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对 “政治陌生人”的恐惧。
美国一些重要的政府公共部门也一直在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发挥政治影响力,据统计美国国务院的主要公共外交部门共维护超过288个脸书主页、近200个推特账户和125个You Tube频道[19]。2000年世界上就有十几个国家开展了在线投票选举的政治实践,2006年美国启动了国会选举在线投票的创举,96%和86%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候选人分别拥有自己的竞选网站[19]。
每天活跃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的海量 “网络政治陌生人”日益引起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各类社交媒体是 “网络政治陌生人”活动的最为重要的场所。最近二十年来有关西方社会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政治运动、政治行为等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特别突出的领域。以颇负盛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为例,其官方网站 (https://www.pewresearch.org)专门开辟了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网络政治 (Politics Online)、网络激进主义 (Online Activism)等栏目,每年发表和公布大量相关主题的调查和研究,这类研究不仅深刻揭示了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相互交织的政治过程,同时也能够让人们清晰看到无数 “网络政治陌生人”在西方政治过程中的角色扮演。
相关研究显示,23%的美国人使用推特,其中69%的用户从推特中获取新闻,大部分用户对这些新闻表示信任[21]。一项以2020年5月1日到2021年5月1日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使用推特,他们的行为几乎都与政治问题有关,33%的成年推特用户具有政治属性,61%的成年推特用户在上一年度至少参与了一项政治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政治选举、签名呼吁、支持候选人、政治捐赠、推发和转推政治信息、基于政治和价值观购买或者拒绝购买某种产品等等[22]。另外一项以2020年5月1日到2021年5月31日时间段,以一百万英语推特用户为样本的研究表明,推特上最多见的政治行为是政治信息的转推,高达62%的推特用户会转发各种政治信息,而转发非政治信息的用户仅占38%。在一些政治事件高峰期,推特上的政治活动也显著增加,例如在2020年5月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杀害、2021年1月6日首都和白宫遭受攻击事件以及随后的拜登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推特上的政治活动尤其活跃[23]。
在政治行为线上线下切换自如,甚至同步发生发展的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厘清虚拟与真实、网络与现实、线上与线下的边界。2022年8月8日发生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搜查前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的突发事件立即引发了美国国内的舆论海啸。大量支持特朗普的公众 (他们往往就是 “网络政治陌生人”的别名)聚集在各类社交媒体中谴责声讨,这种线上政治行为很快演变为线下声援和抗议。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8月11日一个网名为里奇·谢夫 (Ricky Shiffer)的人武装攻击联邦调查局位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办事处大楼,被警方击毙。仅仅一天之后,«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就刊出重磅新闻,揭示了这位网络政治陌生人如何藏身于虚拟空间左右逢源,又如何肉身出界、化虚为实、实施犯罪的整个奇幻过程。这无疑是今天 “网络政治陌生人”的生动个案[24]。
«华盛顿邮报»8月12日披露的事实包括:里奇·谢夫是曾经在美国潜艇服役的海军退伍军人,也是特朗普创建的社交媒体平台 “真实社交”(Truth Social)的活跃用户。“真实社交”是特朗普竞选失败、其推特账号被注销之后于2021年自创的社交媒体。仅在被击毙前的八天中,里奇·谢夫就在 “真实社交”平台上贴出了374条贴文,内容都是呼应特朗普对大选舞弊的指责以及特朗普庄园被搜查,并公开声称 “准备杀敌”“杀死FBI”,甚至公开鼓吹 “内战”。早在2021年4月,里奇·谢夫就向特朗普的儿子发过一篇推文,说自己在 “真实社交”上开了账户,声称:“我在那里等你爸爸。”在现实生活中,里奇·谢夫还是极端组织 “骄傲男孩”(Proud Boys)的成员,这是一个网络极右翼组织 (Telegram Channel),其头目被指控参与了2020年1月6日对国会的攻击。特朗普庄园遭到搜查之后的几天中,“真实社交”的日访问量激增至70万人,但是这个社交平台对于里奇·谢夫等人的诸多极端言论并未删除[24]。对于特朗普及其儿子,对于活跃在 “真实社交”平台上的其他人以及对于现实社会中更多的人而言,里奇·谢夫都是一个绝对的 “陌生人”。«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生动描绘了里奇·谢夫作为一个 “网络政治陌生人”的生存状态,他如何在线上线下之间频繁穿插,如何急于将自己的线上政治意志转化成线下政治行为,如何急于将自己还原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人的诸多细节。
事实上,今天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和以数字媒体为核心的网络虚拟空间这两大趋势正在快速叠加,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陌生化趋势加剧,我们每个人之间彼此正在成为 “陌生人”,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 “不可见世界”的最大现实之一。活跃在数字社交媒体上的 “政治陌生人”每时每刻都在对现实政治发生着真实而重大的影响。然而,这些 “政治陌生人”虽然活跃在虚拟空间,但是并非生存于真空之中,他们在虚拟空间会话、交谈、发声、结社、群集、投票、抗议、声援,其政治参与糅合了现代社会流动性特征、陌生人群体特征、虚拟社区群集特征、网络传播技术传播特征等全部优势,遵循着 “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病毒式感染”等传播心理规律,传统社会中被压制的政治参与意志被重塑、点燃和释放,遍布西方社会的 “政治陌生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