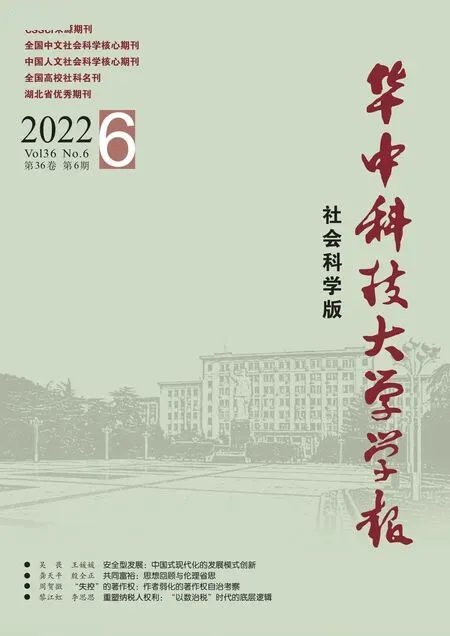正义的双重性及人为德性的塑造
——论麦金泰尔对休谟正义论难题的阐释
朱欣
引言
正义论是休谟思想中最复杂、最具原创性的学说之一。在这一学说中,正义不仅是一套安排财产关系及财富分配的社会制度,也是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休谟将正义视为人为德性(artificial virtue),它具有双重性:“自利(self-interest)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而对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1]500换言之,正义被建立在自利和道德这两个基础上:从其产生的动机来看,正义似乎是有条件的,具有特殊性;而作为道德规范,正义又似乎是无条件的,具有普遍性。休谟道德哲学对自利的强调使其既不同于沙夫茨伯里、哈奇森等主张广泛仁爱的传统道德感学派,对同情的重视又使其不同于霍布斯、曼德维尔等强调自爱的现代自然法学派。进一步,休谟从人性中寻找正义德性的根基,把“指导行为的规范和日常生活的道德心理机制关联起来,使一个容纳了人类心灵诸多情感元素的模型不仅为道德和政治规范提供实践支持,也成为这些规范本身的组成部分”[2]。它不仅与康德式的义务论迥然相异,也与普芬多夫等唯意志论者将道德奠基于神学之上的主张截然不同,这无疑使休谟的正义理论具有了巨大的张力。
正义的这一双重性,恰恰构成了休谟正义学说的难题。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其代表作《追寻美德》(AfterVirtue)中对休谟的正义学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18世纪论证道德合理性的启蒙筹划都失败了,休谟也不例外。麦金泰尔指出:
休谟援引同情乃是一种发明,目的是弥补两组原因之间的鸿沟,一组原因主张无条件地遵守普遍、绝对的规则;另一组原因则支持基于我们特殊的、流变的、受环境控制的欲望、情感和利益而产生的行为或判断……然而这一鸿沟在逻辑上是无法弥补的,所以休谟使用的“同情”只是一种哲学上的虚构(philosophical fiction)。[3]49
麦金泰尔所谓的“鸿沟”存在于正义的动机与规范之间。一方面,正义基于自利的动机而产生,“当且仅当正义的规则有利于我们的长期利益时,人们才会自愿遵守它们”[3]49,正义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正义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又是无条件的,每个人都必须把正义作为义务而绝对遵守。麦金泰尔认为,从实然的情感反应(动机)到应然的道德判断(规范),二者之间存在逻辑上难以跨越的鸿沟,如此一来,动机的条件性难免会削弱正义作为一种德性的规范性地位。
麦金泰尔的批评源于他对正义理论的三个关键论断:(A)正义规则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那么正义的原初动机类似于当代主流经济学中所强调的理性利己主义(rational egoism),一旦正义的规则不能为我们的利益服务,并且违反它们也不会有任何不利后果时,我们就可以正当地违反它们。(B)同情是一种哲学虚构,只能对自利动机引发的遵守规则之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和赞许,无法形成道德动机(1)麦金泰尔指出,在《人性论》中,“休谟明确否认任何利他主义或同情的内在动机,可以弥补基于利益与功利的论辩的缺陷”。Cf.,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M].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49.。(C)因此,正义动机的条件性和正义规范的无条件性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裂隙。为了严肃审视麦金泰尔的批评是否公允,需要厘清休谟正义理论中的以下问题:(1)作为正义原初动机的“自利”,究竟指的是什么?(2)作为道德判断之来源的同情,果真只是一种哲学虚构而缺乏人性的根基吗?(3)同情除了发挥认知功能、影响判断和提出意见以外,它是否具有意动功能,形成不同于自利的道德动机?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旨在通过澄清麦金泰尔对正义双重基础(即“自利”和“同情”)的误解,揭示正义原初动机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质意涵,重新确立同情在塑造正义这一人为德性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对麦金泰尔的批评提出有力的反驳。进一步,本文通过勾勒正义道德动机的生成过程,试图对休谟正义理论的难题进行辩护性的阐释,捍卫正义作为一种德性的规范性地位。简言之,本文想要澄清的问题是:对休谟而言,个人自愿遵守正义原则之动机的有条件性与社会正义规范对个人的无条件性之间并不存在无法弥合的鸿沟,将二者勾连起来的关键在于论证道德动机的存在及其形成过程。
一、正义的原初动机:从人为约定到开明自利
(一)麦金泰尔对正义原初动机的错误阐释:自利不等同于理性利己主义
就正义的原初动机而言,麦金泰尔认为,当且仅当正义的规则有利于我们的长远利益时,它们才会被遵守,这种动机似乎可以自然地推出:当正义规则无法服务于我们的利益并且违反它们也不会有任何不利的后果时,我们可以正当地违反它们。麦金泰尔对正义原初动机的这种描述,类似于理性利己主义,这一概念指的是,当且仅当执行某项行动能使“我”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我”才应该执行某项行动。理性利己主义对“我”应当或有理由做的事情提出主张,而不是将这种“应当”或“理由”限制在道德的“应当”或“理由”之内(2)关于理性利己主义的解释,参见:Cf., David O. Brink. Sidgwick and the Rationale for Rational Egoism[M]∥in Essays on Henry Sidgwick, ed. Bart Schult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99-240; Robert Shaver[M]∥Rational Egoism: a selective and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既然理性利己主义是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人们总是通过理性盘算和利益权衡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它从根本上讲具有道德限度,与正义之间存在本质的、无法消除的距离。正如慈继伟解释的那样,就“理性利己主义”的行为准则而言,“利己主义”指的是目标的性质和范围,而“理性”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既然“理性”只是“利己主义”的工具,那么理性利己主义中的利己因素就是既定的。理性利己主义者不仅无法对既定的自我利益予以道德反思,而且不会对其目的合理性提出任何质疑。因此,理性手段和利己主义目的之结合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理性利己主义必须通过偶然因素的作用,才能让人产生遵循正义规则的行为,一旦正义的要求与利己主义目的发生冲突,利己主义者就会对按照正义的要求决定自身行为的原则产生动摇,那么持之以恒地遵守正义规则就是不合逻辑的。简言之,理性利己主义无法使人产生持久而稳定的正义愿望[4]。
理性利己主义的概念与休谟描述的、基于共同利益感而形成的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存在根本的差别。在分析正义的原初动机时,休谟首先将人心自然拥有的情感,无论是个人的私利、对公益的尊重,还是私人的仁爱都排除在外,明确将正义奠基于人为措施和人类约定之中。休谟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最基本的方面处于“正义的环境”(circumstances of justice)中,它们是:(1)主观环境,人的自私及对他人的有限慷慨;(2)客观环境,自然为满足人类的需要所准备的稀少供应[1]495。休谟式正义的环境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策略性结构(strategic structure)。
策略性结构指“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博弈关系”(3)此外,哈丁、凡德史拉夫等人对休谟的政治哲学也提供了博弈论式的解读。Cf., Russell Hardin, David Hume: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ist[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6; Peter Vanderschraaf, Strategic Justic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5]220-243,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正义德性的性质所决定:“单独的正义行为,就其本身而言,时常是违反公益的;只有人们在一般行为体系或制度中协作时才是有利的。”[1]579任何单独行动的实际后果与它们的因果力量之间存在一个鸿沟,而这种因果力量的最终承担者是正义德性的一般实践。因此,正义行动的总体结果由“频率效应”[6]311-313所决定的,即遵守正义规则的行为必须达到相当程度的数量,正义给社会带来的利益才得以彰显。基于此,人们遵守正义的动机必定源于其对行动后果的信念。一个问题自然出现:既然行动后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信念如何产生?
(二)正义的原初动机:从约定到开明自利
不同于现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传统,休谟认为,正义起源于“约定”(convention),约定并不具备许诺的性质,不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约束力,只是个体在某些行为模式上的聚合。约定本身是一种“行动计划”(scheme of action),是一种包含频率效应的社会互动案例[6]316。这就难免产生协调问题:个体之间是否以及如何在互利的行为模式上聚合?
休谟以划船为例作出解释,两个人在船上划桨,他们同时划桨的条件是:双方各自的行为都参照对方,而且在作出这个行为时,也假定对方做出同样的行为。如果每个人都有遵守规则和违反规则两种选择,那么约定的要点是:(1)几乎每个人都有普遍遵守的偏好;(2)除非存在普遍的遵守,否则个体都会偏好不遵守(4)Cf., David Gauthier. David Hume, Contractarian[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79,88(1).。贝尔(Annette C. Baier)认为,休谟式约定试图解决的问题类似于参与者为两人以上的“安全博弈”(assurance game),它具有以下结构:
(A)如果多数人都不遵守规则,结果就是彼此之间的伤害;
(B)如果多数人都遵守规则,相比于多数人都不遵守而言,结果对彼此更有利;
(C)只要其他人都遵守规则,每个人都更愿意遵守;
(D)如果一些人不遵守,相比于每个人都遵守,结果对遵守的人而言更有害。[5]316-317
基于这一结构,正义约定的缔结将会陷入困境:休谟一方面承认,形成约定的前提在于“每个人感觉到忠实履行约定是有利益的,并向社会中的其他成员表达出这种感觉”[1]522-523。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利益感”必须诉诸实际的社会互动,使得正义行动的频率效应最终产生大规模而稳定的正义行为。由这一悖论可以得出,事实上并不存在正义的起源,因为参与一项约定并不是人们“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具体决定,而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6]317-318。在时间的缓慢进程中,人们一再经验到彼此互动中的不合作所产生的诸多不便,于是“共同利益感”(common sense of interest)逐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
“共同利益感”标志着人们在认知和动机上均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就认知而言,人们对行为模式的结构和倾向逐渐产生同样的信念,他们不仅开始相信每个人都在为同样的动机而进行同样的行动,而且开始产生行动规则的观念。就动机而言,基于共同的信念,人们也开始互相承认(mutually recognized):“我观察到,让别人占有他的财物,符合我的利益,假如他也同样地对待我。他感觉到,调整他的行为也符合他的利益。当这样的共同利益感互相表示出来,并为对方所了解时,它就产生了一种适当的决心和行为。”[1]490个体间的互相承认不仅使人们更加确信自身的真正利益所在,增强了其遵守规则的信念,而且也使他们相信规则的条件必能得到满足。经过认知和动机的双重变化,原初自利被扭转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从执迷于眼前或短期的利益转向对遥远或长期利益的追求,以一种较为间接而人为的方式追求满足,这就是休谟所谓的被重新定义的开明自利,它产生了正义的规则,并且成为遵守这些规则的原初动机和正义的自然义务(natural obligation)[1]543。
开明自利仍然是基于利益交换的考量,因为人们着眼于将来而非过去。共同利益感使人们对他人行为的未来规则性产生一种信心,他们对正义规则的遵守只是建立在这种期待(expectation)之上。值得澄清的是,这种开明自利一旦经过制度的演化而形成后,就变成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和动机倾向、一种恒定的性格特征,类似于休谟所说的“平静的情感”,它持久地敦促人们去关心根本的福祉,进而压倒各种基于具体、直接利益所产生的不同动机。有了这种稳定而持久的动机,人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不断地基于利益的得失利弊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是会在“实践中不假思索地按照规则行事”(5)程农对“利益感”的概念作了澄清,认为“利益感”不单是对财产制度之好处的事实认知,更是人们对财产制度逐渐演化的实践性理解,也就是“知道如何做”的理解,在此过程中就获得了进行某些活动的能力和倾向。参见:程农.如何塑造遵守规则的动机?——休谟观点的新解读[J].人文杂志,2021(5)。。而麦金泰尔在解读正义的原初动机时,混淆了理性利己主义和基于“共同利益感”而形成的开明自利,前者无法形成稳定而持久的正义动机,因而出现了麦金泰尔所谓的鸿沟。
尽管在社会最初成立之时,开明自利作为正义的原初动机足够有力,但随着社会的扩大,单个的不正义行为并不会被轻易地发现,它甚至不会危及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就为某些“精明的无赖”(sensible knave)[7]282-283即理性精明的投机分子提供了搭便车的契机。这些人既遵守通则,又从所有例外中谋求好处。既然对正义的严格奉行并不能保障自利的最大化,那么开明自利的自然义务似乎丧失了普遍的有效性。如何克服自利动机的不充分性,使作为制度和德性的正义获得更好的保障呢?这就引出了休谟对“同情”及它所产生的义务感的论述。
二、同情的认知功能:以“广泛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感
麦金泰尔的第二个论断指出:同情是一种哲学虚构,它在正义德性的塑造中并无实质性作用,只能通过建立道德感而对自利动机引发的遵守规则之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和赞许,无法形成道德动机。接下来将分别用同情的认知功能和意动功能来反驳麦金泰尔的论断以证明同情在塑造道德动机中的关键作用。
对休谟而言,同情不是特定的情感或动机,而是人所具有的一项基本能力,凭借它能实现“有思想的存在者之间情感的迅速传递”[1]363。不过,同情并非对他人情感的直接感受,而是一个观念借助想象力的作用向一个印象的转化。当任何情感借着同情注入心中时,它最初只是凭借他人情感的外在标志(脸色和谈话)为人所知,这种标志使人形成一种观念,由于人与人之间心灵结构的相似性(6)除了相似关系,休谟认为同情的产生还能依赖于其他几种关系,诸如接近关系、因果关系、相识关系、教育与习惯的作用。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 L.A. Selby-Bigge, Clarendon Press, 1978, p.318.,“这种观念就立刻转变为一个印象,获得了相应程度的强力和活泼性,以至于转变为那种情感本身”[1]317。
休谟对同情的论述与人的自然性情的偏私性相契合。尽管同情是指向他人的传导机制,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跳出自我的圈子,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同情始终是以自我的观念或印象为基础的。我们从他人的外部标志所感受到的任何情感,往往是基于自身所存在的与之平行的情感。换言之,在同情机制的运作中,自我的观念或印象始终密切地呈现于人们面前。同情以每个人的自我体悟为基础,是“将自身置于他人境遇的积极的想象力的自我投射”(7)关于同情与自我的关系,Cf., Rudolph V. Vanterpool, Hume on the “Duty” of Benevolence[J]. Hume Studies, 1988, 14(1); 孙小玲.同情与道德判断——由同情概念的变化看休谟的伦理学[J].世界哲学,2015(4)。,其强度必然会依据他人与自我关系的远近而发生变化。他人与自我的关系越是紧密,想象就“越容易由此及彼进行推移,而将我们形成自我观念时经常带有的那种想象的活泼性传到相应的观念上去”[1]318。由此,同情围绕自我这一圆心构成了一个分层的同心圆结构:“最强烈的关注是自己,次强烈的关注扩展到亲戚和熟人;最后才会波及到陌生人和不相关的人。”[1]488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澄清同情如何塑造道德感。休谟认为,道德感(moral sentiment)指的是人们在对他人的性格进行反思时,心中产生的道德赞许或谴责的情感。既然赞许是一种愉悦感,而谴责是一种痛苦感,那么对一种性格特征进行反思是如何产生快乐或痛苦的呢?这就必须借助同情机制来解释。当一种特征对具体的个人或者整个社会是有益的或令人愉快的时候,同情就会“使我们跳出自我的圈子,使我们对那些有益或有害于社会的性格产生快乐或不快,正如那些性格倾向于我们自己的利益或损害一样”[1]579。既然同情是一种心理机制,那么借助这个机制,一个人的感受就能传达给另一个人,由此观察者就能与他所观察的人产生相同的感受。
如此一来,既然同情具有偏私性,那么在同情基础上形成的道德感,当进行道德判断时应该如何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偏颇视角,从而实现无偏性呢?为了克服这一难题,休谟指出:在正义规则建立后,人的自然同情演变为“以旁观者为中心”(spectator-centered)的“广泛同情”(extensive sympathy)理论[8],“广泛同情”是指道德判断或评价取决于旁观者心中产生的赞许或谴责的情感,当他从“一般的观点”(general point of view)出发考察一个人的性格时就能感受到这种情感。该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旁观者并非通过自身利益的视角观察他人,而是根据与其交往之人的感受来审视此人。旁观者通过此人对其“狭窄圈子”所产生的或好或坏的影响而感同身受地产生快乐或痛苦。这种广泛的同情以“同情的双重反弹”(double rebound of the sympathy)原则为基础:如果性格有待评价的人称为A, 与其交往的人称为B,旁观者为C, 那么第一层同情来自于B受A或好或坏的影响而直接产生的苦乐感,第二层同情来自于C对B的苦乐感进行反省而产生的快乐或痛苦。“同情的双重反弹”原则可以有力地克服自然同情的局限性:自然同情和临近情感相关联,它必然会随着对象的远近而有所变化;而“同情的双重反弹”使旁观者C借助对B的同情进而评判A,将旁观者置于某种稳固的、一般的观点,从而避免自身的偏私性。根据这种以旁观者为中心的“广泛同情”理论,道德评价具有了一种公正和客观性。正义之所以是道德的(moral),是因为它具有促进人类整体福利的倾向,旁观者一旦反省这种倾向,就足以产生赞美和谴责的情绪。
简言之,从偏私的自然同情到无偏的“广泛同情”,与其说同情心改变的是进行道德行为的动力,不如说是同情心作为道德评价之媒介的客观程度。道德判断往往限于认知而不涉及行为,不必然影响我们的利益。因此,为了形成不偏不倚的道德评价,人们不必克服利己之心,只需要在无关乎个人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广泛同情”赞同公共利益。基于此,休谟认为“广泛的同情”与“有限的慷慨”并不矛盾:“前者建立在想象之上,坚持对事物的一般看法;后者则建立在内心的情感之上,使人们根据自身特殊而暂时的位置而产生感觉,进而影响行动。”[1]586-587但这是否意味着,在同情心的认知功能与意动功能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距离?在大规模社会中,是否仍旧缺乏取代原初动机的其他有效动机,使人们产生持久且自愿遵守正义规范的愿望呢?对休谟而言,答案是否定的。借助“间接情感”,休谟将道德感与人格的塑造相联,进而形成道德动机。
三、同情的意动功能:道德感、间接情感与道德动机的形成
传统的休谟解释者持内在主义(8)“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区分由福克(W. D. Falk)提出。道德哲学中的内在主义者认为,道德在动机上是自给自足的,一旦我们认识到一个道德要求,我们不需要在认识之外再有一个动机来源,以便根据它来做出行动。对内在主义者而言,道德意识和道德行动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动机鸿沟。外在主义(externalist)者则认为,对道德性质的认识与依据它们来行动是两码事,二者之间存在动机上的距离。Cf., W. D. Falk. “Ought” and Motiv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48,48, pp.111-138.(internalism)的主张,将道德感与人的动机倾向直接关联起来。他们认为,作为道德判断的媒介,道德感本身就具有驱动力:“道德感——我们称之为赞许的特殊情感——是一种令人快乐的情感,凭借它就能产生行动。”(9)Cf., Philippa Foot. Virtues and Vices and Other Essays in Moral Philosophy[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79; J. L. Mackie, Hume’s Moral Theory, Routledge, 1980, pp.52-53.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休谟的道德心理学分析。首先,休谟认为最佳的道德行为往往是自发的,而不是基于对这个行为之功的尊重;其次,尽管有些缺乏有德动机的人(10)根据休谟的《人性论》,“有德动机”(virtuous motive)指的是人性中某种产生善良行为的动机。在这种动机中,原初的有德动机(original virtuous motive)是独立于道德感的某种产生善良行为的动机,它区别于休谟的“道德动机”(moral motive)。因为一旦二者相等同,就会陷入休谟所说的“循环”问题。休谟指出,“为任何行动赋予功绩的原初有德动机决不能是对于那种行动之德性的敬重(a regard to the virtue of that action),而必然来自某种其他的自然动机或原则。如果假设对于行动之德性的单纯敬重是产生这一行动的原初有德动机,那就是一种循环推理”。换言之,在休谟看来,原初的有德动机不可能是道德动机,而只能是非道德动机。Cf.,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 L. A. Selby-Bigge, Clarendon Press, 1978, pp.478-479. 关于“有德动机”与“道德动机”的区别以及对《人性论》第三卷“循环”问题的解释,也可参见赵雨淘:“人为德性与文明社会的秩序构建——对休谟正义理论的辩护性阐释”,《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4期,第110-121页。,仍可能会基于自我憎恨的理由而在道德感的驱使下去做道德要求的事。但休谟使用“可能”这一表达向读者暗示,这些人并不一定会因为自我憎恨而采取行动。仍然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少数人完全不被道德命令所驱动。这种可能性意味着,道德动机是独立于道德评价的。
如此一来,不仅使持内在主义的休谟解释者难以站得住脚,休谟本人给出的反理性主义论证也无法获得支持。休谟反对理性主义者的论证主要在于,它们不能解释道德判断与人的实践反应之间的关系。理性主义者仅仅将道德主张视为单纯的事实,但事实的发现并不会直接促使人们行动,由此休谟主张,行动的最终来源必定是情感[1]457,465-466。那么,能否找到道德评价通往道德动机的其他路径,既能克服休谟传统解释的内在困难,又能有效支持休谟的情感主义论证呢?本文认为,安斯利(Donald C. Ainslie)提供了一条道德感经由“间接情感”(indirect passions)通往人格(person)塑造的道路,在解决上述两个困难的过程中迈进了关键一步;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格的塑造本身不能形成道德动机,二者之间还需要插入对“性格”的反思,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因此,这里在补充安斯利论证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对麦金泰尔的批评。
(一)道德感经由“间接情感”通往人格塑造
上文提到道德化的“广泛同情”是一种旁观者导向的道德观,道德感的焦点在于对他人的性格特征作出道德判断。问题是,道德判断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事实属性,还是能够在塑造人格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如果能够证明后者,就能缩小同情的认知功能与意动功能之间的距离。安斯利的论证旨在揭示:“休谟充分整合了道德感和间接情感,对人的性格特征作出道德判断,与把这些特征视为构成某人人格的有意义特征,是密切相关的。”[9]299
在考察道德感与间接情感之间的关系之前,有必要澄清休谟对“间接情感”的界定。相较于直接源于善、恶、苦、乐的直接情感(direct passion),间接情感是指“由同样一些原则所发生,但是有其他性质与之结合的那些情感”[1]276。骄傲、谦卑、爱、恨等情感就包含在间接情感的名目下。与直接情感不同,间接情感的原因和对象是不同的:它们的原因是具有某些性质的事物,这些性质会产生一种独立的快乐或痛苦的观念,其对象则是自我或他人的观念。换言之,间接情感是以人为导向的情感。举例来说,一个人对属于自己的美丽房屋感到骄傲,这里情感的原因是那所美丽的房屋,而其对象则是他自己[1]279。由此可知,间接情感是对人的评估性反应,能动者(agent)的注意力发生了从原因到对象的转移。既然它们是指向人的情感,无法将能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快乐或痛苦上,因此它们与类似欲望的情感相区别,不能充当意志的动机。
那么,道德感是如何与间接情感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塑造道德动机的?休谟在多处文本中指出,“德和恶对人类心灵产生的最重大影响”在于它们“必然刺激起快乐或痛苦,进而刺激起这四种间接情感之一,即骄傲、谦卑、爱、恨”[1]473。休谟将旁观者对于他人德与恶的道德判断与他们产生的间接情感捆绑在一起。但作为道德判断之媒介的道德感究竟如何与间接情感相关联,并非自明的事实,而是有待澄清的问题。安斯利并不同意将休谟的道德感直接等同于冷静而公正的间接情感(11)Cf., Pall S. Ardal. Passion and Value in Hume’s Treatise[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09-147. 关于道德感与间接情感的关系,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第一种,道德感可被视作间接情感的特殊形式。持此观点的学者包括Ardal、Korsgaard。第二种,虽然道德感与间接情感在结构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二者并不等同。这类学者包括Ainslie、Cohon。笔者更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第一种看法与休谟明确提出的两个观点相悖:首先,在适当的语境下,道德感提供了独立的快乐或痛苦,这是产生骄傲、谦卑、爱或恨的前提;其次,休谟从未将道德感视为“情感”(passion),它更类似于在同情作用下生成的次级印象。因此第二种观点似乎更妥当。道德感与间接情感的相似之处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它们都把与原因截然不同的事物作为意向性的对象。体验一种道德感就像体验间接情感一样,需要注意力的转移,而这种转移依赖于与一个人的显著联系。诚如前文提到的“旁观者理论”,道德认同需要三种人:旁观者C,性格特征有待被评估的人A,性格特征的受益者B。当道德感被唤醒时,C的注意力从B的快乐或痛苦转向A的性格。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感与间接情感类似,都是以同样的方式间接存在的。关于间接情感与道德感关系的经典讨论参见:Rachel Cohon, “Hume’s Indirect Passions”, in A Companion to Hume, ed. Elizabeth S. Radcliffe,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 pp.159-184.,而是将道德感视为针对某人性格特征的一种公正的快乐或痛苦,进而指出,“休谟对间接情感的依赖是为了避免一种关于人格的怀疑论式困惑:在关于某个人的诸多事实中,何以只有部分事实在塑造人格中发挥了作用,或者说与这个人的存在紧密相连?”[9]296-297
安斯利指出,正如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一样,人格与其决定性特征之间的“存在性联系”(existential connection)也不能被合理地识别,因此,休谟引入一种联结机制(associative mechanism)——间接情感——来解释“我们如何根据人的决定性特征而形成其人格概念”[9]297。间接情感,作为人的决定性特征与其对应的人格概念之间的中介,是如何与两端产生关联的?休谟的观点可以概述如下:一方面,就人的决定性特征与间接情感的关系而言,休谟认为有四类能引起间接情感的一般对象:德与恶、美与丑、外在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权力与财富。这四类特征“不只是关于某人的单纯事实,而是与其存在相关联”[1]294-316。另一方面,就间接情感与人格概念的关系而言,人们对于彼此的情感反应(即间接情感)构建了人格的社会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是谁取决于人们对他的各种事实所作的一般反应。这意味着,我们对彼此形成的概念可以由情感的通则来调整:“当足够多的人开始认为某一特征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来把某个人界定为特定社会类型或地位时,那么这个人的地位就与人们偶然对他的看法无关了。”[1]293-294
对间接情感的解释可以重新理解休谟的主张,即“旁观者对于德与恶的道德判断产生的最重大影响是间接情感的出现”的实质意涵。这意味着,通过道德感认识到某人或善或恶的品质,与通过间接情感将这种品质视为此人人格的核心特征,是密切相关的。根据安斯利的分析,作为旁观者理论家,休谟并不要求人们根据道德判断行事,但是他“将道德感和间接情感结成一体,旁观者的情感参与就是对间接情感的召唤,通过这一情感使人们形成对彼此的人格概念”[9]298-299。安斯利的方案不仅修正了传统的休谟解释,将作为道德判断媒介的道德感与间接情感捆绑起来,进而形成人格概念;而且使得休谟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更加具有说服力:对后者而言,即便借助间接情感,仍然不能充分地整合道德与情感,道德认识与道德参与之间的鸿沟始终存在。但遗憾的是,对于正义等人为德性而言,单凭人们对彼此形成的人格概念并不足以形成道德动机,进而驱动人实践正义。为了回应这一问题,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进一步引入对“性格”的省察。
(二)回应“精明无赖”之难题:性格的省察与道德动机的形成
对于大型社会的搭便车者,休谟的回应不免有些悲观。他认为难以找到令精明无赖信服的任何答案。不过休谟随后提出了一个重要理由,以进一步回应精明的无赖:对性格或完整性(integrity)的愉悦享受。无赖们为了毫无价值、华而不实的东西而牺牲了性格上无可估量的享受,他们才是最大的愚者[7](283)。
事实上,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将他在《人性论》中谈及的旁观者理论进一步关联到了“自我”意识上。以间接情感为联结机制,旁观者根据对他人品质所做的道德判断形成了对他人人格的评价,产生了对他人或爱或恨、或骄傲或谦卑的情感。借助休谟“同情的双重反弹”论,他人的情感会传染我们,特别是他们针对我们的间接情感往往会深深地触动我们。因此,由于多数人会厌恶精明的无赖,这就足以使无赖本人“厌恶自己,并再次感到谦卑以及自我憎恨”[10]。也就是说,因为同情,我们在别人眼中可爱或可恨,这种感觉使得我们在自己眼中也变得可爱或可恨,最终驱动人作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
通过“同情的双重反弹”论,旁观者形成的关于我们的人格概念,进一步转化成我们对于自身性格的省察,产生我们对自己的骄傲或谦卑、爱或恨的情感,从而推动我们采取行动。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因缺乏有德动机而产生的自我憎恨,与通过“在反思中打量自己”[7]276而产生的自我憎恨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对于前者,道德主体的关注对象是他人的需要,焦点在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对于后者,道德主体的关注对象则是自己的荣誉以及名声,着眼于主体和自己的关系,以及主体的行为对自身的影响。对前者而言,由于人天然的仁爱或恻隐之心不够强烈,难以产生足够的他向关注,那么因缺乏它而产生的自我憎恨就不足以驱动人实践正义;对后者而言,由于它更类似于一种带有道德性质的自尊,而这一情感人皆有之,它就能够成为常人力所能及的道德品质。
正如休谟所言,“我们为道德感增添巨大威力的另一个源泉是对名望的热爱”[7]276,而“大自然必定已经通过我们心灵的内在结构和组织而赋予我们对于名望的原始倾向”[7]301。由此,通过性格的省察,人们的天然仁爱与自尊相结合,成为道德行动的驱动力,“在反思中打量自己的恒常习惯”使人们关于正义和不正义的情感永葆活力,最终塑造了正义的道德动机。进一步,休谟将第一性激情与第二性激情类比为对名望的追寻与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对名望的追求或者自尊作为更原初的自然倾向,恰恰为自利提供了汲汲以求的对象,这就消解了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与遵守正义规范间的张力。
面对“精明无赖”的挑战,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一方面用人与人之间固有的“人道”(humanity)(12)从《人性论》到《道德原则研究》,休谟对“同情”的使用有所变化。在《人性论》中,同情包含了临近和相似;而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同情等同于临近,人道等同于相似。关于“同情”与“人道”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以及人道相比于同情的优势,参见:Cf., Ryan Patrick Hanley. David Hume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ity”[J].Political Theory, 2011,39(2).代替《人性论》中的同情,并拒斥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自私假设”;另一方面,他仍然主张人的偏私是根深蒂固、与生俱来的。休谟指出,对自尊的恰当运用不是去消灭或者抑制偏私性,而是将它重新定向,使人们从对无限获取财富的贪欲中摆脱出来,引向对自身性格的考察。相比于开明自利的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感不仅具有解释全部道德的正确方向,也能解释人们在悬搁个人利益时对他人的赞许或谴责。然而它们作为道德动机的内在力量过于微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联盟:人们对名望的热爱,即自尊。在道德感的指引下,这种不断“在反思中打量自己的恒常习惯”,不仅建立了正义德性的道德动机,使自尊成为社会联结的纽带和推动人类道德的引擎,而且弥合了正义的动机与规范之间的鸿沟,巩固了正义作为人为德性的规范性地位。由此,休谟也完成了对精明无赖之难题的根本回应:德性就是它自身的酬劳。在道德感的指引下,作为道德动机的自尊将作为原初动机的自利重新定向,从而弥合了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与对正义规范的遵守之间的鸿沟。
四、结语
麦金泰尔对休谟的批判性论断中出现了三个关键性错误:(1)就正义的原初动机而言,他混淆了主流理论中的理性利己主义和休谟基于“共同利益感”而形成的开明自利这两个概念,进而错置了正义的起点;(2)就同情概念的人性基础而言,麦金泰尔将偏私的“自然同情”和无偏的“广泛同情”这两个概念相混淆,进而得出同情是一种哲学虚构;(3)就同情的功能而言,麦金泰尔只看到了它的认知功能,而忽视了其意动功能,从而认为正义的动机和规范之间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
尽管如此,麦金泰尔确实洞察到了休谟正义理论的难题,也即正义的双重性:正义产生的动机是特殊的、有条件的,而正义作为规范对人的要求却是普遍的、无条件的,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无法消除的距离?为了弥合它们之间的鸿沟,休谟的核心努力是证明正义的道德或利他主义动机是真实存在的(13)麦金泰尔认为从《人性论》到《道德原则研究》,休谟从否定同情的内在动机到重新援引这一动机,证明了休谟思想的断裂;而本文经过分析认为,从《人性论》到《道德原则研究》,休谟最终完成了道德动机的构建,其思想是发展的、一贯的。。休谟的论证分为三步:第一步,正义的原初动机是开明自利。不同于理性利己主义,开明自利的概念中蕴含了人们遵循正义规则的愿望,它一旦经制度的演化过程而建立后,就具有相对稳定的认知和动机倾向;第二步,同情从人的利己动机中产生、并与人自然性情的偏私性相契合。然而在正义规则被人为建立后,人天然具有的偏私同情就会转化为无偏的广泛同情。它以旁观者的视角为中心,从“一般的观点”出发,对他人的品质产生赞许或谴责的情感,这使得人的同情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实现更大的客观性。第三步,人们在建立道德化的广泛同情之后,进一步借助间接情感这一联结机制,将道德判断与人格的塑造关联起来,继而在“同情的双重反弹”论的作用下,实现对自身性格的省察,由此在道德感指引下的自尊最终塑造了道德动机。由于这一动机是在以旁观者为中心的广泛同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自身就涵摄着规范性,麦金泰尔所说的鸿沟就此消解。总之,不同于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者将动机和义务彻底割裂,休谟的正义论弥合了规范和动机之间的距离,有效地将情感和认知因素相结合,使得情感成为道德判断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规范性的来源,消解了个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与对正义规范的普遍遵守之间的张力。休谟的人为德性学说将正义的规范性辩护与道德心理学有机联系起来,为当代的正义论提供了宝贵的智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