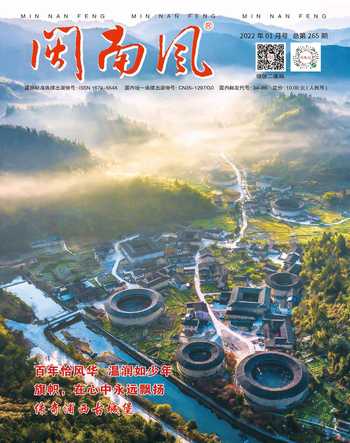我所知道的大海
周丽虹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啊大海,是我成长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最早知道的大海,是从朱明瑛深情款款又豪迈奔放的声音里得来的。真好,大海就是我的故乡。
小时候去老家要渡船,是手划的那种小船,蹲在船沿边,看四周一片白茫茫,天苍苍,船桨哗哗作响,风在吟唱,双手去轻抚浪花一朵朵,浪花儿偶溅到脸上、身上,冰冰凉凉的,很是惬意,自以为那就是“海”了,后来听大人说那只不过是“江”,九龙江,江只是海的女儿,海在另外一头。去厦门坐的是“电船”,船笛声仰天长鸣后飞驰向前,手扶船栏四处望,这就是真正的海了,海水白茫茫,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船之于海就像是座移动的孤岛,所到之处溅起“千堆雪”,蔚为壮观。鼓浪屿在海中执着地矗立着,海如此富有浪漫激情与灵性,催生了这座艺术之城多少文人的雅思、激发了这里多少艺术家的想象。

双鱼岛的海辽阔而静谧,水蓝蓝的,天也蓝蓝的,有那么一瞬间分不清是海水还是天空,躺在柔软的草坪上嘴里嚼动一片叶子,一手撑着地歪着头欣赏那一碧万顷的海天。安徒生笔下的人鱼公主正在天人交战,要么用她的魔匕首刺入王子的心脏,要么自己就得化成泡沫永远消逝在海面。她选择了后者,保全了爱人的生命,成就了爱人的幸福。那时候的海就像此刻双鱼岛的海吧,暖风习习,充满了决择后淡淡的忧伤,很快回归宁静,而关于海的童话就此流传。
镇海角海边的岩礁坑坑洼洼,人们都打着赤脚兴高采烈地踩在上面捡贝壳,一个个巨浪拍打过来,声声尖叫不绝于耳。静静地伫立着,俨然自己是长发飘飘裙裾飞扬的女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的尽头是什么,是远方的牵挂,还是无边的思念。观海听涛,涛声起伏连绵,如大提琴深情咏叹,若钢琴曲优雅动人,似萨克斯清新悠扬,穿越时空的隧道,引领你缓缓回忆起如烟的往事,也许是刻骨铭心的初恋,也许是擦肩而过的遗憾,也许是三生石上一滴泪,也许是十里桃花一世情。
翡翠湾的海是浩瀚而雄浑的,汪洋恣肆,适合勇者们的冲浪。冲浪一族乘着小艇在海上漂流与海搏击,纵横驰骋,动作张狂,尽情与海浪斗智斗勇,内心充满了冒险的刺激与征服的成就感。这边层层的浪朝岸边席卷而来,似千军万马在奔腾嘶吼,而沙滩就像是一条长长的微黄软糯的纱巾恰到好处地缠住它们,万丈钢化做绕指柔。于是海忍让、退却,又野性爆发故态重萌,周而复始。沙滩上光腚的童男童女们互相追逐嬉戏,情侣们成双成对晒着日光浴。良久,一轮夕阳徐徐浮出了水面,此时的大海,也已恢复了平静,它含笑望着这一切,顿悟成了一座弥佛,周围霞光普照,红云流淌,仙乐飘飘。
也曾见过菲律宾长滩岛的海,海水在碧绿与浅蓝与深蓝间不断地交织转换,云瀑在翻飞滚腾,阳光透过云层投射在水面,色彩斑斓,像极了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张着性感的红唇卖萌、撒娇、索求无度、欲壑难填。坐在黑人驾驶的“香蕉船”上,既胆战又兴奋,这里是深海了,海水的颜色更深了,太平洋的风呼呼地吹着,总担心大鲨鱼会冷不丁从身侧身后蓦地闯出,到时候不是得同海明威《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一样与鲨鱼来一场激烈的殊死搏斗,而且还是赤手空拳,想必终极最后不是老渔夫拖着赤裸的鱼骨回去,是鲨鱼拖着我的吧。长滩岛的沙是白色的,据说世界上最细腻。拳王开的“爱琴悬涯酒店”畔海依山而建,海景一揽眼底,这个时候喝喝下午茶看落日缓缓在西山殒落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都说“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海应该也是故乡的最美吧。他乡的海虽也明艳不可方物,但终究少了一些温情。在白塘湾的海边沙滩上,选一块地儿,伙同一群孩童,聚精会神地建一座城堡,或画一个心形。一阵潮水涌来,城堡与心形塌陷,甚至了无痕迹,再重建,再塌陷,再重建,管它泥沙污浊,衣衫尽湿,兀自浑然忘我,一派天真,直到孩童的父母們的呼唤声由远及近,小伙伴哄然而散。而三五只白鹭踮着细细的长腿气定神闲地走过,忽地齐齐飞起,在天空扇动翅膀一字儿排开,“呱呱呱”地叫唤着,飞向海的深处……